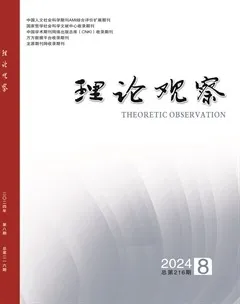1937-1945年侵华日军“扫荡”中焚毁房屋的罪行、动因与影响
摘 要: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在对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过程中,除了伤害根据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抢掠粮食财物外,还焚毁了大量房屋,给根据地群众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侵华日军焚毁房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战争罪行,意图打击敌后抗战的物质基础和抵抗意识。但日军的战争罪行不仅未能打击民众的抵抗意识,反而使根据地军民更加同仇敌忾,强化了中共敌后武装持久抗战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三光政策;烧光;侵华罪行;敌后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8 — 0139 — 08
战火中房屋燃烧的图景是大众关于战争破坏的普遍印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其本土在战争后期遭受了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燃烧弹所造成的房屋焚毁和人员伤亡已经成为日本国民重要的战争记忆而得到充分的历史叙述。与之对比,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留下的焚毁罪行,从史实的专题研究到社会传播领域的历史叙述仍较为薄弱。
已有的关于侵华日军对根据地“扫荡”过程中的罪行研究在政策上聚焦“三光政策”,即以“烬灭作战”等为主。[1]在具体罪行研究上基本上是把“杀”与“烧”并行研究,比较侧重于日军的“杀”行为和重大惨案,或是把焚毁房屋的行为列入财产损失进行基本的研究。[2]实然,日军“杀”的暴行中往往伴随着“烧”和“掠”,但也存在着行为的分离。因此就侵华日军“扫荡”过程中焚毁房屋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存在一定学术价值,但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比较薄弱。[3]进一步考察侵华日军“放火烧房”的动机,可能与屠杀惨案相比更为复杂。与直接的近距离屠杀民众相比,日军基层军官和士兵放火烧房的罪恶感要小得多,放火的技术性难度也较小。因而呈现出行为的普遍性和动机的复杂性,其动机或是对“三光”政策的贯彻或是对“敌性地区”的惩罚与威胁,有时候在士兵和基层军官个体情绪上可能包括长途行军后“扑空”的泄愤。在侵华日军焚毁房屋罪行的另一面,作为受害者的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的,这是已有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由于根据地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与城市知识分子的记载相比,能够表达其内心感性而形成足以研究利用的史料较少也更为散落。[4]日军侵华的暴行使得中国民众更加同仇敌忾,因此,本文尝试利用多方史料,研究侵华日军焚毁房屋的罪行、动机与影响。
一、侵华日军焚毁房屋的基本情况
据1946年4月汇总形成的《解放区抗战八年中损失初步调查》可知,中共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被烧房屋共19518708间。[5]其各解放区分布如下表。
这项统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6年中国进行损失调查,预备对日索赔的战后遗留问题处理的成果。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成立了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设有专门部门调查抗战人口及财产损失,各根据地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46年6月。[6]受国内情势变化的影响,这一调查成果正如文件名一样是一份相对初步的调查。例如调查时,山东解放区辖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5个行政区、127个县。但山东解放区的汇总资料只有83个县的调查统计表,缺乏其余44个县和鲁南区的调查汇总表。[7]47因此,虽然这一统计大体被认为仅是初步的统计,但仍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统计中解放区被烧的房屋间数在初步的统计情况下已经接近2000万间。各根据地数字的多寡大体与各解放区的人口规模相关。其中,冀热辽地区在人口较少的情况下,呈现出较多的房屋焚烧可能是因为日军制造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的暴行。
具体分析,日军放火烧房在地域分布和时段分布上并非平均。以冀鲁边区为例,冀鲁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就是“德平、宁津、乐陵全部及商河、惠民、阳信之部分”,这些区域的日方焚毁房屋的情况明显比津浦铁路沿线的区域要严重得多。1942年“扫荡”后八路军已无法入境的地区如:“南皮、东光、吴桥、平原、禹城边”[8],则日军烧毁村落的情况就相对较少。统计中最少仅为723间的南皮与最多达55600间的乐陵形成鲜明对比。[9]
日军放火烧房的地域性区别不仅仅体现在较大的地理单元内,在小范围内也是如此。在平西,日军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即无法长期驻兵占领的区域“以烧杀为主,敌人宣传说烧的是八路军的房子”,例如“三坡区、深水五区、房良二区这一带房子烧光了”。在经济的中心区涞涿“烧抗日工作人员的房子,不烧群众的房子,挑拨我军民关系。”对日伪军可以控制建立据点的区域“则以怀柔收买诱降为主(在宣涿怀、昌宛之二区及据点附近,房良一区之下半区,涞涿五区及四区),这一部即以怀柔政策为主”。[10]
日军放火烧房的行为在时间维度上也有所变化。抗日战争时期属于太岳第四军分区的山西省晋城市的阳城县在2006—2009年进行了细致的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关于财产损失事件均进行了多人口述采访取得证词。阳城县1938年焚毁房屋451间,1939年为213间,1940年为4890间,1941年为2645间,1942年为2952间,1943年为674间,1944年为969间。考察具体的焚毁情况,在1938年日军进入阳城之际,作为战场的阳城,部分村庄受到焚毁。1939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1940年后随着加强“扫荡”,焚毁村庄的情况反复出现,至1943年后情况才得以好转。值得注意的是统计中日军几乎焚毁整个或数个村庄的行为如“火烧阳晋界”“焚毁贾寨村”“火烧淇讷村”等都是报复性放火焚毁。[11]
日军“扫荡”中放火烧毁房屋的数量占比情况在各地区有较大差异。在根据地中心区比例非常之高,在晋绥区的“汾阳一、二、三道川,交城山地、清太边山、静乐米峪川、凉城蛮汉山,朔县右玉等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房屋全被烧光”[5]26。“鲁中区之蒙阴城,房屋毁坏在90%以上”。[12]但若考虑总体情况,例如山西晋城所辖晋城、陵川、高平、沁水、阳城五县,在战前估算有房屋664548间,战争中损失67125间,损失占比约10.1%。[13]其中房屋损失包括放火焚烧之外的日军飞机轰炸和为修碉楼拆除的房屋,但主体仍是“扫荡”时的焚毁。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受难的村庄与民众。依据根据地相关日记的叙述性的见闻记载,有关日军在“扫荡”时放火烧房记录是极为普遍的。1943年8月景晓村在日记中记载鲁中行军所见“沿途到处可见日寇所遗留下的残暴的痕迹,所路过的大部分村庄是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14]199日军放火烧房的行为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会对根据地的核心村落反复“扫荡”破坏,莒南县的十字路镇从1938年至1945年前后被“扫荡”21次,村庄4次被日军焚毁。“1941年腊月二十一日,鬼子又将前几次残破仅存的几百间房子付之一炬,过年时十字路的老百姓不好意思的塞到邻村人家过年,伏在被烧红的露天的屋框子里,娘一声爷一声天一声哭泣着过了一夜的年节,有个老大娘说:‘不知那一辈子得罪了这些王八羔子,他害的咱好苦情啊!’”[11]83青州的东朱鹿村作为抗日的堡垒村被当地中共干部称为“小莫斯科”,被烧了30次以上。[15]
从日军的回忆史料看,藤原彰记载“当我到达中国战场后立刻体验到的却是日军随便烧毁村庄、任意屠杀农民的严酷现实。”藤原彰对于侵华战争正当性的最初思考就是源自其联队一次放火烧房行为,他回忆联队长山本募“在中国战场的某一村庄,他曾经以怀疑村民串通八路军为由,亲自大声下令:‘烧光。’谁都明白,那个意思就是把一切能烧掉的都一把火烧掉。当我听说此事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是联队长直接下令,所以士兵们更加像发了疯似的点燃了一间又一间农民的房屋。留在村子里的一个老婆婆紧紧抓住日军士兵的脚,请求他停止放火。那个日军士兵一脚把老婆婆踢倒在地,继续放火烧农民的房屋。看到那样的情形,我不由得产生了 ‘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的疑问。”[16]
在普通日本士兵眼中,“放火烧房”已成为一种习惯。1941年才被征募派遣到中国战场的斋藤邦雄就回忆“部队第二天出发前经常会把前一天投宿的村子一把火烧掉”,“听说目的是为了不让敌人使用这个村子”。[17]这种行为频繁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反“扫荡”斗争的军事常识,“干部战士都清楚:敌人一烧房就是拔寨起营撤退的信号”。[18]在战斗中,赖传珠看到日军放火烧房,即判断其撤退,进而制定作战计划。[19]部分日军放火的记载颇为荒诞,山东日军在莱新蒙的“扫荡”中,“从30个村庄经过,彻底烧掉、破坏掉10个”,而未全部焚毁的主要原因并非日军的某种政策或策略,只是因为在“扫荡”的后半段“皇军自己过于疲劳,无力放火,一些村庄才得以保存下来。”[20]32-33在鲁西的日军火烧万家村事件中,“全村300余间房,只剩下20多间,这20多间房不是没放火,是放火时没被点着,后来其他房子火势旺,他们没法再去点了,才留下了这20多间房子。”[7]389
“三光政策”中的“杀”“烧”“抢”往往在日军的“扫荡”中是合为一体的。但如果从“扫荡”的细节看,“烧”可能更为普遍,也更难以应对。在抗日战争中后期的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地方自卫队组织很严,消息很灵通,敌一举一动,我均晓得”,在应对“三光政策”时,“至于杀光,人民根本便不见面,人民到处可以转移,都执有转移证,到外村政权,可以借粮救济”,面对“抢光”,“人民把东西坚壁好了,找不到,纵或找到也不能完全找到。”至于“烧光”,虽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看待,“烧了好房子,还有坏房子,烧了坏房子,人民还可造窑洞”[21],但这也侧面说明了相对于“杀”和“抢”,“烧”更难应对。
考察各个根据地相关文献,在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保卫房子的土办法。例如在临沭根据地“群众就用泥巴把秫秸捆成的房椽糊起来,使火不易燃烧”。[22]淮北抗日根据地动员民兵群众“泥房子与隐藏家具”[23]。太行抗日根据地在民众房屋被烧后重建时,动员群众从“避免二次烧杀出发”,“卷窑洞或盖石板平房”。[24]针对日军放火烧村后不会长期停留的特点,平西根据地部分民众冒着很大的危险“隐蔽在房前屋后”,“敌人点着房走的很快,房主迅速跑进院内,急用水泼或土打,也救下了一批房屋”。[25]此间辛酸与无奈可想而知。敌后根据地的民众面对日军“扫荡”,保全亲人的性命,为求生存尚且不易,更何况是带不走的屋舍。
二、侵华日军焚毁的动因
如前文中藤原彰所回忆,日军放火烧房是有命令有组织的集体行为。日军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则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的作战”“彻底的扫荡”“彻底击灭”“讨灭作战”等等。[1]放火烧房是日军意图摧毁抗日武装抵抗的物质基础的一项军事行动,山西日军明确指示对有敌意的村庄要烧毁破坏。[26]
具体到日军“扫荡”中,放火命令也是由指挥“扫荡”部队的日军军官下达。独立混成10旅团的分队长久保谷幸作在战后供述,其多次放火罪行均是在大队长的命令下有步骤的执行。如1941年6月,“在大队长吉野松五郎中佐指挥下,400名的兵力以包围攻击上述村庄的八路军为目的而侵入,但八路军已撤退,因此依据42大队长吉野松五郎中佐的命令,3中队为放火班,我将村庄东侧的农民住房10户放火,同时42大队将太平村庄的全部民房共60户放火烧毁。”[27]在实战中,在基层军官的命令下,放火烧房也是新兵在中国首先要学习进行的活动。[28]
在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后,日军会进行严厉的报复,这种报复往往就是烧杀的“扫荡”,如在山东潍坊,1938年3月因为抗日武装掀掉了二十里堡附近的铁路,日军随即出动扫荡,“附近村庄的群众大部逃跑”的情况下,日军将铁路附近的二十里堡村、赵家村、沙窝村等10个村庄的房屋大部烧毁,并打死未及逃离的民众60余人。距离铁路最近的二十里堡村从1938年至1939年被日军烧毁三次,每次都是因为铁路被掀后的日军报复。在经历三次日军的报复性烧村后,“该村206户,连第一次被烧后重建的简陋草房遭受三次发火后,只剩30余间房屋。”[7]207日军的这种惩戒的缘由有时候往往只是一张标语、一份传单,在山西阳城县第三区的匠礼村,日军在“扫荡”中看到“村里庙墙上写有抗日标语,就将庙院用燃烧弹点着,烧房计87间”,所幸村里民众早已躲避出逃。[11]332
在山东根据地,当时的中共干部就认为日军的“扫荡”政策之一就是“发现地雷的地方烧房子”。[13]383日军发现地雷就烧房子,其一是因为日军认为地雷的存在都足以证明存在属于“敌性地区”,应予以进行打击。其二就是发现地雷,意味着进村本身可能比较危险,军事上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直接烧毁。驻扎胶东栖霞的普通日军士兵桑岛节郎回忆“扫荡村庄一开门进屋,挂在门户上的手榴弹就爆炸了,在村子里尝试点燃篝火,把原木材烧了,隐藏的炸弹就爆炸了,这种情况数不胜数。”[29]因此,直接烧房有时候也成为日军应对村落中地雷和炸弹的直接办法。独立步兵第79大队副官野间荣作记载在1941年扫荡平西根据地的一个村庄时判断“村里空室清野,有的只是地雷”,在作出不留宿村落的判断后,“在村子西半部的各家门口、木屋门口,选择容易点火的地方,捆扎高粱秆当作‘松明’,一一点上了火。两家,三家,黑烟不久变成通红的火焰,扩展到10家、20家。像在佛教地狱图里看到的红毛鬼那样——通红的脸上发烧的日本兵,挥舞着‘松明’到处奔跑着。在上风头放火的村子,受卷起的旋风煽动,不一会儿就被黑烟笼罩,黑烟变成火焰,化为灰烬。”[30]
即便民众坚壁清野的躲避“扫荡”,但是无法把房舍一起带走。所以,对于日军而言放火烧房不仅仅是事后报复的惩戒手段,也是事前恐吓的威胁办法。例如日军讨伐队在讨伐行唐时,使在民众的门板上写上“快回家来,不然就烧房子”。[21]39日军日常威胁利诱的言语按杨成武记载包括“八路军不消灭,皇军扫荡不停止”,“烧八路军住过的房子”,“跑就烧房子,不跑不烧”,“埋地雷的村庄烧房子,不埋的村庄不烧。”[31]其中可见,房子就其威胁的核心要素。这种威胁不仅指向日军眼中的非治安区域,在日军控制较为稳固的地区,比如沿路的“爱护村”,为抑制中共有效的敌伪军工作,日军以巡查监视,“发现八路军过路或破路不报,便以杀人、烧房相威胁”。[32]
在冀东等地,日军大规模的放火烧房的目的是其意在制造“无人区”的区域。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直接放火烧房、焚毁村落被日军认为是逼迫民众转移实行“集家并村”的有效手段。据统计,长城沿线的“无人区”1.7万个自然村庄被摧毁,380万间房屋被烧毁、拆毁。[33]日伪政权对于一般村落组织拆房子,村民不服从就强制烧毁。[34]日军对于划定的“无禁作地带”的抗日根据地,一开始就是纵火焚烧,摧毁民众的居住条件。特别是根据地如“五指山区羊羔峪、驴儿叫一带,反复烧过20次左右。许多房屋的墙壁石头都烧成红褐色,粉化了。”[34]70日军对许多村庄的焚毁相当彻底,在密云山的“无人区”,日军把“所有的房子完全烧光,甚至一家两家的小窝铺都烧掉。烧得特别彻底,炕拆了,墙推倒,碾子磨完全毁坏,房子周围的草都烧净。”[35]冀东丰润县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文件中也控诉了“皇军”焚毁房屋所造成的痛苦,“谁无房舍,谁无财产,遽遭烧毁,将何以为生”。[36]
在日军的既定政策之外,一些因素可能也助长了日军士兵的放火行为。在文献记载中日军扑空后烧房的行为颇多。日军的“扫荡”往往经历漫长的行军,尤其是小股部队出动时因为情报滞后或假情报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扑空,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37]彭雪枫分析日军“对付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之一就是“很慎重的来对付我们,情况不明不打;没有向导不打;知我部队在甲地,及其前往甲地进击而扑空时,彼通常焚烧房子而去,很少寻踪追击。”[38]因此,有时“敌人因清乡受挫,恼羞成怒,采取烧杀手段。”[39]
这种心态也可以从日军士兵的回忆中去体察,斋藤邦雄回忆“在山区警备队里基本都没啥休息时间,连续好几天都是出击作战。与其说在山里行军,还不如说是在山里兜圈子更好。”从日本基层军官和日本士兵的视角看,战争时期的日常更多是行军,“平均每个月有10天战斗。如果每天平均行军30公里,那么一个月就是300公里,一年3600公里,两年7200公里。”[17]138-139但是在行军出击之后,往往无法“捕捉”到八路军,“有一次我们攻击冀西山区的楼水村,据说那里有八路。在山里走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到了村庄的外围,结果八路军已经不在村里了。这是常有的事:开始听说有八路,过去一看根本没这回事。”[17]126在这种情况下,烧房子往往变成日军部队扑空后的“战果”,因为并非只有人员的杀伤才是战果,“当时日军和八路军作战,目的既有消灭对方,也有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武器,衣服,粮食等)”。[17]126日军扑空后烧掉村庄的房子时,日军军官的理由也是“绝不能让八路军使用这个地方”。[17]143
因此,如果把烧房子视为一种军事行为,并且是在民众已经逃离后烧掉的村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普通士兵的罪恶感。斋藤邦雄回忆“‘不准放火,不准强奸,不准杀人’上头从来没有人对我们做过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把空房子烧掉(这已经算重罪了),其他两条‘不准强奸,不准杀人’倒是没有犯过。现在回想起来反倒觉得万幸。之所以没有犯另外两条,是因为村民们提前听到日军要来的风声,就立即带上财产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算我们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可是总也找不到村民所以也只得作罢。战后清算时,我们部队里没出一个战犯也就多亏了这个原因。”[17]168斋藤邦雄回忆中部队“没有犯过”强奸、杀人的事实仍需要进一步考证,其回忆至少可以说明烧房子是一种普遍而罪恶感要低得多的行为。鉴于日军内部的等级关系和氛围,“烧、杀、抢”这个清剿扫荡令对于平时被束缚的兵士来说,也算是“宝贵”的个人自由行动时间。[20]23可以想象,或许有如藤原彰等在放火烧房时的反思,但大多日本士兵并不会对放火烧房的行为有较大的抵触心理,因而将之视为打击抗日武装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非战争罪行。
三、侵华日军焚毁房屋的影响
战后的损失调查中把被焚毁的房屋和被抢掠的牲畜、家具、被服一起统计,基本视为财产损失的一部分。房屋和其他的财产损失对于农民而言有着较大区别。对于农民而言,房屋可能就是其最重要的财产。华北木材资源并不算丰富和廉价,所以农村住屋的结构多属柱架结构,用原木作柱子,用土坯或烧砖砌墙,柱子其上架横梁,梁上盖屋顶。[40]尤其较好的呈院落的砖瓦房更有可能是祖辈传下来的祖产或耗尽积蓄所建,重建成本不低。已有的研究引述相关资料指出面对日军的暴行,乡村中“富有者所受的损害更大于贫民,民族仇恨更大于阶级仇恨”[41],从房屋焚毁的损失看,确然如是。同理面对日军的“烧房”的威胁,乡村中的富有者可能也会有更多的顾虑。至于不富裕的农民“多数住的是土墙败屋、草棚、茅舍”[42],但对于贫民而言仍属宝贵,且这类住屋更易燃烧。
面对频繁的“扫荡”,根据地民众的居住环境有较大恶化。一些根据地的民众的住房“总是处于烧了盖,盖了烧的反复状态中”[43],重建房屋不易,在“只有墙头无有房顶”的废墟上打窝棚[44]。在日伪军的规划的无人区,不愿下山的民众只能“盖起窝棚马架或住在山洞里”。[45]212日军烧房行为,加之“扫荡”时的抢粮、烧毁农具用具,掳走耕畜家禽,破坏春耕秋收,使大批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49]192
另外,自住的房屋与其他财产不同,它和情感和记忆中的“家”直接联结,因此其损失相比其他财产的损失可能产生的心理创伤更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民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相对缺乏当时自我记录的能够直接表达其内心感受的文字。但在旁观者的笔下,或许仍能体察其细微的心境。山东画报的龙实记录了他在1941年鲁南的见闻:“翻过一个小山头,眼前所见,触目惊心:一个大村庄,被日寇烧成一片瓦砾,就只剩下破屋框了。没有鸡鸣,没有狗吠,没有人声喧哗,全村静悄悄,劫后人家在破屋框里用树枝和高粱秆搭窝棚,权且避风雨,这就是他们的家,应当是炊烟袅袅的时候,可全村没有几处冒烟,满目凄凉,令人心酸。”[46]“静悄悄”的村庄并非没有民众,躲避“扫荡”后返乡的民众只是沉默着在搭建窝棚。这种沉默中所蕴含的情绪或许是复杂的,可能包含着家园被毁的痛苦、愤怒与无奈,但又不是绝望与无助。当然这是龙实在一地的观察,口述回忆和其他记载中愤怒以至痛哭的记载也比较常见。
斋藤邦雄的回忆中有一段关于在太行山区放火烧房的回忆与反思:“有次我们突入一处山谷中的村子,附近山上根本连一棵树都没有光秃秃的。木头在这种地方肯定属于贵重物品,却被我们不管不顾地一把火烧掉。如果要重建被焚毁的村子肯定要花费不止十年的时间。日本兵到处在山间开着桃花的村里放火烧毁自己的家园,从中国人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副魔鬼的样子。哪怕后退一百步来讲,就算日军到处劫掠是出于无奈,那也不该放火。从百姓躲避的山上看到高高扬起的烟柱,他们心里肯定是这么祈求的。”[17]167斋藤邦雄的关于躲避百姓状况猜测可能在细节上都是暗合的。冀热辽根据地的记载中呈现了一段山头眺望村庄的图景,“我们虽然退离红庙子,但每个人都惦念着家乡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就派出几个人半夜溜回红庙子附近山头,瞭望一下红庙子屯的情况。只见满屯火光,如同白昼,浓烟弥漫全屯。我们以为这是日本鬼子在烧房子,在山顶上看着,真是悲愤填胸,有说不出的辛酸。”[47]
远距离目睹自己房子被烧在根据地或许并非偶发现象。这是因为根据地村庄的民众在面对日军的“扫荡”时往往会“跑反”躲避,这种“跑反”多半不会离开村庄太远,或逃往附近的山地,或者是向农地和林地里隐蔽自己。因此,如若日军放火烧房,便可以远眺到燃烧的黑烟。高鲁日记中记载的一次“跑反”是在天亮前得到日军逼近消息,便和老乡一起搬东西到10多里外的山谷躲避,至晚饭后“我们跑到山的最高处,望着河对岸的敌人,他们在王家塔的村外集合,一会开进村子里。不久冒起烟,敌人在烧房子。”[48]176在平原地区,根据地民众也会就近躲避到农地和树林里。冀中根据地一个文艺士兵记载伴随根据地百姓的一次“跑反”,“我和老乡们一起,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49]
目睹意味与惨案的口耳相传或者是中共宣传工作者对报纸信息的宣传相比,民众对侵华日军放火烧房的行为的认知与感受有即时性和现场感。即便未曾当场看到,也会在日军扫荡结束后返回村庄时候迅速感知,从而产生直接的情感冲击。
民众在目睹家园变为灰烬之后,可能会直接产生对施暴者的仇恨。涞源山区一位老乡房子被日军烧毁后,对八路军干部说道“日本鬼子真不是不长人心。”[21]4但这种仇恨未必会直接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支持,甚至会产生对中共的埋怨。中共方面记载“有些地方在敌人烧杀后,情绪很低落,悲观失望,不满八路军,以为八路军不打日寇,不保卫他们的村庄”。[21]7日军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支持抗日武装的村庄进行“烧房子”惩罚,进而通过一定的奖励拉拢村庄,使之疏远敌后武装。这种情况确实有时候也有一定效果,在鲁西地区,中共文献就指出游击队的发展引起了“地主的恐慌”,怕“惹得敌人烧房子、洗村子”,因此组织民团包围八路军游击队,不希望八路军在附近活动。[50]山东八路军干部总结日军的“扫荡”策略之一就是“利诱与威胁并使”,“使群众对我不满”。[13]383甚至,有时候日军也会在村中写“烧房的是八路军”的标语,故意造谣。[58]87
对此,中共从多方面争取民心。在晋察冀根据地,“扫荡”后,日军烧了不少房屋,民众开始很失望。“但是等敌人打出之后,我们立即组织了慰问团到被难区慰问。边区政府拿二十万元去救济,并派军队帮助老百姓整理一切,群众的心马上又转回。他们说,还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好。”[51]同样,在鲁南的“扫荡”后,鲁南支队的干部前往被“扫荡”的张庄,“挨家挨户看望了老乡们,重点慰问了烧房子的那家”,当即“交给村长五十元,让他救济受灾户”,“那家老太太感激的直抹泪”。[52]历城的抗日游击队按房子每间10元的标准对受灾的村民进行了一定的救助。[53]
刘荣在晋察冀的工作中就认为宣传必须建立在对群众的直接救助之后,因为“经过这个过程后,群众看到到底是自家人,又特别相信、爱护,把仇恨心转移到敌人方面,一切工作特别好进行。这说明群众的认识问题是直观的,我们工作应该是曲线的,针对群众的实际利益进行,一切宣传解释工作应在这一个大前提下。”[21]7中共的敌军工作也较注重保障民众的房子,藤原彰回忆在根据地村庄、房屋的墙壁上用日文书写的“‘不许烧房屋’的面向日军士兵的标语和传单非常多,说明房屋被烧毁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重。”[16]36-37这些日文的标语和传单,并非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足以说明中共对于保护民众房屋的重视。太行根据地指示游击队在作战时候“埋设地雷、投手榴弹或打枪时,最好远离村庄”,“尽可能勿在村内举行,否则可能使敌人因受损害而行报复的烧杀”,以“顾全民众利益,为群众设想”。[54]在苏中,新四军通过威胁烧伪军家属的房子,使伪军“不敢下乡来烧群众房子”[55],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日军的暴行加之中共的宣传起到了相当的效果,刘荣记载“进入涞源境内,村落一个一个被烧得只剩下一片砖砾。村子周围完全坚壁的是东西,群众看到我们都回来了,笑容充满了脸。虽然是饿瘦的面孔,但精神上的愉快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21]4
日军的暴行对于民心的影响,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对此有过非常通俗的论述:“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56]
四、结语
侵华日军对中国乡村村庄房屋的焚毁,可以说是日军总体战思想指导下,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战争罪行,妄图通过焚毁房屋打击中国人民抵抗侵略者的物质基础和抵抗意识。在执行层面,侵华日军的“扫荡”方针和报复心理、日军基层军官和士兵的行为等又助长了这种战争暴行,大规模的焚毁房屋和其他战争罪行一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这一战争罪行,铁证如山,应以铭记。
侵华日军大规模焚毁房屋的行为,并未如期所预期地惩罚不合作的村庄和民众,打击中国人民的反抗,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识,进而成为中共宣传、动员的民众持久抵抗的情感基础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群众动员之所以成功,可能不仅仅是其政治技术的先进和组织力、贯彻力的高超,日本侵略造就普遍抵抗意识为中共的宣传动员提供民意的基石。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只有正义战争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持久地拥护。
〔参 考 文 献〕
[1]李恩涵.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实[J].抗日战争研究,1993(04):1-27.
[2]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1937-1945)[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2008(02):171-195.
[3]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伤亡及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华反人道暴行系列研究之一[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80-705.
[4]黄道炫.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J].史学月刊,2018(05):16-25.
[5]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1[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7,26.
[6]张德明.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J].军事历史,2020(01):72-80.
[7]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47,83,207,212,389.
[8]罗荣桓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141.
[9]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3[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027.
[10]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战史编辑室.平西县书记联席会上的报告提纲及结论(1941年2月),平西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一)[M].1982:29.
[11]阳城县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91,244,354.
[12]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83.
[13]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丛书晋城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91.
[14]景晓村.景晓村日记.北京: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2012:199,383.
[15]中共青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青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82,546.
[16]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M].林晓光.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34,36,37.
[17]斎藤邦雄.陸軍歩兵よもやま物語[M].光人社,2009(04):126,138,139,143,167,171,168.
[18]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74.
[19]赖传珠.赖传珠日记[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43.
[20] [日]本多胜一,长沼节夫.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M].刘明华,泽.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23,32,33.
[21]梁山松,林建良,吕建伟.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4,7,39,76.
[2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8):136,152.
[23]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 新四军·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31.
[24]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45.
[25]隗合甫.平西抗日斗争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149.
[26] [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M].杨栋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83.
[27]谢忠厚,张瑞智.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78-181.
[28]刘国光.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2.
[29]桑岛节郎.華北戦記[M].図书出版社,1978:117.
[30]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M].李亚一,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229.
[31]杨成武.杨成武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175.
[32]李健.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交通战/冀中抗日斗争史资料[M].1985(34):199.
[33]陈平.千里“无人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70.
[34]凌源市三家乡窦成祥关于盆子窑村“集家并村”的证言,采访时间2000年10月18日,抗日战争时期朝阳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128.
[35]中共密云县委. 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料选编[M].北京:中共密云县党史办密云县档案馆,2005:164.
[36]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冀东丰润县商民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件(1941年4月16日).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4无人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7-18.
[37] [日]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M].巩长金,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20.
[38]彭雪枫.彭雪枫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262.
[39]汪大铭.汪大铭日记(1939-1945)[M].镇江:中共镇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7:287.
[40]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387.
[41]黄道炫.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J].史学月刊,2018(05):16-25.
[42]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M].附件1,1936:41-42.
[43]隗合甫.平西烽火:平西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3辑[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78.
[44]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联络组.难忘的岁月: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一[M].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联络组,1987:243.
[45]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92,212.
[46]龙实.战地日记[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2002:82.
[47]辽西抗战[M].石家庄: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1983:103.
[48]高鲁.高鲁日记[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87,176.
[49]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冀中分会编.战火中的冀中文艺兵[M].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冀中分会编,1988:144.
[50]常连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52.
[51]解放[N].1940(115)-9-16.
[52]董一博.鲁南抗日轶事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98.
[53]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下册)[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520.
[54]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162.
[55]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197.
[5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3.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