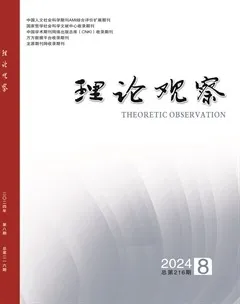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威慑理论研究
摘 要:威慑是一种古典的战略选择。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威慑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威慑的战略作用在于通过维持现状而避免改变现状情况的发生,通过国际行为体施加强制性的战略手段迫使对方改变其初始战略意图。在国际关系中威慑战略的使用旨在通过威慑手段使威胁国际秩序稳定性因素(冲突或者战争)的风险系数弱化而不是真正以威慑手段来激化冲突或者战争。就其威慑的内在本质而言是以威慑的战略恐惧心理使得国际体系中原本容易激化的因素稳定化,如果通过威慑战略使得冲突或者战争的激化就意味着威慑战略的失效。实力、意图、恐惧等现实主义元素是威慑战略得以实现的必然前提,从历史维度和现实实践维度来看,威慑理论在国际体系中应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从形式上来看威慑的作用机理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作为体系结构单元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通过实力的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威慑就是通过运用包括军事、经济、外交或者其他形式的手段的威胁来阻止其他国际行为体采取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一系列行动。
关键词:国际体系结构;战略选择;威慑理论;维持现状;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8 — 0094 — 06
威慑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理论范式,威慑的运用旨在通过基于一国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作为基本后盾并以非战争的形式维持对抗双方现状的一种战略手段,主要是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对方放弃原来的某种念头并回归现状的战略选择。威慑理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性作用,其作为一种研究战争与和平机制的理论方法由来已久,威慑的目的在于有效避免冲突甚至是战争的爆发,避免在对抗中发生进一步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同时也是维持相对和平的路径选择。威慑实际上并不涉及武力的实际使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威慑战略的实践。在维护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方面,威慑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学界关于威慑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从威慑理论的演变历程和威慑理论的内涵维度进行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以及从威慑理论的本质、发展历程以及威慑战略的发展路径等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威慑理论既是古老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国际体系中常态化的实践范式。
一、威慑的本质
威慑(Deterrence)是指一国运用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威胁来迫使另一国放弃原有改变现状的想法而回归维持现状的政策。在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作为体系结构单元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是民族国家)通过实力的使用或者威胁的使用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威慑就是通过运用威胁,包括军事、经济、外交或者其他手段的威胁来阻止其他国际行为体采取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一系列行动。威慑的目的是通过充分运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另一方屈服而放弃通过以冲突或者战争的手段以达到其利益的目的。换言之,就是通过威胁方式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威慑仍然通过以战争或者武力作为其实施的基本前提条件,缺乏以综合实力(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威胁很难达到威胁的目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相对实力对比是确保威慑能够实现的必要条件,以无形的权力政治作为威慑战略的支点,威慑所彰显出来的是立足于综合国力而充分调动资源使另一方充分相信实施威慑的一方拥有足够的实力以及执行一系列威慑行为的意志和决心,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威慑理论还需要考虑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即实施威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与不实施威慑的代价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从本质上来说,威慑战略其实是双方博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双方在可知的相对力量对比的情境中通过战略角力以及综合研判而采取避免对抗的升级。因此,实力较弱的一方会在实力优势一方发出威慑信号的过程中权衡接受威慑的代价和成本以及不接受威慑方威慑的代价和成本,同时威慑理论也是现实主义学派所推崇的权力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威慑理论所凸显出的理论吸引力是比较明显的。
威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策略的运用。由于国际体系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威慑集团(威慑方)与被威慑集团(被威慑方)之间的信息掌握情况存在着差异,这对于实施威慑方与被威慑对象之间容易产生战略误判,加之国际体系压力作用使得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难以把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威慑方基于对对方实力的考量以及所产生的对威慑方的心理恐惧作用使得威慑更加容易被接受。由于相对实力对比产生的权力恐惧和安全保障的双重作用迫使被威慑方接受来自威慑方所实施的威慑,从而使得威慑得以有效发挥作用。威慑的实质表现在双方的心理较量过程,也是源于对相对实力的恐惧,同时威慑发生作用的关键在于实力的不对称,当然也会存在实力相当的双方进行相互威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考虑国际行为体的文化影响、以及民族特性等维度进行分析,因为各国际行为体的文化因素、民族特性等因素也会对威慑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威慑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威胁等手段来维持现状,在不同的情形中威慑的目标也存在很大差异,从军事维度来看,威慑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对方运用武力。威慑能够得到有效实施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反馈的作用,威慑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威胁信号的释放—威胁信号的传递—威胁信号的接收—感知威胁的决心意志,通过这一系列过程的强化与反馈使得威慑能够实现应有的避免战争成为可能的功能。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视角来看,威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有效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以战争的形式对国际秩序造成冲击,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的发展态势;另外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威慑理论可以对外交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威慑手段实现外交的主动,是实现高效外交的常用手段,从而促进双方的战略性对话与斡旋。在国际体系层面,威慑能够发挥缓解结构性矛盾问题的积极作用,威慑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现状的平衡,避免了国际行为体对现有状态进行改变,是修正主义的对立面。威慑战略是基于武力而并非实际使用武力,是以战争相威胁的一种战略选择,通过塑造强大的心理压力而迫使对方放弃原有改变现状想法的威胁机制。
二、威慑理论的发展历程
威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早期,在涉及到资源稀缺的掣肘下威慑手段自然成为当时人们获取稀缺资源的不二选择。在古代的军事史上威慑的运用是比较常态化的战略选择,而威慑形成系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则是在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的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初,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处于兴起阶段,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则处于相对的衰落阶段,到了70年代后期威慑理论重新获得了复兴。纵观整个威慑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发展脉络是随着冷战的发展而发展的,换言之,威慑理论是冷战的产物。古巴导弹危机更是使得威慑理论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古巴导弹危机也是作为典型的威慑形式出现的。在初期阶段的威慑主要集中表现在军事领域,通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威慑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以阻止其他国家采取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或者行为,以惩罚性政策来约束对方的行为方式。在冷战的背景下,威慑理论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要研究威慑理论自然离不开冷战的背景,同样也要研究冷战自然也避不开对威慑理论的关注,而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无疑是第一代威慑战略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布罗迪被视为威慑理论的奠基人,他开创了理性威慑理论的传统,同时他提出了核武器的出现与运用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认为运用威慑来避免战争是核时代国家的唯一理性选择,强调实现威慑的主要方法是双方都具有确保摧毁对方的核打击能力。冷战为威慑理论的孕育提供了良好的时代背景,严重的冲突、理性假设、报复性威慑、不可接受的损失、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威慑稳定性思想等涵盖了威慑的主要研究方向。由于威慑出现的初期基于军事实力的威慑是依靠常规武器进行的,相对来说常规威慑的效果毕竟影响有限,而且受到投送能力的影响常规威慑难以形成全面性的威慑效果,威慑效度自然难以实现全局性的战略性威慑。
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威慑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核武威慑即区别于常规威慑的另外一种威慑形式,因核武器所释放的能量之大破坏力之强是其他所有常规武器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核武威慑的力度远远大于常规武器的威慑力度,威慑的效果更加明显。一方面核武器所能够造成的损失不可逆性的,国际行为体对于核武器的恐惧程度源于内心深处对总体战争所带来的损失的考量,核威慑的存在使得战争规模的不确定性因素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威慑模式囿于其自身的结构特点而难以达到全面威慑的效果,而核威慑所产生的威慑效度无疑比传统武器威慑要大得多。如果是常规军事威慑属于战术威慑,那么核威慑则属于战略威慑范畴,尤其是冷战期间的核威慑已然达到剑拔弩张的态势,而在这之前欧洲国家对于威慑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特别是欧洲均势的背景下威慑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一种战略手段。从军事实力对比的维度来看威慑在维持欧洲均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保了欧洲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从而有效维持了欧洲均势的长期稳定。根据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威慑可以分为古典威慑理论(理性威慑理论)与完美威慑理论,古典威慑理论是基于理性理论体系所建构的威慑模型,而完美威慑理论则是建立在威慑是否可信的假设之上。完美威慑理论认为从能力范畴来说,威胁可以被执行的情况下威慑就是可信的,其将报复的可信性与执行威胁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从能力的大小来界定威慑的可信性。在古典威慑理论中结构威慑理论(Structural deterrence theory)是威慑理论体系中的代表,结构威慑理论(新现实主义威慑理论)的直接来源是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结构威慑理论的许多假设基本上传承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核心观点认为体系结构的权力分布会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结构的存在使得威慑具有均势的特点,通过国际结构的作用使威慑更加具有针对性,所产生的效用也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下威慑成功的概率会有一定的提升,尽管威慑理论系统化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太长时间,但经过几十年以来的发展威慑理论已然越来越趋向成熟。一般而言,结构威慑理论认为:1.非对称的权力关系是不稳定的;2.相对均等的权力分布关系加是高昂的战争成本会促使两国关系非常稳定;3.涉及到战争成本的问题,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战争成本的上升则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下降。换言之,当权力关系与战争成本处于一种不对称的态势时威慑效应就更加明显,也就是当成本大于收益时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与此同时,针对国际体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特征,结构威慑理论还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包括:1.军备竞赛能够增加冲突的成本,从而有助于防止战争的爆发;2.全面的、高效的防御体系不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3.核武器的选择性扩散有助于防止战争和促进和平;4.能够增强任何一方第一次打击优势的军备竞赛,将会危及国际稳定关系;5.偶发性战争是和平最大的威胁。弗兰克·扎克尔(Frank Zagare)曾使用古典威慑理论(Classical deterrence theory)概念来强调威慑理论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性,古典威慑理论与完美威慑理论共同建立在:1.理性行为体假设,国际行为体的偏好和行为选择外生给定,国际行为体根据给定偏好来最大化自身利益。2.国家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体;3.政策选择具有不同的成本,这是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威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威胁使对手以自身所期待的方式行动。
三、体系结构下威慑的路径选择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要求各国际行为体必须依靠自助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安全,而自助的实现是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基础之上的,权力政治是实现国际行为体实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必然路径。因此,各国际行为体不惜无限追逐权力,并通过权力作用把政治权力转化为军事权力,以此来捍卫国家的安全。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基于权力政治的威慑战略是在国际行为体之间通过以实力差距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具备优势地位的行为体的一种战略选择路径,威慑的有效实施需要两个或者多个行为体之间存在实力差距。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国际行为体之间则难以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因为双方之间的实力接近就很难形成权力差,那么战略威慑就处于失效的境地。威慑路径主要是通过常规威慑以及核威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常规战术威慑路径
常规威慑路径是战争史发展以来的历史性选择。常规威慑是基于常规武器的发展历程而言,从历史各时期的发展路径来看,常规武器一直是军事战争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历史的各阶段的发展进程来看常规化军事是古代进行军事战争的基本形式。对于常规的界定主要是集中在使用的频率以及对于军事所采取的反馈机制。所谓常规就是经常实行的规矩、惯例,是相对于特殊情况而言的一般客观规律和表现形式。在核武器出现以前,基本所有发生的战争都是基于常规形式的常规战争,因此,在常规战争发生之前所进行的威慑行为都是常规威慑。人类出现以来各方为了追求各自的根本利益(为稀缺的资源而争夺)而动用各种手段以维护目标利益,战争则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但是如果是在势均力敌的背景下,战争或许无法成为有效的维护利益的手段,因为一旦战争真正发生那么双方的损失程度将会达到持平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战争毋庸置疑是“双输”的结局。因此,对于双方而言相对收益则成为衡量战争能否进行的重要尺度。鉴于此,敌对双方可能考虑的是以另外的非战争形式来解决利益的归属问题,而战术威慑自然成为以非战争形式解决战争形式的战略手段,通过战争后果的威胁避免战争真正的发生,当然除非是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才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因为绝对的军事力量对比容易产生压倒性的战争结果,而均势状态下不易导致战争。
常规威慑是解决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直接矛盾的结构性选择。从孙子兵法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无一不是记载着对常规军事思想的理论研究,从不战而屈人之兵到对于实力的恐惧分别诠释着威慑使用的成功实践到威慑的失效而导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孙子讲究的是从威慑视角对敌人实施威慑战略,通过以军事实力相威胁而迫使敌人放弃以战争形式解决军事对峙,达到使敌人屈服的战略目的。修昔底德则是从国家军事实力对比来诠释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雅典的崛起自然构成了对守成国斯巴达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威慑已然失去了作用,因为战争成为势在必行的态势,只有通过以战争的方式才能遏制崛起国的和平崛起,消耗崛起国的资源能力而达到制约崛起国的发展势头,避免以新兴崛起国为核心结成新的同盟体系对抗老牌霸权国。因此对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来说就不存在有效的威慑作用,对于实力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国家是难以实现通过以威慑手段迫使对方改变其战略意图的。常规威慑在军事发展史上是常见的战略选择,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基于常规威慑手段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是高频使用的手段,用来实现战术威慑的,甚至是从欧洲均势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威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确保通过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手段来实现欧洲均势,确保欧洲协调和持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战争理论深刻地诠释了威慑在战争前所产生的威慑作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威慑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过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的发生频率从侧面反衬出威慑手段的实现概率并不是太高。由此可见,通过威慑手段实现和平与稳定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需要特定条件方能实现的战略目标。
常规威慑是有效遏制战争发生的战略性选择。基于常规威慑的特点而言,在战略威慑范畴常规威慑已然成为制约战争的有效手段,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战略威慑是立足于收益—成本分析的理论范式。国际关系的主题是研究并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门思维艺术,因此威慑理论自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常态化议题,而从使用的频率视角来看常规威慑成为当前威慑手段的常用方法选择。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得日益云谲波诡,战争与冲突成为制约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因,基于资源的稀缺以及对权力(利益)的追求使得战争(冲突)变成获取权力分配的不二之选。一方面,国际行为体通过军备竞赛以强化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权力谋求国际影响力同时通过提升资源的转换能力促进军事实力的提升从而确保军事力量对敌方的压制;另一方面,国际行为体通过军备竞赛使彼此的军事相对实力对比趋于一个均衡的状态,维持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从本质上来看军备竞赛是安全困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彼此双方追求权力和安全的结果。在国际无政府状态背景下,对于特定时期制约战争发生的战略性选择毋庸置疑常规威慑能够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威慑的本质在于以武力为手段迫使对方不去做其原本想要去做的事情,施加外部的压力而改变对方原有的想法(念头)。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威慑理论的效应是比较大的,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需要定期展示进行战争的意愿,尽管其认为那样做在短期内弊大于利但是却有利于后期的信誉,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这样做会有好处,进攻性现实主义把可信的征服威胁作为一种动机可以改变对象国的国家利益,从而使那些反对威胁国的国家与其结盟,该过程被国际关系理论家称作随强(Bandwagoning)。作为主流的战略选择,常规威慑自然成为广大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关注。
(二)常规战略威慑路径
战略威慑相对于战术威慑来说具有更加普遍的政治意义,从影响范围的角度而言,战略威慑的作用远大于常规威慑,战略威慑涉及到的是宏观层面的战略运用,是体现国际行为体综合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反馈的是各国际行为体对于本国资源的调用能力。从军事角度而言,战略威慑包括了常规战略威慑、核战略威慑两种基本模式,分类的标准是基于对武器本身还是因武器的使用而带来的心理影响。一般而言常规威慑是建立在对先进武器本身的使用而产生的战略威慑,以达到迫使对方屈服的目的,而核威慑则是基于对对方心理层面的威慑,其影响力是从心理层面影响对方放弃想要或者正在做的事,因为众所周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各国际行为体是基于理性主义的思考范式来衡量自身风险程度。常规战略威慑是当前国际体系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种战略威慑模式。尤其是在处理局部冲突的过程中其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常规战略威慑的优势在于主要通过先进性武器的使用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一方面,从成本角度来说是比较低的,同时也有利于使得局势处于一种相对可控的态势而不至于时局势升级,保障了局势的相对状态;另一方面,常规战略威慑是基于对称性的战略,即通过先进武器载体的相对比较作用而发挥其放弃原有想法的方式,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对差距,这样才能确保战略威慑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假定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旗鼓相当,或者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小,那么彼此采用常规战略威慑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因为实力相当就不存在以实力对比的差距来实现外部的制衡作用。在这种态势下威慑自然是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则更容易发生战略误判而导致真正冲突的产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行为体均以自助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因此,自助体系下难免会产生安全困境,进而加剧了权力斗争的烈度,同时也意味着常规战略威慑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发挥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对战略威慑的实施方以及战略威慑的接受方之间的处理不确定性信息的反应能力上,能否有效判断对方实施的威慑是有效威慑还是虚拟威慑。
常规战略威慑所涉及到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基于整体实力对比的战略影响范围自然是很广范的,而基于部分力量对比的层面来说则是有限的影响,根本区别在于实力对比的效度,常规战略所影响的范围是局部性而非整体性的,同时在实施战略威慑力量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因战略威慑所带来的行为后果,能否会因为战略威慑而产生新的问题。对于常规战略威慑而言,其目的是通过已有的实力资源迫使对方维持现状或者是放弃原有的想法,从而实现和平与稳定的目的。如果是权力分配不对称,强国通过常规战略威慑使弱国一方屈服当然是可实现的,但是弱国对强国采取常规战略威慑毋庸置疑是危险且无效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实力相当的两国彼此之间进行常规战略威慑,那么实施的常规战略威慑可能是有效的,也有可能是无效的,关键在于双方之间对对方战略意图以及实施战略的决心的掌控程度,在常规战略威慑实施的过程中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整体而言,常规战略威慑的适用范围比核战略威慑要小得多,但是各国际行为体最常用的威慑还是常规战略威慑,因为它实施的相对成本比较小。
(三)新时代高科技威慑路径
21世纪以来,在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毋庸置疑,这将是世界范围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奏,众多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5G技术,量子力学,信息化,人工智能(AI)等无疑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高科技的到来也改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路径。从威慑的形成以及威慑信号的传输路径而言,高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决定了威慑的效率化得以实现,不同于传统的威慑模式,新时期的威慑路径在以高科技为背景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化语言的形式传输至威慑对象的信息获取中心,确保了威慑信号的完整传输以及目标对象的有效接收。在军事体系则是体现在对于军事武备的高速升级,武器微型化,军事武器威力量级化,操作系统的稳定精确性等科技元素让军事性威慑变得更加简单。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威慑载体形式的多元化,同时高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威慑的可实现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从威慑的效果而言,核威慑无疑是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最有效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的不断进步,国际行为体使用核威慑的频率却是越来越低,因为各国际行为体都知道一旦使用核武或者是使用核武相威胁的结果只会是玉石俱焚。从战略层面来说无论是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大国还是中等国家,谁也不敢轻言实施核威慑。二战中世界各国已见识过核武的巨大威力,所以基于核武的战略威慑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
四、结语
体系结构下各国际行为体之间为追求安全和生存而不断地采取增强自身权力的做法以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由于各行为体对于对方的真实意图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对于对方实力增长的恐惧,从而继续发展自身实力的做法同样又引起了对方的恐惧,进而产生各国际行为体为维护自身安全而产生安全困境的现象,威慑则是通过以确定性的军事信息给予对方一种以明确的行为—后果逻辑的思维方式而迫使对方改变其原先的意图或者是维持现状的战略手段。在新(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国际行为体是具备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在面对威慑战略时所考量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动机,威慑的有效性也是通过对国际体系背景下各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应对表现出来的,威慑的目的在于通过以军事实力的方式来迫使威慑对象的放弃原先的意图(改变现状),使得威慑信号通过信号传输—信号接收—信号反馈的作用模式来表达威慑的系统过程。毋庸置疑,威慑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作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通过把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方式开辟了以心理学影响国际政治行为的融合模式的先例,而威慑理论的实践是基于心理学范畴的心理活动作用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丰富,威慑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威慑的形式与内涵都具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威慑战略的使用旨在通过以军事实力的方式来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
威慑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手段而非战略目的,威慑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威慑手段避免战争或者是避免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威慑理论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理论体系中以进为退的思维范式,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是理性行为体,能够通过理性的分析与计算并评估国际体系环境而做出有效的战略威慑以阻止企图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使得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大国会彼此畏惧而试图以自助的方式来获取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和安全,同时也会关注权力分配在体系结构中的动态调整。当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的时候,威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国际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威慑战略对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层面而言,威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抑制国际冲突的产生和扩散,如果能够有效管控威慑战略的效度那么威慑战略对于维护国际整体安全和国际和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威慑战略的有效实施能够遏制修正主义国际行为体改变现状的战略意图,威慑战略的应用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借助实力展示以及威慑信号的释放以达到迫使对方维持现状的战略目的。当然,实施威慑战略的前提条件是威慑的可信度问题,只有是可信的威慑战略才能达到战略威慑的目的。总体而言,威慑战略对于维护国际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威慑战略的实践在于使被威慑方的心理层面发生变化而逐步放弃改变现状的战略行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威慑战略不失为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行为,一方面既能有效遏制对方企图改变现状的战略行为,从而降低国际体系中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威慑战略是旨在通过以实力优势迫使对方改变其战略意图而非实施军事行动以达到战略目的做法。
〔参 考 文 献〕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次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02).
[2][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6]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7]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
[1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12]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14]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5]曹德军.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16]肯尼思.华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7]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次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18]Novikova I. N.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Theoretical Aspects[J].Herald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23(03).
[19]Bain William.Th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Questions, challenges and explor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2023(02).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