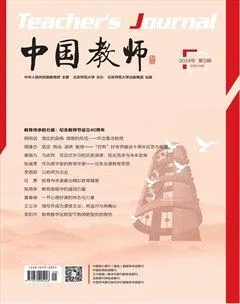割裂与弥合:以历史解释系统建构学科核心素养
【摘 要】历史作为一种“存而不在”的客观存在,需要由历史解释来弥合历史材料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裂痕”。历史解释素养在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居于核心、关键地位,因此,历史解释素养培育是系统性建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主要策略有:以唯物史观赋历史解释之值,以时空观念夯历史解释之基,以史料实证现历史解释之实,以家国情怀铸历史解释之魂。
【关键词】历史解释 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 家国情怀
历史距今而远去,是一种“存而不在”的客观存在。它的“远去”与“存在”共同决定了历史与现实中的人具有在时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间隙[1]。因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式离不开考古发现,绕不开对历史的探究、推论、想象。通过史料实证,历史可以被复原,人们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真相,但纯粹以史料呈现的历史与历史真相之间终归是有“裂痕”的,这道裂痕需要由历史解释来弥合。
一、历史解释和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的意蕴
历史是“过去的事”或“对于过去事的记忆”;解释是“分析原因,说明理由”,强调对事物意义的说明和阐释。将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历史解释”则内涵丰富。杜维运认为,历史解释是疏通、比较历史事实及其所包含的相互关系,以发现其中意义的过程。历史解释以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其本质是一种叙事[2]。李剑鸣认为,历史学家选取的历史事实或明辨历史事实的“真相”,都包含了其对事实意义的理解,因此,确定历史事实是一切历史解释的基础[3]。张耕华认为,历史解释包括史料解释和史事解释。前者包括读懂史料的字面义,探求书写者的原意、引申义(限于文字类史料);后者则侧重探讨历史原因或是用某种理论来解释原因,即借助一个普遍规律和初始条件来对某个史事进行解释[4]。历史解释素养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和《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共同提出的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徐蓝对于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的内涵解读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依据是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基础是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目标是养成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历史事物的能力、方法与态度[5]。可见,历史解释素养强调了“事实”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借助历史解释,学生可以从史料中获取或接近历史真相,并在解释历史中培养分析、说明、评判历史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因此,历史解释弥合了史料、史实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裂痕,使得历史从史料堆砌、史实罗列走向历史认知主客体统一的富有“思想”的历史。
二、依托历史解释系统建构历史核心素养的策略
历史解释素养依托其核心、关键的地位,融通了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使得诸素养由个体走向整体,以“整体功能优化”之态势促成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系统性建构。
1. 以唯物史观赋历史解释之值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方法论,是迄今为止最具科学性、最为思辨性的历史哲学体系。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的历史课程标准都指出,历史教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唯物史观亦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灵魂,是学生历史学习和教师历史教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保证。因此,历史解释的“底线”和“上线”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和“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程度如何”而决定的。倘若没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来进行历史解释,就背离了历史本身,脱离了科学而陷入歪曲、虚无的历史认知旋涡之中,没有守住“底线”的历史解释必然是毫无价值的;倘若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是浅薄的,对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方法论运用是不娴熟的,那么对于历史形成的认识必然是浮于表象而难抵本质的,所对应的历史解释也必然是相对机械而片面的。
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性的,从纵向看,人类历史经历了不同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由此所引发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这样的规律性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尤为明显。聚焦于中国古代史,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因此,对于该时期所发生的剧变务必立足于唯物史观来作出历史解释。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组成社会结构的三个层次因素并阐明了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因而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也应当从这三个层次要素切入。恩格斯认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6]。一方面,春秋晚期“冶炼生铁,铸造铁器”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说明该时期已经逐步完成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转型。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牛耕的逐步推广,使其成为农业生产中最强大的动力。“铁农具”和“牛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并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剧烈变革。最直观的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大量荒地被开垦成为“私田”,诸侯为激发奴隶的生产积极性变更了生产关系,并逐步下放了土地所有权,“奴隶”“奴隶主”的阶级关系开始向“地主”“农民”的阶级关系转变。当诸侯所拥有的土地日益增多并大大超过王畿时,井田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井田制的崩溃引发了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的全线瓦解,西周奴隶统治系统的终结宣告了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封建时代。对上述过程的阐述,运用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将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从本质上进行深度解释。
唯物史观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更迭中的作用机制,演绎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历史各种内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方才可以由浅入深,直抵本质,引导学生抓住历史发展的“关键少数”,使得历史解释从单向、片面、机械走向综合、全面、辩证,从而实现历史解释的增值。
2. 以时空观念夯历史解释之基
任何历史事件都处于一定的历史时间及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历史时间除了所指的历史时期外,还包括该时期内所关联的历史内容及该内容在该历史时期产生的作用、影响。历史空间主要指历史事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7]。时空观念即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同时,时空观念亦是历史解释的一种特定视角,因为观察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对历史进行客观评述必然离不开“时间演进”和“空间范围”所构成的框架。可见,时空联系是构成历史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树立时空观念则是历史解释的基础。
例如,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国并不是从一个点上发展出来的,在这片后来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从新石器时代到约公元前1000年,各个区域的不同文化逐渐接触、互动,彼此交融,最终抟合成一个具有高度同构性的中华文明[8]。夏、商、周时期正是中华文明抟合的主要时期,因此,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理解是理解“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关键。从时间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是一种“更迭”关系,但综合时间、空间来看,夏、商、周并不是纯粹的先行后续、取而代之的关系,而是前后相续的三个共主。时间上,夏的时间最早,之后商取代了夏成为共主,再之后周接任共主,它们存在和发展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空间上,夏文化位置居中,商文化偏东,周文化偏西,当夏成为共主时,其东方的商文化已经存在;当商成为共主时,夏文化也依然没有被消灭;当周成为共主时,专门分封商的后裔继续发展商文化。因此,综合时间和空间因素,夏、商、周之间存在的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同样真实、同等重要。当然,夏、商、周同样发生着深刻的交融,尤其是在周王朝存在的时间里。周王朝建立了完备的统治制度,形成了特有的周文化。而周文化的核心、关键部分被保留下来,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综上可见,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周王朝,中国从一个多元错落的文化领域抟合成为近乎单一的文明系统,这便生动演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时空观念为历史解释提供了特定的时空框架。以时间为经,才能观察、理解、认识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辨明其阶段发展的特点,探寻其演进的内外动因;以空间为纬,才能明晰人类活动的场域,观察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相交织的联系。因此,时空观念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只有回归于历史发生的时空,方能辩证地看待、叙述、评价历史,作出契合客观存在的历史解释。
3. 以史料实证现历史解释之实
相较于其他人文学科,历史学注重“逻辑推理”和“论证实证性”。具有实证意识并学会运用历史证据,是历史学习和培养历史思维的重要途径。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9]因而对于史料实证,应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对史料进行辨析,去伪存真,选取可信的历史资料;二是以史料为依据还原历史真相,能够在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据此进行历史叙述,提出历史认识。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体悟并逐渐养成实证精神,以实证精神来正确看待历史与现实。
例如,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中的“白起坑赵”,可以从多个史料来进行实证分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史记·赵世家》记载:七月,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坑之。对照分析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四十余万赵军被白起坑杀(活埋)”在《史记》中的记载是存在分歧的:一说“四十余万”是赵军在交战中伤亡及被坑杀(活埋)的数量之和,一说“四十余万”即被坑杀(活埋)赵军的数量。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可联系其他文献资料,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着白起与秦王的对话: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料记载,秦、赵在长平之战中分别投入六十余万、四十余万军队。如果秦在战中伤亡过半,那么以秦军的战力推算赵军在战中的伤亡人数,进而推断赵军被俘人数达到四十五万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坑”有“大批集中屠杀”“集中埋葬于大坑”的释义,类似于后世的“万人坑”[10],据此也可推断长平之战中的“活埋四十五万赵军”的说法存疑。此外,还可以选用实物资料进行二重印证。根据《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中的尸骸照片及记载,在60个未经破坏的个体中,近半数头与躯干分离或仅有头骨无躯干。因此,可推测这些人应是死亡在前,埋葬在后。坑中仅有1人可能是被活埋[11]。根据文献资料、实物资料的相互印证以及逻辑推理,长平之战中“白起坑杀(活埋)四十余万赵军”的说法是存疑的。但上述史料重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大、残酷性强、战争中存在坑杀战俘等现象。
所谓“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历史解释应当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有“信度”的历史解释,前提是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辨析,如果条件允许则应注意孤证不立、多重论证,辩证、客观地看待历史,解释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不断接近历史真相,并将历史描述出来从而重现历史的客观存在。
4. 以家国情怀铸历史解释之魂
学习和探究历史不应局限于历史本身,而应具有一定的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这体现的便是历史教育的根本旨归—家国情怀。学习历史,学生应当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进步为使命,从而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以家国情怀为指引的历史解释,才能凸显历史课程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落地历史教育的育人价值。
例如,如何理解北宋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君子之争”?赵匡胤、赵光义等北宋开拓者推出的“重文轻武”“中央集权”举措一方面解决了五代十国时期“武将专权”“地方割据”的痼疾,另一方面也导致在宋神宗时出现了“不得不变”的时局。“王安石变法”不失为扭转北宋颓势、实现国家富强的有益之举。然而,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过度推崇,会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推到正义的对立面,狭隘地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歧”视作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其实不然。《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回答皇帝的问话,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王安石则在其所著的《周公》中写道: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可见,无论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还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都在寻找“治国平天下”之策,只不过二者所主张的策略不同而已。因此,在王安石与司马光身上均可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指的一种“自觉的精神”。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12]。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表现出对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国家富强的不懈追求是其对国家和民族深情大爱的转化产物,这是我们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君子之争”中应当提炼的,是指向家国情怀素养培育的教学立意和育人价值。
历史解释虽然源于过去,但关怀的却是现在和未来,其目的在于人类的幸福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希冀[13]。历史教育需要的不是历史的“冷眼旁观”者,需要的是完成历史与自我交融的历史传承者。家国情怀正是亟须被注入历史解释的一种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要素。历史解释也只有注入了家国情怀,才能真正沁入心田,使得历史教育的价值在人性激荡与生命跃动中落地,实现人的灵魂洗礼和精神重铸。
综上所述,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是内含逻辑关系的统一体,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的“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绝不是无缘无故、随心所欲的,而需要观照五大核心素养进行系统性建构。立足唯物史观,历史解释方显价值;增强时空观念,历史解释方有根基;坚持史料实证,历史解释方成信史;注入家国情怀,历史解释方可铸魂。总之,历史远去而存在,历史的真相需要有这样的解释,历史的意义更需要有这样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郭元祥,王秋妮.参与历史:历史想象及其能力培养[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11):108-115.
[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4-165.
[3]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79.
[4] 张耕华.释“历史解释”[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17):10-17.
[5] 徐蓝.关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几个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2017,37(10):25-34.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2.
[7] 薛伟强,范红军,陈志刚.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85.
[8] 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2:文明的基因[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9-11.
[9]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0.
[10] 孙继民.考古证实“坑杀”并非活埋[J].中国语文,1997(5):392.
[11] 徐峥.教学策略:历史概念间的横纵联系[J].中小学教师培训,2021(6):63-67.
[12]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58.
[13] 赖立新,刘道梁.论历史解释素养表达的情感属性[J].中学历史教学,2022(2):16-18.
本文系2023年杭州市基教教研课题“三维·五融·四阶:指向‘课程思政’的历史情境化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编号:L2023051)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丁荷中学)
责任编辑:赵继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