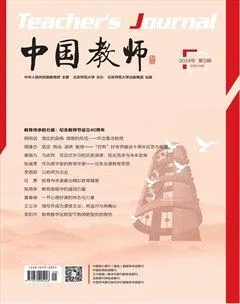教育旅程中的温润力量
【摘 要】本文通过自传性叙述和反思,探讨了教育过程中隐性力量的运作机制及其对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文章以作者三位导师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为案例,描述、分析了教师对学生产生隐性影响的机制,提出教育的真正力量在于深入内在世界,发现和创造自我。教师成为学生真正的榜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师生关系应建立在相互映照与共同成长的基础上。
【关键词】自传研究方法 教育传承 师生互动中的隐性力量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32年,从初中英语教师逐步成长为教育研究工作者。我的职业旅程始于山东兖矿集团一个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学,随后在曲阜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取得比较教育博士学位。在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15年后,我于2021年4月加入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我的职业经历涵盖了教师、学生、研究者和培训师等多个角色。多重身份的融合反映了时代的自由与弹性。每一次身份调整,都是一次新的选择,是个体对未来的新想象。在走向未来的途中,师生关系中的隐性力量发挥着助推或牵引的作用。这是一种温润的力量。
一、为自己创造一个精神空间
我在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读高一时,语文老师王宝龙深刻地影响了我。王老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个子高大。他鼓励我们写日记或周记,并愿意为我们修改。有一次课间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如何表达才能更动人。正好那时我们刚学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他就翻开这篇文章,给我讲解写作题材、方式往往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你看归有光,他一生事业和经历都比较平淡,没有大起大落,因此他的文章几乎都是通过家庭琐事、细节描写来反映主题。比如,在《项脊轩志》里,他详细描写了项脊轩的来历、变迁、人物的典型动作或话语,也写了很多琐碎细节,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情感。”王老师又指着课文最后一段,给我读出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他说:“你看,他不直接写对亡妻的思念,而是通过枇杷树这个意象,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深情。这种手法不仅更具感染力,也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传递出一种绵长而深沉的悲伤。”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读“今已亭亭如盖矣”的声音和语气。
王老师在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读书和写作的种子。此后30多年里,我对写作的热爱和我的写作风格,无论是写诗、散文还是论文,都深受王老师的影响。对于强烈的情感,我不会直接用浓烈的语句表达,而是选择一种平和的词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觉得过于浓烈的表达会覆盖这些想法背后的东西。现在回头来看,王老师对我的影响,就像归有光项脊轩旁的枇杷树,一点一滴逐渐枝繁叶茂。写作—不受外在贿赂的写作—帮助自我逐渐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内在空间,一个足以抵御风霜的内在空间,一个让个体的存在充满意义的内在空间。
有无数次,我在深夜的站台写下描摹心中感悟的诗句;在写给校长和教师的论文中夹带着描摹探索勇气的话语;在观察教研活动时,用平和的笔触记录下教师们眼中的教和学。我始终坚信,这样的写作方式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心灵修炼,是对内心世界的细腻描摹和真诚表达。王老师为我的人生追求奠定了一种底色,让我在远行的路上始终保持初衷。
二、谁有可能成为榜样
在我33岁那年的9月15日,我背起行囊来到了丽娃河畔,来到了黄志成老师身边攻读博士学位。黄老师是上海人,同学们都说他有艺术家气质。在读博期间,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爱和严格要求。黄老师爱每一个学生,关心我们,给我们自由。同时,他对我们的学业有严格的要求,但他很少直接表达他的严厉,总是以迂回、不动声色的方式,让我们领悟到他对我们的期望。记得我写完博士论文初稿时,黄老师的父亲正生病住院。他就在父亲的病床边上,给我修改论文初稿,详细指出其中的问题,鼓励我放宽心态,认真打磨论文。第二天他从医院来学校上课,课后约我谈如何修改论文。从文科大楼出来,我坐在丽娃河边的青石上,眼含热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学术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黄老师要求我们做到的他总是自己先做到。2003年,我刚到上海时,发现黄老师上下班乘坐轻轨时,总是带着一个巴掌大的随身听,原来他在用碎片时间学英语。他的第一外语是西班牙语,但通过碎片时间自学的英语水平足够支持他到英国做访问学者、参加国际会议、讲学、翻译英语学术著作。我至今保持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自学的习惯,正是从模仿黄老师开始的。
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和全纳教育,他的学术坚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记得我刚入校时,他正在研究弗莱雷的教育思想,他说国内出版的很多弗莱雷著作,是从英文译本翻译的,因此有一些错误或偏离。于是黄老师直接读西班牙语原著及相关研究成果,后来他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怎样过一种值得过的幸福生活?这些年我在同门微信群里,跟着他去北极看了美丽梦幻的极光,看他入住童话般的雪屋;看他在非洲大草原上拍野生动物;看他去印度感受古老文明……黄老师的足迹启发我们:努力工作与享受生活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享受生活更有助于创造性工作。
我从黄老师那里还学到了如何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黄老师从不居高临下地告诫我们要怎样生活,怎样工作,不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覆盖我们。在他从教40周年的庆典上,他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几乎很少表扬你们中谁特别用功地做学问,谁发表论文多,因为你们有不同的兴趣,有不同的生涯规划。想把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当然会努力钻研学问,如果喜欢做其他工作也很好。但是我对你们也有底线要求,那就是学业成绩必须达到学校的最低毕业标准。如果有毕不了业的苗头,我就会干预,就会批评。”
黄老师本人活成了我们心目中榜样的样子。赵汀阳曾经指出,“榜样被编造成什么模样,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道德榜样’能够同时是‘成功榜样’,就是说,道德榜样必须与利益上的成功榜样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榜样就失去魅力”[1]144。作为学生的我们,观察到黄老师为人谦和,深受学生敬爱;人生体验丰富,眼中和心中装着世界的大好河山;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在生活中积极探索,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仅在于学术上的突破,更在于生活的丰富和内心的充实。他以自己的生活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把自己活成榜样,不是一种生活态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获取,而是一种教育理念。对学生知识获取以外的东西的影响,如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意义的获取方式等,不能靠说教,要靠对话,靠“商量”,靠榜样。黄老师把自己作为方法,不仅塑造了我们的学术追求,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态度,让我们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三、发起并保持正反馈循环
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个起作用的方式会因为学生的年龄而有差异吗?我在写作本文时突然想到了这个话题,一些具身体验浮现在了脑海。
遇见威廉·派纳(William Pinar)教授的时候,是我33岁那年秋天。此前,我在做过8年初中英语教师之后,考到曲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十分认真地投入了三年时间学习教育学有关的理论,但是感觉只学到了一点点皮毛,还完全没有自己是教育学硕士毕业生的自信。我走在9月底的丽娃河边,内心既焦灼,又满怀热望,脚步匆匆,奔向博士必修课程和各种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学习。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威廉·派纳。从此后一直到现在的21年里,他都是我的导师,在各个关键的时候给我以指导或鼓励。
导师未必是写在文件中由“官方”认定的人,有时他们可能是你在书本中遇到的伟大思想者,也可能是你有幸遇到的对你特别重要、给了你关键指引的“私人导师”。我从阅读派纳教授的自传研究方法理论开始,到见到他本人,接受他当面指导,翻译他的著作,无数次通过邮件请教翻译过程中弄不懂的问题,把研究他的自传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再到参加他的课题研究,学习与应用他的课程理论以及自传研究方法,这些成为我建构研究主张的通道、抓手和动力源泉。
有好多次,或者是当面,或者是通过邮件,派纳教授耐心地帮我解释他写的论文中某些段落背后的考量,他对哪些问题的分析是针对当下社会现象或者针对哪些学术观点。他著作等身,涉及很多领域,我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阅读、领悟他的所有学术著作,然而,就是对我这样一个初学者,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我的问题(当初有些问题非常幼稚)。
我有时候想,我听过那么多讲座,读过很多书,为什么我会觉得派纳教授对我学术研究的影响最大、最重要呢?我感觉主要是因为他对一个热切的学习者的态度所引发的师生之间一连串的、持续多年的正反馈循环。赵汀阳曾指出,“他人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创造者,所以对他者的知识永远不像研究石头,能够仅仅通过细节描写去决定,更重要的是由他人对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做出的反应来决定”[1]350-351。
派纳教授对我的指导和鼓励,帮助我重建了学术自信。他对我的影响建立在导师对学生基于学习过程而展开的支持基础上。他对学生的态度,正是他学术主张的具象化表达。他曾经在1979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课程理论化中的抽象和具体”的论文,在其中他深入探讨了抽象概念与具体的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他强调,抽象概念只有在特定情境中才能展现其真正的价值。他指出,学术研究不应仅限于抽象理论的探讨,而应深入具体的教育实践,关注每个独特的个体,理解并回应他们的差异和独特需求[2]。这正是赵汀阳所说的“他人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创造者”,导师们需要以对待“创造者”的态度与之互动,引发正反馈循环。
四、做一个站在校长和教师背后的研究者
在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的23年里,我专注于研究学校和教师的日常教育实践。我的研究着眼于教育实践中的真实变革,而不仅仅是重复的日常工作。就是说,把目光聚焦在一所学校、一个学科教研组或者一位个体教师本人是如何启动与持续进行教学改革探索的。我会阅读他们的改革设计文本,直接参与或者调研推进改革措施的方式,分析每一个改革转向的原因和方向、共同话语体系的建构方式,等等。我参与研究的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劳动,也不是看上去丰富多样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改进成分的“探索”,而是静悄悄的变革。
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变革,哪些是重复性劳动,我使用杜威的“思维标准”:关键要看这些方法或者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是不是“变得机械僵化,统治着人们,而不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自由使用的力量”“方法的提出有价值还是有害,要看它们使人作出个人的反应时是更加明智,还是诱使他不去使用他自己的判断”[3]。
我常常反思:校长和教师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教研活动,花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我到底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特别是,当他们真的在进行前沿性探索的时候,前路如迷雾一般,因为我的加入,他们真的能走得更稳妥一些吗?我的出现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校本探索的外部视角,还是一些具体的改革策略,还是一种思维框架?我逐渐认识到,真正有意义的支持不仅在于提供具体的建议或策略,更在于引导校长和教师反思和调整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法。我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镜子”,帮助他们看清自身实践中的盲点与潜力,激发他们自主改进的动力。同时,我的参与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试验场,让他们在探索过程中敢于尝试和犯错,从而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中走向真正的教育变革。
我逐渐意识到,我只需要站在校长和教师背后,聚光灯不需要照耀在我身上。我希望因为我的出现,他们更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工作的场域,能从更多维度、更深层次进行反思和自我评估。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帮助校长和教师们构建一种持续改进的文化,使他们在面对教育改革的挑战时,能够更加自信和从容。我坚信,如果他们拥有这样一种教育探索实践的价值观,他们的内在自我会更加充足。这样的场景,不就是王宝龙老师、黄志成教授、威廉·派纳教授带给我的吗?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给我力量,与我对话,做我的榜样,让我从一个山村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自信、乐观、坚韧的教育研究工作者。他们经由我,一定体验了他们自身;我经由他们,感受到无尽的激励和支持,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界限,追求更高的目标和理想。
教育的真正力量在于深入内在世界,发现和创造自我。教育的意义不在于抵达终点,而在于持续创造和体验自己的教育身份和价值。正如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兰默所言,“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一个举着灯,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相逢”[4]。这句话不仅描绘了他人作为榜样的意义,也启示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师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相互映照与共同成长的基础上。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参与,帮助与我对话的教育者在实践中发现这种力量,以此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在教育改革中绽放光彩。正如我的导师们启发了我,我也愿意成为他们探索教育意义的同路人。教育能够传承的,就是这样一种温润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PINAR W F. Autobiography,Politics and Sexuality:Essays in Curriculum Theory[M]. New York:Peter Lang,1994:101.
[3] 约翰·杜威. 我们如何思维[M].伍中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74.
[4] TOMAS T. The Deleted World[M]. FULTON R,translate. Bloodaxe Books,2006:350-351.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