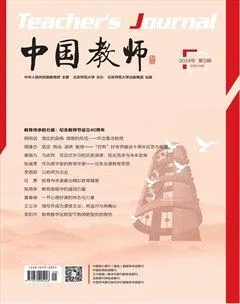教育传承演奏出精彩教育篇章
【摘 要】教育传承是对前辈教育人的经验、知识、技能、方法、观念等的继承和发展,它体现了对往昔教育智慧的尊重,是推进当下教育的一种力量,更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教育传承的实现,依赖于教师的教育情怀、教育理念和教育素养。作者在4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经历过教育科研、教师共学、品玩数学三个教育传承的生动故事,演奏出精彩的教育篇章。
【关键词】教育传承 教育科研 教师共学 品玩数学
教育传承是教育活动的重要部分,它是对前辈教育人的经验、知识、技能、方法、观念等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对往昔教育智慧的尊重,是推进当下教育的一种力量,更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
有人说,最美的教育是传承。我想说,教育传承让教育发展有其“源”,有文脉,很“自然”;教育创新让教育发展有活力,体现“自觉”,体现价值引领。教育传承,是一代代教育人的“教育守望”,是凝聚师生行动的精神力量,是学校走向高品质发展的激励机制,也是促进教育创新的原动力。
教育传承的实现,依赖于教师的教育情怀、教育理念和教育素养。我在4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经历过几个教育传承的故事,这些生动的教育传承故事,演奏出精彩的教育篇章。
一、教育科研:陈清森→任勇→王淼生
陈清森老师是福建省龙岩市教师进修学校的数学组长,初为人师的我在龙岩第一中学当老师时,陈老师是我们专业上的“顶头上司”,他在教育科研方面出道早、成果多。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对教育科研还很陌生,认为教育科研高不可攀,中小学教师只要教好书就行了,教育科研是教育研究专家的事。
陈老师告诉我:“你结合教学实践进行研究,不声张,现在许多老师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先走一步,就领先一步。人们认识教育科研还有一个过程。”
于是,我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同时进行教育科研。要进行教育科研,就要学习;要学习,就要订许多报纸、杂志。我们在闽西山区,相对来说信息不灵,通过订阅报纸杂志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数学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情况,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杂志一到,我和陈老师先各自读,几乎是“读红”了,就是每页都读,都画,还有批语。同时做目录分解,以便日后好查询。有时,看完目录中的某个题目,自己就想“这个题目让我来写,我会怎样写”,把自己的写作框架拟出来,再打开对照是别人写得好还是我的框架妙。那段时间我们读了大量的数学教育文章,为日后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我每周都要到陈老师家去,有时也邀上几位“志同道合”者一并去,人多了,研究的氛围就浓了,大家都进步了。那段时间的日子过得真愉快,正如魏书生老师所言:“忘我学习,处处都是净土;潜心科研,时时都在天堂。”
陈老师与我合写过文章、合编过书,在合作过程中,我悟出了许多治学之道,更多的是悟出了做人之道。1984年,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是就有了在教育科研上的漫漫征程;1988年,我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是就有了“梦圆百书”的不懈追求。1996年,我调到厦门工作,在“教师节”给陈老师寄了一张贺卡,上面这样写道:“师指一条路,烛照万里程!”
2004年,时任厦门第一中学校长的我,引进了一位数学“金牌教练”—王淼生老师,他是解题能力极强的老师,但教育科研成果不太多,课题层次也不是很高,我就从研究解题入手引导王老师“科研”。
就这样,王老师成了我那间颇有特色的书房里的常客。我们在书房里谈论着数学、数学竞赛、数学教育、数学文化、数学名家……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数学解题。那是我的喜好,更是他的追求。谈着谈着,他忽然间觉得可以把他对数学各类题型的巧妙解法汇集起来,我觉得行,就鼓励他着手编书。没想到半年后王老师竟然就把《数学百题 精彩千解》一书写出来了,嘱我写序。100道题,300个图,用A4纸打印出550页,还附有光盘。我觉得我自己是够勤奋的了,但在王老师这一摞书稿面前,我再一次被他的勤奋、睿智、毅力所折服。我在序言里这样说:“读了王老师的书,就能体验到什么叫精深的专业知识,什么叫数学教师的智慧!”
当然,王老师的这本书算是解题研究的书,我鼓励并同时指导他从做教育科研课题入手,提升数学教育理论。他经过文献综述后,决定把颇有挑战的“概念教学”作为突破点进行研究,课题“基于数学教学内容知识(MPCK)视角下的概念教学案例研究”成为教育部规划课题。
课题实施两年下来,他将《概念:数学教学永恒追求》一书让我审阅和写序,我写了《让“冰冷的美丽”火热起来》的序言,序言的结尾处这样写:“能让数学‘冰冷的美丽’火热起来的教师,一定是优秀的数学教师。能让数学概念教学‘冰冷的美丽’火热起来的教师,一定是更有学术涵养的优秀的数学教师。王老师就是这样的教师。”
王老师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教师,我随便说了一嘴:“你再写书,我再作序。”没想到,几年后,他又写了《理性数学:草根教师的永恒追求》一书。我很乐意为此书写序,这是王老师对我的极大信任。他让我见证了一个草根教师可以达到的学术高度,见证了从草根教师走向教学名师的成长之路,见证了理性精神之于数学探索的美丽图景。这成为我想第一个走进书里去欣赏“以草根之力,铸理性之魂”的数学教育璀璨星空的动力源泉。
从40多年前受陈清森老师点化走上“悄悄”的教育科研之路,到20年前鼓励推动王淼生老师积极搞教育科研,再到满目的成果呈现,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教育传承带来的教育者成长的朴素与美好。
二、教师共学:龙岩师友→厦门师友→“星火燎原”
1979年至1996年,我在龙岩第一中学教书。我们一群刚从师专毕业的青年教师都感到自己才疏学浅、毫无教学经验,大家一合计,决定组成一个松散的学习小组。在一位开茶馆的家长的热情帮助下,我们每周六下午3∶00聚集到小茶馆,边喝茶边吃着龙岩花生边谈论着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当一名好老师。我们的晚餐基本上就是一碗清汤粉打发,然后继续谈,一直谈到晚上10∶00左右。那时我们大多单身又都住在校内,回家的路上还在争论,没争完回宿舍再争。
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了读书,一位学长建议我们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那时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苏霍姆林斯基是谁,不知道世间还有这样一本书。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周谈论书中的一个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百条建议是我教育人生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这个“周末论教”渐渐地在闽西地区传开了,受到青年教师的关注。一些来自闽西其他地方的老师,如果要到龙岩办事或经过龙岩,往往会有意早几天来或迟几天回,争相加入我们的“周末论教”。外来的声音让我们的“论教”越论越火,十几年后,我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学习小组里的10个核心成员,就有8个获得特级教师这个殊荣。这,是偶然的吗?
2008年,我在厦门市教育局工作时,参加了厦门市第一批青年教师学习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的读书活动,老师们多次提到“共同体”是受我们龙岩“周末论教”影响而促成的。在那个浪漫的“时光驿站”咖啡厅,“共同体”的老师们谈论起阅读我写的《走向卓越:为什么不?》一书的体会。一开始,我还真是不自在,但我从他们认真的态度、智慧的思考、新颖的观念中,似乎又悟到了什么。我当时的感觉是,在教育被异化、社会心态浮躁的今天,有这么一群教师,远离名利,在纷扰中沉淀书生本色,很值得我敬佩。眼前的一幕,感觉就像当年龙岩那群青年教师身影的再现。
“共同体”多次举办过大型论坛。第一次,我说:“期盼这样的‘共同体’越来越多,若是,厦门教师的阅读就进入了新的境界。”第二次,我说:“我很高兴‘共同体’多起来了,何时能突破100呢?我期盼着。”第三次,我说:“厦门有近千所学校幼儿园,期盼每所学校都能实现零的突破!这样,我们厦门就有1000个学习‘共同体’,厦门的教师能不优秀吗?”第四次,我说:“当厦门学习‘共同体’步入理想之境时,我们厦门的教育就进入了理想之境。”
理想的“共同体”是“家园”:“家园”是温馨之家,是留念之家,是心灵之家……理想的“共同体”是“学园”:从共同之学,到共同之思,再到共同之研,进而各自践行,争取“写下来”……理想的“共同体”是“乐园”:有专业成长之乐,有特色成长之乐,有幸福成长之乐……理想的“共同体”是“创园”:当合谋共论“创”,当积极践行“创”,当论争孕育“创”……
“共同体”走过了16年,实属不易。坚守,是一种耐力,它以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能否坚守下去,往往是卓越与平庸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坚守对成功的意义更大。
厦门没有轰轰烈烈地推动教师阅读,而师者之读却悄悄地发生,这里有行政上的适度引导,但更多的是源于内心觉醒的带有民间性、草根性、自发性的教师阅读。我们在欣赏师者之读这“最美姿态”的同时,给予高度点赞,时时助力,处处呵护,不断点燃和激活教师的阅读热情,让一群充满激情的“阅读之师”,影响另一群“想读之师”成为新的“阅读之师”,再“群群相传”“群群互激”,阅读之风,尽吹鹭岛。当“阅读之师”在厦门群起之时,我所期盼的厦门教育的理想之境还会远吗?
从龙岩到厦门,我看到的是“星火燎原”的教师成长之渴望、之坚守,这是教育传承的力量源泉。
三、品玩数学:幼小初高→三所中学→“遍地花开”
我幼时读的幼儿园办得很规范,每周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的活动内容也一目了然。早操、唱歌、游戏、剪纸、泥工,还有体育活动、讲故事、学拼音、学汉字、学算术,一应俱全。能记得起的智力游戏就有七巧板、火柴游戏、积木、橡皮泥、猜谜语……
有一节游戏课,老师让我们5个小朋友一组,每个人站成一排,背后贴上1、2、3、4、5五个数字中的一个,自己不知道贴的数字是几,要通过观察其他小朋友的数字,推导出自己的数字。老师一声令下“开始”,我们就在草地上“跑”了起来,这“跑”还真不容易,既要看到别人背后的数字,又尽量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背后的数字。在竹子做的围墙一侧,标有1、2、3、4、5五个数字,谁最先准确地站到自己的数字下面,就可以得到五朵小红花,第二名得四朵,以此类推。第一次玩,我得了第二名,不甘心。第二次玩,我动了“歪脑筋”,不用看完四个数字就推导出自己的数字:看完三个即可跑到余下的两个数字处。再故意不站稳,用眼睛的余光看观众小朋友的眼神和呼声,若站对了,小朋友“欢呼雀跃”,若站错了,小朋友“表情怪异”,我就“摇晃一下”站在准确的数字下,屡屡第一。虽有“赖皮”之嫌,现在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不乖男孩”的“智慧成长”。
我读小学时,郭添荣老师总是拿着扑克牌和我们玩游戏,尤其是玩“24点”,让我们“在玩中学数学”。郭老师来上课时,我们就盯着他的口袋,一看鼓起来了,那口袋里一定有扑克牌,我们的眼睛就放光了……
我读初中时,黄荣柏老师时而找些鹅卵石跟我们玩“抢石子游戏”,时而拿个不规则的纸板让我们“剪几刀”拼成一个正方形……黄老师来上课时,我们就关注他有没有拿个布袋,我们一看拿了布袋,我们就乐啊……
我读高中时,曾亚珊老师有时笑眯眯地问我们“欲穷千里目,需登多高楼”;有时带个酒杯和小球讲“蛋碰杯底”问题。有一次在玻璃杯里放些水,当她从布袋里倒出小石子时,多数同学惊叫起来:“曾老师,你要问我们乌鸦能否喝到水,是吗?”……
我很幸运,我的幼小初高的数学老师都会“玩”,他们都能让所教的学生“爱上数学”。就像这句歌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成为数学老师后,也就很自然地“有模有样”地和我的学生“玩了起来”,这一“玩”,没想到竟玩出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龙岩第一中学时,我践行了从“好玩”到“玩好”的数学教育。“好玩”是“引趣”—烧脑游戏、激发兴趣;“玩好”是“引深”—趣中领悟、透视问题。到厦门双十中学后,我把“好玩”升华成为“玩转”实践,“玩转”是“类化”—玩个游戏、洞见一类。到厦门第一中学后,我又继续升华,“玩转”走向了“玩味”,“玩味”是“融化”—研题之史、品题之源。
于是,我凝练出我的教学主张“品玩数学”,品玩是“交融”—玩中悟透、趣中深学;于是,我在全国各地传播我的“品玩数学”教学主张,开明出版社出版了《玩出来的数学思维:任勇品玩数学108例》;于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动手玩的数学益智游戏:思维是可以玩出来的》一书,书中给出300多个玩例;于是,我又深化“品玩数学”,走向“数学‘玩育’”(“玩育”即“玩的教育”)的研究……
在北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积极推广“品玩数学”,“明远读书会”在全国直播我的“品玩数学”,《中国教师》杂志发表我的《点燃乡村教育的“两把火”》一文传播“品玩数学”;在重庆,几所“明远未来学校”开设“数学益智游戏空间”,步入“品玩数学”之境;在厦门,30多所学校开展“益智数学活动”实验;在福州,鼓楼区持续推进“数学‘玩育’”多项实验……还有,同心慈善基金会的“景润同心‘1+2’爱数学”公益活动,将持续培育众多“玩味十足”的乡村数学教师……
看着眼前的遍地花开,我看到了那个最初的幼时种子,在一代代教育者的培育下生根、发芽、长大,直到我自己接过了老师们的殷殷期盼,成为播撒“玩数学”种子的那个人。几十年的教育传承就是一部充满着情怀的教育史诗。
教育传承的每一个故事都能演奏出精彩的教育篇章,都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都是“师道”薪火相传的“顺势而为”,都是步入“做更好的教育”的自觉行动。“教育人”当怀揣“传承”之心,用教育理想追求理想教育,引领教育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作者系厦门市教育局原巡视员、副局长,特级教师)
责任编辑:孙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