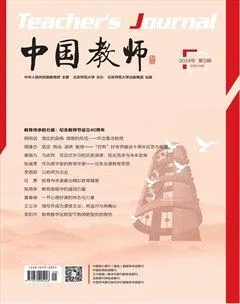以教师为志业
【摘 要】教师职业是饱含价值载荷的“志业”。教师是一个价值概念,教师之“志”是教师之“业”的价值根基。教师志业既是社会结构的价值期待系统,更是教师自身的价值自致系统。教师应处理好“致”“志”“自”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慎独自省、躬行历事四个维度下功夫,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统一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中,将职业、乐业、志业融为一体。
【关键词】教师志业 价值期待系统 价值自致系统
教师之所以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教师职业是一份饱含价值载荷的“志业”,能够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统一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中。“志业”乃是以高度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从事的职业和乐业。教师职业不仅是谋生的饭碗或手段,更是实现教育传承、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的重要的价值力量。
一、教师之“志”是教师之“业”的价值根基
如果说“授业、解惑”的主要功能是育“才”,那么,“传道”的主要功能则是育“人”,而“人”是“才”之价值根基,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进一步讲,教育教学的知识技能是“业”之根本,能够帮助教师“游于艺”;而根植于教师内心深处的价值根性才是“志”之根本,能够帮助教师“志于道”。正如帕尔默在《教学的勇气》中写到的:好的教学不能被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教师内心深处的自身认同与完整[1]。
“教师”作为“师”,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教师这一概念来源于拉丁语Pedagogue,原意是指担任监护任务的奴隶或卫士,其责任是指引(agogos)孩子(paides)去学习[2]。教师这一概念的始基是一种“价值善”:Pedagogue是孩子的引路人,这就意味着教师必须将孩子引领“好”,明确自己要以善的方式来引领孩子,明确知道要将孩子引向何方,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乃是价值引领。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虽然我们可以将教授这些行为—精于做生意、造船、技艺训练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得财富或身体健壮—的人称为教师,但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教师,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引导人从童年开始就追求美德,使之抱着热情而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3]389。教师自身应该是纯洁的、高尚的、是善的,他们必须为孩子们再现好人的希望与心怀[3]407。因此,教师职业的根基在于“价值善”:以善的方式,传授善的内容,以达到善之价值引领的教育目的。即使是纯粹技术性的手段、方法、工具,在教师这份职业中也要受到“价值善”的规约,否则就不能成为“师”,教师之“志”乃是教师之“业”的价值根基。
二、教师志业承载了社会系统的价值期待
教师之“志”首先代表了整个社会之“志”,是整个社会对美好生活和价值之善的期待。在中国,对教师职业的记载可追溯至周代。周代的教育制度较为完善,教育机构包括庠、序、学、校等。教师被称为“师”或“夫子”,是社会结构中知识的传授者和道德的示范者。孔子被尊称为“夫子”“万世师表”,体现了整个社会系统对教师的知识尊重及道德期待。从最早的“师”和“夫子”,到秦汉时期的“博士”,再到隋唐时期的“国子祭酒”和地方教育机构中的“教谕”,以及宋元时期的“教授”和“训导”,每一阶段的称谓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制度设计。这些称谓不仅是职业名称,更是对知识、学问和教育者的尊重,也是中国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崇高的价值期待。
在西方,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Philosopher)被视为教师,这意味着,教师所教导的内容不局限于具体知识,还包含了伦理和生活方式。到了中世纪,由于教育主要由教会掌管,故而教师角色主要由牧师/神职人员(Clergyman/Cleric)承担,强调的是宗教身份与教育职能的结合。到了启蒙运动与现代早期,教师(Teacher)这一称谓开始被广泛使用,反映了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和世俗化。这一时期,教师角色已广泛承担了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社会系统对教师提出了明确的角色规约及价值期待。与Teacher相近的还有Educator这一称谓,强调教师角色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教育专长,反映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
三、教师志业是教师自身的价值自致系统
社会系统的价值期待具有外在规约性,而教师的自我价值期待则是内在生成性的,是使教师成为一种“志”业的内在价值根基。用唐君毅先生的话讲,就是“道德自我”之建立,这一建立的过程永远是人格内部的问题,永远是一种内在的价值生活[4]。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报告厅举办了一次重要的演讲,主题为“以学术为志业”。韦伯用“Beruf”(天职)来表示“志业”,示为神圣的事业、灵魂的事业:含有崇高的意义,类似于英文calling(呼唤)[5]。在韦伯看来,“志业”的含义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志业”是一种怀有信念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实际上,对于教师职业而言,这种精神活动的内核乃是教师的自我价值期待系统,是教师的价值自致系统。
1. 教师之“致”
“致”的功夫直接影响了教师“志”之境界。以教师为志业,意味着教师要在“致”的维度下功夫。教师之“致”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做”或“为”,乃躬行实践之意。“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6]972二是“至”,乃“达到”之意,强调教师作为一种志业所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6]971
2. 教师之“志”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讲学订立学规之时,曾以四事相规,而首言“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6]974作为一名好教师,其专业成长的关键也在于立志,立志乃是致心中那清清然之良知之基、之始[7]。教师职业的崇高、伟大,最终必须落实为教师立志成为一个具有完整德性的大写的人,而且要在充盈自身德性的基础上,立志为整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大先生。教师要为自己“立志”,有志于成为一名“好”教师,坚定不移地守好自己立德树人的价值本分。
3. 教师之“自”
无论是“致”,抑或是“志”,均依托于“自”。在谈到“自”的层面时,就会引出“职业”“志业”之外的第三个概念“乐业”。如果致、志,最终要落实为一种能够“自”驱动的价值使命的话,职业就需要成为乐业,才能最终转化为志业。在乐业的层面谈志业,就会明晰“德福一致”的伦理学基本原理。实际上,在志业层面,教师的辛苦付出恰恰是一种精神愉悦和幸福体验,孟子的君子三乐是也。教师的辛劳付出,能够为教师带来“精神享用性”。做一名好教师,做一名无私奉献的教育者,教师乐在其中、乐此不疲。教师的幸福感不依赖于外在的奖励,而来自内在的心安,教师职业成为乐业,成为可以充分张扬自己生命意义和幸福追求的志业。
“自”是“志”与“业”的黏合剂,使志能够成为业,使业能够成为志。在黏合的过程中,包含几个不同的阶段或境界。第一,零度参与。在此阶段,“自”中是没有“志”或“业”的,此时的“自”缺乏道德主体性,是离散的原子式的个体。第二,漫不经心的参与。这种情状类似于在商场漫无目的闲逛的顾客对商品的浏览。在此阶段,教师职业是一份随时可以换掉的“饭碗或工具”。第三,仪式规程式的参与。在此阶段,教师只需完成“规定动作”即可。第四,迷恋式的参与。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的,教育学是一门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我们可以接着这句话来讲:教师是一份迷恋学生成长的乐业,教师痴迷其中,乐此不疲。阿莫·那什维利说得精彩: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第五,价值使命和意义追求。这样的境界与韦伯所言的“志业”,以及马斯洛所言的自我实现及精神超越异曲同工,教师个体的价值实现与教师职业的社会使命已实现深度的视域交融。
概言之,“自”指向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道德自我”之建构,能够为教师的职业行为找到内在的道德主体性,赋予职业行为以价值根性。如果说教师“职业”更多承载了外在的社会系统对教师角色的价值期待,那么,教师“志业”则更多强调教师“自”身的“致良知”的价值修养及价值实践过程。教师志业是将外在于教师个体的社会系统的价值期待,转化为教师自身的价值实践系统的过程,是将“期待角色”转化为“自致角色”的过程。
四、教师志业修养的具体路径
1. 格物致知与认知修养
以教师为志业的第一步在于,通过“格物致知”从而获得认知修养。此处所谓格者,乃正也;所谓致者,乃求得也。从认知修养的层面看,格物致知即穷究事物之理从而获得对于事物的正确认知[8]。教师应对教师职业之“志”具有清晰深刻的理性认知,只有根基于此,才能为教师的“明明德”打下坚实基础。从德性修养的层面看,格物的知识即是“明明德”的知识,格物之目的乃是为了“尽人性”,进而获得诚明之知,格物致知,即是在行事接物上求至善之知而入正道也。在“志”的层面,“格”之对象并非自然之物,而是心中之善。通过职业认知修养,教师最终获得人伦之知,即伦理道德原则、修己治人的道德认知,使教师在认知层面深悟伦理关系和做人做事的价值原理,从而提升自己的认知修养,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将真、善、美融为一体。
2. 诚意正心与情感养成
若要践行教师之“志”,教师还需要在涵养道德情感上下功夫。道德情感是教师对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所产生的体验、态度的综合。向善的道德情感,能够使教师的职业道德认知获得深层的情感认同,使教师获得自愿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在动力。教师自发、真诚地体验和表达,指向教师涵蕴自身的完美人格和道德美善的成长过程[9]。在此过程中,“诚意正心”是关键,是促使教师从格物致知的道德认知阶段进入到实践阶段的枢纽环节。所谓“诚意正心”,是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正确、坦诚地对待自己的内心情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自然而然地由心而发、由心而生,此乃仁德之基。教师对教育事业和学生的“真情”是发自教师内心最原始、最真实的朴素情感,这种情感是“实感”,来自教师生命存在本身的真实而无任何伪装表演的生命感知和感受[10]。“诚意正心”要求教师避免偏颇之心,克制不良的欲望和动机,不让其牵制本心而影响专注做事,要求教师以端正的心思及清醒的理智来调整、涵养自身的情感劳动,以保持中正平和之心,从而做到情理兼备、修身养性。
3. 慎独自省与意志修养
志业之志,关键在于道德意志,是帮助教师克服困难、立德树人的动力和保证。坚强的道德意志能够帮助教师自觉克服困难,排除障碍,坚决履行职业道德义务,实现职业道德理想,而且教师坚强的道德意志会对学生的意志品质和道德人格产生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具体路径上,《礼记·中庸》提出“慎独”的修养建议,要求在无人监督的独处情况下,仍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坚守道德信念,不让念头或言行违背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时刻不忘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坚持在“隐”处和“微”处下功夫,对自己的念头、言行进行反思、监督、管理,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磨砺出坚定的道德意志。
4. 躬行历事与实践磨砺
教师之“志”业最终要落实为教师“致”的实践。做公正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有勇敢的行为表现,才能成为勇敢的人。以教师为志业,要求教师不断地躬行历事。所谓“躬行”,即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一方面,道德修养的过程要求“躬行”,做到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另一方面,获得道德知识之后也应“躬行”,通过亲身实践加深理解,将道德经验与道德智慧化为己用。所谓“历事”,就是“在事上磨”,即经历不同事务的磨砺,在做事中不断修炼。“历事”可以砺心、养心,尤其对从事教师职业这样一种高度复杂并具有道德挑战性的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修养价值。
概言之,教师应通过事的不断磨砺,提升业务能力,增长道德智慧,涵养道德情感,磨砺道德意志,养成道德行为,通过躬行历事与实践磨砺,最终将职业、乐业、志业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 帕克·帕尔默.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M].吴国珍,余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2] 马克斯·范梅南. 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50.
[3]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3[M]. 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 唐君毅. 道德自我之建立[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5]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2.
[6]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李西顺.教师专业道德建构——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分析工具[J].教育研究,2022,43(1):72-80.
[8] 王绪琴.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34(1):94-99+128.
[9] 罗国杰.伦理学(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47.
[10] 李西顺.教师情感劳动概念界定的三个误区[J].教育学报,2024,20(2):54-6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毕业生就业政策研究”(课题编号:AIA220017)研究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