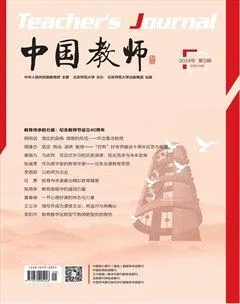作为美学家的教育学家
【摘 要】 本文基于朱光潜“作为美学家的教育学家”这一视角,讨论了朱光潜的教育学家身份,分析了他在教育学方面的文献史料和实践活动,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及历史担当。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与其美学思想密不可分,既注重心理情感的教育,又有直观的物象呈现,并作为教育青年的一种有效路径,延展到国民基础教育。对朱光潜教育思想的诠释,有助于理解“以美育人”的内涵和价值。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的当下,启示教育者要重视美感教育,它不仅可以让人抵制庸俗的思想观念,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实现完整人格塑造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朱光潜 教育学 教育思想 美学
朱光潜是20世纪杰出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教育学家。也正如郭勇健教授所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朱光潜首先是个教育学家,然后才是美学家”[1]。
当前,学界已从诸多方面对朱光潜进行了研究。如,王婷立足文学教育,阐述“朱光潜先生对文学教育的贡献实现了人的求知欲和人格修养的完美统一”[2];黄晶晶则侧重基础教育,揭示“朱光潜的基础教育思想具有批判性与建设性、前瞻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3];袁玲丽从“全人教育”入手,“探索朱光潜教育思想对当今学校素质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的启示”[4]160等。但透过美学对其教育思想的探讨,较为少见。本文首先讨论朱光潜的教育学家身份,然后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和教育实践进行分析,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和历史担当,进而为当代教育提供思想启示。
一 、教育学家的身份确证
在阐述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之前,需要厘清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朱光潜是否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学家的资质。换言之,只有先证实他作为教育学家身份的有效性,才有可能完满地开掘他的教育思想特质。
第一,朱光潜的学术之源始于教育学。从家底说起,朱光潜的“专业”是教育学,而并非美学。早年的求学之路,朱光潜与其他人一样,接受的是传统私塾的教育。1916年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5]3。因慕国故而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因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无奈转投不收学费的武昌高师中文系学习。为此,朱光潜后来在《自传》中叙述这一经历时多有不满:“除了圈点一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略窥中国文字学门径之外,一无所获。”[5]3所谓时也运也命也,朱光潜得到了一次宝贵的留港求学的机会。
1918年9月,朱光潜到香港大学暂编预科班补习一年,尔后正式就读香港大学教育系。“先生主修教育学、心理学、英国语言文学、生理学和哲学等课程”[6]3,同时,“从教育学这门课,他了解教育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如何进行科学教育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论。他还从英国19世纪哲学家兼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名著《教育论》里,认识到智育、德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及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意义”[7]。1922年3月,朱光潜在《时事新报·学灯》刊物上发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这是他第一次从西方学术视角,讨论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疾呼“‘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6]16。同年5月和12月,《教育杂志》分别在其第14卷第5号与第12号刊登了朱光潜的《智力测验法的标准》和《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两篇论文。显然,这时朱光潜已经在教育理论方面崭露了头角,具备一名教育学家的基本资格。
如上所述,在香港大学主修教育学的经历使朱光潜体会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实现兴旺发达,必须崇尚科学和求实精神。这种精神从何而来?从教育中来,从教育学中来,从平等的教育体制中来,从民主的学校管理中来。晚年的朱光潜坦言,香港大学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5]3。由此可见,朱光潜的学术之源起于教育学并非虚妄假说。
第二,朱光潜有富于历史意义的教育学文献论述。1923年朱光潜在香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应张东荪之邀,被聘为吴淞中国公学英文教员和校刊《旬刊》主编,同时兼任上海大学逻辑学讲师,并在当年12月的《教育杂志》第15卷第12号发表了《“道尔顿制”下的英文教学法》一文。“他以一种受过英式教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当时的教育体制”[8]21,对“道尔顿制”在国内学校的实施作出优弊的预判,体现出一个教育学家的社会责任心。1924年6月,“先生在《民铎》第5卷第4期上发表《私人创校计划》”[6]22,文章从五个方面指出当时教育体制的问题:一是学校制度乌七八糟,刻板机械;二是“制”与“官”的勾连,不能独立,以使教育资金亏缺;三是现行教育过于商品化,不合教育的本质;四是按年配课、分班授课、平均发展抑制优才的发展;五是贫困者缺乏平等的教育机会。朱光潜认为要改革教育制度,培育当时社会急需的“领袖人才”。为此他提出培育“领袖人才”的三个必备条件。首先,是耶稣舍己为群的集体精神;其次,是斯多葛学者简朴、淡欲的生活方式;最后,是汲取近代科学所赋予的知识和方法。
通过他对上述教育体制问题的分析,我们读到的信息是,朱光潜作为教育学家的身份已确凿无疑。但是,“领袖人才”果真可以在改造后的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吗?当然不行。朱光潜认为需要创建新的学校,才能实现其教育目的。“这种学校应该由志同道合的理想主义者集股兴建,应有希腊学园和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8]22
1924年9月,朱光潜经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英文教员,后因学潮离开了春晖中学。1925年2月,朱光潜与“先后离开春晖中学到达上海的夏丏尊、刘薰宇、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6]27,加上原在上海的叶圣陶、陈之佛、刘大白等人,在江湾创办了立达学园。在教学实体外,增设立达学会,筹办开明书店和学术刊物《一般》(后改名为《中学生》)。同年夏,朱光潜草拟公布了立达学园《旨趣》。相较前面《私人创校计划》而言,《旨趣》的目的更加明确,内容也更加精练和警拔。他说,人类与生俱来是平等的,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国家和社会也有责任,为个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个体的成长受遗传、环境的影响较大;个人的先天资赋大部分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提高;学校是实现教育改革的着眼点,主要包括:人格的熏陶、诚实的品格教育、培养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意志力五个项目[8]25。
总括起来看,朱光潜不仅是立达学园重要的创办者,还能够把专业训练形成的能力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他的教育学家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二 、“信”:一根度人的教育金针
胡适有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要把金针度与人。”[9]如要揭示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也要知晓其度人的“金针”,还须从朱光潜负笈英国留学前后说开去。
从朱光潜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时他已南下,“因为他没有处于新思潮的中心,而是处在潮流边缘地带的香港的大学校园里”[8]14,所以,他能够以一种远聚焦的眼光来批评地审视五四运动后青年的烦闷现象。此外,又由于朱光潜主修教育学的缘故,他对青年的烦闷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以教育纾解青年的烦闷,这一思路与朱光潜美育思考的起步密切相关,也成为他在之后几年对中学教育问题的关注中绕不开的难题。
事实上,在立达学园创建之初,主要“争取的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5]25,加之朱光潜不仅有其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从教经历,还熟悉底层学生的教育状况,对青年群体的身心发展格外关切。从“他一生共写教育学论文20来篇”[8]16看,要医治彷徨在“十字街头”的青年的烦闷病态,“就要在美术中寻慰情剂,因为美术也很能使人超脱现实”[10]207-208。这里的“美术”并非狭义上的专业训练,而是通过美学的方式,为烦闷的青年提供一种直观的生命体验,即教育学的非功利。
1925年9月,朱光潜等人赴欧留学。他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注册学籍,就得知昔日学生夏孟刚自杀的消息,满怀着悲痛撰写《悼夏孟刚》一文,表达自己对自杀和人生的态度。“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半让现实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观烦闷的路上去,……不过这种消极的人生观不是解决意志和现实冲突最好的方法。”[10]7那么,烦闷的青年何来超越现实的勇气呢?朱光潜指出,“自杀比较绝世而不绝我,固为彻底,然而较之绝我而不绝世,则又微有欠缺”[6]42,他认为青年为人处世的态度,应该是“不绝世”的积极改造世界的敞亮的心态,而不是私自结束生命。
回到朱光潜的教育“金针”为何物的问题上来。他说只身“在外国生活很孤寂,有时不免有一点感想,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因此就说一点心事话。为着要不拘形式地畅所欲言,也为着要和读者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我用了书信的体裁”[11]311。“信”的交流,即朱光潜的教育“金针”。
1926年9月,立达学园主办的学术刊物《一般》正式出版。虽然创刊之际朱光潜已赴英国,但由于他是其刊物编委之一,加之夏丏尊多次催促供稿,故而从《一般》开始发行,朱光潜就有《旅英杂谈》等诸多篇什与当时国内读者见面。另外,“因为当时国内对西学的了解尚不够深入”[8]15,而他的文章既有西式的直观论述,也有传统的哲学思辨,视角独特,手法不拘泥于传统样式,颇得青睐。
朱光潜早期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是1926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一般》杂志上陆续发表的《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系列文章。1929年3月,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并更名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好友夏丏尊在《序》中写道:“各信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话题,作者虽随了各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却似乎也有个一贯的出发点可寻。”[12]2那就是,揭示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身心烦闷与人生焦虑。他以美学家敏锐的思维和教育学家高超的教育艺术,深入青年烦闷的病灶,加以“信式”手术。通过“信”这根教育“金针”,“谈作文,谈社会运动,谈恋爱,谈升学选科等”[12]2,大抵都是关于人生的问题。他指出的情感包括本能和潜在意识,因此,可以直观地看到,他的“金针”具有强烈的心理学成分,他的美学著作也以“心理学”区别他家。在谈到《文艺心理学》书名时,季羡林说朱光潜“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6]89-90。何以冠用“心理学”之称谓?殊不知,心理学不仅是教育学家必修的基本功课,更是作为“美学家的教育学家”朱光潜的显著标识。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出版,“使朱光潜在青年读者中声名骤起”[8]35。《开明》杂志先后登载了一些读者的心声。其中,王守实说,《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可为青年之指南针,可为青年坦途之灯塔”[6]53;史继熏则进一步说道,“少年一切的病症,一切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光潜君和盘托出来,诚挚地送给青年,灌溉我们的生命之苗”[6]53。由于他这时期学术思想尚嫌稚嫩,难免带有个人情绪和历史局限,招来诸多指责。周柏堂质疑道,“朱先生在这书三十九页所讲的话,实在不敢苟同。道德而不能包容恋爱,则必是迷信或他种异类的化身”[6]53;左翼作家巴金、张天翼等人亦批评朱光潜把青年引向逃避现实的迷途[6]54。
但平心而论,如果我们能够剔除个人固有的专业成见,以一个身处烦闷之境的青年身份来细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许,它将再次成为我们的“教育指南”。
三、现实关怀:教育学家的历史担当
朱光潜的教育“金针”始终指向两个维度:一是富有生命气息的情感个体,二是通向澄明的现实世界。前者以培育“领袖人才”、治愈青年烦闷为教育己任,后者则以改造社会、转移风气为核心担当。朱光潜的教育核心理念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朱光潜对教育作出文化性判断。如果说留学期间的朱光潜,其教育学理论仍有缺欠,那么回国后的他,俨然成为知行合一的教育学专家。这时期前后他在美学方面也有作品问世。实际上,在1929年至1932年上半年,他已经完成了《文艺心理学》的主要章节,并将其初稿托人交给朱自清作序。这一期间,“他由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老朋友徐中舒引荐给胡适,并且以他未出版的《诗论》初稿作为其学术水平的凭证”[8]53。1933年,他以《悲剧心理学》取得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当年10月,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和西语系教授。1936年7月,《文艺心理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反响甚大。
朱光潜在美学上的老练,也就意味着他在教育学上的成熟。在谈到“志气”时,他有感当时教育的空茫,认为“没有循序渐进地学加、减、乘、除、比例、开方而想将来做算学上的发明家,那不是立‘志’而是发狂的空想”[13]89。为此,他从“此身”“此时”“此地”说起,总结出“三此主义”[13]91之结论。“此身”是自己做的事,不推诿于他人;“此时”是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事,不拖延至后来;“此地”是在当下做,不以借口幻想到另一个环境去做。而在谈到“民族的生命力”时,他说,“中国人向来偏重道德学问的修养而鄙视体格的修养”[13]93。他举了自身的例子,来说明“世间固然有许多身体羸弱而在思想学问、事业各方面造就很大的人们,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身体强健,造就一定更较伟大”[13]94。
上述问题是朱光潜基于教育学上的一种文化属性的判断。正如教育家怀特海所言,“文化是思想活动,是对美和高尚情感的接受”[14]。朱光潜的教育学兼具美学和教育双重原理。1937年9月20日,他发表题为《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一文。其中,他说“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5]71-72,进而作出“文化教育是国家的命脉”[5]72的判断。朱光潜站在教育学家的现实关怀角度,认为教育更是国家振兴之保证。
其次,风化与修养是实现教育关怀的核心。教育是个慢工夫,哲学大师康德(Immanuel Kant)以报春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大自然把胚芽赋予它们,而要使其从它们之中发展出来,这就取决于适当的播种和培植了。就人来说也是这样”[15]。同样,朱光潜的教育学也没有把知识放在第一位,取而代之的是新道德。他认为只有新道德才能唤醒民众对时代的认识,才能使国家和民族脱胎换骨,实现自由。朱光潜从两个方面给出了教育学的核心答案。第一,风化即教育。新道德靠什么推行?是教育,这也是前提条件。1941年3月23日,朱光潜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21期发表了《说校风》的文章。文中朱光潜从“风”入手,详细分析“风”衍化的五个教育意义(风格、风行、风气、风范、风化)。学校要想实现新道德,必须“在知识情感意志三方面能够交感共鸣”[16]13。另外,“风化”即为“教化”,终成“人文化成”,才能将新道德体系构建的长远目标定为“转移社会风气”。第二,修养即教养。朱光潜的教育著作和随笔较多,其中《谈修养》可直接视为教育学方面的论述,也是承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力作。观其内容,有较多部分谈及民族性问题,以《谈处群》《谈恻隐之心》最为突出。朱光潜认为教育和修养密切相关,必须要有“合群”的共同意识,“改造不善处群的民族性,要以教育和政治加以实践”[8]80。雅斯贝尔斯也有类似的主张:“教养是每个人必须获得并重新耕耘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秩序是存在之明晰性的条件。这是一片属于日常劳作的领地。”[17]故而,修养实为现实关怀的核心教养。
最后,基础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谈修养》出版后的一个月,《中央周刊》第5卷第38期登载朱光潜《有志青年要做中小学教师》一文,深入阐述他对教育职业的理解。朱光潜在文中驳斥,当了中小学教师就是穷途末路的谬论。他认为“中小学教师对于树人大业所负的责任,比大学教授所负的还大得多”[11]134。要实现教育和教育者的自信,一是普及中小学教育,就是说“应该是全体国民教育。全体国民教育没有办得好,人民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就够不上民主政治”[11]134。二是以大情怀从事基础教育,“只要你有可敬爱的地方,年幼的小朋友总是心悦诚服地敬爱你”[11]135。三是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训练、质料、地位和待遇,完善其教师职业化发展体系,使基础教育的社会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
概而言之,朱光潜号召有志青年要摒弃自私,摆脱贪图享乐和安于现状,以积极入世的教育精神,育国家之栋梁,办伟大之教育。这一切皆源自他对教育最现实的关怀、对教育学最本真的把握。由此也可以看到,朱光潜作为“美学家的教育学家”的历史担当。
四、结语
朱光潜“作为美学家的教育学家”,他的美学主要采用经验的、心理的材料,“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8]49,而“美学、艺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与美育关系最为密切”[18]。所以,朱光潜把美育作为教育青年的一种有效路径,以此实现他的教育关怀。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既有一般的普通教学原理,也有源于美学的底色。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在带给人们诸多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机。探讨朱光潜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以美育人”的内涵和价值何为,启发我们要重视美感教育。朱光潜的“美育”并非空泛之谈,而是通过“古松”“希腊女神”等具体物象,直观地阐明实际的教学问题,揭示“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19]。它不仅可以弥补由于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偏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制精神的颓废和庸俗的世界观,能够用美的眼光去领悟、看待人和事物,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有助于保持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纯正的人生趣味,“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10]47。
此外,朱光潜的育人理念亦值得我们思索。他将育人的“教”“学”喻为撑船,“教师是掌舵者,学生是摇桨撑篙的水手。舵固然要拿得稳,方向才不会错,但是水手不摇桨撑篙,船还是不能前进的”[16]13。具体而言,要想使“教”“学”形成合力,“没有情谊做基础,无论制度如何完密,设备如何周到,决难收完美的效果”[20]。故而,教学实践须将情感融入其中,因为这种情感既是美的显现,也是“德育的基础”[4]162。总之,“以全面完善的人格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传递人格的正能量,影响他人,改变社会风气”[21],才可能实现完整人格塑造的教育目标。朱光潜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仍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 郭勇健.教育学家朱光潜—关于朱光潜教育思想的系统阐述[J].美与时代(下旬),2013(8):13-20.
[2] 王婷.朱光潜的文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60-63.
[3] 黄晶晶.朱光潜基础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44-152.
[4] 袁玲丽.朱光潜“全人”教育思想及其启示[J].教育评论,2017(11):160-164.
[5] 朱光潜.欣慨室随笔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宛小平.朱光潜年谱长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
[7] 钱念孙.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14.
[8] 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9]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4.
[10] 朱光潜.大美人生 朱光潜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九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2]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13] 商金林.朱光潜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
[14]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4.
[15] 康德.康德论教育[M].李其龙,彭正梅,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31.
[16] 朱光潜.说校风[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41(321):13.
[17] 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童可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34.
[18] 周宪.美育的学科共同体及其想象力[J].美育学刊,2021(4):1-7.
[19] 朱光潜.谈美 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
[20]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71.
[21] 江飞,黄晶晶.朱光潜尽性全人教育思想[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66.
编后记
“史鉴”自2023年7月开栏以来,呈现了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教育史料与熠熠闪光的教育大家风采,其中不乏视角新颖、论证独到的佳作。本文作者的基础教育一线教师身份令编者感到眼前一亮。“史鉴”的办栏初心是“促进教育史研究成果走近一线教师,更好地服务于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本文的写作与刊用是对这一初心的真诚回应—一线教师需要教育史研究成果,一线教师也能够创造教育史研究成果。本刊欢迎基础教育一线教师、教研员多多关注、学习、研究教育史,于史海钩沉中以古鉴今,令教育之真、之善凝聚为教育之美,实为教育者之幸事。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毅德实验学校)
责任编辑:孙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