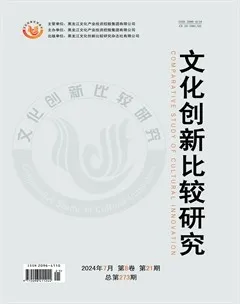宋代吉礼研究综述与展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界对宋史研究的重视,宋代吉礼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吉礼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并在吉礼的文献整理、吉礼“四类”、国家祭祀、民间祭祀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时人对宋代礼典的整理还不够深入完整,再加之受到“唐宋变革论”思想的影响,宋代吉礼研究在“断代礼制史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在讨论宋代吉礼时,可将“大宋史”的理念引入宋代吉礼研究中,从而拓宽研究思路。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动态。
关键词:宋代;吉礼;祭祀制度;民间祭祀;唐宋变革论;大宋史
中图分类号:K244;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7(c)-0072-05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Propitious Rituals in Song Dynasty
SONG Kewei
(Yichu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Yichun Jiangxi, 336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the study of Song history, the auspicious rituals of the Song Dynasty have also entered the view of researcher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ttention of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to the propitious rituals of the Song Dynast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auspicious rituals, the "four categories" of auspicious rituals, national rituals, and folk rituals. However,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epth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sorting of the Song Dynasty ritual codes by researchers, coupl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Tang Song Reform Theory",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s auspicious ritual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overall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researchers can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Great Song History" into the study of Song Dynasty auspicious rituals when discussing them, thereby expanding research ideas. At the same time, researchers also need to have a certa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trend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ancient Chinese ritual system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e propitious rituals; Sacrificial System; Folk sacrifice; Tang-Song Transition; Song history
“礼”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行为规范,随着礼仪制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吉礼是关于祭祀的礼仪,古人认为这种礼仪能够获得吉祥和幸福,故把它归入吉礼。两宋是“古代国家祭祀制度和文化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这个时期的礼制突破了士庶界限,出现了“礼下庶人”的现象,故对宋代吉礼进行讨论能对宋代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21世纪以前,日本学界对宋代礼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相关的学者主要有山内弘一、小岛毅、须江隆等。而国内学界对宋代吉礼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大陆学界的成果主要有杨倩描的《宋代郊祀制度初探》,台湾学界的成果主要有沈宗宪的《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进入21世纪,我国学界对宋代礼仪的研究日益重视,近20多年来,成果不断涌现,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宋代吉礼的基础性研究
吉礼是关于祭祀的礼仪,对于宋代吉礼的基础性研究,是初步正确了解和探讨宋代吉礼的前提,其主要包括吉礼的概念和宋代吉礼的文献整理等方面。
1.1 对“吉礼”概念的讨论
吉礼虽是祭礼,但并非所有的祭礼都是吉礼,如宋代的祃祭是一种祭礼,但其在“五礼”属于军礼而非吉礼。故在研究“吉礼”前,对“吉礼”与“祭礼”的范围进行确定,是研究吉礼的基础。对于“吉礼”概念的讨论,朱溢对其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界定。朱氏在讨论“吉礼”与“祭礼”的关系时,更倾向于将“祭祀礼仪放在吉礼体系的框架下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与‘国家祭祀’等同的概念”,由于学者对“国家祭祀”的判断不同,从而使“国家祭祀的研究范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2 对宋代吉礼的文献整理
宋代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故时人重视文化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编修了一批礼典。宋代官修礼典有《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和《中兴礼书续编》等书目,私人编修的礼典更多,仅撰写四礼(冠、婚、丧、祭)的著作,就约40种。礼典文献是研究宋代吉礼的基础,对于宋代吉礼的文献整理,学界已取得一些成就。早在2004年,王美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宋礼制研究》中,从昊天上帝、五方帝等12个部分,对宋代吉礼文献进行了较早的整理。近些年,学界对宋代吉礼文献的整理取得了较大进展。在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清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该书对秦汉至明代的礼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被称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百科全书”[1]。202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宋元国家祭祀文献辑刊》,“能为宋元时期的国家祭祀的研究提供历史文献支撑”[2],并为研究宋代吉礼提供重要的史料。
2 宋代吉礼“四类”研究
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吉礼主要分为4类,即“天神曰祀、地祗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与武成王曰释奠”[3]。学界对于宋代祭祀活动的关注,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2.1 祭天礼仪研究
祭天礼仪是学界在宋代祭祀活动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这种礼仪的祭祀对象有天神,也有日月星辰。目前,学界对宋代祭天礼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郊祀、天神祭祀、星辰祭祀和明堂礼等方面。
郊祀,是中国古代帝王在郊区进行的祭祀行为。学界对宋代郊祀制度的基础性研究较多,主要包括北宋郊祀制度的演变、内容、机构,郊祀改革的原因、影响。江云从礼制史的角度,探究了北宋郊祀制度的演变[4],同时还对北宋郊祀制度的费用问题进行了探究[5]。王刚讨论了宋代郊祀的运行和参加郊祀的官员群体[6]。曹福铉探究了宋代对官员的郊祀赏赐[7]。此外,学界还对北宋郊祀制度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进行探讨。孙继辉讨论了宋神宗时期南郊祭祀改革对宋代政治稳定的作用,指出当时的北宋政府为了从学术上统一思想,维护其统治的正统性,便对“承载着天命所归”的南郊祭祀进行了改革和规范[8]。袁菊花从宏观的角度,对整个北宋南郊祭祀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讨论,其基本观点与前者相似,也认为北宋君主通过这种郊祀制度,来显示宣示其统治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向民众展示了一种社会伦理秩序[9]。
天神祭祀、星辰祭祀和明堂礼,亦是学界研究较多的领域。关于天神祭祀的研究,王志跃主要从礼制史的角度,通过对昊天上帝与五方帝的关系、祭礼中的道教因素和皇权支配的祭礼体系等内容的研究,探讨唐至宋祭礼的变化[10]。赵贞则从星辰祭祀的角度,将宋代的“德运”之争与大火星祭祀进行了联系,并指出两宋推崇的五行尚“火”和“炎炎火德”有密切关系[11]。杨高凡从礼制史的角度对宋代明堂礼进行了梳理,并对明堂礼的配享对象、明堂大礼赦宥制度和明堂大礼恩赏制度等进行了讨论,并认为这种礼仪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其世俗功能性比前代更突出。同时,这种制度也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给社会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12]。
2.2 祭地礼仪研究
学界对宋代祭地礼仪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腊祭和山岳祭祀等方面。腊祭是中国古代祭祀农业生产神灵的一种礼仪,祭祀时间是腊月。徐立平从祭祀活动、狩猎、赐物和民间活动等方面,对唐宋时期的腊日节的活动进行整理,并对唐宋时期腊日节的特点和衰落原因进行探究[13]。对于山岳祭祀的研究,学界更侧重于研究宋代的泰山祭祀。刘云军从宋代官方东岳祭祀、民间东岳祭祀、泰山封禅、东岳庙的修建和笔记小说中的东岳神等方面,对宋代东岳祭祀的情况进行了阐述,并指出东岳神与宋人之间交流,是一种由“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构成的一个混合体结构[14]。关于宋代的泰山祭祀,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宋真宗封禅泰山,这个事件也是学界较多讨论的一个领域。宫磊对宋真宗封禅的缘起、仪式和影响进行了讨论,并认为这次封禅对宋代的政风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得泰山平民化,并逐步变化为“民俗山”[15]。汤勤福认为泰山封禅的实质是宋真宗解决其统治危机的一种手段,反而是一场政治闹剧。该措施给宋代的政治带了恶劣的影响,并促使宋代走向积贫积弱[16]。
2.3 人鬼之祭和先贤之祭研究
对人的祭祀,主要有对先祖的祭祀、对已故先贤的祭祀和对在世之人的祭祀三种。对先祖的祭祀,在吉礼中称为人鬼之祭,目前学界多从文化视角,对宋代的先祖祭祀进行讨论。王善军从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5个方面,对宋代的宗族祭祀进行了讨论,指出宋代是宗族组织的奠基时期,宗族祭祀即强化了族权,也影响了宋代民间文化,并确立了一种适应当时社会的新体系[17]。游彪指出宋朝是中国古代新型宗族体系确立的最重要时期,宋儒在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新型宗族体系构建了理念。这些理念在元朝以后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从而使祠堂成为民间常见的家祭场所[18]。此外,也有学者对宋代皇家进行祭祀的庙宇予以关注。贾鸿源从三个各具特色的历史时期,对北宋皇后别庙的空间布局和布局特征进行讨论[19]。
对已故之人进行祭祀时,宋人多会通过建先贤祠的形式对其进行祭祀。王美华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出发,将唐宋的人鬼之祭视为一个整体,认为随着释奠礼制度的规范,唐宋时期释奠礼仪逐渐在地方得到推广,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20]。胡利红主要从正祀和随祀两个方面,对南宋的释奠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21]。
同时,中国古代也会为一些功劳大的人物建生祠。学界对于宋代生祠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李怡梅从生祠的时空分布、奉祀对象、生祠的修建和生祠的社会意义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对南宋时期东南诸路的生祠进行研究[22]。张诗瑞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全宋文》中的生祠记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对生祠的影响、意义和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了讨论[23]。
3 宋代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研究
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是学界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宋代吉礼进行研究,其主要讨论宋代吉礼与政权建设、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及吉礼对宋代社会的影响等。
3.1 国家祭祀研究
学界对国家祭祀的讨论,成果较少。谢一峰认为道教作为一种官方宗教,在两宋时期已经融入了国家祭祀体系中,并形成了“真宗模式”和“徽宗模式”两种不同的国家祭祀模式。这两种国家祭祀模式,对解释南宋政权合法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24]。杨俊峰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动态地考察了唐宋之时国家与地方祠祀之间的互动[25]。
3.2 民间祭祀研究
相比较国家祭祀,学界对民间祭祀的关注度较高,其中淫祀和家祭最为典型。淫祀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民间祭祀,亦是学界研究的一个典型领域。学界从多个角度对宋代淫祀进行讨论,主要包括淫祀政策、淫祀观、不同社会阶层对淫祀的态度、两宋政府对淫祀的态度和淫祀对两宋社会的影响等,代表性论文主要有杨建宏《略论宋代淫祀政策》、皮庆生《宋人的正祀、淫祀观》《论宋代的打击“淫祀”与文明推广》、王瑜《宋代“淫祀”观及地方官员的政治实践》《宋代“淫祀”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政治应对》等。
家祭,是家庭对已故先人的一种祭祀制度。刘雅萍从家庙制度确立的过程、家庙的象征含义、家庙的建筑、家祭制度等方面,对宋代的家庙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并指出家庙是时人振兴家族的重要手段,也是百姓与祖先进行交流的一个场所[26]。杨逸讨论了宋儒在墓祭入礼和家祭礼制重构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浦江郑氏为例进行了具体研究[27]。对于墓祭的讨论,李旭在《宋代家祭礼及家祭形态研究》一文中亦有论述。对宋代家庙历史地位的讨论,王鹤鸣认为,宋代的家祠在中国古代家族祠堂发展史中,处于一个过渡状态,其上承唐代家庙,下接明清家族祠堂[28]。
此外,台湾学者杨宇勋从捐资建祠庙、担任祠庙的都会首、为筹集经费而摊派科率、祠庙活动如何模仿官方威仪等方面,对南宋富民如何参与祠庙活动进行讨论[29]。
4 宋代吉礼其他方面的研究
礼典文献是研究宋代吉礼的基础,目前学界多是从礼典的编纂、体例、内容、价值等角度,对这些礼典进行综合研究,有部分学者在讨论宋代礼制或礼典时,亦会对宋代吉礼有所涉及。此外,宋代吉礼也引起了其他领域的注意。在艺术学领域,已有研究者对宋代吉礼中的舞蹈和音乐,进行了较多的探讨。
4.1 宋代礼典中的吉礼研究
尹承在《(太常因革礼)研究》一文中,用较多的笔墨对宋代祭祀礼仪的类型、宗庙礼制和宋真宗时期“神道设教”之礼进行探究,并对《太常因革礼·吉礼》中部分散佚的内容,进行辑佚[30]。尹氏在《太常因革礼·吉礼》中辑佚部分内容,对研究宋代吉礼,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4.2 宋代吉礼舞乐研究
宋代吉礼舞乐研究,主要是讨论宋代吉礼中的音乐和舞蹈,其主要包括宫廷用乐、用乐比较和吉礼中的舞蹈等方面。王雪丽从宫廷仪仗音乐的种类、用乐程序、乐队编制、乐曲和乐章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宋代宫廷仪仗音乐进行研究[31]。李琳对辽、宋、金三朝吉礼的用乐情况进行比较,并认为辽、宋、金之间的用乐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32]。赵艺兰对北宋不同时期文舞祭祀和武舞祭祀进行讨论[33]。李卫讨论了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礼乐制度对南宋礼乐发展的重要意义[34]。
5 宋代吉礼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界对宋史研究热度的提升,如今“中国的宋史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学界对宋代吉礼的具体礼仪研究、吉礼文献的整理,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相比研究更为成熟的唐代吉礼,学界对宋代吉礼的关注度偏弱。
5.1 宋代吉礼研究的不足
第一,学界对宋代吉礼的研究,多集中具体礼仪的个案研究,较少从宏观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由上文可知,学界对宋代吉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个案中,如祭祀活动中的郊祀、宗庙祭祀,民间祭祀中的淫祀等方面。少有学者从“国家祭祀”或“民间祭祀”的角度,对吉礼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相比其他朝代的吉礼或祭祀制度研究来说,显得比较单薄。
第二,在宋代吉礼的研究中,存在“断代礼制史研究不足”[35]的问题。由于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宋代礼制时,多会将唐、宋礼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唐、北宋礼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承接性”。在“唐宋礼制”的模式下,学界在“谈唐”时也多会“谈宋”。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唐代吉礼的研究成果要多于宋代的成果,有“强唐弱宋”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降低了“宋制”研究的断代性和专门性。
第三,在两宋吉礼的研究中,存在着“多北宋而少南宋”的现象。从史料的获取度和丰富程度来说,北宋优于南宋。在目前传世的宋代礼典中,北宋礼典的传世情况要比南宋礼典的传世情况要好。南宋的礼典《中兴礼书》和《中兴礼书续编》“在南宋编成后仅以抄本流传,后散佚不存”,现存的这两部礼典是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版本[36]。从学术思想来看,由于北宋的礼制多继承唐制,“唐宋变革论”在客观上推动了北宋吉礼研究的发展。从南宋吉礼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已有学者对南宋吉礼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性梳理,并对两宋礼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葛金芳指出,到了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宋礼“开始试图挣脱唐礼的束缚”,同时南宋礼制在沿袭北宋礼制基础上“颇有其时代特色”[37]。
5.2 宋代吉礼研究的展望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文认为学界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应在宋代吉礼研究的整体性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这种关注侧重从宏观视角探究宋代吉礼内容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南宋吉礼的研究深度和从“大宋史”的视角讨论宋代吉礼与辽、金、西夏礼仪之间的互动;二是研究者应扩大研究视野,注重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
首先,从“大宋史”的视角讨论宋代吉礼。所谓“大宋史”,是邓广铭先生所倡导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强调“辽、宋、西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38]。但是,这种理念并不是要求要同时精通辽、宋、西夏、金、元的历史,而是在关注某一个领域时“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39]。在研究宋代吉礼时,讨论宋代吉礼与辽、西夏、金、元吉礼之间的关系,是“大宋史”在宋代吉礼研究中的一个表现。
其次,研究者还需加强对南宋吉礼的研究。在北宋吉礼和南宋吉礼研究中,后者是宋代吉礼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学界对南宋吉礼研究的不足,使得宋代吉礼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最后,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关注。中国古代礼制也引起日本、新加坡学者的注意。在《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一书中,朱溢提到的日本相关学者就有57人,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共133种[40]。在吉礼方面,日本学者主要从天神、地祗、社稷、禘袷、祖先和宗庙等方面,对中国吉礼进行研究[41]。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能为我国学者研究宋代吉礼提供借鉴。
6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史学界对宋代礼制研究力度的加大,学界在宋代礼典整理工作的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宋代礼制研究”在21世纪以前存在的“国外研究热国内研究冷”的局面正在扭转,同时研究吉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吉礼是祭礼,从祭祀对象来看,祭天、祭地体现了中国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祭祖先体现了中国先民对家庭的思考,祭先贤体现了中国先民对英雄人物的思考。“人与自然”“家庭和谐”和“缅怀英雄”,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虞万里.礼学文献的渊薮笃实功夫的结晶[N].中华读书报,2021-01-27(9).
[2] 马晓林.宋元国家祭祀文献辑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
[3] 王美华.唐宋礼制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7.
[4] 江云.北宋郊祀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6.
[5] 江云.对北宋郊祀费用的探讨[J].唐山师范学院学院,2015(4):92-95,103.
[6] 王刚.宋代郊祀大礼中的下层助祭官吏群体[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2):107-115.
[7] 曹福铉.宋代对官员的郊祀赏赐[J].宋史研究论丛,2005(00):66-83.
[8] 孙继辉.尊君与礼制:北宋元丰南效祭祀礼制改革考论[D].开封:河南大学,2012.
[9] 袁菊花.北宋南郊郊祀制度变革研究[D].延安:延安大学,2018.
[10]王志跃.唐宋祭礼变化及实施考论[J].广西社会科学,2019(9):93-97.
[11]赵贞.宋代的“德运”之争与大火星的祭祀[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1):18-22.
[12]杨高凡.宋代明堂礼制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1.
[13]徐立平.唐宋时期腊日节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14]刘云军.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8.
[15]宫磊.宋真宗封禅探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16]汤勤福.宋真宗“封禅涤耻”说质疑[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10.
[17]王善军.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J].世界宗教研究,1999(3):114-124.
[18]游彪.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322-327.
[19]贾鸿源.北宋皇后别庙空间布局演变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00-112.
[20]王美华.庙学体制的构建、推行与唐宋地方的释奠礼仪[J].社会科学,2014(4):155-164.
[21]胡利红.南宋释奠礼概述[J].杭州文博,2019(1):150-156.
[22]李怡梅.南宋东南地区生祠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9.
[23]张诗瑞.宋代生祠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8.
[24]谢一峰.常态、变态与回归[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20(1) :28-60,294.
[25]杨俊峰.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6]刘雅萍.宋代家庙制度考略[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62-68.
[27]杨逸.宋代四礼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6.
[28]王鹤鸣.宋代家祠研究[J].安徽史学,2013(3):75-83.
[29]杨宇勋.试论南宋富民参与祠庙活动[J].华中国学,2015(1):192-207.
[30]尹承.《太常因革礼》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31]王雪丽.宋代宫廷仪仗音乐研究[D].天津:天津音乐学院,2021.
[32]李琳.辽、宋、金祭祀天地用乐的比较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20.
[33]赵艺兰.北宋郊祀乐舞仪制沿革略论[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6):35-40.
[34]李卫.南宋绍兴十三年宫廷礼乐的重建[J].艺术学研究,2023(5):48-63.
[35]汤勤福.百年来大陆两宋礼制研究综述[J].历史文献研究,2015(1):276-296.
[36]史广超.《中兴礼书》及《续编》版本考述[J].图书馆杂志,2013(5):85-90.
[37]葛金芳.等著.南宋全史(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44-274.
[38]李华瑞.近二十年来宋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2020(6):117-125.
[39]包伟民,戴建国.开拓与创新: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M].上海:中西书局,2019:430.
[40]朱溢.事邦国之神祗: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1]杨华,等著.中国礼学研究概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456-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