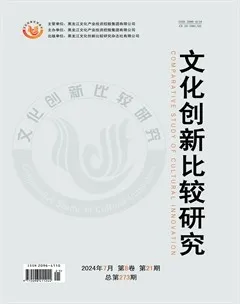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路径探析
摘要: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凝结、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大教育意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更新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所赋予的强大精神力量。该文对国内外关于红色文化数字化的内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单梳理,从育人内容、育人主体、育人客体、技术平台、保障机制等5方面指出了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育人困境。最后,该文提出了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路径,包括:针对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特点,丰富红色文化数字化形式的措施;依据新时代教学背景,提升思政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遵循新时代教学规律,开发与挖掘新型数字化教学平台与手段。
关键词:数字教育;红色文化;协同育人;创新;实践;平台
中图分类号:G127;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7(c)-0043-05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YE Ruiting
(Guangdong Technology College, Zhaoqing Guangdong, 526100, 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e, as a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condensed and precipitated 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as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help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werful spiritual power endowed by red culture.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digitalization of red cultu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 proposes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from five aspects: education content, education subject, education object,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Finally, it propo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measures to enrich the digital forms of red cultur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teaching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enhance the digital education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follow the teaching laws of the new era, develop and explore new digital teaching platforms and means.
Key words: Digital education; Red cultur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novation; Practice; Platform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加快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2023年10月,全国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高了文化对于国运的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数字思政”概念越来越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同,旨在“以数化人、以数助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向时代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范式,它能够打破教育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容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1 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战胜各种困难和艰险挑战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与信念。“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展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文化结晶,也是青年学生学习思政、体悟思想的宝贵资源”[2],“是高校立德树人的育人底色”[3]。
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AI智能、VR虚拟、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对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建筑、文物等资源进行重组、分析,使红色文化资源向虚拟现实、多维立体、动态具象等可视化内容进行数字转化。通过数字化手段,将红色历史、革命斗争、英雄人物等红色文化元素以数字化形式进行记录、保存和传承,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示红色精神,如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等,创新红色教育的方式,开发出丰富多样的符合新时代教育需求的红色教育资源和工具,创造各种红色文化主题的数字内容、游戏、应用等产品,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红色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尚。将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文化,“能够克服传统传播方式的局限性,拓宽红色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渠道,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改变教育方式单一且缺乏灵活性的状况,增加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4];能够让尘封于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的各类馆藏文物打破历史时空的限制,“穿越”到思政课堂中,让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活起来”;同时也能赋予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新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激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在新时代继续传承红色文化精神,推进高校思政工作守正创新,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获得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思政育人“1+1>2”。
2 红色文化数字化发展现状及趋势
目前,国内关于红色文化数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传承、数字化推广、数字化教育等方面。数字化保护如广州起义纪念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将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片和视频等进行数字化保存,“依托数字技术,可以将文物资源虚拟复原”[5];数字化传承如“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化技术采集扫描文物资源后进行数字转化,建立数字资源库”;数字化推广如“红色博物馆”网站和“红色文化广东”网站等,提供多种数字化展品、在线学习和互动交流服务;数字化教育如华南师范大学的红色文化教育中心和广州市革命历史教育基地等,向学生和公众普及数字化红色文化知识。学界关于红色文化数字化及其在思政育人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红色遗址的保护和宣传,需要进一步开展系统性、理论性、一体化的研究,整合、保护、开发与搭建红色文化数字化多元传播平台,在虚拟技术的支持下进行高质量的区域红色文化思政课程创新。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和推广教育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美国教育部在2016年发布了一份名为“教育科技计划2020”的战略计划,旨在促进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英国教育部2019年发布《教育科技战略:释放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加大对数字化硬件和软件设施的财政投入。2023年2月,《世界数字教育发展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应加强政策对话沟通、基础设施联通、数字资源共享、融合应用交流、能力建设合作等,共同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和2030年教育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数字化教育已然成为国际国内教育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3 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育人的困境
3.1 内容困境
内容困境主要表现为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共享的复杂性。目前,红色文化数字化程度参差不齐,尤其是对于高质量、多样化的资源。一些特定时期的历史资料,数字化的工作尚未完全覆盖,难以获取或者整合资源,数字化资源的不平衡分布也导致其融入思政课程的难度增加。各地区已有一些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成果,以广东省为例,2021年6月广东正式上线一款微信小程序“打卡广东红”,该程序主要收集整理广东省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广东特色红色旅游景点、重大历史红色故事、古驿道等100多项红色地标,结合VR、AI多项技术,实现线上线下打卡一体化。但该程序仅是对广东省内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打卡和展示,如在讲授北伐战争时,带领学生“重走北伐路”,结合小程序中的“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旧址”等红色景点在线参观,但对于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省外的行军路线就无法继续利用该程序资源进行教学,难以保证课堂教学内容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关键一点在于数据资料的共建共享,搭建统一的国内红色文化资源平台,同时贯通各个省市地区的数字化教育资源,进行跨区域、跨学科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实现协同育人。
3.2 主体困境
主体困境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教学能力和素质不足,包括教育主体的数字技术操作、数字信息获取、数字创新与应用、数字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在数字技术操作上,教育主体没有接受过比较正式的数字化教学培训,缺乏数字化教学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不熟悉如何有效地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进行教学,普遍存在“本领恐慌”的问题,如网络环境不稳定或网络速度较慢的情况下是否能顺利进行数字化教学,VR虚拟仿真实验室中如何操作中控系统、如何体验VR眼镜等。在数字信息获取上,教育主体需要及时利用教育主体网络工具获取更多的数字化资源,并能够对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信度进行评估和判断。在数字创新与应用上,要求教育主体能够灵活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教学和学习中的问题,开展数字化教学设计、课程开发和教学评估等工作。在数字信息安全上,教育主体要注重保护学生隐私和敏感信息不被恶意攻击和泄露,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数字空间内不被错误思潮影响,提高辨别真伪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3 客体困境
一方面,由于学生个体差异、教育背景和技术接受程度的不同,学生对数字化教学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对数字化教学的参与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学生对新技术的态度、学习动机等,有些学生可能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或者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对数字化教学持怀疑、消极或抵触态度。另外,数字化教学更易分散学生注意力,一些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容易被数字化设备上其他的娱乐内容所吸引,受到社交媒体的诱惑,如微信、QQ、抖音等,而忽视学习任务,学习效果和参与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要避免思政课堂过度娱乐化。教师能否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确保互动过程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避免互动变成纯粹的娱乐活动,平衡趣味性和理论性,成为达成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
3.4 技术平台困境
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教师端、平台端与学生端,将数字化教学模式和传统课堂模式完美衔接。目前,数字化设备和平台尚未让师生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未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优势与潜能。以思政虚拟仿真实验室为例,超星平台提供的VR数据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重要红色遗址纪念馆的简单介绍,缺乏更为生动的VR视频资源,只是完成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易地搬迁”,没有真正让红色文化“活”起来。同时,数字化赋能带来技术障碍和安全问题,如网络连接不稳定、信息泄露、病毒感染等,数字化教学过程涉及学生的个人信息、学习记录等敏感数据,存在泄露、滥用等风险,如教学平台上的资料来源不明,或存在偏颇的观点,会误导学生,影响他们的正确理解和判断。而过度依赖数字化教学平台和工具,也可能导致教学过程出现故障或中断、教学无法正常进行的问题。
3.5 保障机制困境
一方面,数字化教学平台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昂。要实现数字化赋能,需要建设和维护适用于思政课程的数字化教学平台,涉及硬件设备、软件开发、服务器维护等,高昂的成本,对于一些学校而言可能难以承担。另一方面,数字化智慧教育生态保障机制不足,需要制定长期的发展策略和规划。数字化智慧教育需要对传统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转型,而教育体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课程设置、评估体系、教师培养等多方位全方面的变革,需要长期的发展策略和规划,以确保红色文化数字化能够得到有效的整合和推广。数字化教育所需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这些技术发展和更新日新月异,现有的保障机制无法跟上技术的发展速度,导致保障机制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4 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4.1 根据新时代学生特点,丰富红色文化数字化形式
新时代的学生是数字化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与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化技术密切相连,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种形式的信息,对于传统的教学形式缺乏耐心和兴趣,更倾向于多媒体和互动式的学习方式。可以开发红色文化的互动式学习应用,使学生能够通过参与式学习方式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精神和价值观。如红色剧本杀、红色动漫、红色手游等。以红色剧本杀为例,可以将广州起义、深圳抗战战役等历史事件作为红色剧本杀的主题,让学生在游戏中模拟历史情境,锻炼团队合作和推理能力,在休闲娱乐中增强与红色文化的情感互动。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红色文化场景的虚拟实境体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虚拟仿真、混合现实、全息投影等新颖的数字媒体技术,能够打破红色文化教育现实物理空间的约束,从人的感官上延展时间和空间,将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革命史、奋斗史、英雄史映照进现实,让历史‘真实’再现重演”[6],将学生带回重要历史时刻,增强学习的体验感,如《长征路上的红色故事》互动式展览、《红色记忆——延安革命纪念馆》虚拟展示项目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红色文化,从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虚拟技术的使用“需要把握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分类逻辑,界定 VR 技术在红色文化资源中的应用分类。”[7]把红色文化根据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和再生形态,物质形态包括遗址、文物等,精神形态包括人物、事件等,再生形态包括诗词、书法、雕塑等,根据不同形态具有的特色采用VR技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建设红色文化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公园等地标性建筑,收集整理丰富的红色史料,“如家书、遗书、情书、入党申请书等,都可以在数字化时代通过纪录片和沉浸式剧场等媒介形态从不同侧面反映革命战士的革命意志与家国情怀”[8],为师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研究资源。也可以加强开发红色旅游研学经典项目,探寻各个红色景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效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助力地方打造优质的红色文化品牌”[9]。
4.2 依据新时代教学背景,提升思政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
一方面,提升教师熟练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高校可以组织针对教师的专业培训,包括数字化教学工具的使用方法、在线教学平台的操作技巧、教学设计的理念等方面的培训;建立数字化教学导师制度,由资深的数字化教学专家担任导师,指导和帮助教师提升数字化教学技能,解决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组织教师间的案例分享与交流活动,鼓励教师分享自己在数字化教学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相互学习、借鉴,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高校应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为教师提供技术咨询、故障排解、系统维护等支持,保障数字化教学平台和工具的稳定运行,建立与数字化教学能力相关的评价与激励机制,将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纳入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薪酬激励、荣誉表彰等方式激励教师提升数字化教学能力。教师应保持持续学习的心态,关注数字化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和趋势,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数字化教学能力。
另一方面,培养师生数字化学习习惯,实现红色文化数字化教育全过程管理。“培养‘Z世代’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抢占红色教育数字化新赛道是数字赋能‘Z世代’大学生红色教育的重要现实路径。”[10]制定数字化学习指南,明确师生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使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规范和标准。学生定期使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学习,积极参与在线讨论,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等,逐步提高数字化素养。
4.3 遵循新时代教学规律,开发新型数字化教学平台
新时代教育教学可以将信息技术的优势融入教学过程,借助数字化技术,搭建各类数字化教育平台,培养学生数字化学习理念与习惯,如智能化教学系统、虚拟现实教学平台、移动学习应用平台、社交化学习平台、数字化教学分析平台等。以社交化学习平台为例,创建红色文化在线学习社区,为师生提供交流、讨论、分享的平台。学生可以在学习社区中创建个人资料,与同学建立联系,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可以参与论坛讨论,发表观点、提出问题,与同学和教师进行交流和互动,如私信、关注、点赞等。为学生提供学习社区、讨论论坛、在线课程、学习任务、社交等功能,鼓励他们在社区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推动红色文化数字化教育的发展,建立数字化教育的监控与评估机制,并定期对师生的数字化学习和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和反馈,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进行调整和改进。关于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搭建,可以学习借鉴国外数字化教育的经验,国外现已开发的比较成熟社交化学习平台有Edmodo、Schoology、Google Classroom等。如Schoology平台,面向学校、教师及学生,能够实现课程开发与管理,进行学习资源的分配,并对学习过程及结果进行跟踪评估,为师生课堂内外交流提供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目前该平台的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 200万。目前,我国也已启动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首先在广东、海南试点应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优质数字资源共享,计划2025年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应用规模。对于高校教育来讲,全国性的数字智慧教育平台也亟待搭建,确保国内数字化红色文化教育资源统一大市场。
5 结束语
总之,数字化技术赋能红色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实现受教育者在学习中的意识沉浸和思想引领,增强教学过程的体验感、参与感和幸福感。红色文化数字化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重要着力点,能够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带来新的理念和模式变革,不断推动红色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有效传承。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三)[J].前进论坛,2021(9):18-19.
[2] 廖卫华,樊心颖.大数据时代课程思政中红色文化数字化建设探究[J].红色文化学刊,2023(4):91-98,112.
[3] 马闯.红色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逻辑机理、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科学,2024(2):68-73.
[4] 徐茂华,谢嘉滢.重庆红岩文化数字思政的价值意蕴及路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1):26-34.
[5] 张雯雯,行国通,汪家明.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承路径[J].中国民族博览,2023(21):168-170.
[6] 张宝君,骆文迪.数媒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沉浸式教育的检视与策略[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4,38(1):19-28.
[7] 胡艺轩,佘醒,张煜鑫.VR技术下红色文化的审美转向与传承策略探究[J].黄山学院学报,2023,25(6):109-113.
[8] 彭翠,王冠华.太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J].海河传媒,2023(4):37-40,44.
[9] 朱晓莉.媒介融合时代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J].文化产业,2023(30):145-147.
[10]陈思楠.数字赋能“Z世代”大学生红色教育现实路径研究[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3,32(6):6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