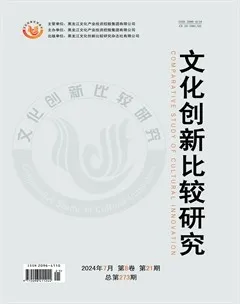文学地图与艺格符换的潜在联系
摘要:“艺格符换”作为对视觉艺术的文字描述形式,不仅具有跨媒介叙事的功能,还拥有图文转换的想象能力。作为融合了文字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概念,艺格符换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就包含了“文学地图”。“文学地图”旨在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说明文学与图像之间有着强有力的联系。“艺格符换”和“文学地图”是两个从古希腊发展而来的概念,从本质上看,两者文学艺术的共有属性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这两个概念作为认识和建构世界的方式,文学在其中的影响非常广泛,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作者的遣词造句和空间意识建构。
关键词:艺格符换;文学地图;视觉艺术;地理;跨媒介;空间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7(c)-0005-04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Map and Ekphrasis
LIN J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Abstract: As a form of text description of visual art, "ekphrasis"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 of intermedia narrative but also has the imaginative ability of graphic transformation. As a comb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l art and visual art, ekphrasis covers a wide range of fields, including "literary map". "Literary map" aims to present and reveal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two narrative language systems of "picture-text", and there is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mages. As two concepts developed from ancient Greece, the common attributes of ekphrasis and literary map influence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in essence.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world, these two concepts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literature, and their influence will gradually affect the author's choice of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Ekphrasis; Literary map; Visual arts; Geography; Intermedia; Space
“艺格符换”作为西方艺术史、文学史上的一个古老术语,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通常被看作是对视觉艺术的语词书写,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艺格符换”具有跨媒介叙事的能力,一方面蕴含着对视觉图像进行语词再现这一从图到文的转换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艺格符换”超越自身媒介特性,追求如绘画般的视觉图像效果。而地图作为一种古老的绘画艺术,作为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之间重要的工具,与艺格符换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艺格符换”和“文学地图”的概念,浅析两者之间的关联。
1 “艺格符换”的概念
“艺格符换”,英文“ekphrasi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修辞学的术语。作为希腊人描述艺术的一种方式,其本意是:“以丰富华美的辞藻生动形象地描述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以及其他各种细节,赞扬作品所表达的美感”[1]。“ek”表示“出来”(out),“phrasis”表示“说出”(speaking),合在一起意为“说出来”。现如今,主要是指用极其详尽的字词对一物体或是艺术作品或是某个场景所进行的形象逼真的写作方法。
通常认为,最早的艺格符换也就是最早用文字解释图像的例子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第18篇中对于“阿基里斯之盾”的细致描述:“神匠先铸战盾,厚重、硕大,精工饰制,绕着盾边隆起一道三层的圈围,闪出熠熠的光亮,映衬着纯银的背带。盾身五层,宽面上铸着一组组奇美的浮景……”[2]此外,荷马倾尽华丽的笔墨描述了五层盾牌上所有的世间万物,从星辰宇宙到平民百姓,读者在读后便会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个极尽奢华的盾牌,这便是艺格符换从文字到图像转化中所带来的跨媒介的作用,文字与图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通过不同媒介之间的跨越形成了照应。而后,由于修辞学及演说术这一艺术形式的消失,艺格符换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寂。到了中世纪,艺格符换作为一种具有隐喻赞美性的文学形式得以传承,其功能从对艺术作品的文字描述变成了有着宗教意义的诗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重建古典文化,使得艺格符换随着古典修辞学再次复兴,如但丁的《神曲》、彼得拉克的肖像诗。
20世纪,施皮策将艺格符换定义为对艺术作品进行诗意描述的文学类型,这使得艺格符换成为一个技术性的术语,并使得文字与图像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系有着延续性。他在《〈希腊古瓮颂〉或内容与元语法》中写道:“它属于‘艺格符换’文类,为荷马、忒奥克里托斯到纳斯派和里尔克的西方文学所熟悉,即对绘画或雕塑的艺术作品的诗的描述,用戈蒂叶的话来说,描述隐含着‘艺术的转换’,通过语词媒介,去复制可感的‘艺术对象’。”[3]自施皮策将“艺格符换”视为一种文学类型之后,其从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立性,并进入了文艺批评领域,“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y)进入学术视野,批评家们往往用“艺格符换”来指称诗歌与绘画、语词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此外,“艺格敷词”由于其自身媒介间性,成为跨艺术批评的重要议题。之后,克里格将“艺格符换”提升到一种诗学原则。他认为:“当诗歌呈现出空间艺术或造型艺术的 ‘静止’元素时,诗歌的艺格符换维度就得到了显现。”[4]艺格符换形成了一种对图像艺术进行文字描述的文学原则。而赫弗南认为:“艺格符换是对形象再现的口头再现。”[5]但赫弗南的定义也并不完美,不是所有视觉作品都可以被视为“形象再现”。本文中,仅将“艺格符换”视为语言对文学艺术的描述、转化和模仿,是一种文类。
艺格符换现在作为当代欧美跨艺术诗学的核心概念,研究价值非常丰富,其跨媒介的属性不仅融通了艺术、哲学、文学等各学科领域,还为当下艺术史及其他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立场。如今的视觉文化如火如荼,语言和图像这两个媒介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图文关系问题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泛,不同艺术形式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开始探索视觉艺术与文字艺术之关系及其变化,“艺格符换”成了跨媒介、跨艺术语境下的热词。
2 “文学地图”的概念
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提到:“地理这门科学是从地图学开始的,而描述方式则是它发展的第二阶段。”[6]文学地图是“文学”与“地图”相交融的产物,但并非“文学”与“地图”的简单相加,核心是以“文学”为主体,“地图”为辅。从广义上看,文学地图是文学世界中空间信息的图形表征或文字描绘;从狭义上讲,文学地图指代的则是文学作品中空间信息的图示化表征。文学地图旨在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7]。文学地图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体的叙述方式。地图不仅给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提供了空间上的标识,同时也给文学符号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文学利用空间叙事的优势也能够帮助地图超越本身的局限性,在不断地解读中产生更多的意义。
美国当代文学空间批评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罗伯特·泰利(Robert Tally)提到,“据我所知,文学地图学和文学地理学正是凭借文字性质而运作的,写作本身是一种空间化形式,取决于读者对众多惯例的接受程度。一旦真实的肖像图或地图呈现出来,它们就会成为补充,有时还会与叙事本身召唤出来的图像相竞争”。由此可见,这种文学地图是围绕文学作品的文本进行构建的,作家通过文字来一步步绘制文学地图,而一旦真实的地图出现时,这种文学地图又可以与现实地图相互比对,从而可以用地图理论反过来深度探究文学作品背后的影响和意义。文学地图可以成为作者想象世界中的向导,也可以是现实地理位置的描述,可以是文学传统,也可以是作品。地图既可以表征和某个作者、角色、作品相关联的现实空间,如福尔摩斯的伦敦、简·奥斯丁的英国乡村、杰克·伦敦的克朗代克、麦尔维尔的太平洋,也可以展示虚构的世界,如中土世界、纳尼亚世界等。
书写行为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制图形式或制图活动,像地图绘制者一样,叙述者必须勘测地域,决定某一特定景观的特征应该包括、强调或减少[8]。文学地图的学理逻辑是,作家无论有意无意,必然会将自己对地理和地域的理解投射在作品中,形成作品中的地理元素及文化内容,并由此组合成文学地图呈现在读者面前[9]。因此,作者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承担了再现国家地图的任务,也负责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地图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属性特征,并在人体这一连接现实世界和概念宇宙的存在链中找到了对等图示,叙事属性则让文学地图的形式和内容合二为一,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空间本质中。”[10]地图既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工具,又是一个强大的概念图形。文学作品中的图形地图兼具直观和隐喻的特征,文字地图虽抽象但其中因想象力而产生的空间性和地域性是单纯的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只有文字和图形相联系,虚实结合,才能发挥隐喻的作用。
3 文学地图中的艺格符换
“艺格符换”的表达媒介是语言。“艺格符换”作为一种具有描述性的语言,在其描述技巧里,与叙事相结合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艺格符换”虽然和叙事密不可分,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但是,“艺格符换”与叙事的区别在于,“艺格符换”在叙述的基础上,试图达到图像般的视觉空间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艺格符换”不能真正地将图像完整地呈现在眼前,语言唤起的是一种想象下的图像。想象力的参与是形成图像的途径。对于读者来说,读者通过描述的场景可以想象出描述对象,这与地图的初步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地图由语言组织而成。地理(geography)的词源表明,其既是一种视觉行为,也是一种语言表述。可以说,言语地图始于古希腊,即“ekphrasis”,非常适合文字的言语地图的刻画。最早的希腊地理学描述便出自荷马的《伊利亚特》。荷马对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所造的这面“巨大雄伟的盾”的描述,是文学上“艺格符换”的最早实例,但也可以被视为一幅宇宙论的“地图”,是对希腊宇宙道德的象征性的描述。它由五层同心圆组成,最中间是大地、海洋、天空、太阳、月亮和星星;往外是两座城池:一个和平,一个战争;还有农业生活和浩瀚的大洋河。也许荷马对阿喀琉斯之盾的描述看起来不大像一幅地图,但它符合希腊语下对地图的定义。盾牌是写有文字的实物,也是一幅环行地球图。可以说,这个盾牌是对已知世界的一种描述。荷马丰富华丽的辞藻让读者读后感到这面盾牌已经浮现在眼前,也看到了丰富的世界地图,这不仅实现了艺格符换从文字转换到图像的跨媒介作用,也展现了一幅文学地图。
此外,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也对地球进行了文字描述。通过苏格拉底十分形象的描述,读者不仅可以利用想象力构建出一个虚拟的世界,还可以获得一个理想世界的文字地图。苏格拉底解释说,人类所居住的只是大地表面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地球才是理想的世界,只有不朽的灵魂才能看见。最后,在对地球的一段描述中,他描述了自己的死亡,也描述了真正的地球:
这个真正的大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首先看到的像是一个十二块皮子包裹的球,色彩斑斓,像是色彩的拼贴画,而我们画家使用的颜色,其实是这些颜色的摹本。可是在那里,整个大地是由那种颜色组成的,比我们这里的颜色要鲜明得多、纯粹得多:这一部分是紫色的,美不胜收,另一部分是金色的,而白色的部分比白垩和雪花还要洁白;大地由其他各种这一类的颜色组成,那些颜色比我们见过的更加美丽缤纷[11]。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地图和文学的发展,文学地图的意象屡见不鲜。但丁对中世纪的地图十分熟悉,在《神曲》中的地图构建中亚平宁山脉将意大利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但丁顺应了基督教中有关伊甸园的传统,将东方放置在了顶端。从象征层面看,《神曲》也充满着对宇宙地图的隐喻。最下层为地狱,南大西洋的人间在中间,天堂在图示的顶端。这幅文学地图不仅实现了文学、地图、宗教的结合,也符合了艺格符换中人们在三者描述下综合的想象。
到了19世纪,简·奥斯丁也入驻了文学地图史。作为女性,其女性话语属于私语空间,19世纪的文本建构是男性的专属。在《爱玛》中有一段对道路的描述:“打算把通往兰厄姆的小路改一下道,让它再往右面靠靠,这样就免得穿过咱们家的农场了……如果你能准确回忆起小路现在的走向——不过要说清楚,那还得看看咱们家农田的地图。”[12]其中可以看出,地图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财产划分的工具,是对权力关系和空间的隐喻。从这段文字的描述中不仅可以想象出19世纪英国乡村道路的划分情景,而且奥斯丁的乡村私语空间体现出了当时社会转型的潮流,这种文学地图以特殊的空间叙述形式书写出了女性角色缺失的现实。而后的19世纪空间叙事发展迅速,麦尔维尔的《白鲸》用文学地图的方式为读者展示了捕鲸行为中的殖民主义的帝国想象。如麦尔维尔描述南太平洋食人族王子故乡的位置:“季奎格出生在科科沃科,那是在西南方的一个遥远的岛屿。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它,实实在在的地方无不如此。”[13]虽然科科沃科是如此之小,世界地图上没有标注,但读者也能在自己脑海里的世界地图上大致找到这个海岛。此外,这里的文学地图所隐喻的是科科沃科作为荒蛮之地,是进入不了西方文明视野的,是极富殖民色彩的描述。
通过以上的种种文学例子便可清楚地看到,艺格符换文字的视觉呈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刺激着读者的想象力呈现出一幅幅地图,而此类文学地图又有着众多的隐喻,不仅凸显了复杂的空间关系,也蕴含着艺术与空间的统一等重大问题。
4 结束语
“艺格符换”和“文学地图”两个作为从古希腊发展而来的概念,从本质上看,两者文学艺术的共有属性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为文学分析提供了逻辑支撑。艺格符换为描述视觉艺术的文字,文学地图为视觉艺术的呈现,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艺术素材,后者为前者的描述提供了真实的事物。文学的视觉描述不仅通过地图共有的文字符号输出了具有文化意义的名称,也提供了现实世界难以到达的想象空间。可以说,艺术化的修辞为地图的形成提供了建构的基础,因而地图也获得了超出自己本身的象征意义。无论如何,“艺格符换”和“文学地图”作为认识和建构世界的方式,文学在其中的影响非常广泛,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作者的遣词造句和空间意识建构。
参考文献
[1] 夏征农.大辞海(民族卷)[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2] 荷马. 伊利亚特[M]. 陈中梅,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4.
[3] SPITZER L. The "Ode on a Grecian Urn," or Content vs. Meta Grammar[J].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1955,7(3): 203-225.
[4] KRIEGER M. Ekphrasis and the Still Movement of Poetry; Or, Laocoon Revisited[M].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5] HEFFERNAN J. Ekphrasis and Representation[J].New Literary History,1991(2):297-316.
[6] 保罗·佩迪什. 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M]. 蔡宗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7] 梅新林. 论文学地图[J].中国社会科学, 2015(8): 159-208.
[8] TALLY R. Spatiality[M]. New York:Routledge,2012.
[9] 张袁月. 从文学地域、文学地理到文学地图:空间视角下的文学地理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149-158.
[10]郭方云. 文学地图[J].外国文学, 2015(1): 111-119.
[11]Plato. Phaedo[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1975.
[12]简·奥斯丁. 爱玛[M]. 李文俊,蔡慧,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3]赫尔曼·麦尔维尔. 白鲸[M]. 成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