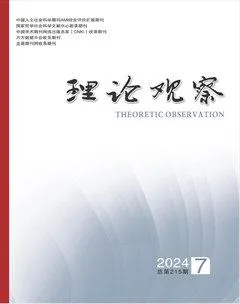青年人“词穷”背后:母语安全危机的技术异化与解困路向
摘 要:技术已经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主导语境,青年人因之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思绪活泼的群体特性,成为新技术应用的领跑者。然而,技术的“无思”误认侵蚀着了人们的深度思考习性,青年人“词穷”的现象级事件成为技术异化具身性的时代脚注,母语表达能力退化、母语思维能力搁浅、母语文化能力断裂是技术异化导致母语安全危机的突出表征。强化母语安全意识、辩证认知人与技术关系、重构母语文化教育是解困青年人“词穷”危机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青年人;“词穷”;母语安全;技术异化;危机解困
中图分类号:HO02;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7 — 0141 — 05
2024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这些年轻人为何“词穷”》的评论性文章,一时间青年人“词穷”现象引起网络热议。随即《北京日报》《浙江日报》《光明日报》《扬子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影响力报刊发表相关评论,分析青年人“词穷”的现象表征、问题根结、治理之方。青年人“词穷”的本质,通俗理解就是“一些年轻人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反映出互联网时代‘文字失语’的现实问题。”[1]不独青年人,伴随互联网之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深度介入,提笔忘字、表达匮乏、语言干瘪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集体症候。笔者在此着意强调青年人“词穷”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有意苛责,而在于青年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职责与神圣使命。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2]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思想、观念、意识这些形上的精神范畴需要通过语言进行具体外化、深入、融合,最终形成认识主体的内在品性。语言在此不仅仅是一个载存这些精神范畴的工具,“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4]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在人们的日用而不知中型塑着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心性。循此逻辑可知青年人“词穷”问题不可轻视,它是典型的母语①安全问题,其背后关涉着青年人之于国家、民族情感依存、身份认同、文化自信的重大问题。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关照当下青年人语言生活之中的“词穷”问题,深入分析“词穷”成因及现象,找出应对“词穷”问题之策略。
一、青年人“词穷”的技术哲学探察
尼尔·波斯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开篇引述分析了柏拉图《斐德罗篇》中关于埃及法老塔姆斯与文字发明者特乌斯的故事。尼尔·波斯曼借塔姆斯之口想要告诫特乌斯们的是:“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5]10我们不要仅从表面来理解这句话,以为作者以及塔姆斯是在斥责特乌斯的文字发明之功,进而认为他们是在斥责文字之罪过。作者尼尔·波斯曼非常明智地在这句话之后做了这样的解释:塔姆斯的意思是“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5]11文字是技术的附属品,这里塔姆斯只是在用文字作为技术的隐喻,他意在强调人们对于技术发明及其应用需要保持必要的意识形态警惕,按照今天的学术话语习惯表述就是人们在享受技术工具理性带来的便利之时,要始终牢记技术价值理性的先前存在,技术价值理性之于工具理性的规训意义。青年人“词穷”背后折射出来的恰恰就是以上尼尔·波斯曼与法老塔姆斯对于技术文明过度嵌入人类生活世界之担忧的时代佐证。提笔忘字、表达匮乏、语言干瘪,青年人乃至大多数现代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词穷”问题。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形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青年人、现代人已经被技术文明尤其互联网技术文明所左右、牵制甚至俘虏。尽管技术奇点论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预想,然而考察人类技术文明的进步史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技术文明不断给人类生存制造危机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5]5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人们遭受着技术文明催动的、普遍性的现代性焦虑。“无论在哪个时代,技术永远都是教育和自律的手段。”[6]281然而,不幸的是在技术占据主场语境的今天,技术俨然已经成为目的。包括教育在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日常生活的各领域均已成为它的附庸。技术至少在过去是人的机能的延伸,而现在则形成“倒置”,甚至人已经成为“多余”或者“剩余”。人们对于技术、教育、人的本质认识成为一道纯粹的数学题,教育与人都是技术的产品,进而“我们吸收的是产品,而不是生产产品的精神”[6]282便成为普世法则、奉为圭臬。青年人“词穷”问题便是在这种技术垄断的语境中,人们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甚至有意识地向技术“投降”的结果。“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5]78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技术哲学的深度追问,洞悉青年人乃至现代人“词穷”成因的本质,论析“词穷”现象的隐蔽日常,提出有效的因应之策,让技术文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好帮手,而不是坏主人。
二、青年人“词穷”现象的递进表征
人们对于技术文明的盲目推崇以及深度依赖,导致技术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技术价值理性踟蹰徐行甚至惨淡退场。笔者借用尼尔·波斯曼“文化向技术投降”的隐喻话语,通过芒福德技术哲学的人本主义进路深度关切并指明青年人“词穷”成因根由之所在。依循芒福德的技术人本主义,笔者认为需要深入青年人日常言语生活深处,揭示青年人“词穷”的隐蔽现象,为应对青年人“词穷”问题做到有的放矢。根据笔者近来的集中观察与思考,认为当前青年人“词穷”现象主要从母语表达能力退化、母语思维能力搁浅、母语文化能力断裂三个主要方面进行递进表征。
(一)母语表达能力退化
由于语言的日用而不知,人们很难察觉语言能力、语言思维、语言文化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只有当人们感觉到提笔忘字、表达匮乏、语言干瘪之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能力、语言素养、语言文化出了问题。笔者从《这些年轻人为何“词穷”》这篇报道中摘录了被访青年的三段话,呈现如下:
1.“我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原本会写的字突然想不起怎么写了,只能求助网络。”
2.“脑子里有许多零碎的词汇,但连不成完整的句子,‘卡壳’了好几次。”
3.“平时和朋友聊天,大家都喜欢用表情包和网络流行语,如果谁发了一大段文字,反而会显得很奇怪。”
不独青年人,我们自身进行对号入座,大概也会有较为深刻的体会。这种“文字失语症”是互联网不断介入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之中潜移默化的结果。“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7]44作为青年人群体的知识代表大学生的整体中文语言水平也不尽如人意,光明日报最近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生汉字书写仅得2分,提醒我们什么?》的文章引发关注,刘思诚等(2019)在《大学生“失语”现象与当代“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一文中指出:“当代大学生‘失语’现象的担忧”[8]问题,同时有论者总结当今青年人及现代人文字失语症主要表现为“被动沉默、词不达意、有口难言,同质表达、高度依赖网络热梗,劣质表达,用笑声代替思考”[7]44-45三个主要方面。可见,包括青年人在内的文字失语问题并非个案,也不是笔者一厢情愿的主观夸张,无论从日常言语生活,还是学术界的探讨,均表明现代人尤其青年人“词穷”在母语表达、思维、文化的不同层面存在着严重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要将其上升到母语安全、文化安全的高度进行深入认识。
(二)母语思维能力搁浅
语言与思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世人熟知。尽管语言与思维二者到底谁者在先,引发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之争,但笔者在此并不想介入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循环论证陷阱。跳出这种无谓的逻辑游戏之外,我们需要了解与把握的事实是语言与思维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更为重要。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实用性功能是大家一致认同的,然而,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语言与思想、文化、情感、素质、思维等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不可否认的是思维等相关概念是一种抽象存在者,人们认可思维的存在却无法触及,这与人类的先天直观癖好相悖。有幸的是语言担负起了承载、外化思维等相关抽象概念的使命。正因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世界出现了语言转向,语言开始冲破工具论的束缚,越发具有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重要维度,甚至语言就是人本身。这无疑是一场思想上的深刻革命,也为语言自身动能的释放提供了先决的理论条件。社会母语是某一国家、民族的通用语言,国家的大政方针、治国理念,民族的情感文化、风俗习惯均要通过社会母语宣化四方。其在型塑公民的思维模式、文化习性、情感认知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然而,当下青年人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中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母语思维能力弱化甚至搁浅停滞值得警惕。很多年轻人在线做社交“E人”,回归现实生活中就成了社恐“I人”,这便是长期使用网络缩略语、流行语导致的语言危机。表达愉快情绪只会“哈哈哈……”、表示同意只会“嗯嗯嗯……”、表示惊叹只会“哇哇哇……”,凡此种种便是思维向技术主动投降的先兆。要么就是拼图片、拼表情包的狂轰滥炸,要么就是恶搞拆字游戏进行的另类创新。语言思维能力呈现粗鄙化、碎片化、直观化的浅薄,深度的语言思维能力被放逐。
(三)母语文化能力断裂
如所周知,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观领域安全的重要方面,而意识形态安全又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关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树立、有效实践。语言又与文化、意识形态存在着更为直接紧密的关系,进而可知作为一个国家、民族、个体的社会母语在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之中的重要性。正如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所指出:“意识形态就是文化的元语言”[9]83,并进一步阐述指出:“凡是有文化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对文化意义活动的元语言解释和评价,也就是有意识形态。”[9]86母语载存着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的历史文化,是树立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自强、承担文化使命的重要凭借。当代青年人乃至现代人整体上存在着母语与历史文化断裂的严重问题。青年人母语文化能力断裂与其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退化是互为表里的,母语文化能力断裂来自前两者的日积月累,同时母语文化的底蕴深浅又会对前两者产生正负两级的不同影响。有学者以语言亚文化为观察视域,以“Z世代”为对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总结青年人的语言表述分类为“反鸡汤式、废话式、矛盾式、缩略式、无厘头式”[10]85-86五种,限于篇幅仅引用一列以说明。其中的“无厘头式”最能说明青年人社会母语表达、思维、文化层面的严重矮化问题,作者列举了“XX子(如绝绝子)、凡尔赛;YYDS(永远的神)、 emo(难过)、dddd(懂的都懂)、拴Q(thank you变音)”[10]86这些例子。它们基本上可以统一在字母词的范域之内,对于字母词的争论由来已久,始终莫衷一是。在此,笔者并非全盘否定字母词的交际功能,但必须看到不加限制的任意捏造会从语言思维、文化的深层侵蚀使用者社会母语的思维运用力、文化感知力。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基本符号,对文化的呈现与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探寻个体或群体心理样态的有效路径。”[10]84长时期浸淫于这种无厘头的言语环境之中,就会形成心理上的思维定势、文化定势,对于自身社会母语、文化的感知与体认就会随之弱化甚至彻底屏蔽。
三、青年人“词穷”问题的应对策略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人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总体来说都是他自身机能的延伸。”[6]281芒福德技术人本主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然而,当下技术的强势俨然使得现实情势开始走向芒福德技术人本主义的反面,加之资本、权力的参与,人们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岌岌可危。在技术-资本-权力三者合谋宰制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扭曲,日常言语生活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也随之异化。前文笔者以技术哲学的视角分析了青年人“词穷”成因及其相关现象,论述了“词穷”背后的母语安全危机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从强化母语安全意识、辩证认知人与技术关系、重构母语文化教育三个主要维度应对青年人乃至现代人“词穷”的根本问题。
(一)强化母语安全意识
“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11]甚至,语言就是政治、文化本身,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领域安全的关键部分,进而语言安全问题就需要认真对待、提升站位。而就某一国家、某一民族而言,“语言安全主要是针对母语安全而言的”,[12]所以,母语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安全问题的复杂化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随之多元复合。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前,可以说语言安全问题、母语安全问题是潜在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便使得人们之于语言及其相关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更加准确地讲是没必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平凡无奇的语言身上。然而,人们的思想意识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进入工业社会已降,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物理隔阂被技术打破,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一体化进程加快,随之而来的不同的语言文化开始频繁交流,语言安全问题正是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必然而生的。所以,我们需要转变固有的思想观念,向广大青年人、现代人讲清楚、说明白当今世界安全问题的非传统转向,讲清楚、说明白语言安全、母语安全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要从国家高层进行宏观的母语安全研究规划,突出母语学习、认知的重要性,植入母语安全意识。可以看到,2022年教育部在《国家语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提高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学生应具有‘一种能力两种意识’(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意识),高校要将其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及标准并纳入毕业要求。”①国家在行动,青年人更应积极响应,深入把握强化母语安全意识的重大意义。
(二)人与技术辩证认知
包括母语安全在内,现代世界一系列问题均根源于人们之于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以及资本、权力的失控导致的包括青年人在内的现代人精神上的普遍焦虑。马克思所担忧的“物的世界在增值、人的世界在贬值”的未来已来。从语言安全层面来看、母语安全层面来看,技术-资本-权力三者合谋之下的语言、母语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已经没有心性去品读语言尤其是自身母语蕴含的丰富诗韵,语言、母语被技术化、资本化、权力化,形成了语言符号的漂浮、悬置,语言、母语与人之间变得越发陌生。“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一直与人类的普遍解放这个政治哲学的主题相关。”[13]32人类希望通过技术的发展将自身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解放出来,恰恰这种对于人类解放的单一理解导致技术工具理性的野蛮生长。“技术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工具。古代技术并非一种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知识形式;现代技术更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13]33,可以说技术自诞生之时就蕴含着与资本、权力的苟合禀赋,在资本、权力的推动下技术工具理性几近将价值理性全线击溃。从语言、母语层面看,人们的日常言语中充满历史虚无主义、权力金钱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的歪风邪气,青年人用“躺平”“摸鱼”“佛系”等语词宣泄着内心的情绪,同时也将自己的理性思考驱除。正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将人之所是的价值理性、精神属性阉割,才导致技术工具理性不断做大。笔者如此批判技术工具理性不是对技术本身的仇视,而是要反复说明人们对于技术要进行辩证认识。我们不否认技术工具理性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技术工具理性的发展必须以价值理性对其进行规训。尤其,在当前以ChatGPT、Sora等强人工智能横空出世的现实语境中,更加需要清醒、冷静地看待技术工具理性的有限性,防止技术工具理性之于价值理性的深度反噬。
(三)重构母语文化教育
四大古代文明之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生生不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断绝,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尽管,今天的汉语汉字无论从音、形、义等多个维度均与古代汉语有着不小的差别,但是汉语之所以本质没有变更,即便几千年之前的原典文本,今天的读者只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知识便可以穿越历史的长河去与我们的先人进行对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等经史子集、楚辞汉赋的文脉气运因之汉语汉字的延承而在今天依旧焕发着勃勃生机。我们有着五千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有着从远古走到现代的语言文字,这是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幸运。青年人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加有责任与义务将这份珍贵的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下去并使之光大。从母语文化教育角度,首先作为青年人自身应该积极培养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广泛涉猎中华优秀传统典籍、拓展琴棋书画的业余爱好,努力做一个有时代气息、 文化底蕴的新青年。其次,国家、社会、学校要积极制定宣传、学习汉语汉字的方略、措施,搭建多方平台,激发、鼓励在校大学生、社会青年人学好、用好汉语汉字的热情与兴趣。最后,要睁开眼睛看世界,通过孔子学院等平台渠道展现汉语汉字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心,借鉴学习西方先进国家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的优秀理念为我所用。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进而重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化教育体系、语言文化气象。同时,辩证看待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便利,不断拓展、打造汉语汉字文化的网络秀场,继续深入组织开展诸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语言文化类节目,打造全民学习汉语汉字的浓厚氛围,实现包括青年人在内的全民学习汉语汉字的常态化、日常化。
四、结语
一个国家、民族的母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身份象征、精神标识、文化图腾。母语之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意义重大,伴随当今世界传统安全的非传统转向显明,文化安全、语言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越发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青年人“词穷”背后是语言安全危机、母语安全危机,兹事体大不可不察。本文以技术哲学的人本主义进路为指向,分析了当下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是导致青年人“词穷”的根本原因,并从技术-资本-权力三者合谋的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青年人“词穷”现象的危害性,进而提出应对、解困青年人“词穷”问题的可行路向。最终,希望包括青年人在内的现代人能够深刻意识到母语表达能力退化、母语思维能力弱化不是小事,母语背后联系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母语是这条文脉得以健康延续的重要保障。青年人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思绪活泼,更应将时间、精力放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发扬中华优秀传统语言文化的伟大事业上。
〔参 考 文 献〕
[1]王志伟.这些年轻人为何“词穷”[N].中国青年报,2024-02-27.
[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71-77.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6.
[5]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0,11,5,78.
[6]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81,282,281.
[7]沈爱国,徐汇紫琳.文字失语症:互联网时代语言表达困境分析与对策[J].传媒评论,2022(12):44-46.
[8]刘思诚,王世铎.大学生“失语”现象与当代“大学语文”教学改革[J].教育科学,2019(02):46-50.
[9]赵毅衡.意识形态:文化的元语言[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79-88.
[10]李英华.“Z 世代”青年心理透视: 语言亚文化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03):83-91.
[11]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2):13-20.
[12]方小兵.母语意识视域下的母语安全研究[J].江汉学术,2016(01):121-128.
[13]余明锋.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23(32):33.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