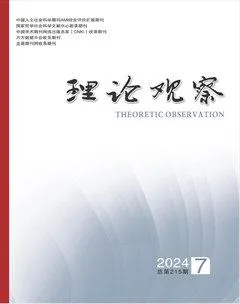乾隆年间山西灵石乡村禁赌探赜
摘 要:乾隆年间山西赌博问题严重,并引发了众多命案,严重破坏了乡村社会秩序。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乡绅群体主持了乡村禁赌活动,部分乡绅试图通过对本村落的范围内的参与赌博及开场窝赌人员罚金、罚戏、送官等措施重构被赌博破坏的乡村社会秩序,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清朝禁赌实质上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推行的政治举措,乡绅主持下的乡村禁赌则是乡村熟人社会中长辈对晚辈的教化,是乡村对于官府禁赌政策的反馈,一旦官府无暇顾及,被压制的乡村赌博则会死灰复燃。
关键词:乾隆年间;碑刻文本;山西灵石;乡村禁赌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7 — 0114 — 06
禁赌是清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深受国家与地方的重视,清朝统治者为了禁赌制定了体系完备的禁赌法律,乡村社会也曾组织开展各项禁赌活动。当前学界对于清朝时期的禁赌研究已十分深入,成果较为丰富。王美英、魏忠、潘洪钢等学者从清朝整体视角着手,认为由于乾隆年间禁赌政策的宽松及官员的腐败,使得乾隆之后社会赌博问题日益严重,并一直持续到清末。①在区域禁赌研究中,学界对于赌博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广东②、徽州③等南方工商业发达的市镇,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朝廷社会控制力的减弱使得南方地区的赌博问题愈加严重。山西的禁赌研究主要集中在泽潞地区,朱文广、魏晓锴等学者④认为清朝泽潞地区的禁赌主要是对后世赌博的防范,而清朝泽潞地区禁赌活动由于禁赌令并未得到长期落实而效果不佳。当前学界对于晋中地区乡村赌博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尝试以晋中地区灵石县乾隆年间的禁赌碑为切入点,尝试窥探乾隆年间官府及地方乡绅在面对乡村赌博日益严重情况下的反应。
一、乾隆年间灵石乡村赌博概况
(一)乾隆年间灵石乡村的赌博现象及危害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繁盛的时代,参与赌博的人群更是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1]清朝初年,受到明末“马吊”广泛流行的影响,社会赌博之风盛行,太宗曾“谕管刑部事贝勒济尔哈朗曰:近闻游惰之民多以赌博为事,夫赌博者耗财之源,盗贼之薮也,嗣后凡以钱及货物赌博者,概行禁止,违者照例治罪。”[2]顺治年间,“南之马吊,北之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穷日累夜,若痴若狂。”[3]康熙年间,江浙一带“斗马吊牌”盛行,“虽士大夫不能免”,且“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诸戏”。[4]雍正时期,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对安徽巡抚提出“又如赌博一事,万不可宽者。”[5]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对山西巡抚伊都立提出的“严保甲,查私铸,断烧锅,禁赌博”[6]等都反映出社会的赌博问题已然十分严重。面对日益严重的赌博问题,雍正皇帝曾以强硬态度对赌博进行全面打击,赌博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遏制。
乾隆皇帝即位后,为了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措施,甚至乾隆皇帝本人“尝于几暇,取 《列仙图》人物绘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7]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乾隆皇帝的带头参与使得赌博活动又逐渐兴盛,“赌博之风,莫甚于今日”[8]。“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9]。乾隆年间的赌博不仅是对社会风气的破坏,更是催生了一系列刑事案件,严重危害了朝廷对基层的治理。仅就山西地区而言,因赌博而致杀人的案件便屡见不鲜,“案犯年未十五,因赌负债,窝主剥衣辱之,遂怀恨购毒潜入其家投毒”。[10]此类恶性案件屡屡出现,乾隆皇帝为此提出“朕览山西情实人犯册内,因赌博酿成人命之案甚多,皆因疎纵赌具赌博所致”[11]。数量众多的刑事案件致使“山西按察使唐绥祖奏稱称、晋省民风。好尚赌博。应严定地方官失察之例。除于咨题案內、牵连赌博、地方官应查参者。仍逐案咨题、随招附参外。其仅止赌博。或斗殴自尽命案、牵连赌博、例应外结者。”[12]
赌博活动不仅在城市之中十分繁盛,偏远乡村亦因“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13]而成为赌博活动的重要地区。浙江建德县就有妇人因“其丈夫日逐赌场,并将家内什物窃去,以供赌博”而“哭甚哀”[14]的情况。乡村赌博的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江浙地区,在山西地区也屡屡出现,“僻在万山中,财资不通,人勤苦多”[15]26的灵石乡村赌博问题亦十分严重。乾隆年间的灵石乡村“游手赌棍来往不绝,诱引子弟习染日迷”[16]460,甚至有“开场窝赌,引诱子弟”[16]459、“专以赌博为生”者[16]484。严重的赌博使得社会治安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舆图览之,自京都、省郡、州城、府市,以至一邑一乡,其绅紟棍徒相聚为赌者,或败产弃业受累于终身,或漂流西东抛妻撇子,或因争起衅致伤其性命”[16]507。严重威胁到清朝的政治统治,因此,在官方的主导之下,广大乡绅主持的禁赌活动在灵石县开展。
(二)灵石县乡村赌博的时空分布
由于乡村赌博材料的欠缺,对于乡村赌博问题的记载多集中于乡村碑刻资料。碑刻作为官方意志在乡村传播的重要载体,现存的碑刻资料虽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古代乡村社会禁赌的效果,但通过对碑刻的分析亦能窥探出乡村社会对于朝廷诏令的反馈及当时赌博的分布区域。
通过现存的禁赌碑的空间分布可知,灵石县现存的禁赌碑主要集中在灵石县金庄里、张志里(如图1)等远离县城、交通不便的西部山区。从禁赌碑的镌刻时间来看,灵石县现存的九通禁赌碑中有八通属于乾隆年间,主要集中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如表1),但道光年间亦有一通禁赌碑存在。此外,漫河村禁赌碑还于光绪二十六年进行了重新镌刻。现有禁赌碑刻的时空分布表明乾隆中后期灵石县官府加强对于偏远乡村禁赌的重视力度,朝廷的禁赌政策已然推行到灵石县的广大偏远山区乡村,并得到了乡村的积极响应。而道光年间出现的禁赌碑及光绪十六年漫河村对禁赌碑的重镌则表明乾隆年间的赌博活动并未被彻底禁绝,官府对于乡村禁赌的要求一直持续到清末。
通过对乾隆中后期灵石县禁赌碑设立位置的整理,可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集中在西部山区这一特点。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灵石西部山区乡村在乾隆年间生活富足,游民数量激增,享乐主义盛行。明中后期以来,山西的商品经济发展十分迅速,逐渐出现了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商帮——“晋商”。清初出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给予晋商贩卖盐、茶等商品的资格,商业日渐发达,促进了以“八大皇商”为代表的晋商团体的崛起。参与到商业活动中的百姓在拥有财富之后开始贪图享乐,修建深宅大院后逐渐参与到赌博之中。同时,康熙时期玉米等高产经济作物的传入,以及雍正时期摊丁入亩的实行,推动乡村人口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灵石县“顺治二年,户三千一百三十二,口两万二百一十四,嘉庆二十一年,清查实在户一万九千一百九十二,口十三万三百二十一”[15]97,嘉庆末年较于顺治年间翻了六倍,在古代较为落后生产力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土地生产力无法于短时间内得到提升的情况下,这部分剩余劳动力逐渐演变为游民,成为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当“因旱未雨,农民闲暇”时,极易出现这些游民中的“赌棍乘隙入村赌”[16]487的情况。而官府有限的衙役逐渐在处理乡村事务中捉襟见肘,灵石西部山区乡村赌博活动自然难以得到官府的有效遏制,这也促使其在乾隆年间禁赌碑的设立。
其次是灵石西部山区乡村交通不便,官府对灵石西部山区乡村的管控力量不足。灵石县“襟汾面岭,南北衢途涖斯土者,外修牧围,内课农桑”[16],县域内连接太原与霍州仅有的两条路线,即仁义铺、常家山铺、韩信岭、高壁铺、冷泉铺等急递铺所构成的急递铺路线和冷泉关、雀鼠古道、瑞石驿、仁义驿等构成的驿路[17]都分布于汾河两岸,并未能辐射到汾西的广大山区。多山的地形和南北横穿的汾河严重阻碍了灵石县之间的交流,也阻挡了位于汾河以东的官府对汾河以西广大地区的有效管控,再加之部分在市镇受到打击的赌博分子因躲避官府追查而转入乡村,使得灵石西部山区的乡村赌博大量存在。同时,由于古代制度推行的滞后性,保甲制在乾隆年间并未在灵石县西部山区得到彻底贯彻执行,同时乡村旧有的里甲制已无法对于百姓实行有效的管控[18],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定时期的官方权力真空,朝廷的禁赌诏令自然也无法在乡村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在此基础上的乡村秩序官府已无力管辖,赌博活动也在此时愈演愈烈。
最后是灵石西部山区乡村教育较为落后,未能实现儒家思想对乡村的有效教化。灵石西部山区乡村由于“地僻民贫”,官方的儒家教化并未能实现。而受到参与商业活动的乡村百姓的影响,山西的重商风气则得到大量的有效传播。重商主义思想冲击了传统封建秩序,使得冒险主义盛行。山西高度发达的商业使得商人在山西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晋商所引领的民风习俗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们不再追求入仕做官,排在四民之末的商贾一跃成为四民之首”。[19]山西巡抚刘于义提出“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20]25再加之康乾时期大兴文字狱,社会文化压抑,在乡村社会追求儒家文化的热情急转直下。山西地区私塾的教育内容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也逐渐向“实用性”靠近,开始教授商业活动所需的各种技巧,以及蒙语、满语、俄语等外语。[19]缺少儒家伦理熏陶的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出现些许松动,本就薄弱的宗族权威遭到更大的冲击,官府不易直接控制的乡村社会逐渐出现了开始尝试突破传统道德,追求个性的解放,寻求赌博等刺激行为。
二、乾隆年间山西灵石的乡村禁赌的治理
(一)乡绅对于乡村禁赌的主持
朝廷作为社会禁赌活动的主导者,是乡村禁赌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官府力量的有限,其在乡村的禁赌活动则主要是在乡绅的主持下展开的,乡绅为乡村禁赌活动的纠首和举事人。乡绅是指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权力掌握者,根据不同乡村乡绅的不同身份,可以将乡绅分为在地方事务中代表官方意志的保长、甲长和乡约、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决定家族大小事务的宗族耆老,以及在地方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地方乡绅。
保长、甲长和乡约是乡绅角色的主要组成部分。清朝初年,山西所承袭明朝的里甲制度在处理地方事务当中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雍正年间的里甲首事赋税造假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的征收。为了应对赋税问题,清政府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基层制度,在地方推行“保甲顺庄”。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细化了保甲法的各项规定,并要求“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踩鞠,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行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12]。山西巡抚塔永宁积极响应,在山西建立起完善系统的保甲体系。此外,乡约也是乡村事务重要的参与者。乡约是清初为宣讲圣谕而设,到乾隆年间,“晋省村庄,无分大小,俱设有乡约。其名目虽与村长相殊,其责任实与村长无异也。”[21]乡约在乡村公共事务中已然成为地方权力的重要掌握者和执行者,与保长甲长共同成为构成乡绅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族是地方乡绅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我国长期存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2]的情况,宗族作为地方权力的重要掌握者和地方秩序的重要维护者,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宗族内部的运行规则,包括对于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和惩处措施。但是由于华北地区的宗族并无族产的存在,北方宗族凝聚力远不如基于族产基础上的南方宗族势力强大,对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也较之南方明显薄弱,基本仅起到号召主持作用。因此北方的宗族耆老的权力亦与乡约的权力相似,大多数为利用自身及官府的影响力而教化震慑百姓,在禁赌中则体现为“许族长协同牌甲禀官究责”[16],而非利用族规进行实质性的刑罚惩处,地方宗族亦为乡绅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深井村、蕃义村的杨氏家族、楼珍村的郑氏家族都是以宗族为核心,宗族成员充当禁赌活动的经理、纠首,其已然成为地方乡绅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宗族基础之上,一个村落内数个宗族的情况使得乡绅的来源不仅限于本宗族,而是数个宗族乡绅的协商联合,逐渐形成了凌驾于宗族之上而囊括整个村落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亦为囊括众多宗族的乡绅群体组织。例如泉则坪村主持设立禁赌碑的是本村刘、成、马三姓16位乡绅[16]。在数个宗族并立的乡村社会,作为主持禁赌活动的举事人为了增强乡村的权力的权威性,通常还会在各个宗族乡绅联合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地方其他知识分子及威望人士的参与,以加大禁赌的效果。漫河村的禁赌活动是在温、赵、宋、王、倪、韩、郭、杨、乔九姓12位纠首的主持之下展开的,其中既有监生赵邦杰,又有温氏宗族的参与,还有其他具有地方影响力的人物参与,其体现出的是一种与乡绅协商致力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公共权力。[16]
乡绅作为乡村禁赌碑设立的主要主持者,其不仅积极担任禁赌活动中的倡导者与管理者,还积极地为禁赌碑的设立出资。
乡绅作为禁赌活动支持者,积极地参与到乡村禁赌事业中,担任禁赌活动的经理、纠首。同时,乡绅作为地方的权威和宗族事务的主持者,在乡村事务中通常掌握着话事权,还积极对于百姓的行为进行教化。
同时乡绅也是禁赌活动中的重要出资人。禁赌活动作为一种持续性活动,往往“劳力废财”,[16]1088为了保障禁赌的顺利推行,乡绅还时常出资相助。
(二)乡绅采取的乡村禁赌措施
乡绅主持之下的禁赌活动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重塑社会风气。灵石境内现存的众多禁赌碑中都明确提出了“严禁赌博,以正人心,以清风气”,[16]566进而使得村民“恪遵严禁,各守本分”。[16]485最终通过禁赌,“将见害事一除,利端潜兴,不惟□日之村落得以安静,即后世之子孙亦□永□无事之福云尔”。[16]459基于此,民间禁赌并非对朝廷禁赌法令的严格执行,而是基于乡村社会内部的一种道德约束,禁赌的措施往往折射出一种警醒意味,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百姓的有效教化,故而常常通过道德惩罚作为主要的惩治手段,很少涉及肉刑。
民间禁赌主要采取道德约束和金钱惩治等措施。基于民间教化的目的,民间禁赌惩处措施主要为献戏与金钱的罚没,其中尤其以金钱的罚没为主。金钱的罚没是惩治赌博的主要措施,对于金钱的罚没数量大多数为“三两”[16]484或“五两”。[16]485同时,还提出“立功有赏、包庇受罚”,打击对于赌博的包庇,鼓励百姓的检举揭发。为了打击包庇行为,乡绅提出“如知情洵者罚银三两”[16]487。为了加强禁赌效果,乡绅充分发动广大村民,提出“倘有一人能捉并获赌具者,公内酬银二两。如知情洵者罚银三两。”。[16]487为避免乡村禁赌中的赌徒归属而影响禁赌效果,乡绅提出“凡属村境,一概查拿。”[16]487且“欲赌不遂,村中混骂者即以赌论”。[16]487乡绅对赌徒的罚款大致为五两左右,对知情不报者的罚金大致为三两左右。对于罚款金额的确定,应当亦有其当中的考量。嘉庆版《灵石县志》记载当时“捕役八名工食银四十八两,门子一名工食银六两,皂吏四名工二十四两,马夫一名工食银六两”[15]。当时的大多数县级胥吏的一年俸禄为六两,此处对于罚金确定为五两,根据嘉庆年间粮食“每石折银一两四分九厘七毫九丝四微五抄六麈六渺一埃一漠”[15]来计算,五两银子的购买力应当为五石左右,应当为当时普通之家一年的正常粮食需求量。这个数量即能对赌徒形成一定的打击,而又不至于过于沉重使其难以生存。
罚戏也是惩治赌博的重要措施,罚戏的数量也大多为三天。在娱乐活动极其匮乏的古代乡村社会,戏曲无疑是百姓最为主要的娱乐活动,亦是乡村社会中影响力最大的社会行为。通过对于赌博者的罚戏亦在最大程度上壮大乡村禁赌声势,能通过社会舆论来对赌徒进行道德谴责、对百姓进行警醒,加强对于禁赌的宣传效果。故而“凡有捉获者除票纠之外,献戏三期”。[16]487在乡村禁赌中,罚金和罚戏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默契而广泛实行,参与赌博及“村中开场窝赌”[16]484者“嗣后倘若有犯,罚戏三天、银五两,一定不恕。是为约。”[16]485对赌博者罚戏还有以信仰来约束赌博的深刻内涵。北宋以后,随着山西戏剧的发展和民间信仰的发达,在无戏台“不惟戏无以演,神无以奉,抑且为一村之羞也”①的观念指导下,逐渐形成了神殿与戏台相结合共同构成神庙的建筑形式,再加之山西高度发达的信仰使得每个村落都拥有多种形式的信仰场所,特别是关帝信仰更是达到了村村有关庙的程度,而作为村落信仰中心的庙宇也就成为处理村落公共事务的中心。“神前献戏三天”[16]484亦是在以村落信仰来对赌博者及窝赌者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和精神上的压力,以百姓对神灵的敬畏警醒百姓,将禁赌活动加之以神的意志,塑造出对于赌博会使人神共愤的精神压力。此外,戏剧中所宣扬的惩恶扬善的观念亦对百姓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
民间禁赌的最后手段是“送官究治”。清朝严刑峻法以禁赌博,提出“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财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23]。雍正三年又加重处罚,“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开场窝赌及抽头之人,各枷号三个月,竝杖一百,在场财物入官”,并规定“地方保甲,知有造卖赌具之人,不行首报者,杖一百”[23]。严厉的律法使得其对于百姓有极大的震慑力,乡村禁赌由于是在官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故而乡村禁赌的措施亦不能忽略官府的作用。当乡村的赌博活动逐渐超出乡绅所能控制的范围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官府势力介入,故而民间常常将“送官究治”作为乡村禁赌的最后手段。以“许纠首赴县具禀,以究其罪。”[16]459来震慑百姓。正谓:“民虽不知王章可遵,岂不知肌肤可爱?即不知肌肤可爱,讵不知桎梏难逃。啧啧详文,煌煌明训,敢云弗从?”[16]507
三、乾隆年间山西灵石乡村禁赌效果
乾隆年间的乡村禁赌是一场试图整顿社会风气的政治活动,但对于禁赌的效果而言,是十分有限的。在乡村禁赌活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中的乾隆四十一年,出现了“灵石县赵张氏等因女张赵氏赌博、偷窃、不服管教,将其勒死一案”[24]。嘉庆、道光年间,灵石县因赌博而酿成人命的案件亦层出不穷,这表明乡村赌博的社会风气并未得到有效逆转,禁赌活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道光年间出现的禁赌碑及光绪年间对于禁赌碑的重镌表明,直至道光、光绪年间灵石西部山区的赌博活动仍很活跃,甚至比乾隆年间更为严重。
在探讨乡村的禁赌时,要充分考虑到朝廷的禁赌律令和乡村约定俗成的禁赌措施,黄宗智提出“只有两者兼顾,才能把握历史真实”[25]。实际上,统治者对于乡村禁赌的目的也仅是通过禁赌来遏制乡村过剩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即使是严厉禁赌的雍正皇帝,亦在禁赌中要求官员“加重不可陡然而举,凡事皆当逐渐相机而增减。”[20]7因此,乡村禁赌虽然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的执行,但其禁赌的措施并不是朝廷法令在乡村的严格执行,而是乡绅在乡村社会范围内对于百姓的教化和号召,其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官府刑罚的恐吓和乡绅的教化而让乡村赌博有所收敛,不至于恶化到动摇社会秩序的程度。
对于参与赌博者而言,乡村禁赌的措施并不是对以往赌博的追责,而是对这种不良行为的劝告,这明显与朝廷禁赌律令违法必究精神有所冲突,但是官府对这种冲突持默许态度。对于官府而言,在乎的并不是禁赌律令的严格执行程度,而是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甚至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这一目的可以忽视禁赌律令这一手段的执行情况。即使在禁赌中出现“巡查捕役、乡约地方逐处抽取规例,规例到手,不但不查拿解究,抑且拘隐出结。”[26]、“关厢内生员之家,竟有公然开场赌博者,聚集无赖,深藏密室之中,地方保长既不敢问,昼夜呼卢,罔顾法纪。”[27],在社会风气并未遭受剧烈恶化的情况下官府亦未做出强烈的反应。
但是,也正是这种宽容,致使在朝廷对乡村的管控力逐渐下降或者朝廷无力顾及乡村时,乡村出现了赌博与禁赌的相互博弈,而在中央朝廷逐渐失去对地方的强大控制时,就逐渐演变成社会层面更深层次的秩序混乱,例如清末的广东地区,正是由于前人禁赌的不彻底,使得在官府忙于解决外国列强侵略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而无暇顾及禁赌活动时,出现了赌博之风有所抬头,直至清政府无力管控广东地方时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为“赌国”。
〔参 考 文 献〕
[1]潘洪钢.清代的赌博与禁赌[J].江汉论坛,2008(09):61-66.
[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5.
[3]汪师韩.叶戏原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4.
[4]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19-21.
[5]余金.熙朝新语(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
[6]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五)[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231.
[7]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895.
[8]龚炜.巢林笔谈(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7- 108.
[9]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78.
[10]顾麟趾.山右谳狱记(光绪二十四年冬饮庐刊本)[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7-8.
[11]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五[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15.
[1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15
[13]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三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60:28.
[15]王志瀜.灵石县志(嘉庆二十二年刻本)[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26.
[16]景茂礼,刘秋根.灵石碑刻全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
[17]张宪功.明清山西交通地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4.
[18]段自成.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97-100.
[19]王晋丽.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山西大学,2020.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5.
[21]石麟奏为遵议内阁侍读仙保条奏弭盗安民办法一折事:乾隆三年九月初六日[B].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04-01-01-0024-017).
[22]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J].中国乡村研究,2003(01):1-31.
[23]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31.
[24]英廉题为会审山西灵石县赵张氏等因女张赵氏赌博偷窃不服管教将其勒死一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B].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题本刑部02-01-007-023486-0010-0000).
[25]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和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6]田文镜.抚豫宣化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232.
[27]陆陇其.三鱼堂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261.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