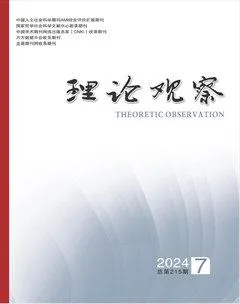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容貌焦虑的产生与抵抗
摘 要:容貌焦虑不只是一种微观的个体情绪,更是一种宏观的在社会机制作用下产生的社会心态。女性囿于容貌焦虑久矣,其原因关联了女性将自身视为一种观赏性客体、将变美视为一种事业、颜值崇拜以及身处“审美茧房”多重维度。对容貌焦虑的抵抗也需从社会引导性别气质转变、实现职业竞争平等、促进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媒介审慎呈现女性形象多方面入手。
关键词:女性;社会性别;容貌焦虑;产生;抵抗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7 — 0110 — 04
一、问题的提出
容貌焦虑是指个体过度在意自身外貌,并因此而产生了忧虑心理与强迫行为。近年来,容貌焦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焦虑。相较于男性,这种焦虑感在女性群体(尤其是青年女性)中更为突出。2021年,中青校媒围绕容貌焦虑问题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59.03%)的大学生存在容貌焦虑,其中女性对自身容貌非常满意的比例(6.08%)低于男性(12.77%)[1]。2023年,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同样指出,容貌焦虑始终是职场人热议的话题,而与男性(45.6%)相比,女性(56.6%)对外貌的紧张度更高[2]。由新氧科技发布的《2022年医美行业白皮书》也体现了这种性别差异,报告指出,2022年医美消费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依然处于不平衡状态,“她经济”力量明显。2022年新氧线上交易平台上女性用户占比高达89.17%,男性仅占比10.83%[3]。
医美整形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女性变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渠道。美妆教程、穿搭分享、减肥经验等“变美秘籍”在互联网随处可见,更是让女性看似能更轻易地改换自身形象,形塑完美身体。只是此等“进步”,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一直以来被美丽裹挟的境况,反而使女性在容貌焦虑的桎梏中越陷越深。“半小时护肤、全天候带妆、无数次医美、一辈子减肥”成为很多女性的日常。社会对美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美的标准却愈发单一。“微笑唇”“精灵耳”“A4腰”“漫画腿”……这些局限性的“美”无差别地规训着所有女性,使女性热衷于形塑自己的身体,却永远无法抵达形塑的尽头。于是,不断产生了容貌焦虑。其引发的负面情绪将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不利于女性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探究女性容貌焦虑的成因与根源,以期促进人们对容貌焦虑的认知与反思,并探究如何对容貌焦虑进行反抗,为青年女性一代提供积极正面的价值引导。
二、关于容貌焦虑的讨论
容貌焦虑可归属于“社会体格焦虑”在社交媒体中的延伸[4]。可理解为人们受社会审美标准与大众媒介语境影响,对自身外貌、体型等身体形象感到不自信、不满意而产生的苦恼心理,从而陷入一种焦虑状态。
容貌焦虑不只是一种微观的心理表现,更是一种宏观的在社会机制作用下产生的社会心态。就容貌焦虑如何生产,许多学者都提到了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联姻”。认为大众媒介出于私利,与资本配合,层出不穷地生产容貌卖点、贩卖容貌焦虑。通过固化受众审美、物化受众身体,误导受众进行身体消费。因为对商品的消费有穷尽,而对情绪的消费无穷尽。在资本和媒介的联合助推下,消费主义陷阱异化成容貌焦虑怪圈。此外,颜值社会下个人形象与身体外形挂钩,容貌被赋值,美被符码化,高颜值被视为一种有助于社会竞争的资本。此类观点不断被宣传强化,是滋生容貌焦虑的意识土壤。技术发展同样会对容貌焦虑的形成产生影响。医美整形技术诱使人们不断修缮五官,调整外貌,以达完美。而追求完美必将与焦虑相伴。此外,美颜P图等技术呈现的美化自我,会与现实自我形成对比,使人产生心理落差,从而容貌焦虑。
关于如何抵抗容貌焦虑,有学者提出青年群体需培养“风清气正”的审美取向。即摈弃单一的审美标准、摒弃颜值至上的审美观念,在建构个人形象时结合自身的审美与风格,不盲从。追求自然美、内在美,看清审美固化背后的消费陷阱与权力博弈,以理性消除焦虑。此外,还要加强对相关行业的监管,特别警惕医疗美容广告中可能存在的构建畸形审美和传递错误价值观的问题[5]。
三、女性容貌焦虑何以产生
女性的容貌焦虑是社会文化与女性能动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女性受社会舆论与大众媒介影响,对自身、对美产生了错误认知,从而出现的心态失调。阐述其生产路径,首先要回答的便是女性为什么会认为自身必须要“美”,又为什么一直无法到达“美的彼岸”。
(一)文化根源:性别规训下客体化的女性
在漫长的父权社会中,女性一直被视为一种观赏性客体,没有“不美”的权力。因为外表美丽与“女性价值”对等,“不美”意味着不像女性、没有价值。于女性而言,生为女人就意味着成为美丽的客体。“美”是一种“职责”,追求“美”、保持“美”是一种“义务”。
这种性别规训,不仅让女性将自身与“美”关联,也让女性内化社会审美标准,时时检视自身容貌。每当与标准有出入时,便会容貌焦虑。而这种焦虑是必然的。因为作为人,本就鲜活各异,不可能完全符合统一的量化标准。况且,从古至今的社会审美对女性身体的要求通常都很具体,过于具体:手要如柔荑,肤要如凝脂,脖子得像蝤蛴,牙齿还要如瓠犀;保持干净整洁是不够的,还要看起来是优雅的,闻起来是香的,摸起来是滑的;像脱口秀演员小鹿吐槽的那样,女人全身上下,头发、后背、胳膊肘……除了第一张脸,全是要精心修饰的“第二张脸”。这些对女性身体的形塑要求,实则是在不断强化男女性别差异,不断凸显父权社会对女性应当美丽、应当温顺、应当被保护的性别定义。对于无理要求与刻板审美,大多数现代女性的做法依旧是迎合,是从头到脚的全套护肤,是定期医美,是时常健身……是容貌焦虑。
女性作为观看对象被欣赏,作为美丽客体被凝视,这一性别文化到了今日,并没有完全消失。女性会因为“不好看”受到贬低轻视,也会因为“好看”受到污名误解。使女性仅仅因为自身外貌而感到羞耻和焦虑。实则是抹杀了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单纯为身为女性这一性别而焦虑。
(二)社会根源:性别分工下女性的另类赛道
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受到冲击。女性也能走出家门,顶起半边天。只是,属于女性的那半天空与男性还是存有差别。因为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并没有彻底改变。“男性赚钱养家、女性貌美如花”的性别分工,依旧存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性别规训,还在滋生。
按照习得的经验,女性可能从很小开始就不愿像男性那样刻苦努力,获得学识与技能。而更愿将时间、精力贡献于提高女性魅力、获得男性认可上,以期在婚恋市场与同性的竞争中取胜。
因而女性的容貌焦虑也是一种资本焦虑,源于女性的竞争心理。有竞争便会有压力,有压力便易生焦虑。女性的另类竞争在网络上被称为“雌竞”。在“雌竞”中,虽然万事万物都要比,但颜值的比较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为了“不输”,女性必须“要美”。而“美”等同于符合社会审美,或者说男性审美。只是社会审美大多刻板肤浅,无法衡量女性的真正价值,反而会让女性陷入焦虑。“美”是年轻,而变老则是自然规律。“美”是身材好、皮肤白,但基因无法改变。纵使打针拉皮、减肥健身“卓有成效”。但女性身上总还会有“不够美”的地方,世界也总还会有“更美”的人出现。执着于“比美”,比到最后,就像白雪公主故事里的皇后,被魔镜控制而不自知,徒生焦虑。
(三)心理根源:社会舆论堆砌下的颜值崇拜
容貌焦虑还源于女性对获得外界认可的迫切期望。俗语有“相由心生”,网络新语有“颜值即正义”。社会对容貌的过度重视,对“美”的吹捧,对“不美”的贬低,到了今日,更加突出。容貌姣好之人常因其外貌被赋予一系列优秀品质,而相貌欠佳之人则被迫与许多负面评价关联。
颜值成为评判人的先决要素。高颜值意味着高认可、高宽容,甚至更被喜爱。偶像明星因其出色容貌,即使犯错,也“颜在,江山在”,依然有粉丝拥护。“最美杀人犯”“最美通缉犯”的“美照”在网上广为流传,将“最美”这样的词语安在“罪犯”身上,明明荒诞,但大家习以为常。“津津乐道”的不是其“罪”,而是其“美”。
颜值崇拜使得女性期待被吹捧、被认可,时常为自身的“美”沾沾自喜,又为“不够美”而忧愁焦虑。当更“美”的人出现,女性便要么“战火熊熊”,要么“顾影自怜”。时刻忧虑自己沦为“被贬低”“被轻视”的对象。崇拜“颜值”,因而被“颜值”所控制。“颜”有“值”意味着“颜”有“上下”,有“高低”。要获得外界认可,便必须“上”、必须“高”。女性在“争上”“变高”的“暗潮”中起伏,却怎么也无法到达“彼岸”。
(四)技术根源:媒介催化下女性的“审美茧房”
女性对美的理解与定义出现偏差,形成了狭隘的审美观念,从而无法正确意识到自我与自我的价值,最后导致容貌焦虑。在这条“错误链”的生产中,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审美本该丰富而各异,包容且多元。但媒介推送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女性对美的判断,误导女性形成单一审美,将女性包裹在一层“审美茧房”里。
通过大数据推送,媒介迫使女性打开手机便能看到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女性图像。这些形象的反复呈现使女性产生误判,认为这是一种“已确立的美丽标准”。而其在媒介上的随处可见,又让女性产生错觉,认为此类形象“具有普遍性”。这种符合大众审美的身体形象,成为女性衡量自身的参照物,成为女性对自身外在的虚假期望。世上不存在同样一片落叶,世上的女性也不可能符合同样一套审美标准。媒介误导女性在妄念中彷徨,在对比中迷失。最后期望落空,自我怀疑。
此外,大众媒介的话语形式也常让女性“左右为难”。一方面,推送暗含父权思想的内容,重申女性要瘦、要美、要被男性喜爱……的性别规训。但另一方面,媒介话语又受当代女性主义的影响,呈现内容常常矛盾,在极力教导女性妆扮成符合大众审美(尤其是男性审美)的同时,又在鼓励女性勇敢做自己,不应为了任何人而改变。此论调,让女性产生容貌焦虑的同时,又为自身产生容貌焦虑而感到焦虑。
四、女性容貌焦虑如何抵抗
女性依旧被困在传统的社会审美里,单一狭隘的美丽依旧被推崇、被追求,有时甚至是病态的追求。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女性自身意识觉醒、做出改变。但在要求女性保持“理性”的同时,也需倡导理性的社会文化。因为在颜值社会与竞争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女性的容貌焦虑很多时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一)社会引导转变:性别气质多元化
“美”作为概念,本身不具有性别取向,是社会将女性气质与“美”联系起来,以此达到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统治。这种性别气质与身体的联系导致女性对身体的密切关注、产生容貌焦虑。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性别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6]。是社会引导着女性不断接受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从而确立性别认同、建构女性气质。是社会将女性建构成“女性”。
社会应改变以往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气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不再热衷于鼓励女性追求所谓的女性气质。在社会上对女性美袪魅,将女性的身体还给女性自己。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抗,需谨慎消费主义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合谋”关系,挖掘并批判那些将“美”与女性捆绑的性别话语,驱赶围绕在女性周围的性别规训,摒弃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审美标准。鼓励女性建立身体自尊与自信,追求形塑健康、具有个人特色的身体,而非性别化、模板化的身体。这并不是让女性变得男性化,而是从性别气质的二元对立走向性别气质的多元化弥合。鼓励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努力拥有双性化气质。所谓双性化气质是指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同时具备男性优点与女性优点[7]。
(二)发展机会均等:抬头不见天花板
抵抗容貌焦虑,需要女性意识到美丽的身体并不是一种社会资本。资本能增值,而美丽不具备此特性。社会需创造条件让女性去追求那些真正的资本,让女性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让女性可以涉足任何行业、晋升到任何高度。
这需要社会增强人们性别平等的意识,重点解决职业中的性别隔离问题。培养女性在职场中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权利意识。需督促用人单位采取稳健有效、毫无性别偏见的招聘与晋升管理制度,使女性平等的拥有进入高层职位的机会。政府还可适当减轻雇佣女员工的企业税费或给予补贴,提高企业雇佣女性的积极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女性自身也须努力涉足“高精尖”领域,投身于“云计算”“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行业,积极与男性竞争,打破男性垄断,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
此外,需改变性别分工的传统认知结构。不再将公共空间与男性联结,而将私人空间与女性关联。在将女性推向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需将男性带回到家庭领域承担家庭责任。挪开女性肩上的双重负担。许多职业女性在结束工作之后,回到家中无法休息,因为需要接着上“第二轮班”(Second Shift),即承担家务和照料责任。结果就是女性在就业市场上不得不寻求更低强度或不影响她们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作与职业,而对应的,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就属于那些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男性[8]。社会应鼓励男性回归家庭领域,解开女性与家庭的单向“绑带”,鼓励男性分担家庭责任、承担母职,与女性一起,成为家庭的“双桨”。
(三)女性意识觉醒:不视自身为客体
“女性美”的定义者与受益者从来不是女性。一直以来,是男性占有着对“女性美”的定义权与解释权。而父权社会长期积累的对“女性美”的定义往往狭隘而畸形。它用单一死板的审美标准桎梏着丰富各异的鲜活女性,给女性的身体架上“枷锁”。女性要觉察到性别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形塑,要积极反抗容貌焦虑,反对“服美役”。争取“不美”的自由。不再将自身视为观赏性的“客体”,而要变得健全、强壮,成为超越性的“主体”。
社会也需和女性一起,努力将勒进女性身体的“绳索”清除出去。不再教导女性将为男性服务作为人生目标,而要让女性接受和男性一样的教育,一起走那条最艰难但也最可靠的路。让女性心智的成长不再受阻,不再以头脑为代价去修习美丽与追求爱情。社会要培养女性的批判思考能力,教导她们勇敢、独立,使她们的所言所行与性别无关。就像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在《19世纪的妇女》(1845)中描述的那样,要让女性“像一个自然人那样得到成长,像智者一样去分辨一切,像灵魂一样自由自在,展示她的各种才能”[9]。
(四)大众媒介审慎:女性形象需鲜活
媒介对大众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人们在媒介上追随审美潮流,按习得的审美在现实中形塑自我。“符合审美标准,获取美貌红利”是现今很多青年女性的目标。只是标准是“从头到脚”的具体而单一,是高颅顶、巴掌脸,是A4腰、漫画腿……,然而,这些标准实则只是媒介制造的与美有关的符号,并非美丽本身。
媒介应当意识到自身正在发挥的巨大影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引导大众树立正向的审美观、性别观与价值观,将更多元更健康的女性形象呈现给大众。应当打破以往刻板单一的审美场域,不再呈现完美无瑕但却千篇一律的女性形象,不再让观赏性(即是否“美”、是否“瘦”、是否“年轻”或是否“温柔”)成为评价女性的标准。勇敢呈现不再是男性附庸,不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和存在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进程重要行动者的女性形象[10]。
〔参 考 文 献〕
[1]程思,罗希,马玉萱.近六成大学生有容貌焦虑[EB/OL].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21-02/25/nw.D110000zgqnb_20210225_1-07.htm.
[2]智联招聘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EB/OL].https://www.djyanbao.com/preview/3451128.
[3]新氧2022年医美行业白皮书[EB/OL].https://www.djyanbao.com/report/detail?id=3435990&from=search_list.
[4]许高勇,郑淑月. 容貌焦虑:议题、身份与文化征候[J]. 传媒观察,2022(09):59-64.
[5]刘传红,吴思琪. 颜值幻象与美丽透支:医疗美容广告批判及其治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05):141-147+187.
[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9-67.
[7]宋岩.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性别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22(06):66-69.
[8]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M].肖索未,译.北京:三联书店,2021:12-13.
[9][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49-192.
[10]卜卫.媒介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8.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