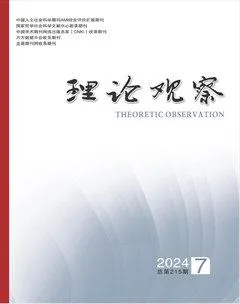再融入乡土:回流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意愿研究
摘 要:本文聚焦回流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意愿,利用西藏日喀则52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回流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较高,但参与行为较低;农户主观规范意识越高,参与意愿越强;农户社区归属感越强,参与治理意愿越高;农户回流时间越久,其参与社区治理意愿越弱。
关键词:社区治理;回流农民工;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C91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7 — 0095 — 09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农民工的回流现象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田梦君等,2023),寻求更多的经济机会(陶玮等,2022)。长期以来,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劳动力(王大哲等,2022),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草原等,2023)。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杜剑等,2023),以及农村地区政策的改革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农村(蔡弘等,2023)。
从社会经济背景看,农民工回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王镓利,2022)、工作机会的减少(熊颖哲,2022)及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的提高(李昭楠,2022)。此外,国家在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加(刘延华,2018),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和农业政策的支持,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工回流可以被视为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整机制(张欢、吴方卫,2023),城市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性和农村地区新兴就业机会的增加,是推动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同时,家庭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乡土的依恋,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传统上,农村社区依靠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共同的价值观来自我管理和发展(柳泽凡,2020)。随着农民工回流到农村地区,使原有的社会网络和治理模式受到了冲击,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动态和复杂性(何强,2020)。这一回流不仅影响了农村社区的人口结构(雷焕贵等,2021),也对社区经济、文化(王山河,2008)和治理模式(刘玉侠、张剑宇,2023)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济层面上:回流的农民工带回了他们在城市获得的技能和经验(闫琳琳、李双双,2022),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创业和创新的潜力(刘玉侠、张剑宇,2023)。同时,回流农民工通常能够带回一定的储蓄(周春霞,2022),这些储蓄被用于改善居住条件、投资于农业等,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社会结构上:由于劳动力流失严重,使得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性别比重(失调)日趋严重。农民工回流使农村劳动力得以重新分配(张喆,2013),对农村地区生产模式和家庭结构都产生了影响(贺小丹、董敏凯,2021),同时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和代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刘达培,2024);在文化层面上:城市的生活经历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何淑婷,2023)。农民工的回流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产生了影响(史璇,2016),他们更希望用所学的治理知识应用于农村社区的管理中,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尽管学界对回流农民工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目前学者研究的数据来源多是中国农民工检测报告、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等全国性宏观数据;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对农民工回流后产生的影响分析多从人力资源、技术、就业等经济角度展开,较少关注回流农民工群体对当地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和行为;第三,目前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东部、中部农村地区,对西部地区关注较少,尤其是西藏回流农民工如何参与并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方面还未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从社区归属感、主观规范视角出发,探索西藏日喀则市回流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意愿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期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和农村社区治理提供政策参考。
二、回流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与群体特征
准确把握回流农民工的概念及特征,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回流农民工”学术界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但其定义基本包含外出时间、回流时间、回流空间的认识等(刘玉侠、张剑宇,2023)。对于外出时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将时间界定为6个月以上;部分学者为了突出回流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特质,认为时间应在1年以上(杨忍等,2018);对于回流时间的界定,部分学者参照人口普查的定义,认定在“6个月以上”(陈世海,2014)。同时,大部分学者认为6个月难以完全排除城乡两栖人口和因处理事务或特殊原因滞留在家的农民工,故回流时间在1年以上才算合理(胡枫、史宇鹏,2013);在回流空间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区分回流地,只要回流到户籍所在地(包括农村、乡镇、县城)即符合界定条件(王炜、许幸莲,2011)。另一部分学者则限定为回流到户籍所在乡村,包括本村和县域范围内的其他村(胡枫、史宇鹏,2013)。西藏由于受其传统文化、政府政策、家庭束缚等影响,除极少数农民工属于长期外出务工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属于季节性转移。据调查数据显示:转移时间上6个月以内的占1.15%;6-12个月的占0.96%;13-24个月的占36.47%;25-36个月占35.12%;36个月以上26.30%。在本研究中将回流农民工外出时间以国家统计局《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界定为准,界定为6个月以上;回流空间上以回流到户籍所在地为准。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主观规范与回流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行动之前感受到的来自外部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往往由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主体对社会中个体施加所产生,如家人、朋友、同事等对某一行为的看法对个体所产生的压力(钟骅,2012)。多数学者在主观规范对个体意愿的影响上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个体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贾鼎(2018)的研究发现环境决策参与的公众主观规范会显著地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决策的意愿;张红等(2015)认为主观规范除直接正向影响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还会正向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胡晨成,2023),对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李守越,2023)。
农村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社区是由邻里组成的,大家共同认可社区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因此,在共同目标的作用下,邻里是除了家庭成员外对自身行为影响最为明显的主体,邻里提供的示范作用,能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人们决策思考范围之内(谢巍,2023)。村民主体对治理的态度受家人、朋友、邻居的影响,当周边的人都在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并且邻里之间有相互监督的效果,会提高居民自身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更利于村民做出有利于社区治理的行为。以居委会为核心代表的社区治理行动主体,既是制度与政策的基层执行者,又是社区内部多方有序治理的实际协调组织者(何威,2023)。作为基层管理者,村委会或者村干部在乡村社区治理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乡村居民和治理的影响非常大。
个体在做出某项行为决定时会受到他人或社会压力的影响。在个人行为决策过程中,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包括来自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的支持或反对,周围邻居以及威望和权威人士的认可或否定,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范和引导(岳羽,2023)。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主观规范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居委会、政府部门倡导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自我认同感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 家人、邻里支持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社区归属感与回流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归属感维度。社区归属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认为自己属于这个社区,愿意为社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卓文昊(2023)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及政府动员对社区参与治理意愿呈正相关;葛亚楠(2023)通过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影响作用;李欣(2020)基于邻里环境因素对社区归属感与居住意愿的影响中发现,社区归属感对于居住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归属感象征着居民对社区的强社区参与意愿,是渴望实现真正融入社区的乡愁(刘悦来等,2023)。回流农民工有一定的社区归属感(胡艳华,2014),社区归属感也是农民工回流的重要方面,作为农村社会中的村民,都有落叶归根的感情,所以社区归属感对农户意愿以及行为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借鉴前人研究,以“邻里关系”“领里互助”来衡量社区归属感。社区归属感越强的人通常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治理(徐淑新,2020),他会更加关注社区的事务,会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活动和事务中,与其他社区成员一起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同时,他会更加信任和尊重社区的其他成员,更容易建立联系和合作。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 社区归属感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 邻里关系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 领里互助频率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回流年限对回流农民工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
农民工回流年限对于被调查对象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外出务工者,他们在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长期生活,受到当地潜移默化的影响发展更为成熟,形成相应的理念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常年在外往往具有更为开阔的眼界(陈秋霞等,2023)。回流年限越久,对社区治理事务越有更深入的了解,其治理观念与在外出务工所认识的治理观念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可能对社区的治理方式不认同,那么就会对其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回流年限对回流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数据来源、样本特征
(一)调查区域选择
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也是西部地区推进发展建设的重要地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资源禀赋好,为了合理开发西部资源并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等。由于政策的影响,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带动了劳动力需求(张华等,2021),产业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批西部农民工回流。然而,西藏外出务工者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阿里地区外出务工人数明显偏低,昌都、那曲次之,而日喀则外出务工人数明显偏高(孙自保等,2016)。日喀则市也相应出台多项吸引人口回流的政策,为回流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以此提高回流农民工的收入。综上,选择日喀则地区为调查区域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抽样调查与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课题组成员对西藏日喀则回流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有效性,课题组成员招募了日喀则当地同学进行调查沟通协助,并对调查员进行农村社区治理的概念与范畴、询问举例、访谈技巧等方面的普及。正式调查前,小组成员以林芝市周边居民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过程显示,课题组设计的变量比较合适,但偏专业化,为保证调研效果,课题组将问卷问题进行了口语化修正。并于2023年12月—2024年3月期间对日喀则回流农民工进行正式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区治理参与等方面。调查共发放问卷570份,剔除数据前后逻辑不符及缺填、漏填等明显错误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21个,有效回收率为91.40%。
(三)样本特征
在样本基本特征上(表1),被调查者男性偏多,因男性居民外出务工较多,女性一般在家持家,所以相应的回流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会较大,符合其事实;年龄结构上,46岁以上的占样本总数较少。针对调查对象而言,样本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家庭年收入方面,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样本量占比较少;样本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中专)及以上占样本比重为22.84%,高中程度占22.65%,初中教育程度占37.24%,小学及以下占比较少。总体来说,被调查样本符合西藏日喀则市实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对象在社区治理意愿以及行为方面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大多数回流农民工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然而,将这种意愿转化为行动的人数却相对 较少。只有“意愿”没有“行为”的参与是不完整的,而只有“行为”没有“意愿”的参与难以持久。要充分发挥回流农民工的主体性作用,就应在激发其参与意愿的前提下,促进其落实到行为(李晓雅,2022)。
五、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治理。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研究说明。构建Probit模型为:
Prob(Yi=1|Xi)=Prob(α0Ti+βiXi+εi>0|Xi)(1)
式(1)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Yi=1表示调查对象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Yi=0表示调查对象没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Xi表示解释变量;α0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Ti表示控制变量;βi表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调查对象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分为有意愿和无意愿两种。“愿意”赋值为1,“不愿意”赋值为0。
解释变量:参考已有的关于农户社区治理意愿研究中显著的影响因素,将个人特征、主观规范、社区归属感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观规范维度,借鉴张红、张再生等学者的研究,调查问卷中设置:“参与社区治理我觉得很光荣”“家人、朋友、邻居及同事支持我参与社区治理”“各级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大力倡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3个变量来测度主观规范。社区归属感维度,借鉴温理等学者的研究,调查问卷中设置“邻居关系融洽”“获得过邻居帮助”2个变量来测度社区归属感。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xb)、年龄(nl)、家庭年收入(nsr)、教育程度(jycd)、回流年限几个方面。回流年限以时间段划分,以1-5进行赋值,“回流年限6个月以内”=1、“6-12个月”=2、“13-24个月”=3、“25-36个月”=4、“36个月以上”=5。
六、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前的检验
本研究先把问卷中的数据结合变量赋值整理出来,用stata.17软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变量相关性检验。通过表4中结果可知,主要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相关,此次调查所得数据通过相关性检验,可往下继续分析。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还要对样本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从表5中可以看到,条件索引VIF值都小于10,可知,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或者存在较弱的共线性,说明模型选择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正确的,可以进行回归。
(二)模型实现
本研究利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根据表6回归模型结果可知,不断对变量进行交叉拟合回归,显著性在几次回归后结果基本一致。由此,也更能检验模型拟合结果的稳定性以及模型拟合度较好。
(三)结果分析
从表6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来看,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主观规范、社区归属感、以及回流年限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性别和年龄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3)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对治理意愿影响显著(P<0.05),回归系数为0.203,在维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有更高的认知能力,能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农村社区治理,在社区治理方面有更高的参与的意愿。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强,这些都会提升农民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孙琦,2023)。家庭年收入水平影响效果显著(P<0.01),回归系数为-0.271,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相应的农户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越低。从受访对象看,家庭收入高的家庭,家庭成员大都工作较忙,他们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经济利益,对社区治理方面相对投入关注度较少,因此使得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下降。
主观规范维度影响效果显著(P<0.01),对回流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H1 假设得到验证。如果一个人感受到的来自社区成员的支持和期望越高,他可能会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治理。且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为社区做出贡献,并认为社区治理是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那么他可能会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会让自己产生一种成就感、自我效能感(岳羽,2023)。
社区归属感层面,回归分析显示社区归属感对农户参与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H2假设得到验证。农户的社区归属感越强,对社区内各个方面的信任度就越高,主人翁的意识就会越强。从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就会越高(温理,2018)。
回流年限指标上,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流年限对农户参与社区治理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H3假设得到验证。新生代回流农民工与农村、土地、熟人社会的联系较少,他们回流后会呈现出更多的不适应性,在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普遍不适应(张世勇,2014)。农民工回流时间越久,对社区治理会有更深的观念认识,对社区治理事务有更深入了解,其治理观念与在外出务工所认识的治理观念方面可能存在认识上的冲突;再一方面可能会对社区治理行为方面越来越不认同,感到越来越失望,进而降低自己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解释变量的影响更稳定,我们试着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先后控制住nl、xb、jycd、nsr这4个控制变量后对模型进行回归(李梦,2017),结果如表7所示。
七、对策建议
农村社区治理是建设和美宜居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本文以西藏日喀则市回流农民工作为调研对象,综合上文的研究结果,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主观规范、社区归属感、回流年限方面都会显著影响回流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因此,应当重点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以提升回流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意愿。
提高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个人素养,加强社区治理认知。大多数农户群体文化程度低,认知能力有限,这样会严重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发展社区教育将有利于提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社区治理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参与意愿行为水平的改善(尚云,2019)。因此,政府应多开展组织相关的教育宣传工作,建立多元资源整合的社会化培训体系,提高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认知和积极性。
形成多元宣传主体,提高村民对社区治理认识的重要性。当前,农户对社区治理的认识水平较低,自治能力较差,认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就是政府的事情,跟自己无关。虽然农村社区都实现了村社共治的局面,但是没有实现与普通农户共同治理的局面,治理主体比较单一。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核心力量(郝文强,2023),应通过居委会鼓励引导农户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发挥模范示范作用,引领村民实际参与,增强主观规范意识。农村是传统的熟人社会,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罗博文,2023)。村干部不仅是政策上传下达的最后接棒人,也是社区治理实施的先行者,有着模范带头的作用。因此要加强村干部在社区治理相关方面理论和技能的培训,并且村干部要主动积极投身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带动农户更好的提高村居民参与意愿。
构建和谐的居住环境,增强农户的社区归属感。社区治理重在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让居民成为社区治理最大的受益者是社区治理的目标所在(钱戴玉,2023),提高社区归属感可以促进农户参与到社区治理。通过建设一个和谐的社区环境(张静,2020),创造更为丰富的社区成员居民交流平台,培养社区归属感,缓解社会压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参 考 文 献〕
[1]田梦君,熊涛,张鹏静.劳动力转移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研究——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调节效应分析[J].世界农业,2023(11):103-114.
[2]陶玮,尹月秀,鲁如艳.祖辈与父辈共育幼儿的教育冲突表现及应对策略研究[J].教育观察,2022,11(03):29-31.
[3]王大哲,朱红根,钱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08):16-34.
[4]马草原,李宇淼,孙思洋.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变化及产出效应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23(09):23-41.
[5]杜剑,徐筱彧,杨杨.高质量就业: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作用的研究背景[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08):58-69.
[6]蔡弘,陈雨蒙,马芒.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23(08):75-90.
[7]王镓利.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财政政策探讨——以浙江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2(12):66-70.
[8]熊颖哲.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英国托利社会主义论贫困问题(1842—1847)[J].史林,2022(06):12-17.
[9]李昭楠,刘梦,刘七军.炊事燃料清洁转型能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于CFPS2018的微观证据[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02):239-248.
[10]刘延华.农民工回流原因、回乡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04):45-51.
[11]张欢,吴方卫.要素价格、产业转型与农民工回流[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25(04):108-122.
[12]柳泽凡.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村干部职业化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
[13]何强.基于交往行为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评价与优化策略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0.
[14]雷焕贵,马慧鑫,赵思宇,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创业与终结的思考[J].理论观察,2021(10):87-91.
[15]王山河.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区的影响研究——对重庆市黔江区新华乡和太极乡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05):65-68.
[16]刘玉侠,张剑宇.对回流农民工的多维审视:基于现有研究分析[J].河北学刊,2023,43(05):160-168.
[17]闫琳琳,李双双.回流农民工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J].党政干部学刊,2022(12):44-49.
[18]周春霞.双创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榜样的行为特征分析及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22,50(18):223-228.
[19]张喆.浅谈劳动力迁徙对劳动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3(05):48.
[20]贺小丹,董敏凯,周亚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与农村资源配置——基于农民工返乡后行为的微观分析[J].财经研究,2021,47(02):19-33.
[21]刘达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的自我认同危机:形成与纾解[J].北方论丛,2024(02):32-39.
[22]何淑婷.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及市民化测度研究[D].南昌大学,2023.
[23]史璇.农民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作用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16(12):12-14.
[24]杨忍,徐茜,张琳,等.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11):2305-2317.
[25]陈世海.农民工回流辨析:基于现有研究的讨论[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03):265-272.
[26]胡枫,史宇鹏.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J].人口学刊,2013,35(02):71-80.
[27]王炜,许幸莲.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现象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91-95.
[28]钟骅.上海菜场布局规划思考与探索[J].上海城市规划,2012(03):92-97.
[29]贾鼎.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01):52-58.
[30]张红,张再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6):523-528.
[31]胡晨成.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心理驱动因素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8(08):63-70.
[32]李守越,尚明瑞.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对耕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J].科技与经济,2023,36(04):51-55.
[33]谢巍. 村规民约、邻里效应对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影响研究[D].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3.
[34]何威.风险防范与危机抵御: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及其实现[J].河北学刊,2023,43(06):178-186.
[35]岳羽. 新乡市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与行为研究[D].河南工业大学,2023.
[36]卓文昊.共享视域下社区参与式治理作用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23.
[37]葛亚楠.哈尔滨市“村改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共治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3.
[38]李欣,辛文玥,陈夫静,等.邻里环境因素对社区归属感与居住意愿的影响——以海口市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28):5-9+14.
[39]刘悦来,谢宛芸,毛键源.城市微更新中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以社区花园为例[J].风景园林,2023,30(08):20-26.
[40]胡艳华.农村劳动力回流后的社会适应与社会保障现状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37(05):40-43.
[41]徐淑新.拉萨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研究[D].西藏大学,2020.
[42]陈秋霞,朱嘉豪,许章华,等.“是否值得”对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村地区的Ologit模型实证[J].管理现代化,2023,43(05):156-166.
[43]张华,刘哲达,殷小冰.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01):73-84.
[44]孙自保,宋连久,刘天平,等.藏族农牧民外出务工影响因素分析[J].西藏发展论坛,2016 (04):14-20.
[45]李晓雅.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村民参与意愿与行为转化研究[D].河北地质大学,2022.
[46]温理.农户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研究[D].安徽农业大学,2018.
[47]张世勇.返乡农民工研究——一个生命历程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44-265.
[48]李梦.企业规模、RD支出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D].东北财经大学,2017
[49]尚云.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居民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D].新疆农业大学,2019.
[50]郝文强,黄钰婷.基层治理的复合联动结构与长效互动机制——基于C市R社区的案例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6):210-219.
[51]罗博文,孙琳琳,张珩,等.村干部职务行为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陕陇滇黔四省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2023(03):162-184.
[52]钱戴玉,孙玲,余栋.“五社联动”协同治理实践与优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3(23):176-178.
[53]张静.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20.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