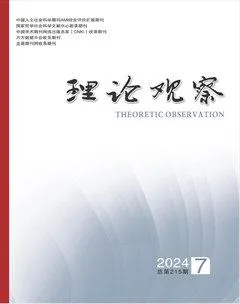黑格尔劳动论题“抽象化的过程”的理论智慧探寻
摘 要:劳动论题的思考在思想界一直是讨论的重点,近年来社会中对劳动认知的歪曲理解迫使得亟需要回到经典作家的劳动论题中,以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为锚点重新审视黑格尔市民社会“抽象化的过程”的理论智慧。在黑格尔的思维进程中,具体的人的主观需要的特殊性需要通过他人的普遍性来进行中介和通过劳动过程来进行实现,人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自我的存在。但是生产的发展使得生产和需要逐渐细致化;马克思发现分工协作的发展又使得劳动技能机械化、固定化,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固化为局部工人,机器也逐步消解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逐步成为了劳动者对立面的异化劳动。
关键词:劳动的特殊性;抽象化的过程;分工;局部工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7 — 0056 — 06
一直以来,“劳动”这一范畴在哲学界、经济学界都备受关注,人类在劳动中体现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是人有别于动物的根本原因所在。[1]马克思所秉持的劳动本体论主张从生产劳动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认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2]。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3],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4]。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劳动的误解、逃避、歪曲等现象,将“劳动”一词与部分重体力劳动者挂钩,认为只有苦活累活的工作才是劳动,这都是对劳动的片面理解,也是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分工理论的歪曲,不利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观的建设。因此,重新回到“劳动”这一范畴的讨论中,回到经典作家对劳动论题的思考与推演中,从而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指向进行新时代下的阐发,不仅仅对劳动者个人的思想能力产生科学的影响,更是在新发展格局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发展的必要理论准备,推动国民财富增加与共同富裕的稳步前进。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论题是对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劳动论题的超越,他在哲学领域中研究了劳动与劳动自由[5],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去对劳动与生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完成了他的劳动论题[6]。以对经典作家理论的思考而形成“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路径在马克思构建他的劳动论题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构建的市民社会中发现了人与人之间“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他认为个人的特殊性和整体普遍性是密不可分的,个人需要通过他人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存在“抽象化的过程”使得个体与他人相互联系,在分工的发展中更进一步地构建起市民社会的基本逻辑。马克思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度剖析起始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对经济现实的考察与理论抽象构建其了政治经济学大厦。其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逻辑诞生于黑格尔市民社会逻辑之上,也成为了重新挖掘黑格尔的劳动观的重要视角,在深入理解劳动论题“从黑格尔到马克思KcexiXJW4dprG4bmSidhIQ==”的发展脉络后,可更进一步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因此,本文期望回到《法哲学原理》中探究黑格尔的劳动论题的理论智慧,重新审视黑格尔的劳动观、挖掘经典思想,并以此加深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理解,以期获得理解新时代下的劳动问题的新角度。
一、黑格尔劳动论题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观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孟祥林(2022)[7]认为黑格尔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他的劳动论题中劳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每个人都是在各自的“利己心”的推动下寻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方法,但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这个过程中,会受到一个未知力量的引导或驱动,致使最终达成一个满足他人的需要的最终结果,斯密将这种神奇的力量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并以此认为在整个经济体的运行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最终同时满足了他人的利益需求。因此,斯密认为一个经济体中的个体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个联系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之下,不同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并不会影响他人的利益,相反还可以帮助他人利益的满足与实现。
黑格尔从斯密的理论中看到了个体“每一个特殊的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在市民社会中相互联系但也相互制约,每一个个体通过“他人”对“我”的认识来认识自我,即自我的认识制约于他人的认识,每一个个体都是其他个体确立自身存在的基础,“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终结,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终结,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8]黑格尔发现,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指向点,但是这个自身的利益一定是需要在市民社会的关系中才能实现的[9],也就是个体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没办法通过个体的自我运动去达到,他一定需要同这个市民社会的其他人发生关系才能到达他的目的[10],因此,“其他人就成为了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11]。在这段论述中,一方面,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中原子化、独立化的个人的“特殊性”与市民社会整体的“人”的群体实现了统一;另一方面,黑格尔将“其他人”视作“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对具体的人的人格的一种降格,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化为“物”即实现利益的手段的作用,这一认识也蕴藏了具体的人的特殊性和市民社会整体的人的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的另一视角。[12]尽管说具体的人的利益实现需要他人的存在才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具体的人”的眼中的“他者”只是自身实现利益的工具与手段,作为现实的个体在市民社会中发生作用的“他者”,在“具体的人”眼中却只是工具与手段,因此利益实现过程中产生的个体与他人的统一,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对立。
作为个体的特殊性的实现受到作为整体的普遍性制约,黑格尔认为“需要和理智的国家”的制度就是在这个辩证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一切方面相互倚赖的制度。”[13]个人的利益诉求以及个人的权利的存在与实现,都同“众人”的利益诉求与权利相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层层的联系中,才可以构建出市民社会。黑格尔认为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的,“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14]每一个个别的人在通过劳动实现自己个人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将“普遍物”也就是“他人”去作为自己实现利益的中介,从而不自觉地按照“普遍方式”将自身的意识、行为等融入整个社会运行的链条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利己动机转化为了符合社会运转的推动力,对普遍性的需求成为了特殊性转化并实现自身的中介。黑格尔用他的分工思想去进一步阐述了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分工导致的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独立化反而推动了人们在生产领域的相互联系,在分工领域中,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实现了现实的辩证统一。
二、“抽象化的过程”:黑格尔对劳动的普遍性的思考
在《法哲学原理》第198节中,黑格尔指出:“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15]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作为黑格尔分工理论的一个理论中介,它连接了劳动与分工这两端,从一端看来,劳动这一行为通过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使得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推动了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另一端看来,分工的“生产的细致化”是根源于这个“抽象化的过程”,这个抽象化的过程催生了劳动的细致化与多样化。但是从这个逻辑链条的两端来看,又是蕴藏着矛盾的,“劳动中普遍和客观的东西”代表着劳动的普遍性,而“生产的细致化”则代表着劳动的特殊性,因为只有在考虑各种劳动之间的具体区别时,才会采用“细致化”这一思维过程。因此,如何理解这个“抽象化的过程”,就成了理解黑格尔劳动论题与他的分工理论的关键点。
(一)“抽象化的过程”与马克思“抽象劳动”的异同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认为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一方面是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则是抽象劳动,二者一体两面,具体劳动代表着商品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抽象劳动是形成商品的价值的劳动,是不同商品的劳动中蕴藏的“一般性”,那么黑格尔认为的劳动中的“抽象化的过程”,是不是就是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呢?
首先,假设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个“抽象化的过程”,与马克思所提出的“抽象劳动”这一范畴一致,都是将现实的劳动加以观念中的抽象。那么,马克思在讨论商品二因素时,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可以使不同种类的商品以某种量的关系或比例进行交换,是因为有某个“等同的东西”[16]存在,这个“等同的东西”必然是与使用价值无关的。商品之所以需要交换,是因为不同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其“等同的东西”必然不是商品的具体的有用性,那么将物的有用性抛开之后,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需要经过人类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不同的商品蕴含着不同种类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因而将这些工人所从事的劳动种类抽象掉之后,就可以发现真正的“等同的东西”是“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7]。马克思在发现交换价值这一范畴存在的基础是等同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之后,他探讨并发现了商品劳动二重性,也就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他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具体劳动,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也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形成了价值,商品价值体现的就是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
进一步说来,如果从商品的角度来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生产的细致化”,也就是不同劳动主体生产不同种类的商品,将劳动者细致化到不同种类商品的生产领域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被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的劳动是如何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呢?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应该源自于人类对于不同种类商品的多样化的需求,但是抽象劳动是将具体的劳动方式抽象掉后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它是同质的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是没有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的,对抽象劳动的追求不会推动“生产的细致化”。因此,黑格尔的“抽象化的过程”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范畴并不相关。
(二)以劳动“特殊性”的实现过程理解“抽象化的过程”
黑格尔认为,劳动的“特殊性”,也就是具体的个人的利益需求,在最初是偶然的、主观的,这个利益需求的满足也是偶然的,这种满足会引起新一轮的、无止境的新的欲望,因此这一“特殊性”的实现是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偶然性和任性的。但是具体的人是处于市民社会的人,他必然受到整个市民社会的普遍性的制约,他的主观需要能否实现,受到市民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制约,在这个需要被实现前,它是主观的、是仅仅存在于观念上的,这个需要能否实现从主观性到客观性的跨越,需要依赖于外在的事物。黑格尔认为,一方面,主观需要可以通过外在物作为中介来实现,这种外在物同时也是其他人“需要和意志的所有物和产品”;另一方面,人的主观需要可以通过活动与劳动来直接实现主观性到客观性的转化。可以发现,黑格尔对于人的主观需要的客观实现的分析,对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见解,黑格尔所理解的两种手段,也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两种情况:第一种途径是个体对物品的需求,通过与其他持有这种物品的需要的交换来实现,在交换前,这种商品属于“他者”,个体对该物品的主观需求需要经由“他者”来进行实现,如果这一需求是不考虑现实情况的、异想天开的需求,现实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无法使得个体的这一主观需求落到现实,这个需求就只是一个思维领域的存在,对现实社会没有影响。第二种途径则是发生在最直接的生产领域中,个体产生主观需要后,通过活动与劳动,将存在于自己观念中的需要落到现实,实现主观需要的客观化。但是这一过程的实现前提是现实的活动与劳动条件可以满足主观需要客观化的条件,如果主观需要过于天马行空、脱离现实条件,也是无法通过劳动落到现实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个人的需要的主观性、特殊性,在精神领域中是自由的、无限的,但是一旦这个个人想要他的主观需要得到满足,他就必须与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发生关系,主观需要也应该考虑现实世界的客观条件。
在这一基础上,黑格尔认为人与动物的需要都会受到某种“局限”,但是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越出这种限制,“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和“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18]使得人得以越出“局限”。可以发现,在黑格尔的观念中,解决这种限制的方法是将需要和满足手段细致化,即一方面将需求细致化、具体化,让庞大的、笼统的需求分化为更细致一级的需求,从而降低实现的难度;另一方面将满足手段多样化、细致化,在满足手段的分化中推动满足手段在各自领域解决各自问题的能力提升,从而越出“局限”。这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有着明显分歧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是人能动地改在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能动活动,不是消极地反映世界,而是在积极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
黑格尔进一步解释道:“为特异化了的需要服务的手段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也细分而繁复起来了,它们本身变成了相对的目的和抽象的需要。”[19]在黑格尔的精神路径中,个体的主观需要的细致化并非是一个基于具体区分(例如类似于商品学基于商品的自然属性、蕴含的具体劳动的区别来详细的区分商品)的原则去对主观需要进行的划分;相反,个体主观需要的细致化反而可以引起对“他者”的普遍性的依赖,在主观需要细致化发展之后,每个个体的个别需要都与其他个体的个别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需要”的整体,但从每个个体的视角看来,他与其他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制约也就更明显。可以发现,黑格尔认为,在“需要”这一整体细分与繁复之后,个体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更加明显且直观,每个个体的目的都变成了“相对的目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具体区分原则的细致划分而更加明显。相对于主观需求没有细致化划分之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如果在前一情况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是一种模糊的抽象,那么细致化过程之后关系是更高一层的抽象。
黑格尔从物质层面上的具体的细致化看到了社会关系层面上抽象的相互关系的明晰,并且在这基础上重新回到了社会上“他人”的普遍性上。他认为个体的主观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在细致化的过程后,这种更高一层的“抽象”使得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明确,“……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而他人,也就是整个市民社会层面的“普遍性”,则成为细致化的需求与手段的实现条件与实现中介,这个普遍性可以让观念上的、抽象的需求以及手段落到现实层面,成为具体的、社会的。黑格尔在他的书中着重标记了“社会的”一词,表明黑格尔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将观念的需求客观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对这个客观化的过程作经济学领域的具体考察与展开,只是指出了“其中介就是劳动”,马克思则使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去考察了这个过程,更进一步地研究了劳动、生产、实践等现实活动的重要性。
三、从“抽象化的过程”看马克思的“局部工人”形成过程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阐述了个人的特殊性与他人的普遍性的辩证运动过程,认为个人的观念上的需要依赖于他人的普遍性的条件去实现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化,并发现了劳动这一转化过程的中介。黑格尔指出,“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使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通过劳动,人们使得自身的需求得到客观化的实现,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存在得以确立。但同时,需要和生产的细致化过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逐渐细化,从而产生了分工,分工在一方面使得劳动技术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从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个细致化过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具体,人与人在社会层面上的相互依赖更加紧密,并逐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必然存在。这就蕴含了对分工的批判,使得黑格尔“劳动-分工”的思维路径与马克思“劳动-分工”的思维路径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同构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阐明了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假设下,分工与协作是如何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在这一篇中,马克思提出了“局部工人”的形成过程,指出了分工的细致化、固定化会使工人只从事某个片面的劳动技能,但是这种固化与僵化却恰恰给生产过程带来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是也压抑了劳动者。这与黑格尔所说的“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有着相近的含义。
在《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这一章中,马克思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体现了协作的一般原则和生产优势,而且发展了自己所特有的生产优势,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有两种形成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分——总”式的过程,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20]在这一形成过程前,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模糊的分工的,而资本家对于生产某种商品的需求与渴望,推动了这些工人聚集在一个工场中,资本家的这一行为使得这些工人之间的模糊的分工变成了在某个商品的生产链条中明确的分工,这种模糊的分工起初是源自于他们所从事的劳动种类的不同,是一种自然性质层面上的模糊的分工。而在资本家推动他们在同一个工厂为着同一个资本家生产某一种商品时,这种分工就成为了一种相对明晰的社会性质层面上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切实地源自于所从事的劳动种类在这一商品生产链条中的位置、顺序的不同。这种分工由“模糊”到“明确”的过程,与黑格尔所阐述的“抽象化的过程”是有着极高的相似性的。
工场手工业的第二种起源,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一类工作的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21],是一种“总——分”的形成过程,这些工人在被资本家雇用到同一个工厂前,是同种产品的手工业生产者,他们之间的“分工”更像是在同一商品的出售方中不同生产主体之间的分工,这一分工是源自于生产主体之间的个体差异,并不是源自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种类的相对独立性,如果以纯粹的使用价值为区分标准,那么这些生产者在被资本家统一雇用之前,基本是不存在“分工”的。他们的“细致化”过程是在资本家将他们雇用到同一个工场中去生产同一种商品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起初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制造这一种商品的流程,但是一些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更高要求的外部条件会推动这些生产者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他们集中在这个工场中的劳动,这个方式就是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开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切,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22]因此,对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推动着这些本身可以独立完成生产过程的劳动者逐步转变为只从事某个特定生产操作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与分工不再是产品间的分工,而是产品内环节的分工,是更细致化的分工。
因此,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把个人手工业劳动分成了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化和独立化到每一种操作都成为了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而这种专门职能在积年累月的劳动经验积累中不断完善并发展到极端,使从事不同操作的劳动者固化为了“局部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生产量也增加了”、“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也得以完成,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局部工人的劳动,那么某一环节的局部工人的劳动便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劳动意义在整个生产链的最终产品的生产之后才得到确证。社会分工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的同时,也推动了劳动的异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23],在“抽象化的过程”之前,个体的特殊性通过他者的普遍性进行中介,更是通过现实的活动与劳动来实现需要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化;在“抽象化的过程”之后,个体之间的需要通过细致化的过程逐步具体,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细致化的过程逐步紧密。[24]但是随着分工的细致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的抽象化与在工人身上的固定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转向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个体需要不再依托于他人的普遍性的中介来得以确立,而是依托于机器的运转。在这一发展阶段下,劳动者的劳动与其自身的真实需求的关联逐步减少,以前只是以他者为实现自身需要的工具与手段,现在这种对“工具与手段”的需求也逐渐消减,劳动者的劳动愈发在“抽象化的过程”中逐步抽象,劳动者不再关心自己劳动的形式与劳动的目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在形式上更具体了,但是在历史的维度看来却更为“抽象化”,更具体的劳动反而成为了“一般性的劳动”,因为这时劳动不再是劳动者确立自身、实现自己与他人的主观需要的中介,劳动已经外化为了不属于劳动者的存在,个人的特殊的劳动与自身的目标的实现不再存在显著关联,劳动的具体形式被事实上地忽视了,成为了“一般性的劳动”。
黑格尔认为无限多样化的手段,也就是在抽象化的过程中逐步细化的手段,依照内容的普遍性与共性而形成一个个特殊体系,形成了等级的差别[25]。事实上,在“局部工人”形成后,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者个人已经被固化在自己的劳动环节中,劳动者之间依托其劳动形式与劳动内容的不同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不同种类、不同环节中的工人;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中,劳动者个体的劳动技能不足以支撑其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不足以支撑自身的提升,因此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阶级关系中,劳动者随着“局部工人”的发展,丧失了自我提升阶级的能力,不仅仅是固化在了固定的劳动环节中,更是被固化在了资本家所设立的社会“等级”中。因此,分工的细致化与生产机器的不断发展,使得本身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确立自身的存在的“劳动”,成为了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存在,更是抑制了劳动者的自由发展;也使得作为生产工具帮助劳动者进行更高效率生产的工具,成为了消解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的联系的阻碍物,人与人之间不再直接通过活动与劳动相关联,而是人与机器相联结,机器在生产过程的发展中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者逐步沦为机器的附庸。
四、结语
在《法哲学原理》与《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哲学的视角对劳动进行了讨论与界定,认为劳动是个人对于自身目标的客观化所采取的活动,是人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中介过程,他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劳动的认识,实现了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在黑格尔的劳动观的基础上,构架了他的劳动观,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展开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论》中以具体劳动的细化——分工为切入点,阐述了与黑格尔“抽象化的过程”具有同构性的“局部工人”的形成过程,发现了劳动者在分工与协作的过程中,不断确证自身的存在,但却最终被机器所束缚的历史现实。黑格尔尽管也发现了这一“机器代替人”的历史进程,但是并未深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的研究与批判,只是停留在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看法中,没有达到对对立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参 考 文 献〕
[1]彭咏思.马克思劳动观及其时代价值简析[J].今古文创,2022(44):56-5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5.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6.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4.
[5]杨建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兼论实践、生产和劳动概念的关系[J].人文杂志,2006(03):21-27.
[6]王金林.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之重构[J].哲学研究,2017(04):3-11+128.
[7]孟祥林.从异化劳动到实践自由:劳动自由得以可能的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02):44-52.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7.
[9]詹世友.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之奥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146-158+198.
[10]周凡,曹江川.论卢卡奇对青年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04):86-92.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7.
[12]吴鹏.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困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03):13-19.
[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8.
[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9.
[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0.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1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5.
[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7.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0.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1.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2.
[2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0.
[24]夏雪.马克思哲学中“劳动”概念之新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02):21-28.
[2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2.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