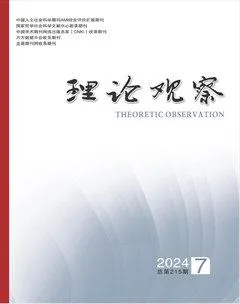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对欧盟外交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欧盟关系有发展、有成果,也有跌宕起伏。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百年大变局准确地定位了当前与欧盟外交的时代框架,是对中欧关系的基本认知和对欧盟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中欧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外交战略中为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国际关系的转型创造了空间和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欧盟区域治理理论的创造性超越,借用了欧盟内部的地缘政治差异性,是中国参与和融入欧洲经济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欧盟;百年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7 — 0011 — 07
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世界多极关系中的一极。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条重要方针,即指出我们要放眼全局,把握在外交关系中的时代定位,这就是“大变局的世界和新时代的中国”[1]。
从国际局势的发展态势而言,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中欧关系的地位处于上升势头,相对于始终居于核心地位的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因为时代的各种变局与多边主义的工具性价值,虽然欧盟的经济与军事地位呈下落走势,但是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有增无减。“2021年双方贸易和投资合作逆势上扬,货物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双向投资稳中有升,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展现了双边经贸关系足够的韧性和强大动力。”[2]在本文中,我们拟从三个维度(百年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习近平的外交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阐明在新时代下,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中国与欧盟外交的思想指导与实践意义。百年大变局是时代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构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习近平外交路线的时代践行。
一、百年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时代发展和国际趋势的变化高瞻远瞩,科学把握历史大势的走向,准确理解历史局部的动荡与波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世界体系变革转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担当与使命意识。
(一)以战略的坚定性应对动荡的世界局势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到当今国际局势的风云多变与中国再一次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历史性机遇。2022年,在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视频会议期间,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尚在全球蔓延不去,世界经济复苏遭遇许多困难和阻碍,乌克兰危机持续发展,还未到拨云见日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欧盟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应该就中欧关系和事关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一些稳定因素。”[3]
习近平对于中欧关系的定位旗帜鲜明,一以贯之。习近平在2013年会晤时任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就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中欧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4]习近平同时表示,中国和欧洲应当增进互信,发挥各自的作用,一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路线与方针的稳定性和恒久性体现了大国领导人的定力与常态,彰显了中国外交的风范。坚持对欧盟外交的一贯性与连续性符合中国和欧盟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贡献与政策基础,也是维护和平与发展国际局势的基石之一。
习近平对欧盟外交的一贯性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权力机制结构性变化之时,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在同一时期,欧盟的对华政策则举棋不定。竞争与合作因素增多,在深化务实合作的同时,与经贸往来相背离的是欧盟对华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知心理,直至在2019年将中国视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即使如此,欧盟内部各成员国远未达成对华政策共识,对华战略定位各怀己见。
正是在秩序之变的形势下,习近平对于双方关系压舱石的坚守才能体现出领袖意识、政治智慧与历史担当。正是在秩序之变的形势下,习近平的一以贯之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我党不会作辍无常,我国不会出尔反尔。我们对欧盟的政策稳定连贯,对待国际形势有着自主的认知,有着自主的政策,不会被某个大国裹挟,不会被某个变局所左右。策略的灵活性是建立在战略的坚定性基础之上,习近平的领袖风范与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外交立场将为中国赢得信任与赞誉。党的二十大之后德国新任总理的迅速访华即为明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并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内政,还是影响人类社会未来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中国开放的脚步只会向前,不会后退。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就会“为我们深刻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科学制定外交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5]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中国对欧盟外交实践的关系?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习近平对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本质性变化的清醒认识,第二是习近平对于欧盟的被动应对与变态应激反应的准确预判。
习近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的各代领导集体相继取得的巨大成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202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国力的高速增长,中国与欧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与国力增强这一生产资料现象相叠加的是在上层建筑衍生的重要现象,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新时代的竞合关系,刘海霞认为,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东方大地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这一点已经完全超越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7]
今天的欧洲中心主义早已不再仅限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其核心价值观仍然是被认为源起于欧洲大陆。欧盟以西欧阵营为核心,西欧是资本主义的策源地,是资产阶级的诞生地所在,资本主义的这一概念即是由西方学界在对欧洲历史与社会进行研究时所提出的——“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还是宋代近世说都是在借鉴了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8]西欧也是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与优越性最早得以显现与辐射世界的地域所在。相比较于美国,欧盟更加秉承资本主义历史和传统的重压,所谓“自由民主”的理念诞生于西欧大陆,“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普遍热望,抑或他们早先的自信只不过是自己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9]。相比较于美国的经济全球霸权地位,欧盟更引以为自傲,或者说惟一还能引以为自傲的是他们固守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欧盟的经济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也许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峙,是两种文明的对峙,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能被视为威胁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巨头西门子集团从1872起即投资中国,在中国拥有超过35000名雇员,中国占据其世界市场份额的十分之一。虽然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加持,西门子总裁约瑟夫·凯瑟(Josef Kaeser)居然在2020年9月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指责我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治理方式。[10]
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在本质上是美国恐惧失去世界领导权的反应。“美国的对外政策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非像其所声称的那样,在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多元化等价值观”[11]。欧盟的政策考虑当然也脱离不了经济与军事因素的权衡,不过,欧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性的崛起更具有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事实上,以中国对于欧盟的经济威胁而论,从实量分析,远远不及非法移民或是难民给予欧盟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尤其是其在应对国际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卓越表现,给欧洲文化与制度自身带来不安全感。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对欧盟外交实践中为外交战线揭示了一种“新视角”。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地缘政治思想的藩篱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国与国之间融合差异的解决思路与指导外交实践的有效原则,共同体思想适合于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松散的情况,适合于不存在缔结盟约关系或是固定合作关系的国家或是组织之间。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与欧盟存在竞合关系的大国,以俄罗斯对欧盟的外交思想为例,能够映照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与智慧。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做出了“欧洲选择”,试图推行“大欧洲”构想,与欧洲融为一体,将“ 融入欧洲”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虽然俄罗斯对“ 回归欧洲” 充满渴望, 也付出了努力,但总体来看,“欧洲选择” 是失败的, 在事关俄罗斯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欧盟并没有与俄罗斯相向而行,俄罗斯也未能实现“ 融入欧洲” 的目标。[13]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情况更是不可收拾,俄罗斯基本上走上同欧盟的彻底决裂之路。俄罗斯的失败在于俄罗斯的“大欧洲”或是“大欧亚”蓝图都是建立在从地缘政治思想出发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欧洲—大西洋主义还是新欧亚主义,它们都无法规避横亘在俄罗斯与欧洲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欧洲自诩为民主文明,将俄罗斯看作具有侵略性的专制政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构建地缘战略共同体,它超越了一切地缘经济问题的框架,摒弃了文化地理和地缘政治经济的藩篱。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向的是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人类共同体面向的国际社会是全球社会,不受地理的局限,“坚持从具有高度正当性、与时俱进的公认价值出发,而非从特定国家的私利或特定国家群体的狭隘观念出发。”[14]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然消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示出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力量,蕴含导向普遍主义的理论潜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定位始终是朝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是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迎合与单向奔赴。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自然而然的消解。酷儿理论、后殖民以及“去殖民性”等概念或是发自于西方文化的内部,或是来自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它们对于欧洲文明的反抗实践,第一是往往用力过猛,流于痕迹;第二是始终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其效应和后果与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悖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化底蕴根植于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深厚土壤,来源于完全独立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宏大思维体系就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可能倾向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为对立面与威胁,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对手和敌人。命运共同体是自律一大一统,是整体思维,不是均势和对峙,不是欧洲二元论的对立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国思想为关照,但是又立足世界与当下的实际情况与现实关切,解决的是全球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和挑战。
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权观为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对于欧洲狭隘人权观的直接回击:人权观成为欧洲国家指责其他文明国家的借口,或者滥用人权标准,将从人权标准发展生成的人道主义理由作为干涉主权国家的正当性依据。与后殖民等西方的理论不同,命运共同体思想不致力于批判,而是直接自我构建其宏大体系,“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15]影响和改变国际社会的知识结构与认知判断,强调“人在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关系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因此,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会主动关照他人权利,甚至首先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而无需借助人权与法律”[16]。习近平外交思想用人类的集体命运与开放诉求自然而然地取代个人主义的封闭世界观,从而以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国际法框架内的观念、制度与地缘政治思想,悄无声息地化解欧洲中心主义的强权政治观。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成与欧洲文明部分组成元素的和解
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五年之后,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出乎国际社会意料地宣布了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的计划,重新给予了巴黎气候协定以巨大的推动力,这是对气候怀疑论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重重一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17]也赢得了欧盟的掌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面对人类共同挑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传承,也有着丰富的学理支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直接的关联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因此,气候变化这一威胁全人类福祉和未来的全球现象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8]在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保护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绿水青山是习近平总书记萦绕于心的追求。这里涉及到一个需要指出的客观事实,那就是生态保护理念的发展首先是在西方得以蓬勃和壮大的,这其中当然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樊志光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西方各自朝着自己的既定方向发展[19]。生态主义本身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反拨和批判,逐渐被资本主义制度接受和吸纳,结果成为西方率先引领的思潮与社会运动,最后落实到制度和法律层面。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欧洲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背道而驰,欧洲成为坚持气候保护的西方主要力量。生态保护发展成为欧洲文明的组成元素之一。
由上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其内在元素上存在与欧洲文明组成元素部分的和解。这种和解并非是中国理念对于欧洲的迎合,它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关联性、包容性、和合性与整体性[20],是中国在价值观、规则观和行动观上的集中表现。习近平的生态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拨乱反正,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某些受到西方道路影响的地方进行纠偏。福斯特指出,全球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这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具有逐利性,市场经济会追求无限制的指数式扩张。[21]习近平的生态思想是与欧洲文明组成元素部分的和解,但是习近平生态思想的来源并非欧洲文明,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张乾元指出,习近平生态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发展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道法自然”的实践观[22]。因此,命运共同体概念在其内在元素上与欧洲文明组成元素部分的和解只是表象,透过现象,本质并不一致。这也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君子和而不同。
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方案。截至2022年7月,在欧洲有27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文件[23]。
(一)“一带一路”借用了欧盟内部的地缘政治差异性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开放[24]。张骥、陈志敏在2015年的文章中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对接的问题,提到了在中欧对接中双重欧盟的视角,认为基于权能和利益的差异, 欧盟层面和各个成员国在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具有各自的兴趣点,也需要中欧之间不断磨合, 针对不同对接对象确定差异化的合作重点。[25]如果说在2015年,欧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仍然是持谨慎欢迎态度,中国和欧盟处于试探期和合作期;在之后,尤其是2021年之后,双层对接渐趋脱节,上层的对接已经接近于脱轨。吴昊、杨成玉指出,2021年12月,欧盟发布“全球门户战略”,通过强调价值观引领、推广欧式规则标准、挤占全球海外融资资源、突出地缘对抗等外溢效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排他性政治条件、设置高标准壁垒、加大海外融资难度、稀释国际影响力等潜在影响。[26]如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讲话所说,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27]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同欧盟理事会主席会晤时,欢迎欧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能同欧盟“全球门户”战略有机对接。欧方并未直接回应。[28]“一带一路”与欧盟的双层对接以理论性的方式存在,在实践中,上层对接目前处于阻滞状态。在中国与欧盟的共赢互通中,单层对接和基层对接更为容易落实与发挥影响力。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在2013年提出,中欧班列开通,“连点成线”“织线成网”,将“朋友圈”做大做广,目前,班列连通抵达欧洲的24个国家与200个城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成果,展现了“一带一路”的蓬勃活力。[29]作为一个整体,随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入拓展与实践,在初期,欧盟尝试建立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关系。在此背景下,欧盟成员国在理论上可以都被归入“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欧盟内部结构复杂,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理念、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明显,呈现出一些不可调和的歧异,“一带一路”计划在客观上发挥了分化功能,放大了欧盟内部的结构性与功能性差异。
最早响应并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是中东欧国家。2014年6月,根据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促进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表述, 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根据各自国家法律法规,欧盟成员国并根据欧盟相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加强经贸对话,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30]。2016年夏,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希腊三国即在南海问题上与欧盟持不同立场。2017年,马耳他、葡萄牙、捷克、希腊和瑞典反对欧盟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措施的提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国家和中国保持密切的投资关系。同年,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希腊在联合国却再次和欧盟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相左。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瑞典之外,全都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协议。在瑞典,则有学者积极推动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22年6月,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即应邀出席瑞典“一带一路”执行小组举办的“‘一带一路’是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之路”的视频研讨会。[31]
综上可知,“一带一路”属于经贸与文化发展的倡议,不是区域性国际经济或是文化组织,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又带有组织的某些特性:参与国之间是在发展地缘睦邻关系,在彼此之间具有文化上的联系,有共同关心的经济利益。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而言,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不可避免地会与地区性经济和政治组织的一体性与统一对外的法律机制有相互抵触之处。中东欧国家不属于欧盟的核心构成,是欧盟逐渐东扩后的新成员。中东欧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入,既有离心作用,引起欧盟权能机关的警惕和防范心理,同时,又具有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了一批欧盟核心国家向“一带一路”倡议的靠拢。“一带一路”对于欧盟的作用,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以离心作用为主,后续期待发挥带动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国际关系中区域治理理论的创造性超越与发展
区域合作组织是冷战结束之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家间合作通用模式。加里·戈茨的统计数据显示,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国家都加入了一个到几个不等的区域组织。[32]欧盟的架构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组织之一,其治理经验甚至构成区域治理最为主要的参考源与参照体系。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智慧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与文化的逻辑衍生和现代转化。比较“一带一路”与区域治理理论中的欧盟架构,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是超越区域治理范式的合作与交流方式,这种超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在组织结构上的超越
框架结构是由不同的区域组织或是区域机构构成,是交汇多重权力的治理机构。区域治理是内嵌于区域框架结构的概念。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33]习近平提出的思路高屋建瓴,是对区域组织框架结构的超越与创造性发展。
以2017年成立的“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为例,这是一个非营利性合作组织,由中国与波兰23所高校共同参与组建。“一带一路”大学联盟的参与形式以协作意愿为衡量指标,虽然有加入机制,但是并无管理机制,并不根据既定目标制定各种入场资格条件。在大学联盟中,有沟通机制,顶层制度供给抽象化[34]。非政治性与区域治理概念的淡出,这是“一带一路”与区域组织框架的根本区别。
2.对于区域性经贸协定的回应与超越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中国与欧盟国家的经贸与文化往来有可能受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区域协定的限制与掣肘。该协定超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试图打造内部高度自由化的经贸堡垒,对中国这一巨大经济体制造市场准入屏障。由于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暂时无法以符合西方尺度的严苛标准互惠开放本国市场,美国策划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排他性地将中国排除在外,旨在削弱中国经济对于欧盟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的倡议本身并不是针对欧盟的具体情况而提出,但是,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在实践上是对于TTIP挑战的有力回应。“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伙伴关系。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洲时指出,中国与德国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个端点,是亚洲与欧洲两大经济体的增长极。之后,《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展望了中欧自贸协定的签订前景。
无论是TTIP,还是中欧自贸协定,时至今日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一带一路”倡议的旺盛生命力远远超过这些区域性协定,在中欧合作中已经有了落地的项目,十年来,中欧班列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铁路运输网络布局和更加便捷的连接,随着中欧班列服务的逐步正常化,中欧班列运输的载货量、运力和频率都呈快速增长态势。[35]
3.对于区域组织地理局限性的超越
在与欧盟外交实践中,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创造性在于它超越了欧盟这一发展相对完善区域组织的自我封闭性。欧盟是在欧洲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中被建构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它是在欧洲大陆上生成的物质空间,是有着共识政治的历史与愿景的特定人群生产与生活实践的构造物,终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积累过程中成就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区域世界。
中国与欧盟并不接壤,因为不在同一地区,可以被认为是地理距离上远离。“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布局上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发散性的贸易与文化网络。网络的扩展与延伸方式是以点带面,由线成片,借力打力,通过贸易网络中各种“凝聚子群”的制造,由此而渗透进欧盟国家内部。
四、结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36]内容丰富精深,中共中央编发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包括了十二个要点。本文选取了三个维度,因为这是三个与中国对欧盟外交联系相对紧密的维度。百年大变局准确地定位了当前与欧盟外交的时代框架,是对中欧关系的基本认知和对欧盟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中欧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外交战略中为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国际关系的转型创造了空间和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欧盟区域治理理论的创造性超越,借用了欧盟内部的地缘政治差异性,是中国参与和融入欧洲经济的有效方式。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欧盟关系有发展、有成果,也有跌宕起伏,起伏来自于时代的大变局,是欧盟与中国实力此消彼长所带来的必然影响。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合作者、战略竞争者和制度对手[3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38]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谋划和建构之下,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在后疫情时代预计从低谷期逐渐步入转圜期,德国总理舒尔茨在2022年访华。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2023年年内访华。可以预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对中欧冲突逻辑和结构性矛盾的清醒认识之下,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将会行稳致远,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1: 11.
[2]金玲. 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2(04): 51.
[3]习近平.中欧应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稳定因素 [EB/OL].光明网, (2022-4-1),https://m.gmw.cn/baijia/2022-04/01/35630511.html,2024-07-28.
[4]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3-11-20),http://www.gov.cn/ldhd/2013-11/20/content_2531441.htm,2024-07-28.
[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1: 15.
[6]刘海霞.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种制度竞争合作的新态势[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04): 37-50.
[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3-64.
[8]刘光临. 回归传统:历史学视野中的资本主义[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1): 14.
[9]〔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
[10]Thomas Wieder, Cécile Boutelet, De《 partenaire》 à《concurrent systémique》 : l’Allemagne gagnée par la méfiance envers la Chine(2020-09-14),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20/09/14/de-partenaire-a-concurrent-systemique-l-allemagne-gagnee-par-la-mefiance-envers-la-chine_6052055_3210.html, 2022-11-23.
[11]肖恩·莱德维特,张文成. 认识中美冲突的另一个视角——评《美中博弈:亚洲的新冷战》[J]. 国外理论动态, 2021(02): 167.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10-25),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
21685.htm,2022-11-23.
[13]吕萍. 俄罗斯的“欧洲选择”分析[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1(06): 59-80.
[14]方炯升. 真正的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J]. 东岳论丛, 2022(10): 25.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424.
[16]茹宁.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示与价值——基于张载“和”思想体系的分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5): 182.
[17]Frédéric Schaeffer, Climat : cinq ans après, la Chine redonne du souffle à l'Accord de Paris(2020-10-10), https://www.lesechos.fr/monde/enjeux-internationaux/climat-cinq-ans-apres-la-chine-redonne-du-souffle-a-laccord-de-paris-1272778,2022-11-23.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355.
[19]樊至光. 与生态保护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987(04): 7-11.
[20]邢丽菊. 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03): 98-110.
[2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破坏[J]. 董金玉,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8(06): 53-57.
[22]张乾元,冯红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1-6.
[23]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EB/OL].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08-15), 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122
&info_id=77298&tm_id=126.
[2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106.
[25]张骥,陈志敏.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1): 36-52.
[26]吴昊,杨成玉. 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05): 58-77.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496.
[28]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举行会谈[EB/OL].光明网(2022-12-01),https://m.gmw.cn/baijia/2022-12/01/36202983.html,2022-12-09.
[29]叶子.中欧班列见证“一带一路”蓬勃活力(望海楼)(2022-08-11)[EB/OL].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811/c1002-32500166.htm,2022-12-04.
[30]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共同文件[EB/OL].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网站(2014-06-09),http://www.cgcpa.org.cn/xxly/2014-10-20/5387.html, 2022-12-06 .
[31]外交部ym7iO5LBzmZGitKDS3SWVm0NKowKnFdfLR46dqLbqG0=.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出席瑞“‘一带一路’是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之路”视频研讨会 (2022-06-29),https://www.fmprc.gov.cn/zwbd_673032
/gzhd_673042/202206/t20220629_10711441.shtml,2022-12-09.
[32]Gary Coertz and Kathy Powers. “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of a New Institutional Form”[J]. WZB Discussion Paper, no. SP IV 2014-106, 2014.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493.
[34]朱以财,刘志民. “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运行何以长效——基于组织学视角的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22(12): 26-34.
[35]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EB/OL].光明国际(2022-12-16),https://world.gmw.cn/2022-12/16/content_36239591.htms=gmwreco2,
2022-12-18 .
[36]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1.
[37]Mathieu Duchatel. La Chine et la Commission von der Leyen : une Europe sur la défensive(2019-12-03),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analyses/la-chine-et-la-commission-von-der-leyen-une-europe-sur-la-defensive, 2022-11-23.
[38]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9(05): 19.
〔责任编辑:秋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