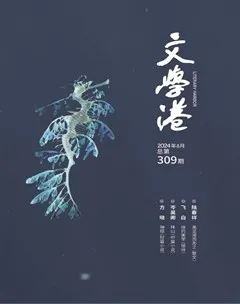旧物册页
铜墨盒
历史学家邓之诚认为墨盒“大约始于嘉、道之际”,这是学界通常的看法,但南京明代海国公吴祯墓葬中出土过一件墨盒,使墨盒的起源变得扑朔迷离,有学者认为吴祯墓中的并非墨盒,而是盛放描眉染用具的盒子——黛盝,我在前人所绘的《张敞画眉图》中就看见过“黛盝”, 吴祯与张敞一样同为“宠妻狂人”,并非没有可能。
墨盒多为铜制,以红铜、白铜为贵,有的墨盒看上去银光闪闪,宛如白铜,其实只是采用了镀铬工艺。墨盒由盒盖和底盒组成,盒盖内侧有个压条固定着的砚板,底盒可放丝绵。出去雅集的时候,可以带个墨条,兑些水,对着盒盖内的砚板磨上几下,墨汁就有了。还嫌麻烦的,就把研好的墨汁倒在底盒的丝绵中,随取随用。无论哪样,都便于携带。
铜墨盒里有一种叫靴盒,不太明白的人听上去还以为是放靴子的器物,类似今天的鞋盒,想到我有一位实现财富自由的朋友,他对穿衣不太讲究,倒是热衷于藏鞋穿鞋,他的客厅里有一面由数百个透明亚克力鞋盒组合的“鞋墙”,他每天从盒子里选鞋穿,天天不同样。
靴盒放在靴子里的“靴掖”中,靴掖之名因藏掖在靴筒里而得,它是一种存放名帖、银票、收据等物件的小荷包,为了防止靴盒硌腿,靴盒就要设计得精致小巧,一般也就一元硬币大小。我看过一只靴盒上面刻了十多只蚂蚱,连后肢上的倒刺都清晰可辨,这种微雕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晚清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位书法家叫张逸君,史料说他性格疏放,不拘小节,常靴插毛笔,手持竹杖行走于街市,喜欢饮酒和泡澡,兴致上来时,对索字者现场挥毫赠送。我细致推敲,认为他的靴子里十有八九是藏有一只靴盒的,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墨汁提供。
在铜墨盒的盒盖上能领略文士风流,他们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刻在上面,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张樾臣、姚茫父、陈寅生的墨盒,署款这三个名头的墨盒不计其数,但十有八九是新仿和“老冲头”,我认识的藏友手头有一方姚茫父之子姚鉴旧藏的白铜墨盒,主图为一山石,上下有竹叶和菊花点缀,左侧落款为“花竹秀而野 茫父写”,他单把墨盒的拓片拿网上拍卖,就卖了千余元,这种传承有序的真品可求不可得。
铜墨盒在以前不仅被文人自用,还被用来作为礼物馈赠亲朋,如鲁迅就送过墨盒给弟弟建人、小友阎秉初。现在的墨盒几乎没人再用了,无论是练字的小学生,还是有名的书画家,大家拿毛笔写字画画时,都习惯用现成的瓶装墨汁,倘若要是拿墨汁送人,会让人感到小气,最少再搭上个上好的端砚或一刀红星的宣纸,这样才会把面子撑足。
铜墨盒在收藏品当中,不算热门,但遇到合适的墨盒,哪怕价格贵一些,我也要买来收藏,怎么说,喜欢都是无价的!
粥罐
以前老百姓家中,少不了粥罐,听这名字易误解为是放粥的餐具,其实粥罐是用来放糖果糕点、花生瓜子等零食的。我们这边把“粥罐”称作“搪缸”,我幼年识字那会,常写作“糖缸”,因为印象里,祖母常从粥罐里面掏出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给我吃。
粥罐起源于明,但存留下来的粥罐以清代、民国货居多。粥罐为圆形大肚形状,罐身为青花、粉彩、墨彩、刻瓷一类的图案,周边有四个系孔,上置一圆盖,盖顶有钮,常见的为狮子钮、寿桃钮,其中寿桃钮又名蜘桃钮,因为看上去又像一只蜘蛛趴在上面,我想这可能是当时的匠人有意为之。狮子、寿桃、蜘蛛均是民间的瑞物。
就粥罐自身而言,也有好寓意,其谐音“做官”,故旧时民间需求量大。做官为尊,是国人不朽的情结,旧时所谓“志在书中”,说到底就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谋得一官半职,从而凌驾于他人之上,继而富贵发达、光宗耀祖。但做官历来是高危职业,我所知道的一位处级干部,在下属被查后,他夜不能寐,每日早上四五点就赶到办公室,惶恐一阵后,最终还是难逃查处,此君在任上时,相信风水,把单位东墙开一门,放“紫气”进来,保自己青云直上。由此说,不是砸了东墙就有“紫气”,不是放了粥罐就能做官。
和多数陈设瓷一样,粥罐讲究一对,民间不仅讲究“好事成双”,好物也要成双,一对粥罐的价值远超两只不同样的单只粥罐。这和椅子又略有不同,椅子是两张为对,四张为堂,八张为厅,现在存留下的一“厅”的老椅子极难看到,很上价。
粥罐的盖子易破碎,所以留下来的很多老粥罐都是缺盖的,因不完整价值也就低了。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喜欢买来种蒲草、养金鱼、装茶叶,放在台案上,自能滋生出一种雅气。小说家张恨水客居重庆期间,居住环境不佳,房屋漏雨,下雨前夕,他们一家人就预先将盆盆罐罐搬到屋漏之处,恨水先生故给房屋起了一个“待漏斋”的雅号。我以为,这盆罐之中,会有一只粥罐,随着雨水“嘀嗒、嘀嗒”落入罐中,恨水先生的脑海中会产生一个新的灵感。
本地“尚文斋”的博古架上摆了十多个粥罐,标价不菲。我知道其中一只粉彩桃花仕女粥罐没有本钱,是店主罗二“赢”来的。三年前,一“地皮客”和罗二喝酒,喝着喝着,两人打起赌来,“地皮客”把多瓶“牛栏山”酒倒入刚“铲”的粥罐里,说罗二把里面的酒喝光,就把粥罐送给他,喝不掉,就要花五倍的市价把粥罐买走。罗二毫无惧色,捧起粥罐,仰起头,“咕噜咕噜”一饮而尽,一旁的“地皮客”瞠目结舌,只得把粥罐拱手相送。
闲话印章
印章并不是文人才有,像我父母同属工人阶级,早年发工资时,他们都要在工资表上盖姓名章,确认后,会计会递上纸票及钢镚若干,同时还附有一细长的纸条,上面是蓝色圆珠笔填写的薪资明细,字迹很小,视力欠佳者往往要凑到眼前细细地看。
父母的印章都是有机玻璃的,上面还有风景花鸟一类的图案,常年挂在钥匙扣上。我还见过戒面为姓名章的铜戒指,戴在手上更不易遗失了。当时发工资、取汇款、打借条都要盖印章,若是没印章,按个指印也算数,我父亲工厂有一位不识字的老季就是这么取工资的。
有一年笔会,我看到书画家老贾忘带印章,他就直接在画款后按了个指印。国画没印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有的书画家会直接画印章,上海的谢之光、江苏的孙龙父都擅长此道,所画的印和盖的印区别不大。有书画家甚至会用指纹作画,如大画家溥心畬,他喜在宣纸上按下指印,周边施加点缀,组成草虫、翎毛、走兽。我看他所绘牧牛图,以指印组成牛身,毛茸茸的颇具质感,这样的作品无从作伪。
印章和书画一样,讲究名头,要是治印者有名,用印者有名,印章料子雕工又好,那印章就贵了。今年我在旧货摊上购得一对黄寿山石印章,雕薄意山水,卖家不识边款,我一看,知是“戴发”,其人为民国东台篆刻名家,曾供职于中央印铸局,常凯申六十生日时,戴发曾钤“百寿图”印屏为之祝寿,获常凯申亲书“篆刻精雅”书法回赠,不料后来戴发因此事遭害,未得善终,故存世作品极少。这对印章,因有这等“捡漏”经历而更值得把玩。
印章中的闲章比姓名章贵,这是因为闲章买来还可使用,他人的姓名章买来总不能盖到自己作品或藏书上,但有年份的名书画家字号章是有人买的,我认识的古玩贩子黄三不但经常买,还自己买来印谱找人仿制,他做这么多印章全是用来造假书画。这个行当虽有暴利,但不建议沾手,前几年,南京有几位专仿林老散之书法的高手接连西去,坊间说法是,林老命硬,能克死作伪者。
史上最喜欢盖章的皇帝是清代的乾隆,他的印章据统计至少有500余方,很多重量级书画作品上都有他的印迹,而且都是一连串的,由此可见这位帝王对宝物有着多么的痴迷。乾隆过世后以大量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陪葬,然最终还是陵墓被盗,尸体身首异处,陪葬物散失四方。乾隆自号“十全老人”,结合他身后之事来看,是多么的讽刺!
倒是吾乡的前辈藏书家戈秉直的印章让我印象深刻,他在藏书上通常只盖两三枚印,其中有一常见的印文为“留与千秋万目看”,这使我想到徐悲鸿的一枚藏画印,刻有“暂属悲鸿”四字,这两枚印章都显溢出一种洒脱!任何珍品都是过眼云烟,是留给后世的遗产,纵然向天再借五百年,也不会永远拥有!
笔山
昔年常州文物商店搞促销活动,我和老范驱车前往,瞧了半天,发觉所售之物折后价格依然坚挺,最后我只买了一件价格还算适中的清代洒蓝釉笔山,前几日,家人打扫时不慎将之碰落到地板上,幸运的是整体无碍,只是底侧磕掉了西瓜子大小的一块。
笔山又有笔搁、笔架之名,它的造型或如“山”字,或如山峰状。旧时文人的书桌上、县衙的公案上,账房先生的办公桌上,都少不得此物,书写暂停时,将毛笔搁在笔山的凹处,使墨汁不会污染它物。放置毛笔的文房用品还有笔架、笔床,笔架宛如袖珍衣架,横梁上有多个凸出的细棍,用好的毛笔洗净擦拭后,将笔杆顶侧的绳子挂在细棍上。笔床为长方形,上有排列的圆槽,毛笔可放卧其上,但其行世较少,偏为冷门。
案头的笔山,显现了古人对山的崇拜,“仁者乐山”一语并非空穴来风,封建帝王在山岳举行祭祀大典,官绅人士在庭院中堆砌假山,寒酸秀才置办山水盆景放在案头,隐逸的高士干脆搬到山中定居了。纵然阶层不同,然对山的情感却一贯热忱。在正史野史皆享有大名的才子祝允明,右手生有六指,他将之比喻为山,因号枝山,这个名号显然比他的本名更为响亮。
早期笔山造型丰富,接近现实形象,多者有十余座山峰组成,故可摆放多支毛笔。有部分笔山为木、石材质随型笔山,其是天然生成,造型胜于人工造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未是为迎合人类,却契合了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想到我手头藏有一石,为当年游历新疆时,在喀纳斯湖畔所捡,上有白纹,极似奔跑的角鹿,把它放到郁郁葱葱的蒲草丛中,似乎有李白“林深时见鹿”的诗境。
有笔山,还有笔冢。南朝智永和尚、唐代书家怀素都曾将用坏的毛笔埋于地下,号称“笔冢”,这些废弃之笔,想来也是堆积如山的,称作笔山,亦不过也。笔山埋葬于地,被泥土侵蚀、腐化,直至消失。而积累在心中的丘壑却渐渐高大起来,成了一座座不朽的高山。
曾在拍卖会见到苏州大画家吴待秋旧藏珍珠灵璧石笔山,色如乌漆,声如磬玉,名家的加持,让珍品更显珍贵,故以高价落槌。记得藏友老姚手头有一件吴待秋的行书手札,这两件吴氏之物虽在旧时光里打过照面,如今却只能天各一方了。
油纸伞
戴望舒的《雨巷》是一条很美妙的巷子,行走其中的丁香姑娘,虽无清晰的模样,却让人着迷。她手中的油纸伞,是我关注的另一个焦点,看到它,我会想到卤菜摊,多年前,逢到雨天,本地的卤菜摊都会支起一把油纸伞,悠长的卤香味无数次穿透雨帘,传入我的鼻息当中。
卤菜摊的油纸伞,比丁香姑娘的油纸伞要大很多,壮汉撑起它也要颇费力气,其伞柄取自杯口粗的毛竹,安插在设有圆孔槽的基座上。在伞下抬头仰望,是一片黄褐色,因色彩,我常想到了“皇天后土”这个成语,每个人都在皇天后土之间为生活努力奔跑,我们继承了祖先夸父的优秀基因,不断地在追逐心中的太阳。
油纸伞以竹为骨,油纸为面。油纸之“油”为桐油,桐树果压榨出的油汁,刷到皮纸上,成了具有防水功能的“油纸”。以往卤菜摊上不仅有油纸伞,还有摊主裁好的若干方方正正的油纸,这是专门用来包猪头肉、酱牛肉等卤味的包装纸,卤味的油脂浸润着油纸,油纸上映出了斑斑点点的油渍,馋嘴的孩子,最终还要把油纸来回舔上几遍。
许是生不逢时或生不逢地,我没有邂逅过撑着油纸伞的女子,就是撑着油纸伞的男子也很少见过。本地的居民,雨天多用黑布伞,雨季,于高处观望菜市场,黑压压的一片,使得原本阴沉的天气变得更为黯淡,但嘈杂声依旧,水产、蔬果、肉品混杂的气息未减半分,买卖双方的心情一直没有受天气影响,人间的烟火是雨水浇不灭的。
在江南,菜市场定然也有这样的场景,只不过是以油纸伞取代了黑布伞,风雅之地,绝对有风雅的日子。有一年雪天,我行走在杭州的西子湖畔,走至断桥处,我想到了白素贞和许仙,民间故事里的许仙,撑着油纸伞,在江南邂逅了爱情,人蛇虽殊途,但在油纸伞下,有情者终成眷属。
文艺作品中的油纸伞,可以风花雪月,也可以激情澎湃。刘春华所绘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上,天空中乌云翻滚,青年毛泽东身穿长衫,左手拳头紧握,右手挟着油纸伞,意志坚定地行走在山路上。泛红的油纸伞,像一个燃烧着的熊熊火炬,即将点燃革命的火种。
在尼龙布折叠伞横行的现在,我怀念起油纸伞,还特意去网上买了一把手工油纸伞搁家里,想趁下雨时派上用场,但好几次都没想到,所用的还是折叠伞,看来,我已不由自主地受现代生活所摆布了。
紫砂壶
我办公时所用的是紫砂杯,此杯淘自旧货市场,买时还包着牛皮纸,可见库存未使用。杯身上刻有“泰建公司成立卅周年纪念”,当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订制物。杯子购价大几十元,和新紫砂杯价格相仿,但重要的是这样的紫砂杯没有火气,能封存茶香,热天里用它泡茶,隔夜茶也不会发馊。
紫砂杯主要出自宜兴,是宜兴盛产高品质的紫砂土。宜兴的紫砂土和景德镇的高岭土一样,充实了当地的仓廪,富足了当地的百姓。我的宜兴朋友老章曾很自豪地和我说,宜兴人属于“老天赏饭”,说这话时,他刚签好了一份三百万的紫砂餐具合同。
明里的道理是“靠山吃山”,但“吃山”也是要有资本的!倘若宜兴没有好的匠师,做的紫砂器物粗劣不堪,且不经用,那又怎么能行销各地。宜兴紫砂器物能享誉天下数百年,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沉淀,人文的沉积,匠心的积累。
宜兴紫砂器有数百种之多,以紫砂壶最为得名。紫砂壶据说是明代书童供春(一名龚春)发明,他随主人吴颐山在金沙寺陪读时,向僧人学得了制壶手艺。吴颐山虽后来得中进士,继而以提学副使擢升四川参政,官做得大,名气却没有供春响亮,以致有人评述,“学宪风流久零替,世人梦想知有龚。”供春壶在当时就很珍贵,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说。传世有一把供春款的茶壶,藏于故宫,见其照片,黑褐色,表面有状如树皮的疙疙瘩瘩,有专家认为是老仿,然真伪并不重要,能从上面窥见前人的艺术风骨,能从中引发持久的学术话题,这远超了物件本身的价值。
供春之后,制壶高手喷涌而出,明清民国至现代,名头大者有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裴石民、顾景舟等人,特别是陈曼生与紫砂艺人杨彭年、杨凤年兄妹合作的“曼生壶”,以十八种式样闻名后世。陈曼生因壶而名,他的书画作品自然水涨船高,友人荣华几年前以近三十万元的价格买了陈曼生行书诗轴,挂在茶室,风雅绵延,品茗者无不要多看上几眼。
大名家的紫砂壶,物稀价高,常人难以染指,不光经济上不允许,眼力上更是达不到。要是想收藏紫砂壶,可买清代、民国的商品壶“试试水”,这种壶价格至少千元,其壶底往往会有圆形或方形戳记,有的干脆直接是花押、龙印、宝鼎款一类的图形。部分商品壶在紫砂表面还施了釉、加了彩,称为釉彩紫砂壶,这种壶艳丽多彩,但我觉得偏为繁琐复杂,艺术上不一定都需要加法。
清代、民国商品壶中最便宜的是桶壶,一般数百元就能得手。桶壶没有手柄,顶上边侧各对应两个小孔,需要自行配上铜提把。我有一只民国大桶壶,圆形牛鼻式壶盖底上的戳记霸气十足——“顶海洋桶”,大概寓意有着海洋一样的容量,验证后,果真有点意味,装下大半茶瓶的热水问题不大,同时还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这类紫砂桶壶,实用性大于艺术性,在民间还有个称谓叫做“田壶”,意指昔日农人劳作时,将壶放在田埂,歇息时,用之饮水。若把所有品类的紫砂壶比作一个家族的话,桶壶就恰似一个胖胖壮壮、憨实质朴的底层劳动者,用它泡铁观音,兰花的香头好像能积聚起来,能在颊齿间立地生根,舌面上一片明亮香润,当然这不排除是心理作用。但它在闲暇时带来的快乐,已然很令我欢喜。
拂尘
世间多尘埃,尘世一词绝非无中生有,唐僧惠能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到底带有理想色彩。有尘就要清理,拂尘与扫帚、鸡毛掸子、拖把、吸尘器等用具应运而生,但拂尘几乎无人使用,它与我们的凡俗日子保持着“清高”。
名为“拂尘”,拂尘最早却是佛教徒用来对付蝇虫的,面对蝇虫的骚扰,他们不愿意杀生,故用拂尘驱赶它们,但这是很费力的事情,因为蝇虫还会往返再来。换做我,我会点燃香茅草熏赶蝇虫,我以为,它比艾草的气味要好。夏日里,闻着香茅草的味道,喝着醇厚的普洱熟茶,出一身大汗,洗一个痛快淋漓的热水澡,一觉睡到自然醒,这可理解成精神层面上的拂尘美事。
拂尘更多的还是道人在使用,老宅附近有一清代所建的玉皇宫,我幼年时,宫中唯一的老道已是七老八十的样子,老道终年拂尘不离身,他经常把拂尘插入道袍后领,提着篮子上街置办生活用物。那拂尘须毛是一把纯白色的马尾,比老道的银白色胡子还要白亮,拂尘杆子约是黄杨的,看上去光滑润泽,应有很长的年份。
街坊邻居很尊敬老道,原因是老道会给人治病。老辈人说早年北郊有一病患,喝多了酒在荒坟地里躺了一夜,醒来后,长时间头痛难忍,多方治疗都没有效果,老道看了看,将几味草药研磨成末,配上麻油捏了几个药丸,铺在锡纸上,用蜡烛烘烤,让病患嗅了几下,接着又拔了一根拂尘须在病患鼻孔里挠了挠,不久竟有一条小虫从鼻孔中掉出,头痛从此痊愈。老道羽化后,拂尘不知所踪,据说被市博物馆收藏了。
历史剧里,常见太监手持拂尘,传圣旨时都要带着,很有仪式感。京剧《百花亭》里,伺候杨贵妃的高力士、裴力士手中都有拂尘,他们似乎用拂尘安慰了失意醉酒的贵妃。太监的拂尘,当然不仅仅是仪仗器,他们会以拂尘清理宫中器物上的灰尘,也会以拂尘来驱赶苍蝇蚊子,再高的深宫大院,都挡不住飞虫,如果太监看到有苍蝇蚊子叮咬皇帝,上前拍打会视为不敬,坐视不管又等于渎职,这时拂尘就马马虎虎地解决了问题。
“手拿拂尘,不是凡人”,按此语解释,使用拂尘者都是高手。其实不然,器物只是给个人形象锦上添花的道具,它永远不会提升一个人的内质,就像白石老人放下常持的竹杖,他还是我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书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