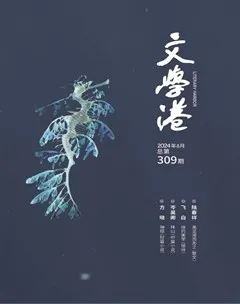小镇旧事
小镇呈长条形,像一截腊肉,挂在西秦岭山梁上。
镇子中间别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破烂不堪。村子随意摆在路两侧,路边丢着两排二层楼。
这条公路,前几年修过,最多五年时间吧。修之前,砂石路,坐个班车,把屁股能颠成花。尤其城里人下乡,走在这路上,那娇贵细嫩的屁股实在受不了,走一路,定会骂一路。路修好后,看着平坦了不少,至少不颠屁股,不被汽车扬起的灰尘埋掉了。可没想到,这路,没走几年,就报废了。按理说不该这般“娇嫩”啊,修好时间不长,也没有多少大车压迫,但事实是,这条路彻底废了,不是隔三岔五塌方,就是随处破损翻浆,大锅口一样的深坑,让整条路狼狈不堪。实在想不通,拿着群众的钱,修这么一条下三滥的路。讽刺的是,这条路至今没有验收,而路政府又要重修了。对此,公路沿线老百姓一提起这条路,十分恼火,破口大骂。
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加宽此路,当时还是记工分,全乡的人都参与其中。母亲背上一块干馍,早早就跟村里人一道出工了。工程结束后,母亲领回一个搪瓷盆和两条擦脸毛巾,以作纪念。白瓷盆,盆底印着红漆大字,特别醒目,我们家用了很多年,颇为结实。
公路东头,是小镇的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要上高中就得去另一个镇子,或者进城。不过我上学时,不时兴上高中。好学生都上了师范。中等的,极个别上了高中。其余的上了技校。最差的,打工去了。
我上初三那会,中学东西各四排房子,前三排是各年级教室,后一排是教师宿舍。房子都是砖混结构。红砖裸露在外,缝隙里填着水泥。屋檐上一根根木椽直愣愣撅出来,挂着一串串灰尘和蛛网,在我们的叫喊里飘来荡去。屋檐下,有几个燕子窝,窝下地上,铺着一层白乎乎的粪便。一开始有燕子,捣蛋的学生老用石头打,燕子不得安生,就弃窝而去了,它们肯定很是愤怒和无奈。教室墙根下,到冬天,我们排一排,晒暖暖,挤麻子,时间一久,红砖被磨蹭得光亮。学校的四周栽着白杨,都钻到了云朵里。树干上,刻满名字,有些已毕业多年了,名字还在,但树皮已皴裂,名字多模糊,谁又知道谁是谁呢?我毕业后多年,中学盖了新教学楼,拆了教室,砍了杨树,学校面貌大变,旧痕不存,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了。
当时,中学校长是我们村人。虽跟我们家非亲非故,但觉得是一个村,心里暗藏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某种自信和骄傲。想来也是很奇怪哈。
沿公路再往西,是一些砖瓦房。接着走,是一家银行,当时叫信用社,现在叫农村合作银行。这是镇子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我对信用社有印象,是因为我三爷。三爷是我们村信贷员,也就是信用社在各村的业务代理人。他家里有个绿色大铁皮柜,钱就装在里面,我见过。那时候,家里穷,村里很多人也穷。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是父亲最犯愁的时候。因为随着一场春雪或者春雨,麦地就要撒化肥。紧接着,清明前后,得种洋芋、葵花、玉米,还得用化肥。化肥主要是尿素和磷肥。每年买化肥要五六百元,这是个大支出,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咋办?贷款。父亲就去找三爷,虽是亲房,能贷下来,但年复一年地贷,实在不好意思,再说,年底,咋还,又是个问题。
后来,每次来镇子上,看着铁皮大门圈起的院子,我就想到父亲贷款的事。那时年少,总以为钱是他们在院子里生产的,像制造作业本一样。
银行斜对面,就是我教学的中心小学。小时候,我在中心小学参加过几次统考。那时候,学校还是土房子。可能是我们学校小,每次来统考,都觉得中心小学特别大,大得老是找不见考场。学校门口有一棵弯腰驼背的柳树,每到统考,柳树下就摆满了小摊。凉粉面皮、冰棍、作业本、橡皮、铅笔盒、糖葫芦、果丹皮、彩色铅笔、麻子、大豌豆,还有好多,都是我想要的。不过好多东西都是看一看,过过眼瘾罢了,因为母亲只给了五毛钱。五毛钱,买一碗凉粉面皮吃了,就不能买别的了。虽然咽着干馍,衔着口水,在地摊前晃来荡去,但还是舍不得花钱。麻子大豌豆家里有,没必要买。彩笔实在喜欢,但不实用,不能买。最后,思来想去,五毛钱都捏出了水,买了一个铅笔盒,背回了家,用了四五年。那是我上学用的第一个铅笔盒,之前,用的是装过青霉素的纸盒。
现在,柳树没有了。学生来统考,都背着满书包的零食,装着满兜兜的零钱,在小镇几家商店里出出进进。他们再也不会拿着五毛钱为买什么而犯愁了。当年,那个卖面皮凉粉的老人,或许早已经去世。那个背着背篓卖小玩具的人,估计老了,孙子也上小学了。那个走近十里路来售卖零食的人,或许早已改行,另谋生计了。
小学斜对面,也就是信用社隔壁,是戏场。以前,戏场是土院子、土戏楼。小时候,我们全学区的六一节目就在上面演出。戏楼大多数时候空闲着,每年五月,唱大戏,就在上面。我刚到镇子上教学时,正逢唱戏,父母来看了几天戏。与其说是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看我。
戏场隔壁,是兽医站。我们村有人在兽医站当兽医。兽医吃公家饭,铁饭碗,常年穿一身藏蓝色衣裤,戴顶蓝帽子,一看就是干部模样。兽医站以前常有牲口去看病,现在养牲口的人很少了,看病的自然也就寥寥无几。我看过给牛打针,那么粗的针管,跟胳膊一样,牛站那儿,唰一下,在牛脖子上扎进去,牛没回过神,就已经打完了。给骡马打针就没那么容易了,有一次,我看见一头栗红色的马拴在木桩上,缰绳拴得很紧,马头抵着木桩。穿蓝大褂的兽医刚凑过去,马就撂蹄子,乱踢乱叫,性子暴烈。兽医叫两个人找了杠子,趁马跳起还未落下的一刻,插进两腿中间,一绊,马身体一晃,像一堵墙,轰然倒地。那两人冲上去,压在马屁股上,兽医刚近马身,马“轰隆”一声拾地而起,犹如倒塌之墙猛然站起,把三个人全掀翻在地。马脖子一扬,“嘎巴”一声,扭断木桩,拖着缰绳和半截木桩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那次正是六一,我们去参加汇演,中午无事,趴在门口看到这一幕,笑得屁滚尿流,结果被兽医站的一个小青年骂了一顿,赶走了。
兽医站隔壁是卫生院,我去过一次,没啥印象。我们看病,一般都去另外一个镇子的卫生院,一是近,二是那里的大夫水平相比好些。
沿着路,再向西,一侧是林分站,一侧是邮电所。
再行,就到了乡政府。我祖父退休之前,在这里工作过几年。他本来是可以弄个官当当的,但当时我们家口大,粮食少,养活不过来,地里活也多,忙不过来。在县委工作的祖父就被曾祖父叫了回来,在离家近的公社上班,这样便于照顾家里。那时的人,好像没什么进城不进城的观念,也没捞个官当当的欲望。人的活法,都很简单。后来,祖父上了年纪,就到小镇来工作了。
我上小学时,有年六一来镇子上,在祖父宿舍住过两天,那时乡政府还是单面老楼。
后来,我当记者,有一年,某村有群众反映退耕还林的事,同事接到选题后,拉我去做采访。我们冒雨拍完,最后没有播出。乡政府的领导找了人,托关系,把我们稿子枪毙了。后来,我们还曝光过一个粮食直补的新闻,乡上领导跟我一个亲戚熟,问了我号码,欲联系让我删掉,但节目领导已安排播出,我无力停播。当时我也没有接听他电话,我知道一接电话,事情就变得复杂。那件事,把乡上领导得罪了。后来偶有见面,颇为尴尬。
过了乡政府,便是民房,再没啥了。
小镇逢集的日子是农历逢一四七。因为人少,即便逢集,人也寥寥无几。除过初夏卖农具、草帽,腊月里办年货,马路两边会摆些摊子,平时,只有三五个小摊,常年坚守着,卖点蔬菜、农药、农具。
这就是我所在的小镇,在中国万千小镇里,一个普通到可以被忽视的地方。在西秦岭,它挂在一千六百米海拔的山坡上,风吹,它发出清苦、简单的声响。
我们村子,只有学前班和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到十里外的附中去上,那里有一到五年级、初一初二。我在附中上了三年,三年,早晚来回走的路,OH3KxhlDC20RA8PTeTkvbQ==加起来,能否绕地球一圈,真不好说。上初三,就得到秦岭的镇子去。初三前半学期,我吃住在姑姑家。上学,也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山路。后来,表哥结婚,我住的那间屋子要用来当新房,我就到表姐(姑姑二女儿,嫁到镇子上)家里吃,在她一个朋友家里住。吃住虽在两处,但也不远,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毕竟在镇子上,省了早晚跋涉。就这样,度过了初三后半学期。
中考,我考上了师范。如果考不上,计划上高中。如果上了高中,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又会走上哪条路,想不来。同样想不来的还有,我在初三那年生活过的院子,会于九年后再次回去。
在秦岭小镇,我忘了是在哪里拿到表姐家院子钥匙的。
那个院子在街道北侧,进巷道,百米左右,右手边便是,红漆铁门,门口有斜坡,水泥硬化过,但多有皲裂,缝隙中长满野草。开门,铁门哐当有声,吓人一跳。铁锈如沙,簌簌落下。推门而入,满院疯长的野草扑面而来,紧紧将我抱住,差点摔倒。院子只有春节时住过几天,其余日子就这样荒芜着,任由尘土覆盖,任由野草疯长,任由野猫出入,任由山鸟起落,任由空寂弥漫。院内,正房是一层平房,贴了瓷砖,坐北朝南。地基很高,近一米,得上三个台阶。中间客厅,两侧厢房,一间当卧室,一间当库房。西边,一间平房,也贴了瓷砖,当厨房用。东边,是一间土坯老房。
除去荒芜,院子还是几年前的模样。时光似乎从未走远,九年,九年在院子只是长了一些毛边罢了。
猫儿草、天萝卜、苦苣、苍耳、艾蒿、牛筋草、车前草、蒲公英、灰灰菜、荠荠菜……这些野草此刻忙着把院子填满,它们无法抵达的地方,都空着,空得让人心惊胆战。
我睡在他们住过的厢房。除去大门,我只有一把钥匙,仅能打开这间厢房,其余房间,门都锁着。我开始守着偌大的一座院落。我成了野草和山鸟的伙伴。我觉得自由,这么大一处院落,可以任我走动,任我坐卧。我似乎成了这院落里孤独的王。
初三后半学期,中午、晚上,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回到这个院子,吃过饭,就到另外一户人家家里去睡觉。那户人家和表姐男人关系颇好。女主人三十出头,很年轻,也很健壮。生有一儿一女,名字我实在想不起了。家门口总是拴一头牛,牛粪成堆,有干有湿。我住的屋子,是间厢房,很窄小,除去一盘土炕,仅有一条通道,供人进出。炕平日是那女主人填的。用的干牛粪,真烙,靠窗口烙的搭不住脊背,我只得挪到炕沿处。女主人一家跟我非亲非故,但对我很好。我穿过的衣服,她会拿去洗。做了好饭,会打发孩子端给我一碗。也没有收我一分租金,还帮我整理屋子。有时,儿子不会的作业,她打发过来,让我辅导。女儿小圆脸,腮帮两坨红团团,憨憨笨笨,很是可爱,平时总喜欢跟我玩,她还没上学,我用笔在她手腕上画了块手表,她嫌少,又让我在另一只手腕上画。玩一会,女主人喊,快过来,哥哥要学习,你窝在那边,打扰什么啊。女儿嘟着胖乎乎的小嘴,悻悻出门,然后一回头,说,哥哥,明晚你还给我画表啊。我盘腿坐在炕桌前,摊开作业,说,行。
表姐家里,当时有六口人。他们夫妻,一女一儿,还有太公太婆。我念初三那会,太婆身体还好,太公瘫痪在炕,不能动弹。表姐和男人下地劳作,每天的饭,便由太婆做。太婆信佛,平日穿一身黑,斜襟黑布衫,粗布黑裤,脚上黑布鞋,头上黑帽子。大方脸,手脚麻利。每天,饭做好后,用洋瓷碗盛满满一碗,端到老伴跟前,喂着吃。太公伸着干瘦的胳膊,咿咿呀呀,在空中画着圈圈,告诉太婆盐多醋少。他饭量很好,一顿一大老碗,连汤带面,可人依旧瘦得皮包骨头,卷在被褥里。他就这样卷了很多年,有没有卷出一丝火星呢?我趴在方桌上吃饭,不知他认识我不?他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他就那样一直躺着,从我出门,再进门,天天如此,从我初去他家吃饭,再到我毕业离开,月月如此,甚至年年如此。
后来,我进城上师范去了。二位老人也相继过世了。具体哪年过世的,我不大清楚。
坐在廊檐下,看着蒿草掩映着的土房子,木门锁着,还是那把老旧黑锁。房子久不修缮,快要坍塌了,像一个人,站久了,弯腰裂胯,稍不留心,就会跌倒一般。那屋里,我有九年没有进去了,虽然时光流逝,老人故去,可那生活过的场景,我依旧历历在目。
我常想,是不是当我推门而入时,太婆依旧黑衣黑帽,坐在炕沿上打盹。供桌上的香,青烟缭绕,香灰积了半截,落下了,悄无声息。太公依旧瘫在炕上,两眼睁着,空洞而寂静,他举了举瘦胳膊,又放下了。他听见骨头睡去的声音,像一张黄纸,盖在了碗上。
这般想象一久,便有些害怕了。尤其晚上,空旷的院落,如一口井,装满了星辰和风声。青草深处,藏着蟋蟀,对月弹琴,琴声低沉。除了小镇上偶尔传来的狗叫,一切,安静极了,静得可以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听见风把蛛网揭起的声音,听见月光落在台阶的声音,听见我的心跳,像手指叩打着胸膛。
我一个人睡在宽大的炕上,满屋漆黑,恐惧弥漫开来,生怕过世的太婆推开门,喊着我的名,叫我吃她做的馓饭。或者,太公突然起身下炕,拄着拐棍,颤巍巍走进来,向我借火点烟。想着想着,鸡皮疙瘩便落了满炕,头发都直愣愣竖起来了。
有时下雨,闪电划破苍穹,锋利的光,钻进窗户。我躺在炕上,被闪电映亮。闪电也映亮了光秃秃的墙壁和屋顶。好久没有一个人听雷声了。那些闪电,像一双手,伸进来,一瞬间,翻开我的肉体,像翻开一本书,它要寻找什么呢?有时天晴,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能看见挂在南边的星辰,一颗,两颗,三颗,风吹着,闪闪烁烁,像灯芯一般,风大点了,就会被吹灭了。那一颗一颗的星,孤独极了的样子,多像我。
这样的夜晚,我会想些什么呢?我忘了。
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在这里会活成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铺开。一切都像蒿草,不为什么,只是生长罢了。
就这样,九年后,我再一次回到这个院落。那些曾健在的人,已经离开这里。在世的,去了远方,寻谋生路。离世的,也去了远方,远得我们再也无法相见。唯有我,还在这世间,活于青草中。时光从我身上画了一个圈,或者丢了一个盹。抑或只是我,在时光的侧面,出了一趟门,捉了一次迷藏,而后,又回到了时光的正面。
是命么?我被齐腰深的草锁住,难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