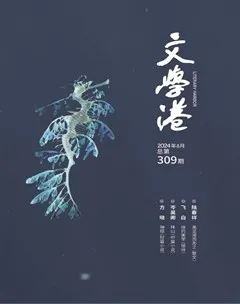北山有先生
闭关方喜得幽栖,
何用邦候更品题。
自分终身守环堵,
不将一步出盘溪。
一首《缴回太守赵庸斋照牒》,何基一诗成名。
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福建赵汝腾(号庸斋)新任金华太守,拜访在北山脚下盘溪之畔讲学的同门师兄弟何基,敬慕他的才学,推荐他入朝为官。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儒生而言,入朝为官是实现理想的最好方式,况且,此时的何基已五十六岁,仍是一介布衣。而何基却以这首诗,一句“自分终身守环堵,不将一步出盘溪”,逃离了“学而优则仕”的集体价值观,拒绝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泥水,也拒绝得让人肃然起敬。
一
其实,早在赵庸斋之前,同门师兄弟、金华太守杨与立已拜访过何基,对他的学问与修养深为赞许。金华府多次邀请他主讲丽泽书院并出任山长(相当于校长),他都拒绝了。
何基拒绝的丽泽书院,由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金华学派”创立者吕祖谦创办,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与之比肩的其他三个书院分别是朱熹主讲的白鹿洞书院、张栻主讲的岳麓书院、陆九渊主讲的象山书院。毫无疑问,丽泽书院的山长,是金华八婺大地道德学问、朝野声望出类拔萃的人物。金华府的邀请,实则也是荣誉。
何基一拒再拒,不仅自己出了名,盘溪作为何基的出生地和讲学地,也出名了。盘溪成为学问的净土,先生的圣地。
盘溪,发源于北山之南,穿后溪河村而过,流入婺江。
春雨初歇,后溪河村草叶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水珠,角落里草丛中的蛛网,也挂上了两三点。水淋淋的水泥路上闪着一片薄光,地上有零星的打落的叶子,晌午的村庄异常安静,似乎天地间只有盘溪的水在流动,在耳边震响,又似隐在岁月的深处。
盘溪溪水充沛,河水夹带着微黄的泥沙,湍急处泛起片片水花。溪流两边,是砌得平整的堤岸,有些地方是水泥面,有些地方露出鹅卵石砌面。鹅卵石砌面是灰黑的光阴颜色,其间生长着一两株翠绿的草,似乎再拨开那些鹅卵石,就能看见何基与学生论学的画面,赵庸斋叩开书院的门的情景。
盘溪边留有一条道路,并不宽敞,大概是因为这条路形成时间有些久远,来不及迎上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两边,簇拥着一个个宅院,溪上有密集的木桥,溪边建有多处埠头,埠头上有浣洗的村妇。
“这个村庄古时名盘溪村,现在叫后溪河村,我们都是何基的后人。”后溪河村支部书记何宝平说起何基,难掩心中的自豪。后溪河村约有九百五十口人,大部分从事苗木种植,由原后溪河、贤里、毛村三个村庄合并而成。原后溪河的村民,大部分姓何,显然都是何基的后人。
村中有纪念何基的“何北山祠”,面溪而建,抬眼可见尖峰山。何宝平书记说,经多方考证,“何北山祠”的所在地,就是当年何基讲学之地。村里的老人们说,在他们小时候,“何北山祠”的门外是一口长方形的池塘,池塘与盘溪相邻,盘溪之水流经池塘而过。池塘前的盘溪上,由五块大石板拼凑成桥,名“五板桥”,出入“何北山祠”,都要从五板桥过。
想来,数百年前的盘溪村,人口并不稠密,这里应该另是一番旷远和静寂,水声和着琅琅书声,阳光洒在一个个蓬勃的脸颊,在溪流、林涛、山风、鸟鸣中,一位位学子来到这里,一位位儒生从这里走出去。
二
何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他的祖父何松,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官至徽州通判。父亲何伯慧,曾任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被称为“崇道公”。何基是次子,自小身体清弱,寡于言笑,年纪颇大才开始接受教育。
何基第一次出远门,是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这一年他二十岁。何伯慧任县丞的江西临川,来了新县令黄榦,在当地开办书院收徒授业,何伯慧命何基和兄长一起拜黄榦为师。
黄榦是朱熹的大弟子和女婿,是年五十六岁。在此之前,朱熹通过对黄榦的全方位考察后,临终前视黄榦为自己的正统传人,黄榦接过了“程朱理学”传播传承与发扬光大的接力棒。
入门之初,黄榦首先教何基兄弟俩为学根本乃“治学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何基从此开始全面系统学习理学思想和朱子“四礼书学”。
七年时间转瞬即逝,二十七岁的何基决定返回金华教书育人。临别时,黄榦又叮嘱他:“但熟读《四书》,所学融洽贯通于胸,道理自见。”黄榦的“临别之教”,成为何基终生坚持、递相授受的为学之法,也奠定了“北山学派”以四书为基,熟读精思、浃洽胸次、明理见性的学习进阶和学术基调。
在盘溪之畔,何基潜心研学,安静教书,过着朴素的布衣生涯。“村烟澹澹日沈西,岸柳阴阴水拍堤。江上晚风吹树急,落红满地鹧鸪啼。”何基的日子,应该如他的这首《春晚郊行》,村烟西落,江水拍岸,晚风吹柳,满地落红,他在四季的变幻中风雅,在风雅中感受生命的美好和流逝。
北山脚下的这位先生,数十年来并未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直到有一天,朱熹门人杨与立叩开他的门,他的才学和朱子学脉才为人所知,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学生多起来就教书,邀请出山就拒绝,何基的生活依然如故。但他的儿辈们又难免为生存而担忧。何基劝道:“丈夫何事怕饥穷,况复箪瓢亦未空。万卷诗书真活计,一山梅竹自清风。”(《宽儿辈》)何基劝儿孙,其实也是陈述自己的内心:大丈夫哪里需要怕饥穷呢,何况家里也没有揭不开锅。这万卷的诗书才是真正需要去努力的,这满山满眼的梅竹都是清风。他在理学的世界里全神贯注、浑然忘我,甚至常常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何基七十六岁,理宗诏他为史馆校勘(宋代校订宫中藏书的官名),接着诏为崇政殿说书(宋代为皇帝讲史,解释经义的顾问),又特补迪功郎(为文官职)添差婺州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他都以病老力辞。南宋景定六年(1265年),度宗又有诏命,何基也没有接受。
何基的人生履历很简单,他这一生,出远门求学七年,在盘溪畔讲学五十多年,只做成了一件事,攀上一座高峰。
我想起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
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侣,
然后,把门紧闭,
她神圣的决定,
再不容干预。
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只有一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小镇,其余时间都在家中,在火炉旁烤面包,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但她缔造了美国诗歌的传奇。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何基以布衣之身去世,享年八十岁。何基死后第七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恭帝赐谥号“文定”。清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何基从祀孔庙,列东房先儒。
三
何基,是一颗理学的种子,也是一颗先生的种子,这颗种子落在了北山脚下盘溪之畔,便在这片土地茁壮成长,繁衍成荫。
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冬天一个普通的日子,三十八岁的王柏来到北山脚下,来到盘溪之畔寻找慕名已久的何基。此时的何基四十一岁,对理学的理解已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王柏向何基道出自己决定放弃仕途寻求理学真知,以及自己在求学中的困惑和孤独,渴求指点。何基听王柏诉说自己的决定和困惑,一如遇见故人,似乎在王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勉励王柏刻苦求学,并用胡宏之言教他:“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间。”
从此,何基与王柏亦师亦友,在理学的世界里同行三十五年。盘溪之水,北山上的明月清风,都无数次见过他俩亲密无间的身影。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王柏引荐二十二岁的金履祥向何基求学。六十六岁的何基看到年轻的金履祥,想起了自己二十岁时拜黄榦为师的情景,对金履祥倾囊相授。后来金履祥卜庐建居,何基为他题匾额“仁山”。
站在“何北山祠”的盘溪之畔,遥想脚下这片小小地方,何基应该走过无数次,王柏、金履祥也走过无数次,他们经过此地,传承了何基的理学,也从此处展开自己的人生。
在往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何基、王柏、金履祥师徒三人在各自的书院里,践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理想和追求,任外面风吹雨打、荣华富贵。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何基离世,同年,许谦出生。元大德五年(1303年),三十二岁的许谦在兰江听了金履祥讲学,即拜在金履祥的门下。后来,许谦一直跟随金履祥在金华吕成公祠讲学,深得金履祥欣赏和器重,寄予厚望。
后来,许谦在东阳八华山中设立了八华书院,亲撰《八华讲义》教学,一时间八华书院闻名于世。许谦从事教育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记录在册的学生就有千余人,由黄榦传给何基的“程朱理学”,经王柏、金履祥,许谦递传,成为宋元朱子后来的三大分支中的重要一支。他们四人被后世称为“北山四先生”。他们传授朱学,但没有墨守朱学,许多地方都有创新。“北山四先生”被后世奉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他们推崇“道本文末,文以载道”,也将婺学思想融入其中,形成了独特风格。
后来,王柏、金履祥、许谦也从祀孔庙,“北山四先生”以一个特殊的组合为后人敬仰。
四
我随着盘溪逆流而上,溪水潺潺,满山新绿,越往上走,越安静。立于其间,心也就安静下来,这样的山水,最适宜种养理想。
因为理学理想,何基在此开宗立派,开创了北山精神;世代为官的王柏放弃了仕途;金履祥摒弃举业,一生不仕。许谦一次次拒绝朝廷任命,先生之名名动四方。他们传递理学,也传递求真求实的求学之道,传播儒者的操守。
他们虽然隐于江湖,但从未放下过家国。
王柏目睹百姓困苦,向金华地方官连上《社仓利害书》《赈济利害书》,主张州府加大对贫民的救助。南宋王朝内忧外患,王柏上书提醒朝廷务必加强军事重镇襄阳的防务。襄阳被元军围困,金履祥屡次献策,其中“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且备叙海舶所经地形”更被后世认为是可行的奇策。
北山脚下,后溪河村旁,是何基长眠之地。何基之墓原在长山石门附近的油塘,在历史风云中屡次被盗被侵。2010年,何氏子孙将何基之墓迁回后溪河村。站在何基的墓园中,异常安静,只听见鸟鸣起落,风声阵阵。这里的安静,不仅在于这里的环境,更在于何基内心宁静的一生。有什么比内心的宁静更为宁静呢?
在时代的舞台上叱咤风云,是一种追求,在名利场外甘于寂寞与清贫,何尝不是另一种追求?何基不是随群的大雁,他是一只有着独立智慧和品格的孤鸟,是北山的竹和梅。他守着学人的寂寞和清贫,汲取天地养分,在阳光和星辰下摇曳一树芳华,创造了“北山先生”独特的生命形式。
我抬头仰望延绵不绝的北山,这不仅是一座地理山峰,更是一座人文的山峰、信仰的山峰。这里不仅传承着朱子文脉,也保存着一颗纯粹而宁静的学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