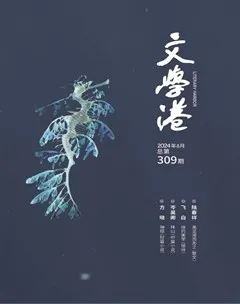一袋百家米(外二篇)
旧杂志上看到这么个题目,30年前的一段记忆被唤醒。我家也有过一袋百家米,是奶奶沿着村子,挨家挨户讨回来的。
时间回溯到1994年的下半年,记忆这么清晰,是因为那一年村子里发生了很多大事。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方经济迅猛发展,村子里到广东打工的青壮年很多,我的同龄人没有考学的,也基本随父辈到南方谋生活去了。用他们当年的话来说,钱真好挣啊。只要能吃苦,一天挣个百十来块毫无问题。而那时候,普通老师的工资不过两三百块。
我当时正在师范就读,妹妹早早结婚后也跟着婆婆一家人到南方“扫钱”去了。果然,学缝纫的她,在路边支起一个小摊,专为附近工厂的打工仔们补补衣服,换换拉链,半年挣得的钱,已足以让我妈怀疑我读书的意义了。
村子里的怪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先是一户人家在外打工的壮年儿子突发疾病辞世,噩耗传回,老父亲经受不住打击,当即就撒手人寰,留下70多岁的寡母和孀妇弱子。记得他们家有六个孩子,大女儿才十三四岁,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兄弟,路还走不稳。全村人都摇头叹息。可村人还没从沉痛中缓过神来,又传来噩耗,某村民在广东出了车祸,也是当即丧生。
这实在太可怕了,村子里一下子人心惶惶,家里有外出打工的人更是紧张不安,一面托人带信叮嘱自家人注意安全,一面着手请来戏班子,接连唱了半个月的戏。说是怕年轻人不理农事,不守故里,冒犯了苍天,以此谢罪。
我好歹受了点教育,并不信这个,总觉得是大家忙于挣钱,忽略了休息,极度疲倦会导致猝死;农村人骤然进入车水马龙的大城市,也未必懂得交通规则,过马路稍不留神,也极易发生意外。但奶奶相信是村人触犯神灵,神灵要惩罚大家,于是带走了不守故土的壮年男子。
其时爸爸并没出去打工,但奶奶仍极不放心,说怕是阎王爷生气时殃及无辜。她一面张罗着给爸爸算命,一面更为虔诚地吃斋念佛。听算命先生说爸爸那一年命里有一冲,解法就是讨百家米来吃。于是,年逾古稀、弯腰驼背、已多年不出院门的奶奶,拄着拐杖,挪着一双裹过的小脚,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去讨一把米。她怕别人嫌弃,还特地买一些水果糖,人家给她一把米之后,就往人家孩子手里塞两颗糖。
据算命先生说,这事情只能是为娘的亲自做,所以奶奶坚决不要我母亲帮忙,她每天做好早饭就出门,等她不知怎么弄回那一大袋子百家米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接下来的日子,奶奶每顿做两次饭,一次是用百家米给爸爸炖饭,一次是给我们全家做饭。我不知道那一袋米爸爸吃了多久。但奶奶带着虔诚,不厌其烦地做,倒确实让家里安心不少。这些是我放寒假时听母亲说的。
等到春节来临前,村子里的打工大军返乡,热闹得不得了,人气一旺,这事情也就过去了。
而今,奶奶也去世廿余年了,那些吃百家米饭的日子,爸爸一定没忘记呢。
我的父亲是农民
父亲生于1950年,做了一辈子农民;年过六旬后,农闲时节还常跟着母亲到镇上做计件工,因为“田里的活儿大多交给了机器(指插秧、除草、收割之类的事),人总不能闲着呀”。的确,忙碌了一辈子的父亲,大抵没有退休的概念,也没有休闲的习惯。
父亲念过高小,一手字写得不错。小时候家里的扁担、水车、风车(一种手动鼓风,把粮食中杂质分离出去的传统农具)等大大小小的农具上,都有他的毛笔姓名,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他年轻时还做过村里的会计,做的账本,我小时候见过,很是整齐清爽。有一次他指着我一塌糊涂的练习本批评时,专门拿出来给我做过示范。
父亲爱看书。漫长的冬夜,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父亲就在一旁扎扫帚搓麻绳,闲下来也翻翻小说,看到有趣处,还会跟母亲说上一段,我们也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白天他下地劳作,我就拿过来乱翻,《隋唐演义》《呼延庆上坟》《杨门女将》都见过,还有《黑牡丹行动》《天涯孤旅》之类的现代小说。如果说文学有启蒙的话,父亲无疑是我们姐弟几人的文学启蒙老师。
家里无甚藏书,那些书父亲也不知打哪儿借来的,此外大抵是拿到什么看什么。这个爱好,他持续了一辈子,这也是他的思想能跟上时代的原因。我们逢年过节回家,他跟念过新闻硕士的女婿聊起时政来,头头是道。我先生也毫不吝啬地赞美:老爸真厉害,国际国内大事全知道呀。父亲则呵呵笑纳,并不多言。去年他带母亲来宁波看眼疾,在医院陪护了半个月,竟然把弟弟带给他的一卷《习近平著作选》读完了。很难想象他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读完几十万字的情景。我妈一出院就跟我们抱怨,说父亲一天到晚跟个书呆子一样,买饭、打水还要她来提醒。
父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绝对算得上一股清流,我和妹妹则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村的其他女孩子,小学、初中读着读着就辍学了:要么回家带弟妹,要么帮父母干农活,要么干脆外出打工。能读到高中,已属凤毛麟角。彼时我家姐弟四人都在上学,母亲也念叨负担过重,说某某家孩子到南方打工,一年挣回好几千;又说女孩子读书,倘若考不上大学,高不成低不就的,耽误了年纪,婆家也不好找......我不知道父亲动摇过没,但他给我的话是:“别听你妈的,只要你读得进去,我砸锅卖铁也支持。”
在大多数人向“钱”看的年代,他难得向“前”看,我才有机会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现在回故乡偶遇一些长辈,言谈间还会听到他们懊悔自责,怪自己“没眼光”,耽误了自家姑娘。
幼时的记忆里,父亲不苟言笑,对我们姐弟几人甚是严厉:不能睡懒觉,早起后姐姐和妹妹分工打扫屋子;上学前相互扎好辫子;弟弟早晚两次把牛喂饱;姐姐放学后需帮奶奶收叠晾晒好的衣物;夏天没有大人带着不准下河游泳;傍晚家门口的落叶浮尘要打扫干净……诸如此类,倘若没完成,是要受惩罚的。有一次弟弟贪玩,放学后忘记放牛,爸爸劳作回来,发现牛依然系在牛栏里,饥渴得团团转。他生气地从柴堆里扯出一根棉秸秆,抽得弟弟屁股上好几道红印子。我弟弟此后再也没忘记过自己的职责。
因了这严厉管教,年幼时,我们姐弟虽没能力到田间地头减轻父母的负担,但我家屋里屋外,一定是左邻右舍中最干净的,地面扫得一尘不染,门口还泼上凉水压尘。乡邻们收工回家,光着脚板踩过,都会赞叹一声:“贤圣(我父亲的名字)家的几个娃儿真是勤快,这门口,啧啧!比街上的水泥路都干净!舒服!”我们听了很骄傲,干活就更加卖力了。
长大后,我们先后走出家门,远离故乡。上了年纪的父亲,仍是不苟言笑,但明显温和多了。他忙好田间地头的事,家里洒扫浆洗的活儿也承包了。母亲说父亲有“洁癖”,其实哪是什么“洁癖”,父亲是习惯了整洁,又心疼母亲跟他一样忙里忙外,还要颇为费时地准备一日三餐,就自觉承担其他家务活儿罢了。
如今,我们姐弟各自成家立业,分散在四处,家里就父母两人。农闲时节,母亲去镇上为工厂打包,父亲忙完田间杂活,就骑上他的小三轮,给母亲送午餐,顺便也在厂里打打包,晚上再用他的小三轮载着母亲一起回家。
最近几年,母亲眼疾频繁发作,来宁波看过几次。医生叮嘱,要尽量少出汗,否则不易康复。回家后,父亲不让她下地劳作,家里的十多亩稻田、五六亩棉地、一口大荷塘,还有门前屋后的几块菜地,基本就靠父亲一个人打理了。我们劝他承包给别人,自己就种点蔬菜吃吃够了。他眼一眯,说,那哪成?做得动总是要做的,农村人不种地,那还不是个废人?其实我们知道,他已经不大做得动了。一辈子的重体力活儿,早已磨损了他的筋骨。他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疫情三年,我们没怎么回故乡。去年6月间,母亲眼疾复发,父亲带她到市人民医院去看,医生说再不手术,眼角膜怕要“烂穿”,建议立即转到省城大医院去,可是省城人生地不熟,父亲着急了,这才给我打电话。他一向怕麻烦儿女,除非万不得已。
母亲做好角膜置换手术后,因要定期复查,留在宁波养病,父亲也在我家陪着。可他身在甬城心在家,半点也放不下地里的活儿,三天两头打电话给邻居问询情况:稻田要灌水了,他央求邻居帮他一起灌上;禾苗要杀虫了,他联系人谈好价钱,让人选择合适的天气帮地里杀一下;等到九月初棉花“炸”了,这是纯手工活儿,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帮他摘棉花了。他一定要回去。我们劝他,去年收成大约多少,毛估估包给别人算了。他说,那哪成啊?于是他一个人回去,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把棉花朵朵摘下来,分拣好,再运回家,前前后后不间断忙了半个多月。
其间母亲不放心,打电话嘱托二舅、小姨去帮忙,好歹减轻一下我父亲的负担。二舅、小姨赶紧放下自家地里的活儿,每天来回奔波二十多公里,帮了父亲好些天。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去问询情况,闲聊之后,二舅没忍住,悄悄告诉我,说父亲被坐骨神经痛折6O4PmBn2FPmrG59MYDSCgQ==磨得苦不堪言,每天都是忍着剧痛在劳作,这才揭开父亲报喜不报忧的谎言,我在电话这端听得满心难过,母亲更是急得连连叹气,说,“你爸就是这么个人!”
唉,我的父亲,他一向不愿让我们操心,所有的苦和累都独自承受。
父亲这辈子,本来是有机会脱离农田,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的。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曾获得一个参军的指标,体检都通过了,但由于母亲当时怀孕,父亲不放心,加上是家中长子,就放弃了难得的机会。后来镇上招工,爸爸又得到一个离开农村的机会,但这次,他把指标让给了自己的弟弟——我的叔叔。现在,风里雨里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跟小他两岁的弟弟站在一起时,怎么看,外貌上相差也在十岁开外。
母亲谈及往事,每每感叹父亲“选择失误”,一辈子吃苦。父亲倒是毫不介怀,说“人各有命”,又对我们说:“你们几个现在都过得不错,我也知足了。”
眨眼快到暑假,又可以回去看看父母了。其实每次回去,看着父母日渐衰老,总会莫名心痛。但父亲从不觉得自己老。我们一回去,他就忙着张罗“城里买不到”的新鲜菜蔬:荷塘里刚抽起来的藕带,而且一定要“毛笔尖”,因为这样清炒出来才最嫩最好吃;地里刚掰下的玉米棒子,拿回家就剥开柴灶煮了,因为此刻才最鲜最香甜。此外,菜地刚摘下的西红柿、四季豆、嫩黄瓜,塘边刚割下的茭白,塘里刚捞起的鲜菱、刚摘下的莲蓬……
母亲看他又是塘里又是地里忙个不停,笑道:“家里的还没吃完,你弄这么多回来也吃不了。”但父亲不管,一面收拾着,看我们大快朵颐,一边心满意足地反驳母亲:“刚摘来的新鲜,他们在城里哪里吃过这么新鲜的菜!”这倒是真的,网购再发达,从田间到锅里,总隔着好几道程序,哪像眼前,田间地头刚摘下,转眼就进了我们的嘴里,真正“鲜掉眉毛”!
写到此处,忍不住要咽口水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大约也在巴巴地等着我们放假呢。
默默无闻的父亲啊,你是儿女们走向外面世界的起点,也是我们回望故乡时那盏温暖的明灯。
母亲的背
母亲的背驼得厉害。尽管做了骨水泥填充术,却再也没有伸直过。
这些年来,我只是寒暑假回去逗留很短时间,记不起她的背哪一天突然就驼了。她来过几次宁波,背驼之后,说再也不想出远门了,“怕丢人”。弟弟说,生老病痛,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再三劝说她过来住些天,她的孙子外孙都读大学去了,我们也都空巢了,工作之余有闲照顾她。她有些难为情地笑:“我这样子,哪里还出得了门,背驼得跟奶奶一样了。”我黯然伤神,不敢告诉她,她的驼背比奶奶严重多了。奶奶直到85岁过世前,也没她驼得这么狠,可母亲今年才70出头。
年轻时做事风风火火,以能干享誉十里八乡的母亲,似乎很难接受腰背再也无法挺直的事实。她最初发现这一点,是从抱怨衣服不合身开始,她嫌弃妹妹买给她的衣服后面短一大截,前面又未免过长,还说“鞋不差分,衣不差寸”,现在机器做的衣服,到底不如以前裁缝师傅量体裁衣。父亲告诉她,不是衣服的问题,是她的背驼了。她一脸不可置信,“鬼扯吧,驼得这么狠?”我们听了难过,幸好家里没有大的穿衣镜,她看不到自己的驼背。
记忆中,母亲一生极要强。她两岁时我外婆过世,继外婆生下三个舅舅两个小姨,母亲刚满十八岁便嫁给了父亲。她出嫁前,在娘家后母的严厉监督下,早练就了十八般本领:插秧割稻、采桑养蚕、纺纱织布、缝衣做鞋、打柴挑水、养鸡养猪、种菜做饭,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有时候,还会参与乡村红白喜事的席面上,为当事人家整个十桌八桌的流水席。我之所以对农村母亲们的各种本领如数家珍,并非书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幼时天天看到妈妈忙忙碌碌的身影,耳濡目染记住的。印象中,一年四季,她从未有过休息的日子。
我父亲性子相对温和,做事没那么急躁利索。母亲却是不甘落后于人,插秧比别人宽两行还能最先到头;割稻子也是又快又整齐,与父亲并肩劳作时,方便父亲赶上,时不时要帮父亲割一些;挑草头(割下的稻子,捆成垛,方言叫草头,一担百十斤)到禾场里,父亲一趟,她一趟;割麦子捡棉花,栽油菜薅芝麻地里的杂草,她永远是那个手脚最麻利的人,别人惊叹她做得又快又好,她感谢后母从小的严厉管教。
冬天是农闲季,她就跟爸爸一起挑台基,从屋后农田里、或门前干涸的河心里取土,一担一担挑到门前屋后。几个冬季下来,硬是把屋后的斜坡,挑成了一方高高的新台基。后来叔叔结婚,就是在这块地基上盖的新房子。门前呢,屋外本来比堂屋低半尺,也被填得跟屋内一般高,要不是有青石板门槛拦着,下雨怕是要往家里倒灌。很多年后,我问她,为何要那么累,就不知道歇一歇么?她说,年轻时有力气,也闲不住,不觉得累,农村可不都是这么过的么。
除了挑台基,她还到处割柴。灌溉渠边,高高低低的灌木、荆棘、艾蒿,凡是能做柴火的,都被她随身带着的镰刀割倒,随地晾晒几天后,再去捆好挑回来,那是比稻草棉秸秆更熬火的好柴火。有时候,她砍下的柴足够整个冬季煮饭过年。年关时节,腊八过后,农家基本是不停灶的:蒸糯米、炒粉子、打豆腐、熬麻糖、烧卤菜、动发锅(故乡方言,即油炸各种食物),哪一样都少不了柴火,而且需要劈柴(也叫硬柴,树干劈开晾干而成),她割来的那些灌木,正好派上用场。再说,她也要帮爸爸省下稻草棉秸秆之类,用来烧砖块盖房子。集体分的柴草有限,不够的部分,都是她自己去想办法。
冬天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烧砖。砖坯是趁秋天雨水少时就脱好的。爸爸负责和泥脱坯;至于翻晒、码坯、风雨来临前为砖坯盖塑料膜,则多是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一起完成的。电影《隐入尘烟》中,马有铁和曹桂英夫妇在暴风雨中为脱好的砖坯盖塑料膜的情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极为常见。辛辛苦苦做好的砖坯,大雨一淋,就功亏一篑了。因此,在砖坯入窑之前,得时时关注天气,故半夜闻雷声而惊起,飞奔到禾场给砖坯盖塑料膜的事,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跟电影中一样,大多是父母冒雨拎着马灯去完成的。
终于要烧砖了,砖坯一板车一板车拉到土窑边上码好,再一块一块送到窑肚里码成特定的行列,然后封窑顶,开始烧砖。父亲是村里唯二的烧窑师傅,懂得看火候,经常被十里八乡请去帮着上窑、观察火候、确定下水时辰——砖烧透后,要封住火口,只留下个一寸见方的观察洞口,然后从窑顶往窑里注水,让砖慢慢冷却下来。若火候没把握好,下水太早或太晚,烧出来的砖要么半红半青,要么扭曲变形,只能勉强盖猪圈或牛棚用,大半年的工夫,差不多就白费了。另一个烧窑师傅是隔壁的火生伯伯,父亲的手艺是跟他学的。他比父亲大十来岁,为方便照顾家里,只在附近人家看窑;远一点的村庄,烧窑的火候,就由我父亲去把握了。
整个烧窑期间,妈妈是很忙的,她不仅要保证柴火够用,还要给帮忙烧窑的人准备一日三餐和宵夜。我们姐弟尚小,实在帮不上什么忙,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母亲需要人作伴时,跟着她忙碌的身影,来来回回走在乡间的田塍上Ae9zyClE2v0gIGgdmqwAhORlrkcf5iHl6Z5jRSygj0g=。
乡下的冬夜,寂静而冷清,我跟着母亲,一板车一板车把稻捆从禾场的柴垛边,拉到土窑门口的空地上,空板车拉回禾场时比较轻松,妈妈就说些她小时候的事。偶有兴致,还会说些谜语让我猜。我到现在还记得几个:“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这是辣椒;“一棵树,矮又矮,下面挂着紫口袋”,这是茄子;“一根藤,高又高,上面挂着大马刀”,这是刀豆。我很奇怪妈妈的谜语怎么都是关于蔬菜的,莫非都是她现编的,只是为了和我讲话,以对抗茫茫无边的夜的黑?
我第一次看到子夜时分的银河系,明亮的牵牛织女星,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后来上高中,地理老师曾让我们一群住校生半夜起来观察星座,年过半百的老师利用手电筒的光柱,指点着夜空现场教学:这是大熊座,那是天琴座……我的心却一下子被带回到乡村冬夜冷寂的田野和柴火熊熊燃烧着的土窑前。
除了长年累月的户外劳作,在家里,妈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一家老小做鞋子。这活计通常安排在雨雪天,或者农田也在休息的岁末。记忆中,村里开会时,母亲们大多带着一只纳了一半的鞋底,满会场除了村干部扯着嗓子的讲话声和人群嗡嗡的低语声,还有棉线索在洁白鞋底上用力拉过时,有节奏的“刺啦刺啦”声。妈妈纳的鞋底厚密硬实,鞋底纳好后,以食指中指关节轻轻叩击,回声清脆。这样的鞋子,鞋底不易浸水,耐穿耐磨。
但我们小时候淘气,村前屋后疯跑着玩,跳绳、踢毽子、跳房子,都是费鞋子的。往往鞋底还好好的,鞋尖就烂了,大脚趾头也探出来,那是跳房子踢瓦片时,踢出的洞。现在想想,真是不珍惜母亲的劳动,母亲却从未因此骂我们。倒是有一次放晚学,突然下雨了,我跟同学一起飞跑着回家,其时地面已泥泞不堪,同学的妈妈送木屐过来,半路遇着我们,一边帮同学清除鞋帮上的烂泥,一边骂,“怎么不打赤脚?是怕脚发芽么?”虽是在笑骂,也似乎跟我无关,但这话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再遇到雨天,只要不是太冷,我都会拎着鞋子赤脚回家,记忆中,也并没因此得到母亲的表扬。大概是她太忙了,对下雨时是否要脱鞋子打赤脚这事,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
由于长年累月的劳作,母亲的腰背硬生生被生活压弯了,弯得越来越接近90度。她自己只是觉得衣服越来越不合身,却不相信自己比奶奶的背驼得更厉害。或者,她是知道的,只是不想承认。常年累月在灶台边忙一日三餐的她,总该感觉得到,灶台似乎越来越高了吧?
唉,劳碌一生的母亲,跟父亲一样,在她人生的字典里,有一切,唯独没有“休息”二字。
原载于《江北岸》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