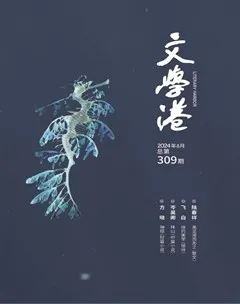后山(散文)
有一年春天,母亲领着我走在重山之中。同行的还有村庄里一个待嫁的姑娘。她们采摘映山红。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一朵花都显得很高。傍晚,一片青瓦在松树丛中露出来,母亲说,我们到家了。我们从远处的山岭绕行到了后山,山脚下就是我家的房子。这是我此生对母亲的第一个记忆。母亲在一只古朴的瓶中插了一两支映山红,搁在窗台上。白天和夜晚,母亲空时就会对着它织衣纳鞋,我坐在她身旁。母亲偶尔会抬头看向花后面的窗外,那是在思念远方辗转江河湖海之上的父亲吧。
在村庄里,我有十一个同龄人。那时小学下午三点就放学了,我们一群顽皮小子奔向学校边的山上,山连着山,从这山跑到那山。五点多,我们到达村庄的后山。在大荒地的草坪上,玩起各种游戏。快六点了,母亲看我还没归家,只要朝后山吼一嗓子,我便能收到她的信息。后山第一重是大荒地,往东是小洼、团炮、大洼,往上一重是蚱蜢山,最高处那重山叫毛尖。躺在毛尖上,离天很近,看白云,看星空,每一片白云都可以在星空中幻化成仙女。风吹芦苇,飒飒有声,但天地是那么的静,十里之外原野上劳作的人声息可闻。儿时一直以为,毛尖那边就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等翻过附近山脊赶集很多年后,有一天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已经无数次到过后山的背面。
二〇二一年冬天,因为一抽烟就眩晕和血压升高,我终于下定决心戒烟。戒断反应实在难熬。入睡困难,中途易醒,还有脑部、心脏的诸多不适,不仅焦虑疑病,甚而有时觉得死亡也不过咫尺之遥。在惊恐潜伏着随时准备显影的夜里,为了能从如山一般重的恶劣意念中逃出来,我开始试着回忆故乡的点点滴滴,尤其是童年的人、事和走过的路。有一刻,念头定格在了后山,然后就再也走不开去了,也无须再寻他处了。后山,与其说有记忆的宝藏,不如说藏着我的整个童年。于是,城市一个个难眠的暗夜里,我在想象重归故乡明亮的后山。后山,也再次成为歇宿地,安放一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孩子的虚弱、痛苦的魂灵。每一条路,每一块巨石,每一棵树,每一垄菜地,每一个劳作的人,每一头牛,甚至每一朵花,每一块苔藓,每一缕风,每一片白云,每一次喊声,都与某个似乎已然忘却但其实多少年一直等待被想起的记忆紧密相连。我尽可能放慢意念的触角,祈望它能与曾经真实发生的同频共振。父亲和母亲回到了他们的三十岁。我走过每一条山路,听风看云,牵牛嗅花。在山风中劳作的父亲和母亲,会抬起头来笑着看看路过的我。有时,他们和那时的我打招呼,也有时,那时的他们是和现在的我打招呼。一切重又正在年轻地发生着。沉重的情绪雾瘴渐渐消散了,在后山的某一处,焦躁的念头黯然陨灭,睡眠濒临了。
后山不仅安放了我的童年和多年后的孱弱灵魂,也安放了我的祖辈们。他们在集体划分的山林里劳作一生,死后也安葬于此。与我这一代人辗转漂泊异乡最终不知安身何处不同,我没有问过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是知道死后落脚地的,那么生前与它日日接触又有何感想?爷爷安葬在后山,他兄长早亡三天,兄弟俩死后依旧相邻,墓碑相距盈尺。后来,奶奶也安葬在后山。
每年清明之前,总要回老家扫墓。这是父亲除了酒之外对我的唯一要求了。即使酒,父亲也只是规劝,在我成年外出之后,回家做清明却不容商量。阳历三月刚过,父亲就会来电话提醒距离清明还有几周,周末天气分别如何,回乡计划越早越好,以防后程下雨没有腾挪余地。早些年,是小叔、父亲和我,后来是叔叔、两个堂弟、父亲、我和妹妹,有时婶娘和小姑也去,印象中那时母亲从未加入上山的队伍。后来,人事更迭,小叔和父亲也把祭奠事宜做了分工,除掉三代之内的祖宗共祭外,再往前的祖辈两家各做几棺。妹妹外出读书也不参加了。只有我,这个长房长孙,无论在外读书还是工作,父亲都要求我回来的。这样,做清明的上山路上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了。再后来,上山路上终于出现了母亲,父亲、母亲和我,这是到了母亲已经开始担心父亲身体的年月了。持续了几年。然后终于有一天,上山路上只有母亲和我了。父亲每年做着清明,做着做着,也把自己做进了后山。我们祭奠的祖坟里,父亲也成了其中一座墓碑。
印象中后山上从未见过桃树。父亲故去之前两年,在父亲兄弟墓前,我看见两棵清瘦翠绿的桃树并肩而立,桃花璀璨如血。父亲说,这桃花开得真好,我要写一首诗。我说,今年才看见它们,明年更长些,会开得更好。下一年,却不知是节气未到,还是雨水过于充沛,我们上山时,两棵桃树竟然没有开花。一身青绿,在满山之间,也就泯然于众了。父亲和我都看见了,父亲没有说话,我说,今年没有开花。父亲笑笑,也没有给出什么理由。我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不祥感觉。父亲终究没有为桃花写诗。这一年端午凌晨,父亲突发脑溢血,二十四天后,故去。那时之前,乡下流行火化,而且要求统一在公墓安葬。我随舅舅、叔爷去了公墓,还找朋友帮忙,但仍然被告知公墓业务繁忙、人手有限,最早五天后下葬。回来与家族老人们聚一起商议,说政策现今有所宽松了,决定还是土葬。就这样,父亲也进了后山。捧着骨灰盒在送葬队伍前面走进后山的途中,我在想,也许父亲是不喜欢后山的。父亲壮年时把生意搬到集镇边的国道上,可能就是想逃离什么,但他终究又回来了,不管他愿不愿意吧。他葬在奶奶旁边,那也算是重新陪伴在母亲身侧,是一种生命回环和圆满了。
后山上有映山红、迎春花、金银花、老虎花、紫藤,还有很多我不知名的花朵。每年回家做清明我都要摘一些映山红。后来不再采摘了。就让它们生长在山上吧,在漫山青绿中暗自绚烂和凋谢,不是更不辜负天时和生命吗?再有一年春日,路过一个老乡门口,看见一束火焰般繁盛的映山红,已经长成了一棵高挑的树,问所由何来,答曰挖自后山。也曾起心动念和母亲说起,可否在后山物色移栽一棵下来,精心培育。但终未出口。映山花,啼血杜鹃,在父亲故去后,更不合适了。
有一年做清明半途,我对母亲说,我要上毛尖去看看。小路难行。真实的大荒山原来是这么窄小,那些年我们觉得总也跑不到边。也不再是一览无余的草皮红土,而是长满了杂树,中间更是架起了两根芜杂的电线杆。我走到蚱蜢山就放弃了。听说山林里又出现了野猪。以前山路寸草不生,路也宽阔,两边全是纹理明晰的山地和满山耕作的人。现在土地荒芜,已被茂密的草树覆盖。路边尽是新旧不一的坟墓。旧时人物,叔伯爷婶,也已经终成黄土。
村庄的屋舍原都窝在一起,屋檐相接,推窗可见隔壁人家饮食起居,曲里拐弯的青石小路也因终年难见阳光而潮湿难行。四邻虽因此并不疏远,但细碎矛盾也层出不穷,有些因袭祖辈积怨更是无解。不知何年,村舍与后山之间筑起一条土路,尽管狭窄、尘土飞扬,也算通衢的县道了。村舍至后山呈向上攀升之势,土路高过多数人家的屋顶,车辆仿佛在人的头上开。或许是出于这些原因吧,父亲一结婚,就开疆辟土在土路与后山之间换来地基,建房单过。车辆压过土路的轰隆声不再是夜里的噩梦之源,反而成了一道风景,儿时的我看着从一座山坡上出现终又消失在远方山麓深处的车辆,总是梦想着赶紧有一天去远方。
父亲的房子是第一户,没多久,父亲的堂兄也搬迁上来了,在左边。然后是隔几代的堂兄也搬到右边来了。父亲这一代人读过些书,多是老三届的高中生,胸有抱负却因推荐考试政策而错失入学机会,那年月,贫寒子弟几无被推荐的幸运。但他们显然又是不甘于窝在乡村的,脱离纠结缠绕的村舍似乎就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个标志和象征了。再后来,又是祖上外姓入赘村里的两户。每家的孩子都和我差不多年岁,土路之上也乍然热闹起来。在原先的村舍与后山之间不仅有了土路,还有了我们,而后山也似乎就是我们独享的了。
早些年,父亲外出做过各种生意,卖毛线,做粉丝,卖石磨,挑小鸭。父亲得管手下三十多人的吃喝住行。每两三个月过去,快到父亲回来的时节,母亲就安排我站在土路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与后山连绵相接的远方山麓,等着父亲的身影出现。父亲从那里出现再走到家,也不过十五分钟,然而这提早知道消息的片刻就能让母亲人生平添许多喜悦、激动和幸福,我也是。父亲三十出头,就结束了在外奔波的生活,扩建房舍开办了炕房,孵鸭子,后来又开起了加油站。
一九九七年,道路规划改变,新修国道横贯五公里外的集镇而过,门前乡村道路上行人日渐稀少,加油站生意也就门可罗雀了。父亲不愿抛弃旧业,决然卖掉老屋,举家迁往集镇,开办新的加油站。这本是不得不为的无可奈何之举,但因地基、建房、重新置业而大额举债。父亲在债务中困顿了十数年之久,等终于脱身,他已迈过五十五岁,岌岌晚年了。从搬到土路之上,再搬至国道,看似都为一时情势所逼,但在我的感觉里,父亲似乎一生都是在逃离,逃离被宿命钉在那的乡村。而我,看似已成功逃离了,却又因为自己在经营多年的城市依然感觉无根,仍不时念想着重归故乡。
买去父亲老屋的也是一个村里人。丈夫在外务工摔断了腿,用残疾赔偿金支付了购房款的一半。他妻子从胎里带出来的残疾,左手手掌向下窝在掌心处一生无法伸直。我回故乡做清明时偶尔会看见她,她会客气地说声,地里有青菜,摘点带回去吧。不知哪年,他们推倒了原来的老屋,建起了二层小楼,但原先临路的加油室一直没变,西侧供炕房师傅歇宿的长排房子也一直在,还有猪圈、厕所,也多年保持原样。再过几年,可能因为路上车辆少了,而且也铺设了水泥路面,父亲原先在门前种植的数十棵杉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无需再防灰尘,它们被连根挖去。再有一年回去,多余地挂了很多年的父亲堂兄用隶书写的木质招牌——晓晓加油站,也从加油室的墙上被摘除不见了。我不知道屋前的那口多年前酷夏之际十几个乡亲打的十三米深的水井是否还在,是否也已被填平。我每年路过老屋一次,但从未拾级而上,进入它。再又一年,高高垒起的种杉树的石基坍塌了部分,石块滚落到马路上,占据了部分路面,也无人清理。马路之上,相比初时,更多了几户人家,但几乎不见门开和有人走动。村人也越来越少了,年轻点的都外出务工,也有少数如我一样,流落外乡似乎再也不回来了。
一个村庄的人,往上数五代都是一只锅里吃饭的人,买房者的亲戚也是我的童年伙伴,有一年在我生活的城市里偶遇,交谈中得知他竟也已在此地生活多年,但户口还一直在老家。我们聊着童年游戏趣事、伙伴们走向、故乡风土人情、老宅,他说他家老宅门前两棵桂花树被某人挖走,他找那人,那人却不承认,为此过去了很多年依然愤怒难消。他又说,虽然已在家乡县城里置了房业,但老宅他仍然找人修缮过,这些年他只梦回故乡,从未梦过现在住的县城房子,而总是回到老宅,那里面的点点滴滴都是小时的样子。我突然说,你能否去和你那亲戚说下,我想把我父亲的房子重新买回来。他确定我不是开玩笑后,嘿嘿笑了笑,然后满口应承下来。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帮我说过没有。大概率是没说。因为事后没有人会把我的这种话当真。
年关前,我联系上父亲堂兄,又说到想买回老屋事宜。他问,你买来干吗?我说,自住,我还是想回村里。他说,现在村庄和当年不一样了,没什么人了。我说,你帮我去说说,问问价。他说,等机会,我试试看。
晚年的父亲开始写诗。他写过一些关于山的诗,比如2018年9月22日,《恒山玄空寺》:龙游天下落恒山,小寺腾空峭壁间。疏影风来惊日月,佛光窗入照人寰。钟声云载枝头渺,梵语烟沉鬼域般。莫道壮观千古在,谁知太白几时还?2019年5月21日,《小重山 送春》:一道残阳水卷风,流光桥急速、夜匆匆。花前疏影透帘栊,胭脂淡、奁匣换姿容。远树啭山中,枝头横点点、落无穷。堪怜此景觅行踪,春何往、几度问苍穹?但没有一首是关于后山的。这些年,学习、工作和旅行,我爬过很多山,生活城市里的宝石山、老和山更是每月都要登临几次,但除了后山,从未有山入梦来。也许在父亲心中,后山是要逃离的。我不知道父亲如果知晓我想买回老屋,会作何感想和评价。母亲是不赞成的。对老屋没什么好留恋的,母亲说,你父亲也不在那里了。但在我,买回老宅绝非一时念想,而是已成执念。我会复原它最初的格局,而且要在平层之上造一座阁楼,开窗面向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