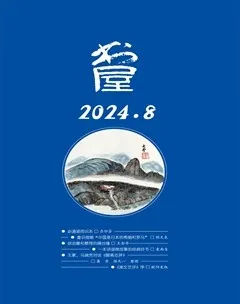痖弦与洛夫的友情与诗情
洛夫(1928—2018)与痖弦(1932—" )是享誉海峡两岸的诗人,他们逾一个甲子的友情与诗情是华语诗坛的传奇。
痖弦回忆,第一次见到洛夫是在1954年11月下旬,从复兴岗学院影剧系毕业分配到左营不久。一天,左营“四海一家”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迎新活动,在即兴节目环节,一位帅哥走上舞台引吭高歌,唱的是李中和写的《白云故乡》,博得了一片掌声。帅哥唱完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走到坐在最后一排的痖弦面前,问他是不是叫痖弦,痖弦带着几分腼腆回答“是”。帅哥便说“我叫洛夫”,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本新出版的《创世纪》创刊号(1954年10月出版),扉页上写的是“哑弦兄赐正" 弟洛夫敬赠”的字样,落款日期是11月24日,将“痖弦”的“痖”错写成了“哑巴”的“哑”。在这之前,他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见过各自发表的诗作。痖弦接过《创世纪》,对洛夫说,自己读过他发表的诗。洛夫高兴地说:“这个诗刊我们已经出了创刊号,希望你入伙,张默和我再加上你,一起干一番事业!”一周后,张默来找痖弦,一见面就热情地说:“我们非常希望你入伙,加入《创世纪》。”两人就《创世纪》的计划和发展谈了一个多小时,事情敲定后,然后一起兴致勃勃到附近的小面馆喝了两整瓶乌梅酒。这样痖弦就正式加入了《创世纪》团队,开始第二期的准备和编务工作,并分摊三分之一的印费(当时每人一月的薪水才两百元新台币,每期刊物的费用需四百多元)。就这样,由三个年轻人结成的《创世纪》“铁三角”(洛夫语)在左营形成了,在它的支撑下,一个诗刊及其衍生的文学社团的生命,发展、延续了半个多世纪。2024年,这份诗刊将迎来七十周年的诞辰纪念。
三个年轻人,性格各有特点,洛夫有“湖南骡子”脾气,憨厚而刚直;张默办事干练,直人直语,行动带风;痖弦则沉静而稳健。工作中的磕磕碰碰是少不了的。张默和洛夫一旦吵起来,痖弦就成了“他们中间的缓冲地带”,不会闹僵。回顾《创世纪》走过的艰难岁月,洛夫深有体会地说,这份刊物能够坚持下来,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志趣,相互的尊重与默契,以及性格上的截斩补断、优弱互济”。痖弦谈到三人合作办刊的体会时说,诗人都是十分个性化的,绝对地排他,三个个性鲜明的人办一个刊物要一直融洽相处是十分不易的。但三人互相欣赏、吸引,并善于彼此保护,才一路携手走下来。正如李白的诗所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由于彼此形成了很好的友谊和默契,从而做到了“一辈子在一起,比亲兄弟在一起的时间还久”。对台湾岛上的文学刊物、社团的兴衰司空见惯的白先勇赞扬,“《创世纪》是九命猫,永远死不掉”;余光中羡慕地指出,“《创世纪》的幸运就在聚而不散”。是难得的因缘际会和彼此的珍惜,成就了宝岛诗歌史上《创世纪》的传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办刊时,三人都是二十多岁,洛夫年岁最长,张默居中,痖弦最小。以年齿排序,洛夫被尊为老大。在痖弦眼中,年长四岁的洛夫,似乎比自己大了很多,也成熟很多,因此他平时注意维护洛夫大哥的地位,向他请教也多一点。在左营工作期间,痖弦与洛夫一度既是同事,又是室友。两人住在一间宿舍里,经常彻夜谈文学诗歌,并一起“飙诗”,你写一首,我写一首,比赛看谁写得快、写得好,就像当年高更和凡·高飙画,凡·高画一张,高更也画一张,彼此对着干,将每一首诗的诞生都看得无比庄严,仿佛自己写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诗。尽管暗中较劲,但两人从来没有因为这种写诗“比赛”翻过脸,所以远比高更和凡·高走得久。
痖弦对洛夫既尊重又佩服,尤其佩服老大的见识和文字功夫。他回忆和张默五十年代末编辑《六十年代诗选》时,诗选编好后,觉得序言很难写,于是求助洛夫,洛夫接手后,很快就写成了,痖弦和张默读了都很满意,将它“置于卷首,感到这才像一本正式的书”。此后痖弦与洛夫、张默多次合作,主编了《七十年代诗选》《八十年代诗选》《中国现代诗选》等,并一同成功策划了不少推动海峡两岸诗人交流的活动。
痖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搁下诗笔,将主要精力投入了编辑和评论,为推动台湾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了《聚伞花序》《记哈客诗想》《诗人小札》等数十万字的文学评论、随笔,成为集诗人、演艺家、编辑出版家、评论家于一身的宝岛文化名人。痖弦的老友余光中曾撰文对痖弦一生的成就作出高度评价:“痖弦先生对于台湾文艺的贡献依分量之轻重,该是诗作、编辑、评论、剧艺。他写诗,是扬己之才;编刊,是成人之美”,“评论以回顾新诗发展与为人作序为主;剧艺则以主演《国父传》闻名……”,“但是痖弦最大的贡献,仍应是现代诗之创作”,这些诗作“量虽不丰,质却不凡,令文学史家不能不端坐正视,更遑论一笔带过……”,“从他停笔迄今,已近半个世纪,无情的时光显然忘不了他”。
余光中依分量之轻重将痖弦一生的活动概括为写诗、编辑、评论、剧艺四部分,表明痖弦主要是一位诗人,兼具编辑、评论家和演艺家等身份。
而洛夫则将主要精力投入现代诗创作,凭借不断推出的一部部新作,特别是七十三岁以后创作的三千行长诗《漂木》,登上个人创作的巅峰,赢得华语诗坛的高度赞誉。以至于搁置诗笔多年的痖弦,在公开场合笑谈自己是“早年结扎”,洛夫是“高龄产妇”。尽管如此,宝岛诗坛并没有忘记痖弦。1999年,他早年的长诗《深渊》和洛夫的《魔歌》一道被评为台湾文学经典。
为避开台湾岛上的喧嚣,痖弦和洛夫退休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后移居加拿大,两人分别在大温地区的列治文、三角洲购置了一幢宽敞的独立屋,并各自为新家取了一个不俗的名字。洛夫的新居名为“雪楼”,洛夫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在冬天可以在二楼凭窗观赏雪景,另一方面则寓意自己纯净、冷傲的个性,意味着一种孤寂、冷静的存在。痖弦则以妻子张桥桥的名字将新居命名为“桥园”,它的寓意就是爱,是痖弦为妻子和一双女儿构筑的爱的家园。两家相隔约二十分钟车程,因为琼芳和桥桥的密切联系,洛夫、痖弦更是对方家中的常客。2005年桥桥去世,女主人走后,桥园顿时冷清。2017年6月,洛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不久洛夫去世,痛失相交逾六十年的故人,痖弦倍感伤心。温哥华的文学团体几次去桥园采访痖弦,谈到洛夫时,老人都难免落泪。伤心的同时,痖弦对洛夫褒扬备至,称赞《漂木》是华语诗坛“航母”级的史诗,并借用弘一法师的话,说洛夫一生“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一位“完成”了的诗人。痖弦的这些评价都被研究者作为权威性的观点,写入有关报道或论著中。
洛夫对机智幽默、才华过人的痖弦很欣赏,他在执笔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选·序言》《〈创世纪〉五十周年特刊前言》《洛夫谈诗》等文章或著作中,称赞痖弦有一支富戏剧性的诗笔,写的诗幽默甜美。他对痖弦的长诗《深渊》等现代诗的实验之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赞扬痖弦的《诗人手札》是“脍炙人口的现代诗话”。
这两位在诗坛上惺惺相惜的诗人,生活中更是像兄弟一样亲密相处。1959年,洛夫与陈琼芳情定金门,洛夫的朋友中第一个知道的就是痖弦。第二年,琼芳从金门调往台北平溪的一所小学,痖弦的名字便经常出现在洛夫给爱人的书信中:
下午辞别他们(按:几位台大的学生),我与痖弦便沿着大街散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告诉我说:“你的陈小姐很棒,风度非常好,是不?”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余光中太太说的,他说余太太非常欣赏你……痖弦风趣幽默极了,天分很高,个性尤其温和可亲。他虽未见到你,但对你印象极佳,他很想见到你,但目前受训较忙,将来有时间我会带他来平溪一游的。
……今天上午我仍决定礼拜天去看你,可是刚接到好友痖弦来信,约我星期日上午十时在台北市见面……所以星期天我不能来平溪了。请你原谅。……
1961年10月10日,洛夫与陈琼芳在台北结婚。由于痖弦、张默等好友的全力操持,婚礼办得风光、热闹。以饰演孙中山闻名的痖弦作为伴郎,给洛夫、琼芳这对新人的庆典出彩加分。婚后,洛夫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痖弦“很关心我们婚后的生活,他说我能娶到这样好的新娘,是我前世修来的”。
琼芳不久从平溪调来台北市,他们在台北定居后,痖弦自然成为这个新家庭的常客。后来痖弦与张桥桥结婚,桥桥与琼芳又成了亲近的闺蜜。这两个甜蜜而充满文化气息的小家庭,赢得了台湾诗坛和文化界不少人的称羡。
洛夫练习书法,也是接受了痖弦的建议。洛夫的字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算是写得较好的,痖弦便建议他在这方面着意发展一下,洛夫接受了他的意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五十岁的洛夫在写诗之余,开始研习书法,广泛临摹碑帖,并拜台湾著名书法家谢崇安先生为师。不到十年的时间,洛夫在书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经过几十年的沉潜苦练,到晚年已十分纯熟,自成一家。
1991年,痖弦以一笔补偿金在老家南阳盖了一座房子,作为以后回乡探亲的住所,房子由老屋拆下的旧砖与新砖混合砌成,有香火传承之意。洛夫特意用擅长的行草,在四尺宽的宣纸上写了一首《痖弦以泥水掺合旧梦在南阳盖座新屋》的隐题诗(藏头诗),作为礼物送给他:
痖默缘于尘世的
弦断,而内部的喧嚣须
以非耳之耳倾听
泥性与根性同其不朽
水把他送上岸就一直维持着泪的咸度
掺着血的酒脸色越喝越白
合十的掌翻开来随即掉下一捧四十年前的雪
旧是旧了些
梦制的棉袍上缀满了新的补丁
在菟丝花正从
南方回来寻找妹子的时候
阳光温暖仿佛童年。他在水边
盖了一座瘦小的桥一间青灰瓦屋
座落在忧郁而出颤动的红玉米上
新砖旧砖都是大地的骨头,一经砌合
屋顶便爬满了偷窥的天使
诗中写痖弦年少(十六岁)来到台湾,从此与远在南阳家乡的父母隔断联系(“尘世的弦断”),但诗人的乡情不改,中原之子的个性不移(“泥性与根性同其不朽”),今天这幢旧砖与新砖混合砌成的新屋,既沉淀着痖弦四十年前童年的旧梦,也表达出对先人的告慰与缅怀,同时寄托着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菟丝花、红玉米都是痖弦诗中出现过的意象,“瘦小的桥”喻指痖弦的妻子、桥园的女主人张桥桥。痖弦对洛夫这首用心的诗作十分欣赏。1992年9月,痖弦回大陆探亲,将洛夫的题诗带回南阳,装裱后悬挂在新屋大厅的粉墙上。洛夫这幅以别具一格的隐题诗和行草书法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众多乡亲前来观赏。
2005年,痖弦发妻桥桥去世,这对痖弦是个很大的打击。这年除夕夜,痖弦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雪楼向洛夫伉俪提前致旧历新年的问候。洛夫感动不已,写了《除夕痖弦夜访》一诗表达纪念和感谢之情:
略带病容/所以步履也就从容了/咳嗽/比鞋声
先一步进入厅堂/然后通的一声坐下/有着历史的沉重
……
他喝口茶说:/就只剩下一屋子寂寞的青铜器了
还有一串/孤悬风中丢了魂的红玉米/不朽……
……
而家么/却已被桥桥连同冷锅冷灶/搬去了深山……
……
窗外仍在下雪/摇椅上小猫诗意地躺着
桌上的酒杯诗意地空着
……
他的弦/是真的痖了……
这首情调感怆的诗,以沉重、悲戚的语言,写出了桥桥走后桥园的冷落、空寂,表达出洛夫内心的伤悼和对失去老伴的痖弦的深切同情,这是作者和琼芳对桥桥的再一次送别和深情缅怀,催人泪下。
……
2018年洛夫去世以后,陈琼芳将洛夫生前写给她的部分书信整理出版,请痖弦题写前言,痖弦写道:“如果两家人,先生和先生是好友,情同兄弟,太太和太太也是好友,情同妯娌,这在中国称作‘通家之好’,洛夫、琼芳、我和桥桥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再加上洛夫和我同营吃粮,隶属同一单位……结婚的时候我又是他们贤伉俪指定的伴郎,……再加上一起办诗刊《创世纪》六十余年(现在还在办)。两家人又都移居加拿大,同住在温哥华,关系真称得上非比寻常,简直可以说一辈子都在一起。……”
这段话为洛夫和痖弦一辈子的友情、诗情及两家数十年的交情作了感人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