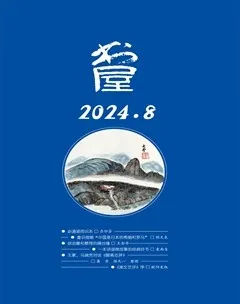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
自2002年第一次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处女作《长门赋》以来,阿袁创作的每一篇小说都延续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在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总能够找出一些经不起审视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就会以绕指柔的方式成为故事内在的矛盾,这和我们熟悉的人物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情感纠葛是不同的。在任何小说中都会有矛盾,即使是在汪曾祺那种岁月静好的小说中也有,只是说这种小说中矛盾不表现为一种剑拔弩张的冲突,更多是以语言、形式本身等来展现,或者说,矛盾在这里就表现为一种张力。任何好的小说都是有张力的。阿袁曾在一个访谈中阐释了她的创作动机,她看了《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小说,觉得特别好,但绝对不会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相反,她很喜欢毛姆的小说,比如说《午餐》,对她而言就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于是受它的影响写了《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这个短篇小说。但不论是托尔斯泰、普鲁斯特还是毛姆的小说,都是在写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只不过《战争与和平》中的背景就是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
着眼于以《公寓生活》为代表的阿袁小说,它们与毛姆那种日常和惊心动魄更为靠近,也更为靠近我们第一印象的“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其实不只是毛姆,阿袁一贯推举的作家,像爱丽丝·门罗、约翰·契弗、克莱尔·吉根、契诃夫、李翊云,甚至还包括石黑一雄和格雷厄姆·格林的一些小说都是如此,都写的是平凡的生活小事,但经由他们的笔,平凡也变得不平凡。阿袁说过一句话,叫“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但人生很多时候经不起审视的”。上述作家就是将这种经不起认真审视的人生认真审视,将它们展现在读者眼前,或者用贬词褒用的修辞来看,是有一种“暴露癖”。当然如何展现“暴露癖”,“暴露癖”展现的效果如何,各个作家是各不相同的,譬如说阿袁直接承袭的是毛姆《寻欢作乐》的毒舌,又承袭了门罗《乌得勒支和约》那种幽深平静的叙述方式,也承袭了钱锺书文本中的女性书写方式和张爱玲笔下的文艺情调,最终形成了她独特的“将简单的事情讲复杂,在复杂的事象背后有一个幽深主题”的叙述方式,将来龙去脉不断皴染,像剥洋葱似的,似乎永远藏着一半没讲完的内情,吸引读者一次次观察到日常生活中新的惊心动魄。
《公寓生活》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在阿袁的小说中,除了《小诗经》自带一种强目的性的正派作风,其他的小说都有一种天花乱坠、花团锦簇、艺术性的光芒盖过了思想性的观感。所谓的“公寓生活”,和张爱玲笔下那种充满市井气的小市民的公寓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一个在上海,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公寓,鱼龙混杂,人与人在熟悉与不熟悉的界限之间徘徊,有些破败但又生机盎然;另一个是高校的“青椒”公寓楼,里头住的都是博士,还有一个活跃度高的聊天群,活动范围局限于高校,生活于斯的人互相之间知根知底,但又有一种“高知”的乏味和酸腐气;但不论是在张爱玲还是阿袁笔下,公寓里生活的人不论阶层与社会地位,都是凡人,都有抛却外在东西的嬉笑嗔痴,从猎奇的眼光来看,都是饮食男女。因而,这就是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和阿袁《公寓生活》日常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面,那些除却了附加东西的最本真最赤裸裸的人,尤其当普通读者对他们知之甚少,甚至只有一个模糊的光环式印象的时候,经过作家祛魅和事无巨细的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便或者此起彼伏,或者一直保持一种高亢的姿态,一切都因读者的个性特征和阅历而异。但毫无疑问,只是程度不同,它确实存在。
如果说,在小说的主人公文学博士潘苡宝身上,还看不出太多这方面的惊心动魄的话,那么在她的师姐马小芒博士身上就很能体现这一点。潘苡宝养了两只猫,名字叫斯万和布丁;和父亲老潘亲热,喜欢联合他一起对母亲周莉莉采取反抗和卫护自己思想独立性的措施;对谈恋爱、结婚不怎么上心,遇见合适的男人再说,绝不将就。除此之外,就是在自己的教学和日常生活中游走,有点慢悠悠的有条不紊的态度。而这可能对年长一辈、思想有些保守的人来说会有一点“惊心动魄”,但这类人群应该是不会有耐心将阿袁的小说看下去,或者说勉强看了一本以后就不会再看第二本;而思想不那么保守的年长一辈和年轻的新一代人,潘苡宝的言行取向和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不说是认可,至少也是深有体会的,那这类读者阅读完《公寓生活》之后就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而是另一种有关“心心相惜”的复现型心理机制了。所以,女主人公潘苡宝身上缺少的和这篇文章命题相关的品质,在师姐马小芒等人身上反而非常吻合。
作者阿袁的声音经常介入小说中,几乎每部都是这样,这已成为她的一种写作惯例和策略。惯常的写作规范告诉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要让人物自己说话,每个人物都有他们的生命轨迹,作家不应该用自己的主观话语介入笔下人物的人生,这样是观念先行的象征,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毫无疑问是失败的。然而,阿袁的小说却是一个反例,即使她认为自己以往的小说都是从人物出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看到某个想写的人,便以其为原型写一篇小说。而她跟笔者说也曾用过另一种方式写小说,那就是这种观念先行的方式,比如曾在《十月》上刊发的《有一种植物叫荚蒾》和在《广州文艺》上刊发的《像春天一样》,似乎也行得通。当然,不管是这两种写作生成方式中的哪一种,其实都是作者话语介入的写作。它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进行一种缠绕式的“连篇累牍”的发声,而到这种“连篇累牍”的时候,恰恰是阿袁写作“爽感”到来的时候。于是,作者自己的声音盖过人物本身应该发出的声音,起到补充故事主体情节甚至是引领故事发展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读者经常诟病的“掉书袋”,但它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写作,几乎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照样取得了巨大成功。只不过,阿袁在《有一种植物叫荚蒾》和《像春天一样》中更进一步,但也只有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读者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微妙之处。
这并不意味着阿袁完全放弃了“让笔下人物自己说话”的创作策略。其实还是一个分寸感的问题,阿袁在课堂教授小说写作的时候,一直强调这一点。阿袁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坚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依旧有几条岔路,一条通向理念式写作,一条通向类型化人物,做得极致的可能是卢梭的《爱弥儿》这类小说。而阿袁显然是要更进一步,不仅在于写作技巧,也在于书写当今时代的人物,比如说她曾对契科夫对年轻一代写作者的指导意义产生自我诘问。契科夫小说虽然因为他所书写时代的缘故,可能有一些难以适应当代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过时。而正是在这一复杂的作家个人创作机制的引领下,以《公寓生活》为代表的小说才会有另一维度下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这可能是大多数读者身临其境但却未曾意识到的存在。
活色生香的东西和庄严的现实主义交相辉映,在作家本人的加持下,共同构成了阿袁在当代文坛上近乎异数般的存在。或许可以用阿袁的短篇小说《亲爱的苏图》创作谈中一句话来收尾,那就是:“我们偶尔可不可以也过一过不正常的人生?”在这里,笔者以“不正常”一词对《公寓生活》这部小说做了个性化阐释,即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我们偶尔也可以过一过“学优品不优”的人生。这也许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的深刻之处。
放在知识分子写作的谱系中,阿袁的小说与齐邦媛《巨流河》、宗璞《南渡记》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题材大不相同:在后者的写作中,并不存在将“日常生活”作为限定词的“惊心动魄”,而既是“日常生活”,又要“惊心动魄”,有一种平凡中的伟岸与责任。阿袁的写作或许可以称为一种“新知识分子写作”,或者说“新文人写作”,从钱锺书《围城》一脉沿袭下来,在当代,和张者的“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等同属一类。但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其一,这种“新知识分子写作”并不可以简单视作“传统知识分子写作”的延伸,也不可以说是背面,另外这二者并不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它们在当代可以同时出现,交叉并行,只不过从源头来看,确实是“传统知识分子写作”在先。此外,“传统知识分子写作”可能对“新知识分子写作”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其玷污了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和光辉形象,而“新知识分子写作”则以先锋态度和对当代知识群体的写实著称,对“传统知识分子写作”的近乎卫道者的形象不屑一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不同方式的写作,不论是“传统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日常生活的风骨”“惊心动魄的人格魅力”,还是“新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惊心动魄的日常”“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在当代并行不悖,都有着庞大的读者群体,引起学界重视。其二,阎真、张者等的写作都是“惊心动魄的日常”,因为他们太过于写实和白描,以致到了尖锐露骨的程度,而阿袁的写作则以古典诗词入手,以典雅的语言娓娓道来,在花团锦簇中超越了“为写知识分子而写”的理念,充满了“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的延宕感,而这或许就是阿袁小说在“新知识分子写作”谱系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