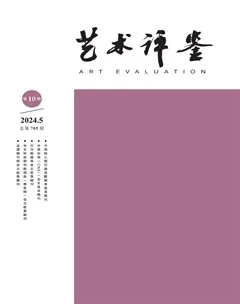白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交融研究
【摘 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背景下,白剧作为承载着600多年以来深厚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少数民族戏剧形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成为研究的焦点。本研究聚焦于白剧的音乐韵律、人文精神、宗教内涵及民族特性,通过分析其跨世纪的传承与发展脉络,探讨在弋阳腔融入后所形成的特殊艺术风格,以及白剧在民俗文化与戏剧史上的地位。本研究不仅旨在深入挖掘白剧的艺术特征与历史变迁,还着重强调其在当代社会中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这一研究对于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及推动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白剧 声调韵味 音乐分析 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0-0141-06
白族戏剧体系主要由吹吹腔与大本曲两类组成,二者共同构筑了白剧的核心。吹吹腔戏曲,历史悠久,早在“白剧”正式命名之前,便已在大理地区广泛传播并达到成熟阶段。大本曲,作为一种盛行的说唱艺术样式,在大理平原地区深受白族民众的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剧目革新与表演实践的频增,大本曲进化为大本曲剧种。基于增强白族戏剧多样性及组建专业剧团的需求,吹吹腔与大本曲实现了融合,共同被界定为同一剧种——“白剧”。
一、白剧研究的历史和发展
白剧的历史悠久,其源头可追溯至明代洪武年间,当时从中原地区传入大理的吹吹腔戏与本土的大本曲相互融合,共同孕育了这一独特的剧种。然而,历经时局变迁,到了民国初期,吹吹腔戏遭遇了衰落的命运,逐渐退隐至偏远山区。直至1962年,这一蕴含白族古老文化精髓的戏剧形式被正式命名为“白剧”,标志着其身份的确立与重生。白剧的唱词创作深受白族诗歌“山花体”的影响,普遍采用白语与汉语双语演唱,展现了丰富的语言美感。其音乐体系中包含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唱腔曲调,每一种都富有表现力。在表演上,白剧强调节奏感与规律性,风格古朴纯正,遵循着一整套严格而规范的艺术程式,体现了白剧深厚的传统底蕴与审美特色。在国内,白剧的研究历史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50—70年代:起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促进白剧剧种体系的建立健全及白族专业化剧团的实体化进程,戏剧研究者广泛实施田野作业,深入剧种发源与流行的腹地,精细探究剧种的历史变迁与现存生态。这些实证性研究活动为白剧研究奠定了基石,包括但不限于吹吹腔与大本曲的直接考察、剧本曲谱的收集与编纂,以及对剧种历史根基的初步探索,同时以编年序列形式描绘了剧种演进的路线图。《云南兄弟民族戏剧概况》一书集成了8篇白剧研究论文,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广为流传的剧本与曲谱资源。其中,《白族吹吹腔剧、大本曲剧的发展和改革》一文,更是集中探讨了白族戏剧种群的演化问题。
(二)20世纪80—90年代:发展期
20世纪80—90年代标志着白剧研究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与深化阶段,研究重点从基本的历史叙事转向了深入的史学理论分析,从而促进了对白剧历史线索更为精细的理解。面对戏剧界普遍面临的“危机”挑战,白剧如何在逆境中维持生命力并持续发展的议题,成为学术界聚焦的重心。这一时期,吹吹腔的起点、变迁过程,以及白剧整体的发展脉络,构成了研究者们集中探索的核心问题。黎方在相关研究里论断,吹吹腔的雏形可回溯到安徽、湖广地区的吹腔与罗罗腔传统,这些戏剧样式伴随明末清初大西军的迁徙传入云南地区,随后逐渐与白族本土的文化、语言、艺术表达及宗教信仰融合,并吸纳了其他戏剧流派的特点,最终演变成具有独特风格的白剧吹吹腔。《中国戏曲志·云南卷》中关于“白剧”的记述表明,吹吹腔的起源可能植根于民间的歌谣和唢呐演奏实践。其发展在经历了与外来音乐风格及戏剧形式的融合后,于清朝雍正至乾隆年间初显形态,并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逐渐完善成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类志书、集成及资料集的编纂工作,对白剧历史的研究成功地由简单的描述性记载,跨越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性分析,标志着该领域知识研究的重大飞跃。
(三)21世纪:深化期
进入21世纪后,白剧的研究领域迈向了一个深化的崭新阶段。这一进展不仅是学科内部深化演进的自然响应,也受益于多种外部积极因素的协同促进。此时期,对白剧剧种发展历程的挖掘达到了新的深度,所累积的研究成果成为构筑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标志着白剧历史研究正式跃升至理论解析的新高度。具体来说,《云南少数民族剧种发展史》的第二章、第六章第一节及第七章第一节,从宏观角度系统化地概述了白剧的发展轨迹。此外,《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的第八章专门针对白剧,全方位剖析了其历史背景、当前状况,包括剧团运营机制、演员队伍构成、代表剧目的分析、舞台艺术实践的探索以及演出传统的继承等内容。在《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的三卷版本中,针对白剧的探讨进行了详尽的历史回溯及深度分析,着重探讨了吹吹腔与大本曲两种戏剧类型的发展轨迹。薛子言和薛雁全面概述了白族吹吹腔的剧种演进史;而张亮山则深入挖掘了吹吹腔的起源流变、艺术表现特点及其舞台呈现形式,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与拆解。《大本曲简志》,主编单位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并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03年正式发行。作为首部专注于大本曲的专著,它全面论述了大本曲的历史变迁、地域传播、保护现状、创新趋势、代表曲目、音乐特性及其民俗关联。
二、白剧经典剧目中的音乐分析
(一)《望夫云》音乐分析
作为少数民族戏剧中的标志性作品,《望夫云》在艺术表现上独具匠心。1980年11月,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文化部的联合邀请,大理白族自治州白剧团不负众望,将这部精品剧目带到了首都北京的舞台。随后在返程路上,又在成都成功举办了为期十一场的公演,广受好评。该剧的一大亮点在于其创造性地融合了白族传统音乐元素,既保留了古老的“吹吹腔”之韵,又巧妙融入了叙事性音乐“大本曲”的特色。这种双重声腔的结合不仅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彰显了艺术创新的魅力,同时吸纳了多样化的民间音乐素材,细腻地传达了情感深度,有力地表现了戏剧张力。其音乐构思既深邃抒情又富有戏剧冲突性。
1.遵循白语声调韵味,精准把握唱词风格
白剧唱词依循“山花体”,格式典型为四句(七七七五)、五句(五五七七五)及八句变体(七七七五重复),展现了白族诗韵的基础架构与特色。道白部分采用“汉语白音”,保持汉语表达的同时,蕴含白族语音的独有韵味,如“宫怨”开篇阿凤的吟唱所示:“锦鸡触地音留痕,无影矢啸耳边震;邂逅陌路情愫生,心随风而逝!”在音乐创作实践中,作曲家张绍奎坚持与白族语调的自然起伏相协调,巧妙地在旋律骨干音周围布置倚音以作修饰,并审慎地嵌入衬词,力图实现吐字清晰及腔调圆融,从而深化了唱腔的艺术内涵与外延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白族民间音乐中天然倚音较为稀缺,张绍奎却创造性地大量植入前倚音作为装饰,紧密呼应白族语言特有的声调模式。此番设计不仅使唱腔韵味深长,也使得旋律呈现出丰富多变的节奏感。尽管这提升了对歌手技艺的要求,却也使得音乐作品更接地气,洋溢着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2.通过变换拍子和速度刻画人物
在第三幕“定情”部分,曲作者通过精湛的节拍与节奏编排,巧妙地塑造人物性格、氛围及情感层面,展现了高超的音乐叙事技巧。以4/4拍构建民众欢腾舞蹈的场景,生动映射出群体的生机与活力。阿龙与群演的对唱片段,利用2/4、3/4及3/8拍的灵活转换,刻画了阿龙对理想爱情生活细腻而深沉的憧憬。阿凤初现之时,4/4拍的运用象征着她从宫廷樊笼中解脱,悠享自然,漫步田野的宁静与自由,心灵沉浸在清新的自然之美中。随后,通过2/4与3/4拍的交替,阿凤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鲜明,展现了她的开朗、美丽、善良及艺术才华。群众对唱环节,则以加快的速度和4/2拍的调整,再现了民间庆典中欢歌笑语的生活气息。阿凤与青年群演的多重对唱中,变拍手法的融入精妙传达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波动。旋律的平滑过渡,如同一幅生动的山水画,深刻描绘了白族乡土文化的多彩与深厚。进入第四幕,面对阿凤身陷南诏宫廷的困境及其长期所承受的封建礼教重压,其内心情绪的压抑与焦灼,仅靠单一拍号难以充分表达,因此采用复合拍子,凭借拍内力度的动态变化,推动音乐的情感深度与动力,既丰富了乐曲结构,又深刻强化了阿凤唱段的情感强度,深切传达了她冲破束缚、向往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3.程式化在戏曲音乐设计中的有效运用
《望夫云》的音乐构思巧妙融入了大本曲的典型结构序列,即高腔、平板、复高腔、脆板与复平板,这一序列构成了白剧音乐中一个显著的“程式性架构”。作曲者在忠实遵循该程式的同时,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独创性,实现了程式与剧情发展的有机融合而非简单模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紧密贴合台词情感的起伏,精挑细选大本曲的音乐素材来细致刻画主角性格:利用高腔强烈凸显南诏王的傲慢自大、孤独高傲及霸权气概;而平板旋律的运用,则细腻传达了阿凤公主面对君父时内心交织的紧张、反叛与悲痛。乐章末段,作曲家通过对原始高腔素材的节奏扩展与速度减缓,以及旋律逐渐攀升的手法,增强音乐张力,深刻揭示了阿凤公主深邃的悲情世界。至于罗荃法师的角色塑造,则巧妙采纳并调整了脆板的节奏,生动映射了其狡诈与残忍的特性。尤其在阿凤的标志性唱段中,“面临君父流放之命,心潮涌动无边哀愁;深深鞠躬别离宫闱,决意远离皇权纷扰”。作曲者打破常规高腔旋律程式约束,通过节奏的刻意放缓,加深了情感的挖掘,有力呈现了阿凤公主对封建压迫的不满与悲凉,从而在艺术层面实现了对旋律程式运用的拓展与深化。
(二)《阿盖公主》音乐分析
《阿盖公主》的音乐独具魅力,它巧妙融合了白族民歌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剧中运用大量民族乐器,如三弦、芦笙,结合交响乐团,营造出既传统又磅礴的音响效果。歌曲与唱段设计精巧,既有激情澎湃的对唱,也有深情细腻的独唱,完美贴合剧情发展,深刻表达了角色间的爱恨情仇,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1.复调与对唱的巧妙融合
在《阿盖公主》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复调技术,通过不同声部线条的交错与对话,丰富了音乐的层次感与表现力。特别是在对唱段落,两位或多位演唱者的旋a6ApF8xddYvUKab2El5OyLhC5N2oYOB6m76jhH2MbTM=律线不仅各自独立且富有个性,还在和声上相互支撑,形成和谐又不失对比的音乐画面。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角色间复杂的情感交流,还展现了作曲家深谙传统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的融合之道。例如,在公主与其他角色的重要对话场景中,通过紧密交织的声部和精妙的和声进行,增强了戏剧张力,使观众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波动。
2.民族乐器的创新运用与音色探索
《阿盖公主》在器乐编配上独树一帜。它通过对传统民族乐器如二胡、琵琶、笛子等的创新使用,以及与西方管弦乐队的有机结合,创造出既具民族特色又不失现代感的音乐语汇。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各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表现力,如二胡的哀怨绵长用以表达人物内心的忧伤,琵琶的清脆跳跃则展现欢快场景,而笛子的悠扬高亢引领听众进入辽阔的意境之中。同时,作曲家借助现代作曲技法对这些传统乐器进行重新编排,如使用不常见的演奏技巧、特殊的音效处理等,为传统音乐赋予新的生命力,使得整部作品的音响色彩斑斓,充满新鲜感。
3.音乐结构与动机演变
《阿盖公主》在音乐结构上采用了主题变奏的发展手法,以一个或几个核心音乐动机为基础,通过调整节奏、变化旋律线条、配置和声乃至转换音乐风格等方式,随着剧情的推进不断深化和丰富音乐主题。这种手法不仅保持了音乐的整体统一性,还使得音乐随着故事发展展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例如,公主主题在不同场景中的再现,通过速度的变化(从慢板到快板)和调性的转换,既反映了角色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也推动了音乐情绪的起伏跌宕。此外,作曲家还通过对主题片段的拆解重组,创造出全新的音乐段落,这些段落既保留了原始动机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音乐新的表现力和戏剧效果,展现了作曲家在音乐结构构建上的深厚功力。
三、白剧音乐中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及其文化认同
(一)从州级团体与县级团体共同发展看文化认同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剧团,作为白剧艺术传承的核心载体,是该地区独一无二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它集戏曲、舞蹈、声乐及器乐的创作与演绎于一体,隶属于第二类公益事业机构。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该团不仅创作并上演了大量高度评价的戏剧作品,还荣耀地五度进京演出,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其作品库中珍藏了诸如《红色三弦》《苍山红梅》《望夫云》等近一个世纪的经典,为白剧艺术界输送了叶新涛、张绍奎、马永康和杨益琨等诸多大师及无数英才,集体揽获国家级与省部级嘉奖超百次,在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界树立了卓越的标杆。
与此同时,洱源县白剧团与云龙县吹吹腔艺术团作为两股重要力量,共同引领着这一艺术形式的繁荣。洱源县白剧团,起始于1959年的洱源县文艺工作队,专攻白剧短剧与大本曲的创新演绎,《审公公》和《孤雁成双》等力作屡获表彰,在当地及更广泛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云龙县吹吹腔艺术团于2016年更名为“云龙县吹吹腔民族艺术工作团”,积极推广吹吹腔小戏,《春风送暖》和《古村新曲》等剧目深受观众喜爱。两团携手并进,共同构筑了白剧艺术在专业与业余剧团间的繁荣景象。
(二)从民间戏班文化交融看文化认同
戏班作为戏剧种类展示、延续与发展的基石,构成了剧种创作与表演实践的实体平台。同时,它也是专业剧团的支持力量和传承机制的关键环节。在正规剧团体系成型前,众多源自民间自发组建的戏剧团体已蔚然成风,这些由热爱戏剧的群众和民俗文化的追随者构成的社群,因为对戏剧艺术的共同热爱而聚合,逐渐演变成观众群体的一个核心部分。同时,在云龙县内,有8个吹吹腔艺术团体活跃于民间,显示了该地区对此艺术形式的持续热情。相比之下,白族大本曲领域中的非职业剧团则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态,横跨南腔、北腔、海东腔三大风格流派,每个流派下都有多支大本曲演唱队伍活跃。
(三)从民族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看文化认同
白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宝藏,特别是其多样化的民间音乐、诗词歌赋以及舞蹈曲调,为白剧艺术的繁荣发展与创新变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活水。《数西调》剧目独到地融入了白族“本主节”庆典,通过斋奶诵念经文与神汉巫舞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既神秘庄严又富含本土宗教气息的舞台氛围。“白子情怀”片段即是对白族特有“屋寿庆典”传统的生动再现。白剧在艺术提炼中,吸收了“凤羽霸王鞭曲调”与“白族大典音乐”的核心精华,经过精致的艺术处理,生动展现了凤羽地区文化的非凡特色与韵味。《望夫云》中的“绕三灵”桥段,借用了白族同名节日习俗,主角阿龙与阿凤以白族歌调对唱,情感交流细腻,配以“霸王鞭”“八角鼓”等传统舞蹈用具及“剑川东山打歌调”,以歌舞形式展现了“绕三灵”节日的欢乐与和谐。
现实题材作品《和谐家园》,取材自洱源郑家庄的真实生活,叙述了七个民族共处一村的温馨故事,深刻探讨了民族团结的意义。该剧的音乐编排博采众长,既包含了白族热情洋溢的“霸王鞭旋律”,又融入了傣族婉转细腻的葫芦丝名曲《月下凤尾竹》,同时吸纳了彝族活力四射的“打歌”、藏族豪迈奔放的“锅庄舞曲”,以及纳西族节奏明快的“打跳”音乐。这样的音乐多样性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剧作的艺术感染力,还深刻地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对话、理解和艺术上的和谐共生,展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魅力。
四、未来白剧的发展路径
(一)垒实文化生态基土,保证剧种有“物”所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实物载体的存在性。前者着重于表现形式及其深层文化意蕴,涉及舞蹈、音乐、曲艺、戏剧、文学等非物质领域,通过非实体方式代代相传。此类遗产的传承主要依赖民间口头传播,历经岁月积淀,成为民族智慧与文化深度的载体。因此,针对这些“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策略,应聚焦于其独特属性,推行“动态保护”理念,旨在维系其活力与真实性。白剧艺术,作为源自民间实践的文化瑰宝,是民众生活智慧的集体体现。它在人际互动与传播过程中不断演变,甚至发生变异,这就要求保护措施必须具备灵活性与适应性,避免将其简化为静态文档或影像记录,仅仅作为图书馆或档案馆内的收藏品。这样的做法只会使其失去原有的活力,成为静态的“展示性遗产”。艺术的真正活力来源于民间的实践活动与传播,白剧艺术唯有在民众中持续实践与广泛传播,才能充分展现其璀璨的艺术魅力。一旦脱离民众基础,白剧艺术恐怕将面临衰落乃至消亡的严峻风险。
(二)提升创作者的创作能力,加速推进白剧艺术创作
少数民族戏剧乃至全国戏剧领域普遍面临编剧人才短缺的问题,遴选杰出编剧的工作尤为艰巨,这一瓶颈严重影响了基层剧团的发展壮大。针对上述挑战,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项策略:一是应吸纳具有专业艺术教育背景的编剧人才,他们通常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能够为戏剧创作提供扎实的支撑。二是其核心策略在于实行“实践融入”方案,创设贴近现实的环境与平台,促使这些人才深入民间,沉浸于本土文化的氛围之中,以避免创作脱离实际,确保艺术作品能深刻反映民情民意,与公众情感形成共鸣。三是对于编曲人才的创作,应强化民间音乐资源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同时,在借鉴传统与创新融合的道路上,有效整合其他民族戏剧音乐素材,丰富创作素材库,增强音乐创作的多样性和深度。
(三)提高呈现者表导演技能,促进白剧艺术的活态化传承
导演,作为剧组的灵魂人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与纽带作用。他联结编剧与演员,为剧组运作构建起稳固的基础框架。对于白剧导演而言,应当深植于白剧艺术的肥沃土壤之中,精深研究其表演体系,细致分析并概括优秀作品的表达艺术,持续积累个人的艺术修养与文化底蕴。面对白剧武戏匮乏的现状,导演应当深入发掘白族吹吹腔的传统艺术宝藏,系统整理珍贵资料。在保持白剧独特性的同时,导演还探索规范化与创新性的表现手法,为学习者与表演者设定清晰的发展路径。对于白剧演员而言,应立足现有艺术水平,积极向白族社区汲取灵感和养分,全心投入白剧角色的创造,灵活穿梭于专业舞台与民间表演之间。同时,借鉴诸如洱源县白剧团等成功案例的经验,不断磨砺演技,全面提升个人艺术素养。只有对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同,才能赢得外界的尊敬与认可,进而真诚地展现白剧的艺术魅力,生动演绎每一个剧中角色。
五、结语
自弋阳腔与大理文化融合以来,白剧音乐跨越数百年的时空维度,悠悠传响,蕴含丰富的人文情感、宗教思想及民族认同感,赋予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在中国多元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景观、戏剧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阔天地里,白剧以其独到之处卓然而立。尽管白剧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戏剧类别存在共性,但其独特的文化内核、价值观念及艺术表现形式,构建了无可比拟且不可或缺的文化标识性。因此,对白剧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不仅是对这一艺术形态本身的维系,更对其他文化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启迪与省思。
参考文献:
[1]李源,王崇屹,曹莹,等.国家级非遗大理白剧现状及传承发展策略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15):91-96.
[2]刘发有.云南少数民族戏曲剧种音乐的形成与发展[J].民族音乐,2022(04):36-38.
[3]王蕴明.盛开在苍山洱海的白剧之花——杨益琨表演艺术浅识[J].中国戏剧,2019(11):15-18.
[4]谭志湘.砥砺前行的白剧为民族剧种的发展贡献了什么[J].民族艺术研究,2020(06):20-24.
[5]王虎.白族舞蹈对丰富白剧艺术的发展将成为一块智能“芯片”[J].大众文艺,2020(11):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