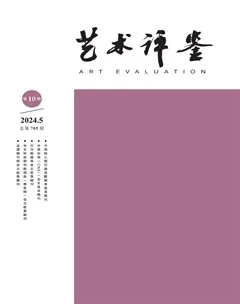论艺术审美伦理导向中的文化影响
【摘 要】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社会的全面影响已成定势,现代艺术审美伦理的研究同样无法回避文化问题。大众文化时代所承诺的审美解放却时常陷入审美困惑之中,这迫切要求审美伦理在价值和意义层面实现自我确证。在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冲突与交融不断地体现出其本真的价值和持久的生命力。同时,文化研究的理念方法和话语实践,也为审美批判提供了审视和鉴定审美价值的坐标。
【关键词】古典美学 艺术审美 审美伦理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0-0165-06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现代审美趋势的变革,以及中国古典美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这三者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也对现有的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推动了艺术创作和观众体验的变革,引发了对大众文化时代审美问题的深刻反思。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发展走审美伦理之道的批判理论,应当在古今融合的基础上,巩固中国美学理论的精髓,并延续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
一、文化对艺术审美伦理的影响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等杰出人物在文化和美学领域留下了深远影响。梁启超先生发起的“文学革命”,是近代中国最早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闯进国门的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改革尝试,被视为时代的进步象征。这场运动在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不自觉地迈出了思想启蒙和美学发展的重要一步,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运动”铺垫了前奏。“五四运动”爆发后,知识分子强调个体的创造性和自由,提出了反传统观念和新文化运动的口号。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和美学观念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同时也激发了新思想的启蒙。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涌入也催生了中国思想家对传统价值观和美学理念的重新思考。
在西方,自早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文艺研究所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及文艺对生活的功用以来,文艺就被认为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其文艺思想紧密地与社会环境相结合,明确地肯定了文艺是为社会服务的,主张站在政治标准的立场来评价。柏拉图认为:“如果作品价值影响是负面的,那无论他的艺术性多么高,也需毫不留情地把它清洗掉。”从这一观点出发,文艺的功能被强调为社会的教化与引导,这虽然与近代的文化概念不完全类似,但这些早期的哲学观点为后世的文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帮助7dd894eebfc02d7dd9401ec9fbd7a934f0a386a96c14b6cde3d431fad9d03b54人们理解了文艺作品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
从文艺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不同时期,文艺与现实的作用关系存在着不同的形式,艺术与生活也曾分属不同的领域。时至今日,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界限,文艺不仅恢复了对生活的直接作用,甚至使今日的社会生活在总体上呈现出审美的外观,总体上也符合美学原则。
近代许多中国艺术家和思想家接触了西方美学和艺术运动,进而推动了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观念的融合,使社会对艺术的接受和反应也发生了变化。观众不再仅仅注重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而更加追求艺术作品的技巧和形式美。这意味着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解读变得更加多元化,他们可能因自己的经历和情感而对同一件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这种多元化的审美体验使艺术作品更加具有包容性,能够触及不同观众的内心。
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本身正处在这种内部革命和外部交流的复杂局面中,但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它也进行了适应、创新和批判反思。在数字艺术中,人们积极寻求中国古典美学与数字媒体之间的连续性,在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平衡中,既有对其的适应,也有与其结合的表现,总之是冲破了旧意义上的统一,达到了一种新的和谐。这种数字工具、媒介、表现形式的出现,扩大了艺术表达和实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观点:数字艺术已成为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下探索中国文化身份的平台,其本质是具有便捷传播方式的媒介。这种技术的进步是艺术发展应该适应的对象,因此,应将科技进步理论作为美学发展的核心方向。
显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下中国美学正经历的一个现代化转变。然而,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刚刚开始,无论是基于社会原因还是自身理论的革命性进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都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中国古典美学在现代化的转变中,由一种超脱利害的审美心胸发展出一种“他律的”“快餐式”的审美潮流。除此之外,审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边界正在隐去:审美活动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艺术形式的范围,逐渐深入到大众的社会生活中。占据大众社会生活重心的,已经不是纯粹的绘画、文学、音乐等经典艺术门类,进行审美活动的场所也从艺术馆、美术馆等固定场所解放出来,扩展至电子媒介、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审美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空间中。
理论家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的美学特征就是“快感”:“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中。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性的语言也有很大区别。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的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也正为这种“快感”开辟道路,诸多种类的艺术作品、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无论是对艺术创作者还是观众来说都是一种刺激。这种频繁的刺激会导致两种极端的方向:其一,社会审美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格式;其二,它会引导以这种技术革命来完成目的导向的艺术创作潮流。这两种发展方向,无疑对艺术的长远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它们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生命力的一种消磨,将艺术推向一种“消遣式的”“无意义的”娱乐。例如,如今兴起的部分“沉浸式”艺术体验馆,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互动的游戏”。它虽然标榜着艺术作品的形式,但完全丧失了艺术作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从根本上割裂了情感和文化背景,带来的不过是技术革命下的一种新奇的体验。
二、艺术审美伦理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卜祀燕饮、钟鼓玉帛的活动,体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这种礼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后世哲学、美学的基础。中国人审美意象的源头活水可以说来自于此。从某种角度来看,礼乐的功用是它最初将生活与审美建立了桥梁,“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从最底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礼乐文化的这种鲜明特点,也决定了当时思想的包容性。关于音乐、舞蹈、礼仪、诗歌等一切美的问题的思考,都牵涉于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甚至与经济问题交织。与西方动辄诉诸悬置的哲学思辨不同,我国的文化源头自始就更加紧密地与社会生活相贴合。古代中国并无翻天覆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变化,因此中国文化在近代之前都一脉相承。中国哲学也承续了“礼坏乐崩”的社会生活问题。为了使士人从精神世界受到冲击的彷徨与痛苦中得到拯救,它没有从容地走向抽象思辨之路(如古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古印度),而是尝试探求人间世界的生命真意,系统地追问、反思日常生活现象的意义。
就哲学和美学思想史来说,一般选择从《老子》开始叙述中国美学史的开端。从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老子》几乎蕴含了所有中国美学思想的萌芽。在老子的哲学系统中,首先是对存在世界规律的抽象概括,而后便是在尊重存在世界规律的基础上,掌握生命之道。老子认为,生命的最大特点在于“柔”,因为“柔”意味着生长、潜能、不断发展的可能。与此相对的则是“壮”和“老”:“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五十五章)。事物达到顶峰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衰败,事物的“壮”是背离发展趋势的,其中包含了更潜在的含义,是将生命之道的“柔”作为现世世界的永恒追求,是以现世生活的无限发展为最终追求。老子还对“柔”的追求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十章)。老子哲学的长处便在于对生命整体过程的观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求现世的生长、发展,实现自身的潜能和价值。他对于生活价值的肯定,还表现在对战争引起的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伤害行为的反对。他说:“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在此便能发现,中国古典哲学不同于西方古代哲学。西方人往往因现世世界的苦难而假象出来世与上帝,以此来逃避现世、追求来世,并寻求心灵的慰藉。中西方文化迥异的所在之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盎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老子的哲学思想在之后得到了庄子的继承和发展。庄子对于生命价值、现世生活意义的追问比前人更加深入。庄子的大部分哲学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审美的态度,形成了古典哲学中道家体系的美学系统,这一系统主要凝聚在其著作《庄子》内七篇中。这些篇章无一不体现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追求,其中核心理念倡导人们回归当下生活的实际,以领略“道”之“大美”“大乐”。庄子用大量的篇幅展示了一些掌握生命意义的人,他们与天地合一,与大自然的生命共存。这种意象世界的描绘来自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和不懈追求,它缓解了人们对于生死、得失、人生苦乐的忧虑。庄子不仅倡导对死亡不忧虑,还倡导人们追求一种对生命和生活的豁达和自足。
从《庄子》著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记载的其本人——“庄子钓于濮水”“庄子行于山中”,还是他描绘的意象世界——“有着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庄子本人是一个富含生活情趣的人。在他对生命价值的判断下,虽然有宿命论的倾向,但仍然追求通过“心斋”“坐忘”获得自由的现世价值。庄子认为:“生命的本相如同大樗,无需受绳墨规矩的限制,故不夭折于斤斧之下。世间中人却总要在把捉和寻觅当中求取安全感,所以总不能避免绳墨规矩的束缚。奔忙渐久,心智既老,反把桎梏安居,错认他乡是故乡。”
庄子的思考不仅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也体现了他在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态度。他认为,只有超脱了社会生活的束缚和世俗的利害得失,才能达到“心斋”“坐忘”的境界,才能在有限的一山一草一木中把握宇宙世界的无限生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所追求的现世价值相矛盾,而这正是审美心胸对人格心灵的塑造意义,超脱利害的无功利追求并不意味着无益于人生。
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哲学史中,越是看似无用之物越是大有深意。尽管庄子的时代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但“安享无用之困苦,普外物而自得”的理念确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精神源头,更是融彻在生命之道中的审美理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在于化礼乐于生活,寓高明于中庸,以追求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统一为毕生的目标。可以说,儒家学说是完全入世的,普罗大众的道德伦理,世界的真理只在于人世间的祥和安乐,尤其是人的幸福。在肯定现世价值方面,孔子也有所论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他倡导无虑死亡,关注现世生活。另外,孔子认为可以将人的毕生修养安放于社会生活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即存在于对现实生活的认可和肯定的基础上。从他将诗的功能凝练为“兴”“观”“群”“怨”就可以看出,他对审美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功用极为关注。诗可以“兴”,是这组概念中的核心。“兴”的含义在于欣赏诗时所产生的意兴盎然的情感效果。兴,起也,也就具有了审美效果上的深意。其他的概念都是建立在“兴”的基础上的社会功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儒家的艺术观念,即以文艺的形式提升自身修养,陶冶自身情绪,以及净化社会环境,让人用温柔敦厚的修养去进行更好的社会生活。
儒家对于社会生活的阐述,李泽厚曾说过:“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界生活之中;这样,也就不需要舍弃现实世间、否定日常生活,而去另外追求灵魂的超度、精神的慰安和理想的世界。”
儒家认为,人与世间万物、自然是共同源自天地,具有相通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质。在这一点上,儒家观点和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截然不同,它强调的是共为一体的关系。世间万物,包括人类,都源自天地的和谐秩序,因而无所不通,无所不美。儒家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之深远也在于此。它为人对现实世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人的生命中最普遍、最持久的价值追求,不在于惊鸿一瞥、过人一行,而在于日常生活的平静之乐。在日常的平静生活中寻乐,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现世价值、注入丰富意义,进一步将人生经营为一件艺术作品,愈到晚年而愈能体会其中的妙境。
三、艺术审美伦理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生活价值乃至生命价值的追求在中国历经了近千年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深化,各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受此影响。18世纪,当西方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时,也逐渐兴起了这样一种美学思潮,西方的哲学家也开始注意到了人生的情感作用和真理中的生命体验,这种思潮在20世纪初的法国达到顶峰,形成了完整的生命哲学的系统讨论。生命哲学不再追求关于完美生命经验的纯粹理论知识,转而追求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目的。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无法通过抽象的理论世界,只有通过内部的直接体验才能得以理解。在这样的几乎波及全球的美学思潮下,在中国也形成了受此思潮影响的美学命题,理论来源一方面来自西方美学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即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命价值。
近代哲学家与美学家都怀有一个以复兴中国哲学来复兴中华民族的信念,这样的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人生活、情感、人生意义及生活价值的重要皈依和依托。因此,对中国古代生命价值、生活价值的探讨和研究,是努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一种尝试。现今,艺术理论界对艺术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艺术形式、艺术创作等方面,而在艺术审美泛化的趋势下,对中国古典哲学中生活价值的研究关注较为有限。
强调艺术或美学应当面对现实生活,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需求,这条道路仍在探索,但暴露的问题也很多。虽然这使得艺术和审美与现实社会更加靠拢,为美学或艺术活动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但这种下沉也带来了一些危险的引导倾向。在如此庞大的下沉市场中,艺术创作者应当选择“做给自己”还是“做给你看”,这一问题引发了“我们要做什么”和“他们要看什么”两种分歧。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显然后者更具有吸引力。
类似的问题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例如,陈伯海在全球化背景中提出的“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对当代审美趋势的理论梳理和探索。他强调“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与艺术活动中的“美的消解”有关,也与日常生活“美的泛化”有关。而刘悦笛则更加明确地表示:“传统美学的超越性也被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生活化所化解,大众文化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实趋势,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
其实不然,审美与生活回归的理念或者说这种倾向,与中国古典美学并不矛盾。中国古典美学者或哲学家的一生,本就是生活中的一种美学。当代美学的建构也并不如空中楼阁一般,正如苏珊·费金(当时国际上最重要的美学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的主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今天,美学与艺术领域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是美学与生活的重新结合。在我看来,这个发展趋势似乎更接近于东方传统,因为中国文化里面人们的审美趣味是与人生理解、日常生活结合在一体的。”亚历山大·内赫马斯也曾说过:“不仅欧美有生活艺术智慧,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更具有生活美学传统。”中国传统美学所扎根的儒、道、释R5xJ52jdf/sFytU8O1p0TA==的哲学基础,在某种角度上都可以定义为一种“生活美学”。例如,上文所述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即便超越生活,但也始终归于生活并未脱离生活。
这里以禅宗为例,禅宗之所以得以成为儒、道之外中国的第三大思想文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于“生活”的理解更加贴近中国的文化传统,融合了现实与超越两个维度。禅宗并非像印度佛教那样抛弃现实、否定现实,而是强调回归现实、回归本然、在现世中追求“乐”与“美”。禅宗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摒弃了宗教观念,更加肯定人的思想、情感,这种肯定推动了人们在生活中寻求乐趣的进程。禅宗认为,现实生活的一切都是禅意佛法的体现——寒天热水洗脚,夜间脱袜安睡,早朝旋打行缠,风吹篱倒,唤人夫劈蔑缚起……这种生活的描写自然成了其审美的对象。
另外,禅宗也曾提出了关于审美功利性的态度。永嘉玄觉禅师认为:“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
如若不识道先居山,即使身处清静的山中环境,也会丢失了居山之目的,内心也不会平静。相反,如果对道有认知后再居山,那么便无所谓山中的环境,即使处在纷扰的红尘,也会因为心的安宁而寂静。后世禅师也普遍认可永嘉玄觉“先识道,后居山,再体道”的观点。总的来说,禅宗对山居的态度是一种审美的态度而不是功利的态度。山居不是禅僧得道的最终目的,而是识道的一种表现。这也为现代生活中处处审美的泛化,提供了一些哲学意义上的见解。“识道居山”的内涵应该在当代审美的思潮下被重视起来。
韦伯曾说艺术在人们的生活里承担的是一种世俗救赎的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
当代审美的日常化似乎带来了审美的解放,摆脱了依于“仁”志于“道”的老路,随时随处都可以让所有人都置身于审美空间的享受。但当代这种“生活美学”的变迁对遍处于生活中的人们来说,并非是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审美理想。这种“救赎”的美感体验显然不能与传统艺术带来的“意境”“气韵”及崇高、优美、悲壮来对比。总之,在“生活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传统美学中“生活性”审美理念的基础,需要汲取传统美学中的感性和精神性要素,同时也需承担起在世界美学共同发展趋向中,让中国文化、中国美学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融合的担当。
四、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的持久吸引力体现在其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和相关性上。传统美学是灵感和指导的永恒源泉,提供了深刻的文化连续性。“艺术文化研究”与现当代社会密切相关,一些文化社会研究也影响着它的内涵,例如,娱乐性、商业性、通俗性。这些作用客观上对美学理论带来物质性和功利性的影响,这与中国传统美学自身所要求的无功利性的特质相矛盾,自然将出现审美异化、主体地位下降、身心关系被物欲裹挟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以上问题,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表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值得挖掘、值得重新溯源的“古典生活美学”范本。因此,中国的“艺术文化研究”不能只依赖于西方的思想资源,而应该以中国语境为基本,发掘“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从而为现代美学的建构提供本土资源。另外,“艺术文化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即构成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具有不断自我理论更新和超越的适应力的,这也是“艺术文化研究”得以发展的力量支柱。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彭峰.中国美学通史:第八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3]邱敏.关于数字化艺术的特征及其反思[J].中国美术研究,2022(02):166-171.
[4]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5.
[5]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M].北京:三联书店,1982:285.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三卷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17.
[8]孙焘.中国美学通史:第一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9]陈伯海.“人诗意地栖居”: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J].江海学刊,2010(05):11-20.
[10]刘悦笛.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
[11]五灯会元:卷一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004.
[12]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