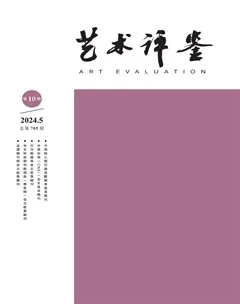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探究
【摘 要】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传统艺术在中华文化中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为了推动传统音乐的活性传承机制,增强民族音乐在全球舞台上的显著性及其非凡价值的认同,同时激发当代音乐创作的新颖性与活力,本研究致力于剖析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结合的策略。研究焦点集中于揭示如何有效地将民族音乐特色嵌入现代作曲技巧之中,以促进两者深层次的结合,保障传统音乐遗产的创新性传递,这是当前音乐创作领域亟须重视并深入探索的议题。
【关键词】民族音乐元素 现代作曲技法 现代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0-0063-06
中国音乐历史悠远,经年累月的积累孕育了繁复多变的民族音乐元素,深刻烙印着民族的独特性。器乐层面,诸如唢呐、锣鼓及二胡等代表性乐器,鲜明地展现了民族风情;而在音乐形态上,豫剧、京剧等中华戏曲瑰宝,蕴藏了深远的历史意涵与文化积淀。我国丰厚且兼收并蓄的文化底蕴,为民族音乐多样性的维系提供了温床,为本土音乐艺术的兴盛构筑了稳固基石。然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对民族音乐的发展轨迹提出了新的考验。在此背景下,探索民族音乐传承与国际化并进之路,促使其与当代音乐风格无缝融合,成为该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本研究专注于系统发掘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巧结合的策略,旨在为中国音乐艺术的创新进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作曲技法概述及发展历程
(一)民族音乐概述
中华民族音乐,源自各民族漫长历史的熔炼,是一种富含独特文化标志与深层精神意涵的艺术表述,深刻映照民族特性与人们的情感世界。它植根于民间土壤,紧贴人民日常生活的实际,直观映射社会风貌与民众情感的广阔图景。在国际艺术领域,中华民族的音乐以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在国内声名显赫,亦在全球艺术界激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其音乐元素涵盖民族戏曲因子、民族旋律、特有演唱技艺与节奏模式等,彰显了特定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精髓与音乐遗传。尽管面临着现代流行音乐的不断冲击,但民族音乐的深入探索、理解及其内在价值的挖掘工作依然活跃且具有重要意义。民族音乐领域范围广泛,涵盖戏曲、说唱、舞蹈、音乐及多样化的民间器乐表现形式于一体,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结构复合的音乐生态系统。鉴于中国地理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域民族孕育出个性鲜明的音乐风格,这些多样化的传统音乐对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深刻且多元的影响,成为音乐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与灵感宝库。
(二)现代音乐作曲技法概述
在当下的音乐创作实践里,现代作曲技法构成了作曲家艺术构思传达的核心框架。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创造性的深度挖掘,它紧密融合个人创意、情感体验,并映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现代作曲技法依托于深厚的音乐理论基础与精湛的专业技能,通过精密的结构布局与组织,以达到情感与理念的精准传达。自20世纪初期以来,现代作曲技术蓬勃兴起,旨在探索并拓宽音乐表达的界限,超越传统和声与结构的框架。例如,勋伯格所创立的十二音体系,通过半音的序列化处理,实现了音高使用的均等性;而微分音音乐的介入,则通过引入非常规音律的音高,增进了音阶的色调多样性。序列主义的拓展,进一步将序列概念应用于节奏、力度和音色。电子音乐的发展则凭借电子工具和技术的革新,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声音创造维度。这些现代作曲技术不仅促进了音乐语言的多元化发展,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为音乐艺术的持久繁荣注入了新鲜活力与无限可能。
(三)现代音乐在西方的发展
20世纪的西方音乐舞台见证了创新思维与技术飞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催生了一大批后现代及先锋派作曲群体。这些先锋艺术家们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引领了一场深入的艺术变革运动。得益于19世纪文化复兴思想的滋养,这些音乐巨匠超越了常规的和声与结构的局限,勇于探索边界,孕育出多样化的音乐革新流派。如印象主义利用丰富的音响色彩捕捉瞬间的情感波动;多调性音乐挑战了既定的调性体系;噪音音乐则开创性地融入日常生活声响于音乐叙述之中;无调性音乐彻底摒弃调中心概念,开启了音乐表达的新维度。这些音乐先驱与西方后现代文学的探索相互呼应,共同体现了对既有规范的质疑与解构态度,以及对新颖表达方式的不懈追求。在音乐界,这场运动不仅颠覆6b3c8110f9fa0e6486876f91695eeecd0a781a67f0fb5ee1ffdbc58522f32517了古典音乐的传统,更是一次对音乐本体与表现潜能的深刻反思与重构。通过这些前沿尝试,西方现代音乐构建了一个多元、复杂且不断进化中的艺术生态系统,彰显了音乐作为艺术学科随时间推进自我更新的强大能力。
(四)现代音乐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现代音乐的兴起虽滞后于西方,但其发展速度惊人。20世纪末,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启发下,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呈现出蓬勃景象,佳作迭出,代表作如《新霓裳羽衣曲》与《怀旧》。这些作品不仅深植于丰富的文化底蕴之中,也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已抵达成熟阶段。回望20世纪初至1949年,即现代音乐的萌芽期,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响乐作品问世,它们不仅为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础,也预示了未来音乐探索的轨迹。此间,作曲家积极探索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包括民族乐器、民间舞曲及节日旋律,与先进的作曲技巧融合,力图开创一条独具特色的音乐创作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界亦紧跟时代步伐,这为音乐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产生一大批讴歌新中国、新生活的优秀作品,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
二、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结合的策略
(一)民间戏曲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
民间戏曲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质之中,历经漫长的历史演进与积淀,孕育出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蕴含着非凡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文化意涵。当前,音乐创作者积极从戏曲中汲取独特的音乐语言与表演美学,展现出融合传统精髓与现代风貌的创新趋势。这种联结民族音乐精华与现代作曲技法的创作手法,不仅为音乐领域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还借由现代音乐媒介赋予古老戏曲新生,使其在当代焕发新的艺术光芒。作为承载博大历史文化信息的艺术载体,中国戏曲涵盖了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等多样流派,各具历史悠久且个性鲜明的传承背景。遗憾的是,年轻一代对戏曲的接触与深入了解的兴趣渐减,导致戏曲艺术的社会关注度与参与度下滑,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为重振戏曲艺术并维系其文化活力,众多现代音乐人有目的地在其作品中嵌入戏曲元素,旨在通过提升艺术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促使戏曲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重获公众的瞩目与活力。
在当今音乐创作领域,融合戏曲旋律作为创意策略已成为主流趋势,诸如《霸王别姬》《悟空》等流行作品明显展现了这一特点。以李玉刚的代表作《新贵妃醉酒》为例,该作品堪称京剧艺术与现代流行乐完美融合的典范,为听众带来了新颖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将京剧的核心要素与叙述技巧精妙地结合到流行音乐架构之中,并运用流行音乐的手法去诠释京剧复杂情感与叙事结构,这些作品有效地增强了观众与音乐的情感共鸣,深刻阐述了艺术创新的本质与意义。此跨界融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还拓宽了音乐创作的象征性边界与情感层次,深化了人们对于音乐艺术无限魅力及深层潜能的理解,印证了跨文化、跨时空艺术融合的广阔视野与深刻效应。
(二)民族音乐旋律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
在探索现代化旋律构造的创新路径中,少数民族独特音乐特征的融入成为不可或缺的创新策略。该实践涉及识别并挑选与目标现代音乐节拍协调一致的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以此作为创作的基底。这不仅巩固了音乐表现的力度,还开辟了观众理解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及文化传统的特殊视角,激发了听者遐想并维护作品的独特性,构成了验证现代作曲技法与少数民族音乐深度整合可行性的重要标准。遵循前沿作曲理念,作曲家需精确选取与预定节奏框架相匹配的少数民族音乐样本,围绕这些精选材料规划作品主题,并特意提取能够凸显民族风情的音乐片段,融入旋律构思之中。同时,利用精湛的技艺设置激情高昂的音乐部分,以增强音乐的情感冲击力。在创作实践中,倡导跨领域灵感的采纳,建议作曲者依据个人的艺术审美,从多样的作品中选取一到两种标志性的节奏模型,或灵活地在既定节奏框架内部嵌入新鲜节奏元素,通过精细的编排技巧实现不同节奏系统的和谐共生,进而在节奏感知上创造出既新颖又极富吸引力的艺术体验。
作曲者在推进现代音乐创新的征途中,深切认识到少数民族音乐技巧综合的多元价值,将其视为增强艺术语言表现力的关键要素。当前,在音乐创制的实践框架中,多元性与复调技艺的应用旨在深化作品的艺术内涵,而少数民族音乐的一大亮点,在其深深扎根于丰饶文化土壤中的复音结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层次分明的声部肌理。在创作的微妙融合阶段,将现代作曲技法与少数民族音乐精粹无缝对接,对于提升曲目声部的组织深度及音乐的多彩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复调技法的部署策略应当涵盖深入剖析并比对不同源流的音乐作品,摄取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并考虑融入支声法,这要求作曲者全面权衡旋律线条、调性色彩及节奏模式等多元音乐维度。复调技艺的核心,在于双重创作手法的并置使用:既有音乐素材的直接模仿与原生资料的创新转化,旨在拓宽音乐表现的多样性边界。经由这一融合途径,音乐作品的音响架构经历了解构与重构,化身为多个既独立又互动的声部,深刻体现了复调音乐的美学精神。民族旋律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联袂,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吸引力,也精确符合了听众对音乐深度与复杂度的审美期待,成就了音乐的“空间维度”,赋予作品以无法复制且情感强烈的音乐标识。
(三)民族特色唱法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
少数民族音乐的演绎实践彰显了其独特技艺与风格特征,这些独树一帜的元素赋予民族声乐持久的吸引力与广泛的听众基础。在现代音乐作曲技法的视野下,融入少数民族特有的演唱技法已成为一种强化作品艺术底蕴并开拓新鲜听觉体验的战略。举例而言,蒙古族音乐的民间歌谣可划分为长调与短调两大类别。长调以其绵延的结构、悠缓的节奏及自由流动的形式,深情勾勒出广袤草原的壮丽情感画卷;而短调则以其紧凑的编排与活泼的节拍见长。蒙古族民谣深刻反映了民族的日常生活习俗与深厚的文化传统,其演唱特性鲜明,音色浑厚有力,歌词内容广泛涉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草原的深情眷恋以及个人情感的细腻描绘。如经典曲目《忧伤的诺恩吉雅》,巧妙借鉴了蒙古族长调中“诺古拉”(意指颤音)的精髓,并通过波音技巧转化和应用;而作品《心底之歌》直接从蒙古族长调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富有特色的钢琴作品。在这样的创作探索中,“诺古拉”这种长调中常见的颤音技法,被创新性地嵌入西方音乐的编曲手法中,借由钢琴演奏的波音效果模拟长调中的颤音韵味,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突显了音乐创作的民族特色与深远的文化根基。随着民族歌谣跨地域传播的不断扩大,现代音乐的作曲与演绎越来越吸纳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特别是长调音乐的运用,它为表演艺术家们开辟了基于个人情感的即兴变奏天地,使得演唱中旋律的灵活调整成为可能,全面展现了草原文化的非凡韵味与独特魅力。
(四)民族音乐节奏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
节奏作为衔接民族音乐精髓与现代作曲技术的桥梁,其精细的调控成为融合两者的根本所在。当前的音乐创作环境显示出对数字化工具的深切倚重,利用这些工具来构建复杂多变的节奏与节拍框架,这一做法不仅丰富了音乐的层次感,还拓展了音乐表达的边界。我国悠久的民族音乐传统,虽然根植于口头传授与自然韵律之中,但与数字化理念存在着诸多契合点。具体来说,通过对传统节奏模式实施量化分析与编码转换,可以使民族音乐的内在节奏得以科学保存与流传。因此,为了达到民族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术的无缝融合,并保持现代音乐创作的高端艺术水平,强化节奏节拍的数字化加工技术变得尤为重要。这涵盖了运用先进的音频编辑软件精确编排并模拟传统节奏模板,以及利用算法开发来探索和创新节奏构造的过程,目的在于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为现代音乐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与无限的创意潜力。
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结合过程中,融入民族音乐已成为提升当代音乐作品艺术维度与广度的核心策略。细致开掘民族音乐内蕴的节奏多元性及深厚文化意涵,并与现代作曲技术的创新实验性相融合,能够孕育出既贴合时代脉搏又深植文化根基的音乐创作。此类跨界音乐实践,不仅强化了音乐作品的文化归属感与国际普适性,且为听者提供了更为多元立体的听觉享受,有力驱动了音乐艺术跨越界限的交流与进步。作曲家们深化探索节奏节拍的数字化处理路径,既是技术层面的革新之举,也是促进音乐艺术多样性与持续演进的关键路径。
三、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在《在青翠的山谷里》中的结合与体现
(一)关于《在青翠的山谷里》的概述
《在青翠的山谷里》是作曲大师刘聪的标志性音乐创作之一。这是一首特意为花腔女高音定制的独奏曲目,彰显了他音乐创作领域的博大精深。刘聪凭借《鸟儿在风中歌唱》等前期杰作而声誉卓著,于2002年完成此作,深刻反映了彼时对生活情境的艺术化领悟。创作之际恰逢春令,本应生机勃发、芬芳四溢,然而却遭遇华北地区连绵沙尘之异象,这种自然反差遂成为作品构思的灵感来源。该乐曲精巧汲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粹,经由细致提炼与创新重塑,与现代作曲技巧实现了巧妙结合。此联结不仅为作品镌刻了鲜明的民族印记,突显浓郁的地方性特征,还深刻揭示了作曲家刘聪独一无二的音乐叙事手法及创作风格,印证了他在个性化艺术探索道路上的不懈追求与卓越成就。《在青翠的山谷里》因之搭建起一座沟通音乐民族属性与现代性的桥梁,成为地域性、个性表现与时代精神浑然一体的典范,洋溢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沉的思想内核。
(二)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旋律的结合
苗族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少数民族,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音乐艺术,尤其以“飞歌”为代表。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形式,“飞歌”承载了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其风格清新超逸,旋律高亢且充满动力。这得益于其独特的小三度音程运用,增强了音乐的创新性和表现维度。为提升作品的艺术层次及旋律美感,并深植民族地域特性,当代作曲家广泛探究并借鉴“飞歌”的音乐结构与技法,此途径成效显著。例如,《苗岭的早晨》是1974年白诚仁先生成功借鉴贵州黔东南苗族“飞歌”灵感特意为俞逊发新发明的口笛创作的曲目,曾被中国艺术团在世界演出,享誉海外。1975年由作曲家陈钢创编成为小提琴曲,开辟了新颖的艺术表达路径。随之,飞歌逐渐成为众多作曲家创作的基石,催生了一系列杰出的经典之作。旋律作为构筑音乐作品的基石,其核心地位无可替代,历来为作曲者所重视。刘聪的《在青翠的山谷里》即为一例。这部作品通过融合苗族飞歌艺术资源,不仅巩固了节奏韵律,还确保了旋律的新颖、纯粹,产生了深远的艺术影响力,深刻印记于听者心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传统民族音乐素材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标志着当代音乐创作对民族性和创新性深度融合的深度探索与实践范例。
(三)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节奏的结合
现代音乐创作领域在节奏构造方面显著受益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在采纳并转化其音乐节奏与舞蹈韵律的实践方面。以《在青翠的山谷里》为例,这一作品的节奏架构还直接吸取了彝族传统舞蹈“阿细跳月”中标志性的前四拍节奏模式。这一融入不仅是对民族音乐传统的致敬与再创造,更是赋予了作品鲜明的民族性标识。通过巧妙融合“阿细跳月”节奏的核心元素与苗族“飞歌”旋律的独特韵味,这部作品实现了跨音乐风格元素的高级整合,极大地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创造了一个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听觉体验空间。作曲家在乐章末尾采取了自由节奏的处理手法,这不仅丰富了音乐结构的层次,还有效地提升了音乐的内在张力与整体的饱满度。此外,灵活部署的虚小节结构策略在作品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音乐流畅过渡,还彰显了作曲技术层面的大胆创新与深度探索。作曲家还广泛运用模仿自然界鸟类鸣叫声的音乐拟声技巧,旨在音乐表达的维度上实现景象与意象的深度融合,追求音乐形态与内在情感表达的高度统一。这些通过对自然声响的间接再现,深刻传递了大自然的灵动神韵,让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之中。整个作品因此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与动态的美感,深刻体现了音乐与自然世界和谐共生的美学愿景。
(四)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曲式结构的融合
音乐作品《在青翠的山谷里》采纳了一种标准的二部曲式架构,其内部构造的对称性展现了作曲家深厚的技术掌控力。通过一个精心构思的引子段落,不仅预置了音乐的情绪氛围与主题轮廓,而且为后续音乐进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有效地导向并构筑了全曲的高潮点。作曲家巧妙配置了一个25小节的引言性质的前导段与紧接着的28小节核心主题段,这两部分的布局促进了音乐能量的积累与释放。在A部分结构中,遵循了古典的起承转合模式,但在第四乐句特意减弱了收束的强度。这种方法不仅维护了情感对比的鲜明性,也为音乐的后续演进预留了想象余地。B部分通过对A部分素材的展开,运用变奏手法及上行四度的模进策略,加强了作品的独特个性,赋予音乐以活泼跃动、弹性十足的艺术风貌。在调性安排上,作品固守G大调系统,机智地在第三部分融入属音元素,与引子形成呼应,增强了音乐的内在逻辑性和连贯性。作品在音乐高潮与对比强烈的章节中,采用高潮延缓技巧,经由尾声部分的深化处理,逐渐积累并最后释放所有音乐动能,抵达全曲的顶点。这种结构处理方式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内在紧张感,也保障了音乐表述的全面性与深度。
四、结语
当前,我国一批前沿的作曲家在其音乐创作探索中,已主动将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尽管作曲家们的技法支撑根植于现代作曲理论,但他们的创作灵感明显汲取自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宝库。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体现在钢琴伴奏的编排艺术与旋律构思上,而是全方位地贯穿于作品的各个构成要素之中,从而成功打造出一种超越传统界限的音乐叙述模式。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不仅为少数民族音乐的革新与拓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也为我国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引入了新颖的活力与深邃的文化底蕴,塑造出独特的“中国风”标签。这种结合,不仅确保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连续性与普及,同时在中国现代音乐与全球音乐场景的互动中增强了多样性的对话交流与辨识特征,凸显了音乐作为文化传播媒介与活化文化遗产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段君妍.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作曲中的融合与应用[J].戏剧之家,2023(33):97-99.
[2]程旭.民族音乐元素与当代作曲技术的有机融合——以叶小纲钢琴作品《纳木错》为例[J].名作欣赏,2023(36):176-178.
[3]姚依.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在中国近现代双钢琴作品中融合探析——以陈怡《西部钢琴组曲》为例[J].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2022(12):59-64.
[4]范琳琳.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的有机融合[J].教育艺术,2023(10):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