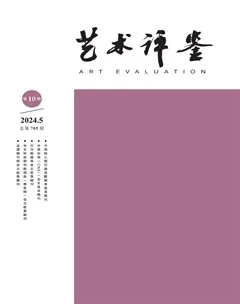浅析木刻套色版画的艺术魅力
【摘 要】套色木刻是木刻版画的一种类型,它是在原有黑白木刻版画的基础上,加上多种颜色套色而制作。朱世伟近年来的套色木刻艺术作品以戏曲表演为表达题材,立足于传统文化,在画面中用绝版套色木刻技法呈现内心世界,体验戏曲表达和客观存在的矛盾统一,因而人物和场景打破了现实的时空限制,穿插以花为代表的视觉符号,自由融合。其作品技法精湛、表达角度独特、有较高的艺术品位。贵州本土戏曲在朱世伟的版画中获得新的艺术呈现,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时代性、艺术性,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为中国当下版画创作走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照。
【关键词】版画 套色木刻 正安马马灯 傩戏 繁花 视觉语言
中图分类号:J2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0-0051-06
当今的艺术领域内,版画艺术是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一种视觉艺术门类,它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它的艺术成熟是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发展起来的,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传承价值。自从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引入中国以后,它在中国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都在政治、文化及人们的生活日常中产生了重大作用,在当下的中国时代环境中有着非凡意义,在文化传承和艺术拓展上都有着特殊价值。版画这一艺术样式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得以传播和拓展,在艺术表达的技术和理念上打破了西方艺术的“范式”要求,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凸显出特殊的艺术语言内涵。画家们立足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地域文化,在版画创作表达和技术语言方面不断探索,形成多样化的版画样式和版画创作群体。尤其是套色木刻版画,在技法日趋成熟、手法更加丰富的当代艺术家手中,仍然是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之一。这种以多块色板套印而成的木刻艺术,按颜料种类的分法,分为油印套色木刻和水印套色木刻。若从制作技法出发,则分为有骨套色、色块套色、有主版套色、无主版套色、绝版套色等五种木刻版画。尽管种类多样,分类不同,但是套色木刻的审美特点还是集中于刀味和木味等。其造型概括精炼,阴阳两刻的相互成就、色彩的自由明确才是套色木刻的魅力所在。
绝版套色木刻又称减版木刻,数百年前西方就使用该技法创作版画,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思茅地区得以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贵州,朱世伟在大学学习期间接触到该技法,并在之后的版画创作中不断完善探索。当时,国内版画家对绝版套色木刻的认知属于比较小众化的状态,版画家对技法的研究大多是在掌握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的持续实践并获得经验,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一技法的使用就是极具个性特点的。绝版套色木刻通过在同一块木板上的反复刻制和印制实现色彩叠加,减版的过程就是颜色叠加的过程。过程中的制版、刻制、对版、上色、印制等都是极为讲究的,版画家们使用的方法各异。在朱世伟的套色木刻作品中,观者可以解读的角度是多样的,从技术技法、画面结构和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可以逐一体味。
一、朱世伟套色木刻创作的题材来源和情感基础
美术作品创作的题材,或者说构成画面的视觉符号,是现当代绘画创作中所有画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艺术探索、形成个人艺术语言的过程中画家对题材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题材体现出画家在艺术表达过程中需要呈现出来的世界观、艺术0/gyLHJrq1oUIh1Pla9pMw==观,从题材上可以看出画家在艺术表达方面的主观倾向和学术态度。另一方面,题材的选择是和画家的“技术”联系起来的,这里所讲的“技术”,是指画家个人化的艺术技法和画面形式,题材选择必然和“技术”是一个能够自然融合的有机整体,这样的画面才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题材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自然选择,其实它来源于画家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主观判断,既决定内容又承载形式,在某一方面影响着绘画作品呈现出来的质量和张力。
朱世伟先生是贵州人,在这片土壤上,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往往对乡土题材有着难言的赤子情愫,因而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他不凡的审美角度、扎实的技术功底,以及自然朴实的表现手法。在当今浮躁喧嚣的社会环境下,这是每一个艺术家难能可贵的精神。
地戏主要流行于贵州安顺地区,是傩戏的一种。相传是六百多年前明军在贵州屯兵时由江南地区传入,传承至今保留了完整的戏曲样式和文化特点。一锣一鼓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和,地戏中的唱词腔调浑厚深沉、激昂高亢;地戏中的舞蹈动作多表现战斗打杀场景,动作刚劲粗野、朴实雄健。地戏表演很注重面具、衣饰、道具装扮,有多种固定的人物角色和剧本。在新时代,艺术家的作品创作题材自觉关注传统文化,并不断以自我的角度创新呈现,安顺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成为当地艺术家表达传统文化的选择,尤其是在贵州,各个艺术门类都有对其深入研究的践行者。在贵州美术创作领域,朱世伟无疑是以版画语言表达安顺地戏题材的代表性画家。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贵州自然环境和乡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直接而长期的,他笃诚地选择安顺地戏作为切入版画表达的题材元素,用绝版套色木刻的方式呈现他内心世界中的“傩面繁花”。马马灯主要流行于贵州北部地区,是人们自娱自乐的一种灯戏。近年来,朱世伟的绝版套色木刻作品围绕安顺地戏和马马灯这些题材,在作品的技法特点、个人表达,以及艺术品位上不断研究,形成强烈的个人表达风格,在全国版画界获得认可,且多次在全国性版画展览中都获得最高奖。
安顺地戏作为一种在当下保存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存在意义和艺术表达意义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它承载着时间的流逝和现实世界的流变,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进。朱世伟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及艺术情感体验出发,选择以安顺地戏的人物为艺术表达的主要对象,呈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对艺术的敏感,以及对时代环境下安顺地戏的绘画可能性认知,他在表达过程中依托绝版套色木刻创作的技术手段和本体语言,在绘画技术层面和艺术表达层面都形成独特的风格特点,同时,在刻画具体物象的过程中打破现实场景限制,在艺术观念上与时代同步,以解构和重构的方式形成画面的象征性观念表达。
二、朱世伟套色木刻创作的技法表现和主要特点
朱世伟的作品中,对绝版套色技法的运用过程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程度主要归因于颜色的多少和尺幅的大小。他的作品通常会有十余个色彩的叠加,颜色多的时候达17个版次,这就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要经历17次反复刻制与印制,如此繁多的版次在国内使用绝版套色木刻技法的版画家中是不多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的版画都是小尺幅的,现代版画打破传统版画习惯,大尺幅在版画创作中出现,这是一个适应当下审美多样性的选择,然而,大尺幅的版画在制作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对版的准确性、纸张的伸缩性、多次印制对原版的消磨和损耗等,朱世伟在创作过程中主动面对这些难题,创作了多件大尺幅作品。作品《高台地戏》是“多彩贵州”大型书画双百创作工程入选作品,作品色彩版次有14个,由尺寸为200cm×260cm的三联画组合构成,画面人物众多,以姿态各异的地戏动作组合呈现高台地戏这一表演形式。画面以具象的手法进行叙事表达,空间上打破常规的视觉习惯,画面层次极为丰富,使安顺地戏这一历史文化遗存通过版画形式完美表现出来。
朱世伟的绝版套色木刻在人物造型方面特点明显,与众多表现人物的画家不同,他并不去重点描绘人物个体的特征和繁复的服饰构成,而是用富有节奏感的自由造型实现对安顺地戏群体特性的呈现。在作品中用线性强化人物动感,服饰、道具的刻画都围绕动态的表达进行,流动的线条、飘扬的动态是他构成人物造型的主要方式。在个体人物的比例关系及群体人物之间的大小上,不拘泥于现实存在的比例和透视,依照画面和个体表达的需要自由处理。作品《迷离花盛》中,地戏人物的头部、肩部被放大,腰部、腿部被缩小,这样的比例构成使傩面的特点在画面中大面积呈现,人物比例的调整使得动态感更强,人物与道具、花卉、动物及背景自然融合。
朱世伟的绝版套色木刻在色彩运用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方面,他强调画面色彩之间强烈对比,对比色、互补色在5aca13551b1e0df8bf087839d86bcd0991a877f674ada013abe208e38c611835作品中大面积运用;另一方面,他在印制过程中通过色彩叠加形成画面色彩的层次关系和微妙变化,使色彩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厚重感。作品《蝶变》以红、黄、蓝、紫构成画面主题色彩,这样矛盾的色彩组合在绘画作品当中是不多见的,色彩之间的抗衡、对比使画面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作者用色彩和造型符号的组合变化使这种矛盾性在画面中消解,形成和谐的画面,这种方法是极富原创性的。这些丰富的色彩使得作品中的各个要素矛盾统一,构成一幅灵动的画面,巧妙而丰富地实现了作者主观情感的表达。
艺术作品的创作需要在依赖于作者对周遭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和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朱世伟的版画创作无疑是具有代表性和表现性的。代表性体现在他与当下艺术家切入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基本相同,并能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价值;表现性在于他通过自己对题材的选择和充满张力的表达拓展出具有戏剧性、历史性、生动性的画面内容。作品《与鹤共舞》中鹤的形象并不明显,主体是在空中飞舞的人物形象,将人物与建筑、动物结合起来,有静有动、以静显动。为什么是“与鹤共舞”而不是其他符号呢?鹤是一种鸟类,是自由的物象,同时,它也是一种带有吉祥寓意的动物,其“长寿”的象征有时间延续的指向,将它作为画面当中的“关键词”是有深刻含义的。这种选择显示了朱世伟独到之处,一切自然而然又有拓展的可能性,这显示了画家在创作中的可能性、画面呈现的可能性和艺术作品表达的可能性。“傩面”与“繁花”,是朱世伟构成其画面的主体符号。他用傩面及地戏人物为画面内容,加入各种形态盛开的鲜花穿插,使人物置身于同一环境中。画面使用的超现实主义方法让画面符号与现实物象既有联系又形成差异,画面中的空间是叠加的、时间是穿越的,超现实组合形成多元的时空感,使安顺地戏这一题材的表达超越时空局限,现实的、想象的、历史的、当下的元素都能在作品中获得解读。作品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尊重、审思和解构。作品《怒放》以繁盛的鲜花为主体场景,大小不同的数个地戏人物穿插其间,好似在花间行走、飞跃。“傩面”与“繁花”组合形成神秘、深沉而浪漫的主观画面。选择以安顺地戏为创作题材,以狰狞、张狂的傩面搭配娇艳、团簇的繁花为画面主体内容,契合朱世伟对当下的认知。
朱世伟说:“我的地戏系列作品,一幅幅连载在一起,就像一个大舞台,现实中的人物通过面具、戏服,吟唱着自己的生活,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述说自己的内心。画者无意,观者有心,理解我作品的观者或许能在作品中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吧!”地戏中的元素来源于生活,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的军屯氛围中提炼出来的表演形式,而这样的元素呈现在朱世伟的版画作品中以后,他再次对地戏中表演出来的要素进行独特的视觉提炼,画面中的空间不再是地戏表演的真实空间,而是由三维转向二维。所以,朱世伟版画中的空间既有平面结构,又有立体造型,在视觉呈现的二维和三维中自由切换,这是他画面空间表达呈现出来的重要特点。当然,这也是现当代绘画中画家所惯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大家不再拘泥于平面或空间限制,按照自己的创作理念和画面意图自由选择,实现画面表达中更多的可能性和原创性。作品《丰收》主题思想立足于国家乡村振兴及文化惠民的战略布局,同时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贵州地域性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版画创作对乡村振兴建设,以及文化惠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相关历史文化的传播,以及促进相关地域旅游业的发展和乡村环境的优化,同时版画作品能够充分展现出乡土气息,让观者可以通过版画更直观地认识乡村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历史风貌。作品通过马马灯的题材作为创作切入点,一是因为它的历史久远,深重厚实;二是因为它在贵州民族戏曲中保留完整,具有代表性;三是因为它是当地人劳作、节庆过程中常见的表演形式,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马马灯俗称“送瘟灯”,是用以驱瘟、祈福、消灾的古老灯戏,是民间喜闻乐见并广泛流传的一种古老灯戏,扎纸车、纸马,扮成各种神灵和人物,以祈福消灾。明代时期马马灯就已出现,清代时则较为盛行,至民国时期也曾一度兴盛,是老百姓祈福纳祥、欢庆节日的方式。马马灯在正安县小雅镇附近一带十分流行,演出内容主要以三国时期的故事为主,融合弹、拉、说、唱、演等各种技艺,服装打扮鲜艳明亮,唱词语言多为村言俚语,表演形式则粗放优美、幽默谐趣,场景十分热闹。
正安马马灯有特定的演出流程,即分为报事、关公解皇嫂、钟馗盖魁三个阶段,演出时配以锣鼓进行,三阶段不分开演,且连接为一体进行。演出角色有报事、关羽、甘糜二夫人、车夫、马夫、钟馗等。通常马马灯的演出一般在院坝进行,两个幺妹手持竹扎彩布糊成马头状,两个马牌(花鼻子)持马鞭,四人且歌且舞,一唱众和;还有两人双手持彩杆灯笼站于场外,另有主唱和锣鼓手。马马灯近年来在正安县小雅镇多有表演,目前正安县马马灯已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自它在民间产生、形成以来,作为民众驱瘟纳吉和消灾的重要方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备受流传区域的百姓尊崇,百姓每逢家有瘟疾或节庆,都要请戏班来演出,以祈福纳祥,保人畜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朱世伟套色木刻作品以绝版套色木刻为创作手法,用传统的艺术语言体现当下的民族文化形态,艺术语言的选择与表达对象之间完美融合、互为一体。画面结构打破常规的视觉习惯和透视规则,用众多的地戏表演人物穿插于画面,以超现实的手法安排人物、场景及画面整体结构。画面人物众多,故事丰富,突破传统绘画单一视觉中心的规则,以多个情节、多个点位、多个人物形象为画面刻画重点,突出地戏表现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元性、自由性,使观者在欣赏作品时犹如观赏一部情节丰富的电影,让画面有一种流动感。正是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传统的中华历史故事魅力、乡野村民的朴实教义,以及奔放的舞台表演激情,让艺术家们不知不觉地走进最美自然,融入人民生活,朱世伟正是多次深入此情此景,因而才创作出那些优秀的美术作品。
平面和立体是现当代绘画中画家进行画面创作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绘画是平面的,但作为造型艺术的语言表达,它又必然要借助立体的关系进行呈现,这里面就存在极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如果思考得深入、实践得具体,这个从某种意义上矛盾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并促使画家形成艺术语言,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作品将呈现出似是而非的气息,甚至显得不伦不类。在朱世伟的创作实践中,平面和立体的关系在画面中的呈现极为协调,对他而言,这个矛盾关系的处理一直都是自然而然的,地戏符号特点的提炼和无关内容的舍弃是他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朱世伟套色木刻创作是对贵州文化的独特表达和对中国版画语言的进一步拓展
贵州是文化特点极为鲜明的地区,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织,构成贵州独有的文化状态和视觉呈现。贵州美术作品创作对贵州地域文化的表达是深入的、多样的、具体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所产生的“贵州美术现象”是贵州地域性文化表达的顶峰,当时,一大批贵州本土艺术家通过雕塑、版画、水墨、工艺美术等多种形式在中国正步入对西方现代美术的学习和进行自我文化的审视语境下表达贵州本土文化,在北京频频举办美术活动,引起全国美术界的极大关注,“贵州美术现象”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版画家中,董克俊、曹琼德、王建山是“贵州美术现象”产生的直接参与者,贵州版画的发展和贵州版画创作脉络一直与贵州地域文化的挖掘有密切关联,几乎所有代表性版画家的作品都与贵州地域性文化表达相关。朱世伟作为贵州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版画家代表,其作品内容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贵州地域文化特点,生活的环境、学习的传承、艺术理念的形成共同促成他当下对贵州地域文化的理解。与前辈画家相似,他对贵州地域文化的理解是敏感的、深入的、个性化的。对安顺地戏题材的表达,国内有很多画家都在尝试,朱世伟在题材的把握、画面的提炼、艺术本体语言的深入、画面中哲理性思辨的表达等方面都是极为独到的,多年的绝版套色木刻创作实践形成的经验积累让他成为安顺地戏题材表达画家群体中的成功者,为当下艺术语境中的地域性表达提供了新的样式和可能。
在朱世伟的版画作品中,除了对绝版木刻版画创作本体语言技术探索和个性化艺术表达方式研究外,还充分体现出美术创作的地域性、时代性特点。艺术史上留存下来的美术作品在地域和时代性方面的呈现上都是极为充分的。地域和时代决定了艺术作品产生的空间和时间,艺术作品之所以存在地域性和时代性特点,是因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依赖于人,艺术作品的欣赏依赖于人,而人是地域和时代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于既定的地域和时代,跳出空间和时间限制。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让大家在欣赏和评价的时候产生共鸣,正是因为体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当时的空间和时间逻辑,让更多的人得以理解。艺术家所体现出来的个性更多依赖于地域性、时代性特点的创新性表达,而不是脱离于地域性、时代性特点的个人认知,这也是所有艺术家要面对的一个命题。看清了自身存在和想要表达的地域环境,思考自身所处和想要表达的时代特征,才能认识自己和自己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才能准确找到表达的切入点,这个角度如果是很清晰的、精准的,所表达出来的要素自然就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它是艺术家个人在深入提炼地域性、时代性特点以后的自觉呈现,这样的呈现也必然是具有艺术性的。朱世伟绝版套色木刻作品从当下的现实环境来看,从作品题材、表达主题、本体语言和艺术观念几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四、结语
作为画家,理应根植于大自然和乡土元素的土壤,而套色木刻版画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绘画相比,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除了色彩丰富、层次分明外,由于是手工制作,每一层制作都需要创作者精心雕刻和手工上色,每一件作品都是作者独特的个人技巧展现,都是创作者对艺术审美的特殊感悟,所以每一件成功的木刻套色版画艺术品都具备独一无二的艺术特性。而从朱世伟的绝版套色木刻作品中还能感知到他对文化的自信、生活的自信、艺术表达内容的自信,以及艺术呈现方式的自信。他的作品通过“傩面”与“繁花”的相互交织,戏曲表演与真实生活的相互映衬,在画面的空间表达上寻求自己独特的处理方法,在画面的色彩运用上找到强对比色彩在画面和谐融合的有效路径,在画面的艺术造型上探索出适合主题呈现的自由组合,这些创新性的表达构成中国版画界独树一帜的样式,实现了绝版套色木刻创作一种新的可能,为中国当下的民俗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创作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参考文献:
[1]李屹,邬建玲.朱世伟《繁花与苍山》开幕[N].贵州都市报,2017-10-01(14).
[2]张健健.怒放的繁花,遥远的苍山——朱世伟纸上作品的神话诗学[J].贵州画报,2023(24):18-29.
[3][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