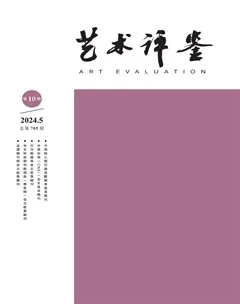21世纪以来李嵩《骷髅幻戏图》国内研究综述

【摘 要】李嵩是南宋的著名画家,其《骷髅幻戏图》的画意之谜从古至今争议不断。国内学者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接力,从图像学、隐喻、宗教、钤印、鉴藏、比较研究等角度对《骷髅幻戏图》展开了深入探讨,学术成果颇丰,对于往后之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然而,相关的研究方法仍有待与时代跟进,诸多可深入研究之点面亦有待挖掘。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李嵩《骷髅幻戏图》的国内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关键词】《骷髅幻戏图》 李嵩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0-0043-06
《骷髅幻戏图》(见图1)为绢本设色团扇面,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今人多将其视为南宋画家李嵩所绘。据相关学者考究,其名可能出自楼钥之诗《戏和三绝·傀儡》;也有研究者认为“骷髅幻戏图”于古文并未呈现,古文中仅出现过“骷髅执扇”“骷髅弄婴图”等说法,因此该名称可能出现于近现代,并沿用至今。
观此扇面,可见左有李嵩名款,周有多方钤印。画面左侧,一大骷髅着薄衣,戴幞头,盘腿坐于地,其右腿弓起,左腿贴地盘附,右肘似支右膝,右手控一悬丝傀儡。大骷髅身后,一妇人胸脯袒露、神色平静、席坐于地,正乳婴,其眼神偏向画面右端。大骷髅与乳婴妇人后有一砖土台,上方竖板标写“五里”二字。画面右侧,有一身姿更娇小、神色慌张、双臂展开似作袒护状的妇人,还有一地面爬行似伸右手抓取小傀儡、约莫两三岁的婴童。左侧之大骷髅与乳婴妇人身前还有一货担,装有大量物品袋囊。背景平坡圆滑延伸至画面最右,右侧边缘与右侧底部边缘伴有竹子与荆棘数枝。该画面色调左深右浅,左以重色绘之,右有大量留白。除此之外,黄公望所作的《醉中天》小令中“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寻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识破个羞那不羞?呆兀自五里巴单堠”的描述,也成为后代学者对该画作进行解读的切入点之一。
北宋时期,风俗画的发展已达到顶峰,而到了南宋,风俗画的寓意和创作动机或许隐含更深层次意义。李嵩曾作为南宋著名的宫廷画师,绘制过多幅表现南宋生活现状的风俗画,《骷髅幻戏图》所携带的魔幻色彩使之特立于其众多画作之中,引发后人的无限思考与探索。整理《骷髅幻戏图》相关文献并对其综述,立于全局而纵览其研究现状,能探出较多可深入研究之点面,可见该画作仍有较为广阔研究前景,例如,当今学者对左侧妇人是否为职业奶娘、大骷髅生前身份地位、该画作是否为端午扇等产生一系列争议,导致国内学界对该画的解释思想有较大分歧。从“大综述”这一独立研究角度入手,不仅能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方向作出指引,对李嵩本人认识的深入和艺术学科的发展也有一定推动作用。
一、《骷髅幻戏图》的图像学研究现状
大多数学者选择从画作所呈现的图像本身入手,尤其注重人物动作、服饰和发髻的历史形象特点,并结合多数同时期文学诗画作品,以佐证其研究结论。
(一)傀儡戏
我国傀儡戏相关考究可追溯至汉代,宋代更是悬丝傀儡戏的繁盛时期,幻术表演在民间甚多。该画作中,席地而坐的大骷髅伸出右手,以数根悬丝操控小骷髅耍戏,妇人与孩童围绕观看,孩子表现得稀松平常、毫不讶异,或许这正是宋代世俗生活中傀儡艺人穿梭于街巷卖艺的真实写照。
廖奔在《〈骷髅幻戏图〉与傀儡戏》中谈到宋代悬丝傀儡(提线木偶)已具有相当高的表演水平,艺人们技巧纯熟,走街串巷的傀儡戏表演具有感染力。除此之外,他认为傀儡戏与儿童的游戏密切相关,例如宋代市肆中常见悬丝傀儡玩具,因此将画作题目“骷髅幻戏图”解读为以傀儡戏演绎人生具有合理性,结合傀儡戏能够帮助后人更准确地理解作画寓意。
大部分学者均肯定了李嵩将傀儡幻术戏法绘于画作之中的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该画作的创作体现了宋朝繁荣的社会生活,以及良好的政治文化风气,同时也能反映画家个人对世俗生活的关怀。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知,《骷髅幻戏图》中大骷髅控小骷髅是“傀儡艺人在街巷表演傀儡戏”的这一说法,大概在学界已达成共识。
(二)人物的职业身份
《骷髅幻戏图》中,神色、体态、着装各异的几位人物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其中,人物的身份与职业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通过图像学研究、写实性研究等不难对人物的职业身份进行一系列猜想,但因观察和思维的角度多样,或许目前较难在学界达成统一。以笔者观之,研究《骷髅幻戏图》需要大胆接纳不同的新旧观点,从多角度、多方面分析入手,以此得到对其中人物形象最接近的认识。
1.“妇人乳婴”形象
诸多学者将目光移至大骷髅后方的乳婴女子,该女子袒乳育婴,至今仍谜点重重。李嵩曾多次在画面中展现“妇人乳婴”的形象,此类女子形象能对南宋两性关系、女性地位等社会学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
廖奔于《〈骷髅幻戏图〉与傀儡戏》最先提出此画为傀儡艺人于街巷拖家带口表演傀儡戏。施莉亚、申梦鸽等人均认为该妇人来源于贵族之家,因为她身上的服饰并非出自平民家庭。此外,亦有学者认为,妇人袒乳育婴是社会风气开放包容、两性平等的表现;妇人正思念去世的丈夫,大骷髅与小傀儡为妇人脑海中的幻象。
近两年来,有研究者提出,该乳婴妇人更有可能是职业乳母。两宋时期对女性的束缚较为严苛,礼义廉耻与社会伦理规范女性的行为准则,因此,普通女子当街袒乳育婴不符合社会现实。然而,两宋时期乳母高度职业化,为乳婴女子形象出现于街巷提供了可能性。有学者通过妇人发饰、衣着,推测出该妇人为富贵人家的奶娘,张廷波于《乳婴育儿还是祛病避瘟——宋代李嵩〈骷髅幻戏图〉图像寓意补证》对这一说法进行补充说明:“宋代社会并非如此包容与开放”,尤其是南宋理学对社会影响日益深重,寻常人家的女子难以在陌生环境当着陌生人的面哺乳。可见,在南宋社会,女子当街哺乳的可能性很低,该画作中的乳婴女子极有可能属于一个特殊群体,即职业乳母。南宋时期,幼儿存活率并不高,女子社会地位较低,若是急于生育更多子嗣,哺乳期导致女子难以快速怀孕,因此中上层家庭女子亲自哺乳的现象并不普遍。职业乳母出身低微,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或许她们的生活习惯较为随意,当街哺乳并不难为情。
该乳婴妇人形象对于研究《骷髅幻戏图》的图像寓意至关重要,并深刻影响着学界研究此画的思想方向,但目前仍存在较多矛盾点有待深入研究探讨。例如,若大骷髅戏耍小骷髅逗婴童的这一画面均属于乳婴妇人脑中幻象,则并无“当街哺乳”一说,该女子为职业乳母的推论将不攻自破;若该女子实为职业乳母,那么2023年之前针对该画作研究的思维方向一直存在较大误区,如马卿等人认为本绢画“以乳婴妇女为讲述者,她在回忆丈夫在世时的温馨场面”,其研究成果定也会与实际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
2.“大骷髅”形象
《骷髅幻戏图》中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象即画面左侧戏耍提线小骷髅的大骷髅,画面的主角也正是这只大骷髅,部分学者曾指出大骷髅是“鬼魂的形象化”。结合时代背景后,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该画与宋朝的傀儡戏紧密关联,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大骷髅即傀儡艺人。多数学者如廖奔、施莉亚、王一帆等人认为大骷髅为傀儡艺人或游方艺人,且部分提出黄公望所作小令“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寻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若切换视角细究,大骷髅不是傀儡艺人也并非全无可能。杜七龄则认为大骷髅是权贵之家的仆人,还有少数人认为大骷髅是一位货郎,例如马卿。另外,也有极少数人分析货担里的货物后,认为大骷髅仅是一位过路人。
大骷髅的衣着是主要研究线索之一。汤雯雯于《“未尝死 未尝生”——李嵩〈骷髅幻戏图〉探析》有提到,大骷髅所着衣物并不像傀儡艺人的戏服,且身穿戏服戏弄孩童似乎不方便,也不合理。杜七龄在《〈骷髅幻戏图〉绢画中人物形象的图像学研究》中通过研究大骷髅有脚幞头、衣着后,提出大骷髅的身份“高于货郎”,但“比权贵低”,且半透明纱质衣物似是李嵩为突出大骷髅崎岖骨架而刻意为之。除此之外,杜七龄还发现大骷髅似驼背,大概是因为长期参与体力劳作,如挑货担。
诚然,经过数代学者探索研究,“大骷髅”身份之谜逐渐走向明朗,但也不可否认,学界对该画中“大骷髅”的形象研究尚不全面,如今对“大骷髅”身份职业的讨论大多仍停留于猜想层面。
二、《骷髅幻戏图》的哲理与隐喻研究现状
李嵩《骷髅幻戏图》从古至今争议不断,其背后的画意解释和哲理隐喻更是后代学者不断探索的方向。笔者文献整理期间发现,宋人的生死观和自然观、画面的荒诞隐喻和讽刺世事等题材常出现于视野。
(一)节日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众多,《骷髅幻戏图》的画面寓意可能与端午节和七夕乞巧节有关。
1.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又称“端五节”“端阳节”等。古代有端午送扇的节日习俗,到了南宋,端午送“画扇”成为惯例。
少数学者对《骷髅幻戏图》的研究结合了“端午送扇”这一节日习俗,即认为李嵩在扇面上作画受到端午节节日的影响。马蝶在《以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谈作品与观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谈到,画面中心的“竖向折痕”可证明李嵩是在团扇面上进行绘画,因此该作品可能是李嵩出于“私人订制”的动机而进行的创作,而非李嵩本人的“自由创作”。由此可知,端午节送“端午扇”的习俗极有可能成为创作此画的社会原因。
2.乞巧节
俗传七月七日夜牛郎织女相会,此夜被称为“七夕”。此时,民间活动颇为丰富,有穿针、乞巧、看天河和祈祷福寿等。
七夕乞巧节中“乞巧”的本意是“求子”,《骷髅幻戏图》也有可能是用于描绘七夕乞巧的画面。有研究者解读“与儿弄摩侯罗亦骷髅者”中的“摩侯罗”为宋代“磨喝乐”,蕴含求子寓意。不过,王一帆于《宗教视域下的南宋风俗画释读——以传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中有力质疑了这一推测,他提到:因为读音相近,宋人百姓常以讹传讹,把“摩喝乐”与佛教“摩睺罗”混淆,因此多数研究者也将二者等同,但二者无论是外观还是寓意都有较大的区别,“摩睺罗”在佛教中并不含有hklrCaMd8Sx45CPOl5OJQjRJrl/jxkQ3ZFmLQVqL0S0=求子的期盼。由此可得,《骷髅幻戏图》是否与七夕节有关,确有待商榷。
综上可知,民俗节日对李嵩的创作动机或有较大影响,但相关文献较少,尚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二)宋人的生死观
李嵩作为南宋著名的风俗画画家,其创作的内容具有思想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生死转化、因果轮回、“齐生死”观皆是解读画面寓意的重要观念。
画面中的大骷髅是最能直观体现宋人生死观的形象,学界对大骷髅寓意的解读繁多。马卿在《如幻如戏生与死——再看李嵩〈骷髅幻戏图〉》中通过宗教思想幻化、生死观、流行风俗等方面也对画面进行诠释:画中内容可能是一场幻境,是“思念所致”,且“终究是一场梦”。马卿还提出,这幅画通过妇人脑中的幻境展现了变化无常的人生,以及中国人“视死如归”与“知足常乐”的观念。汤雯雯对画中生死观的解读还有不同看法,她读“庄子叹骷髅”的故事时感慨“大骷髅”可能既“未尝死 未尝生”,又“是生也是死”,因此,她也在文中留下自己的疑问,即李嵩是否要在本画中表达“死是痛苦的,生是欢乐的”之意。
除了马卿,聂子健于《李嵩〈骷髅幻戏图〉合理性与荒诞性研究》中有提到,画中可见“死”与“生”的矛盾对立,李嵩呈现于画面中对情感错乱无序: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以及对现世社会的失望。汤雯雯《“未尝死 未尝生”——李嵩〈骷髅幻戏图〉探析》中有谈道:“其一,常见观点认为,‘大骷髅’是死去的人,可能用于表现乳妇对死去丈夫的思念,也可能用于作者表达对亲友的悼念;其二,常见观点认为,‘大骷髅’是生者,可能是李嵩在生活中的所见。”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妇人与婴孩象征生命的延续,骷髅则是生命的终结,和“庄子叹骷髅”典故一样表现生与死的对立,隐喻顺应自然的道家生存之道。
清代《夜谭随录》中“骷髅”意指鬼怪,即认为“骷髅”意象与死亡相关。人生疏忽无常,骷髅曾经也是活生生的人,所有人都会经历“桃李面”变成“骷髅”的过程。李嵩在《骷髅幻戏图》中呈现给世人的骷髅形象究竟传递了怎样的生死观,仍需后人继续探讨。
(三)宋人的自然观
不少学者如施莉亚与吴蓉对《骷髅幻戏图》的写实性略有提及,但仅停留于视觉层面的感受判断,并未结合现代科学手段对其进行分析。通过李嵩《骷髅幻戏图》研究宋人的自然观是较为新颖的切入点,笔者整理文献后可得,目前学界联系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本幅团扇绢画的学者仅有一位,文献也仅有一篇。
邢珂于《〈骷髅幻戏图〉的写实性探析》借助现代自然科学,运用跨学科研究法对画面骷髅的形象与创作过程进行了全面研究与解读。第一,邢珂深入且细致地探讨了《骷髅幻戏图》中骷髅骨骼绘制的严谨性。文中通过骷髅的颅骨和牙齿排除大骷髅为动物骨骼的猜想,并对比画中骷髅骨骼与真实人体骨骼,研究其白骨化程度,由此对画中大骷髅的骨骼进行初步分析,得知“大骷髅”形象的写实性极高。第二,邢珂挖掘了该作品中的写实性由何而来,并将此画与西方绘画中的骨骼进行横向对比,最后结合时代背景,以宋代实证土壤与原发的自然观对文章论点进行详细佐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骨骼绘制的严谨性时,作者应用现代软件“3dbody解剖”进行佐证,其软件页面截图呈现于文献中与原画局部进行对比。此外,在“从骷髅胸骨缺失研究其白骨化程度”的部分,作者结合杭州气候背景与《尸体变化图鉴》所记载的尸体变化情况,发现李嵩画中骷髅的白骨化情况与实际的软骨脱落现象吻合,可见画家用功之深,李嵩对骷髅造型的精准把控绝非靠印象与幻想得来,由此可从实证精神的角度对李嵩进行新的认识。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成熟,《骷髅幻戏图》的研究不可仅停留于对画作表面的主观臆想,更多科学从业者若是积极参与相关研究,《骷髅幻戏图》的写实性探析或许还可进一步完善。
(四)合理性、假定性与荒诞性
经文献检索,笔者发现研究主题明确限定于《骷髅幻戏图》合理性、假定性与荒诞性的文献仅有聂子健与申梦鸽所著两篇。
1.假定性与合理性
申梦鸽于《人物角色存在的假定性与荒诞性——以〈骷髅幻戏图〉为例》中谈到,“假定性”是“戏剧中约定俗成的以假乱真的表现形式”,但这种“真实”实则是一种“假象”,是“人眼错觉产生的幻象”。由此,她提出《骷髅幻戏图》中的“假定性”表现于人物、地点和情节的合理性与人物角色层与关联层的合理性。
施莉亚谈到,李嵩笔触的质感与量感充盈写实性,质地变化细腻,具有“合乎画理”的入微表现力。聂子健于《李嵩〈骷髅幻戏图〉合理性与荒诞性研究》中则是直接点出其合理性,例如对物象质感的写实表现,以及画面中能反映出的社会现实。
2.荒诞性
荒诞美学是指人能从文学与戏剧中得到的一种不合理、不真实的主观感受,“真”与“幻”的矛盾若是充斥着画面整体,则能带给观者别样的美学感受。
聂子健认为,人物身份与衣着均不合理,例如从具有贵族气息的衣物可推断画中人物身份不低贱,但家庭中的男性角色却扮演“阴森恐怖的骷髅”,并且戏耍身份低微的傀儡艺人所擅长的“傀儡戏”。除此之外,他认为画中“生”与“死”主题存在矛盾,大骷髅形象的出现极其不合理,具有超现实性,部分研究者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意。申梦鸽认为,画中的“荒诞性”表现在着装的矛盾性、“生”与“死”的矛盾性、画面中心情节的荒诞性。
除了上述学者,还有诸多研究者对李嵩画中的幻境表达称奇不已,感叹其中作者真实经历与虚幻遐想的碰撞恰合画理。
(五)以鬼画人,讽刺世事
部分学者指出,鬼怪题材是画家们通过隐喻手法“以鬼画人、讽刺世事”的重要载体。李嵩出身平民家庭,做过木工,李崇训赏识他并将他收为养子,他勤奋刻苦、继承养父遗志,后入画院做了袛候。李嵩的出身让他深刻了解南宋时期百姓平民的生存现状,因此他常创作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风俗画,例如《货郎图》《四迷图》《春溪渡牛图》等。关于《骷髅幻戏图》中是否隐含对社会的讽喻性,不少学者对此展开过具体探讨。
1.隐喻政治
廖奔认为,傀儡艺人操纵傀儡的表演方式容易让人产生无奈、无助的联想,操纵者与被操纵者皆是行尸走肉,无论操控与被操控均会殊途同归,他称赞其可谓画家的“神来之笔”。不少学者均指出,李嵩作为宫廷画师,不可直接指出对政治的不满、对傀儡政权的无奈,因此,他“假借宫廷与民间常见的骷髅戏”,把问题抛给观者。
2.隐喻南宋百姓生存状态
有研究者发现,南宋多战乱与饥荒,骷髅形象具有大众化普及趋势,《骷髅幻戏图》可能隐喻了南宋人民的悲惨生活状态。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频繁的战争使粮价上涨严重,最终导致百姓无力支付高昂的粮价,某些地区频繁出现食人的正常生活状态,食用后剩下的骨头甚至成为孩童的玩具,骷髅对百姓来说并不陌生。此外,有学者认为李嵩受到战乱与灾害的影响,期盼人民多子多福,同时也通过该画表达了对战争残忍、百姓流离的无奈。
(六)作者与观者的互动关系
《骷髅幻戏图》寓意之谜因缺少作者李嵩本人自传与著作解释说明,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观者思考与探讨。具体谈到此画中作者与观者互动关系的文献仅有一篇,即马蝶所作《以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谈作品与观者的互动关系》。
马蝶发现,正是因为观者对此画意义不明的意象产生好奇心,才产生了推动观者与作者之间跨越时空的互动。若观者联系自我生命经验,并结合时代背景与自身想象力对作品进行解读,便能够实现不同时代之人的“延期对话”。
三、《骷髅幻戏图》与宗教研究现状
“骷髅”的形象多出现于宗教,李嵩对世事观察深刻,思想存在多面性,道家之“齐物”“乐死”,佛教之“寂灭”“涅槃”,或许都在这幅《骷髅幻戏图》中得到了生动诠释。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李嵩《骷髅幻戏图》中所蕴含的宗教思想争论不断,但皆有据可依、论述全面。笔者经文献梳理后总结出下文几处研究成果。
(一)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宋代已完全世俗化,可体现当时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佛教艺术中,骷髅形象并不难搜寻,如明代《顾氏画谱》中有抄录吴来庭《李嵩骷髅图跋》。
骷髅形象屡屡出现于宋代文物中,过往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与佛教有关。康保成指出,印度佛教密宗多用骷髅作为装饰,密宗中的“髑髅成就法”与“傀儡戏”之间相差无几,他认为“全真教用傀儡图与傀儡戏的说法应该是从佛教密宗中学来”。
有学者指出,宋代文物可能是受到佛教“白骨观”的影响。王一帆联系佛教五门禅法中的“白骨观”,对画中可能蕴含的佛教寓意进行解读,认为《骷髅幻戏图》中“妇人”“大骷髅”“婴孩”的形象较为对应,以警示观者“人生无常,四大皆空”。
除此之外,王一帆还指出“骷髅作戏”的表现方式与佛教“骷髅法”十分相似。画中“大骷髅”之骸骨如生者一般活动,与佛经中记载的“骷髅法”中“通过某种操纵机关之类的办法使骸骨活动”的做法或有关联。他认为,“骷髅法”可能是李嵩傀儡戏的前身,《骷髅幻戏图》大概亦与民间佛教弘法实践有关。
(二)道教
从北宋时期开始,道教有了世俗化趋向,南宋新道派出现,道教平民化成为主流。
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典故。古往今来,“骷髅”之意象经过文化史上的多次变革,若要探讨骷髅意象之意蕴内涵流变,定是绕不开“骷髅”相关的文学模式,例如《庄子·至乐》篇中两篇关于骷髅的典故。其一为“庄子叹骷髅”,蕴含着“生为劳役,死为休息”的寓意。其二曰:“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对于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汤雯雯认为,“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与李嵩《骷髅幻戏图》的寓意接近。
学界还有不少观点认为南宋李嵩受全真派影响深远。全真教以王重阳为首遵从道家精神,对传统道教发展继承。王一帆在《宗教视域下的南宋风俗画释读——以传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中有谈到,为了让弟子戒色心、蠲除爱欲,王重阳多次画《骷髅图》并赋诗以警示门人。全真教的骷髅画、骷髅诗即用来告诫门人,生死无常,若欲羽化登仙,必须静心修炼,这种生死观与庄子“齐生死”的思想一脉相承。王一帆认为“骷髅与婴孩并置”,从道家角度来看,“或许也是其修炼理论的一种图示”。
四、《骷髅幻戏图》的钤印、鉴藏与衍生创作
李嵩作此画距今已隔八百多年。随着社会时代背景的不断流变,除了画意,李嵩《骷髅幻戏图》上的钤印与后世鉴藏、衍生创作也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
(一)钤印与鉴藏
笔者经文献整理后发现,有关《骷髅幻戏图》的钤印、鉴藏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陆飞《〈骷髅幻戏图〉鉴藏考》最具代表,且参考价值高。此类文献数量虽少,但陆飞对此调查全面、叙述严谨,在笔者看来相关研究已然在走向完善。
1.钤印
《骷髅幻戏图》画上已有钤印九方,若再加上题跋上的钤印,即可见二十一方。笔者发现,学者们对此提及较少,但识读钤印是研究《骷髅幻戏图》不可缺失的一环。
陆飞在《〈骷髅幻戏图〉鉴藏考》较详细地使用“钤印识读”的方法,他大致交代了所有钤印的识别成果,并指出其图像与题跋的所有钤印之中,占大多数的为“珍秘”“真赏”等耿昭忠之印,除此之外,还可见耿嘉祚“会侯珍藏”之印、“大痴”“黄氏子久”等黄公望之印和其徒弟“玄真”之印等,其中最早钤印为黄公望与王玄真之印。他于文中较明晰地陈述了各个钤印方位,并发现李嵩的其他作品上也可见上述钤印反复出现,例如《货郎图》。
2.鉴藏
画家李嵩所生活的南宋距今已近千年,该画作流传、鉴藏的历史动向已较难考究,但仍有少数专著中留下过《骷髅幻戏图》的传承痕迹,少数学者对此也有相关学术发现,例如陆飞。
陆飞指出,识读钤印之后可知最早钤印属于黄公望及其学生,其后,该画被耿氏父子收藏,但耿氏著录中并未见其相关记载。另外,通过陈继儒所著《太平清话》可知,陈继儒曾收藏过此画,而且他在《陈继儒秘笈》中对此画有过相关阐述“金坛王肯堂见而爱之,遂以赠去”,也让后世知晓陈继儒最后将此画送予王肯堂。除此之外,陈撰所著《玉几山房画外录》可得知,此画大概在道光之后流入故宫。
(二)题跋——小令《醉中天》
《陈继儒秘笈》中有记载,“予有李嵩《骷髅团扇》,又有一方绢,为休休道人、大痴题”,可见,《骷髅幻戏图》之画伴有“休休道人”与“大痴”的题词。其中,“大痴”即黄公望,因其号曰“大痴道人”,人称“黄大痴”。另一“休休道人”即黄公望的学生——王玄真。此小令即为黄公望所作、其弟子王玄真所书。
黄公望题跋的《醉中天》小令是《骷髅幻戏图》衍生创作之一,或许对于理解《骷髅幻戏图》有益。王一帆于《宗教视域下的南宋风俗画释读——以传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指出,小令中寄寓庄子“齐生死”的观念,“苦和愁”即有“生人之累”“生为劳役”“劳我以形,苦我以生”之类意味,庄子“逍遥无待”的境界于其中有所实现。学界对小令的重视程度不浅,并已将其内容作为画意的重要佐证材料。
(三)其他衍生创作——苏绣《骷髅幻戏图》
古往今来,《骷髅幻戏图》相关记载众多,其衍生创作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经文献检索,笔者发现真正学界留名,并有学者参与研究的衍生创作屈指可数,唯有苏绣作品《骷髅幻戏图》值得一提。
当代苏绣作品《骷髅幻戏图》由姚惠芬、姚惠琴姐妹及其绣娘团队协力创作,于2017年在第五十七届威尼斯艺术展的中国国家馆展出,已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广泛好评,有少许学者已对此进行过研究,笔者对此不再展开叙述。
五、结语
国内学界对南宋李嵩所绘《骷髅幻戏图》的多年研究,使得其“谜画”身份正逐渐走向清晰明朗。鉴于其不菲的学术价值,笔者查阅了相关五十余篇文献,对其成果分类梳理后也整理出部分遗漏与缺憾。
第一,学界需对《骷髅幻戏图》中部分人物身份进行更准确的考究——该画面中人物的身份信息是对画意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二十多年来,画面中所有人物的身份未在学界得到统一,学者们从历史、衣着、动作等不同角度均能得到不同的猜想,可谓争议不断。笔者进行综述后总结可得,“乳婴妇人”的身份还需沿“职业乳母”的方向深入研究,因为“职业乳母”的说法出现于近五年,结合历史后可知其具有可靠性,但相关研究少之又少,需要更多研究者参与佐证。
第二,前人研究手段较为单一,跨学科研究相对较少,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的学者仅有一人。笔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合理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将大有裨益。更多科学从业者也可以参与对《骷髅幻戏图》的探讨,结合生物、数学等专业知识开阔《骷髅幻戏图》的研究视野。
第三,笔者整理文献后发现,许多观点大同小异,近年来新发现渐少,因此难以排除学界对《骷髅幻戏图》研究热情衰减的可能。《骷髅幻戏图》题材小众,大多相关文献学术性较强,可读性与趣味性较弱,由此,笔者认为,学界也应在考虑《骷髅幻戏图》相关研究专业性的同时,跟进文章的可传播性,若忽略此点,未来受《骷髅幻戏图》自身魅力吸引而前来研究的学者将更少,往后的研究将更为艰难。
第四,阅读陆飞《宋李嵩〈骷髅幻戏图〉鉴藏考》后,笔者认为陆飞提到的“多图像之间的互文性、实证性研究较少”言之有理,也可供往后研究者进行参考。
第五,《骷髅幻戏图》相关比较研究太薄弱,相关文献仅有一篇。多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画意的理解、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画家李嵩。更全面的比较对《骷髅幻戏图》、宋代艺术、画家李嵩具有缺之不可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李嵩生活的时代距今已八百多年,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骷髅幻戏图》如同一段尘封的历史,在时间的沉淀下独具韵味。尤其是21世纪以来,学界对《骷髅幻戏图》的研究逐渐深入,而画中深意仍在经历一个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总之,尽管困难重重、步履缓慢,《骷髅幻戏图》的学术研究步伐仍有向前接续迈进之趋势。
参考文献:
[1]陆飞.《骷髅幻戏图》鉴藏考[J].美术学报,2020(04):95-101.
[2]廖奔.《骷髅幻戏图》与傀儡戏[J].文物天地,2002(12):24-27.
[3]马卿.如幻如戏生与死——再看李嵩《骷髅幻戏图》[J].艺苑,2009(08):16-18.
[4]汤雯雯.“未尝死 未尝生”——李嵩《骷髅幻戏图》探析[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5年.
[5]杜七龄.《骷髅幻戏图》绢画中人物形象的图像学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3(10):13-15.
[6]张廷波.“妇人乳婴”形象身份考——以南宋李嵩画作为例[J].美术,2022(10):105-111.
[7]马蝶.以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谈作品与观者之间的互动关系[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21年.
[8]王一帆.宗教视域下的南宋风俗画释读——以传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94-101.
[9]邢珂.《骷髅幻戏图》的写实性探析[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22年.
[10]申梦鸽.人物角色存在的假定性与荒诞性——以《骷髅幻戏图》为例[J].大众文艺,2019(07):92-93.
[11]施莉亚.李嵩《骷髅幻戏图》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
[12]聂子健.李嵩《骷髅幻戏图》合理性与荒诞性研究[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