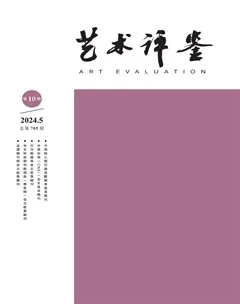秧歌与花鼓关系初探
【摘 要】艺术起源和不同艺术形式的关系是艺术研究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秧歌与花鼓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中两种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作为汉族民间舞蹈的一种形式,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地区,深受群众喜爱;花鼓舞也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舞蹈形式,尤其在南北方交汇地区备受青睐。秧歌和花鼓都以鼓作为伴奏乐器,这两个民间舞蹈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本文就其两者溯源及其关系问题进行探析。
【关键词】“宝山地秧歌” “陈官短穗花鼓” 艺术形式 联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0-0031-06
“宝山地秧歌”和“陈官短穗花鼓”都是山东地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山地秧歌”发源于山东省青岛市,“陈官短穗花鼓”流传于山东省东营市,分别是秧歌和花鼓这两类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宝山地秧歌”和“陈官短穗花鼓”为例,引出对秧歌和花鼓这两种民间艺术形式溯源及其关系的思考。
一、“宝山地秧歌”和“陈官短穗花鼓”概述
(一)“宝山地秧歌”
“宝山地秧歌”源于明末清初,又名“宝山秧歌”,当地称“耍耍”,它发源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宝山镇黄山后村,流传于古胶州西南乡和灵山卫扒山村,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一种以歌舞为表现形式的民间艺术形式。具体而言,它隶属于胶州秧歌中富有特色的南路秧歌流派。
“宝山地秧歌”距今传承到第六代传承人,约有380年的历史。其北至胶州、高密,西南到日照,东至灵山卫,西到诸城,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风格特点。2007年和2021年,“宝山地秧歌”分别入选为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
(二)“陈官短穗花鼓”
“陈官短穗花鼓”起源于明清时期,又名“打花鼓”“秧歌鼓”,主要分布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陈官乡及其接壤的周边地区和商河等市县,流传于黄河三角洲的广饶县陈官乡陈官村,是山东省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距今约有120年的历史。其艺人所创制的“花鼓”在鼓槌的尾端系有鼓穗,并且能以穗击鼓,所以得名为“短穗花鼓”。2006年和2008年分别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秧歌同样属于我国民间舞蹈传统文化,其历史价值意义非凡。
宝山地秧歌与陈官短穗花鼓多用打击乐进行伴奏。传统的地秧歌艺术形式相较于花鼓较复杂,伴奏乐器也随之多样化。地秧歌乐队分武场与文场,文场乐器由唢呐、二胡、笛子等组成;武场乐器由鼓、锣、钹等组成。陈官短穗花鼓艺术形式较为简单,传统花鼓形式由鼓、镲、唢呐等伴奏。
二、秧歌与花鼓溯源
(一)秧歌
秧歌在中国已有千年的历史,它结合叙述、歌唱、舞蹈三种元素,也就是将诗歌、音乐和舞蹈和谐统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街头的乞讨表演。秧歌要考据其源流相对困难,传说东北地区在唐朝时期早就有了秧歌,在元朝时期,这一艺术形式有时和宗教结合起来,或为皇帝的娱乐项目,所以历史是悠久的。后来在东三省一带流行的秧歌逐渐转入关内,又传遍华北五省,甚至传到安徽西北一带;如今,秧歌已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脚步扭遍全中国,已经成为解放的象征、胜利的标志。学术界关于秧歌起源的研究说法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宋代“村田乐”说(娱乐说)
秧歌这一舞蹈艺术经历了从田间地头的简单娱乐到今日广受欢迎的民间艺术演变。老百姓喜闻乐见,学起来较容易。从一开始的田间作乐,再到后来由于社会战乱频发作为一种乞讨形式,展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如今更是以广场舞的形式深入人心。老百姓从秧歌中寻找乐趣,通过扭秧歌来强身健体。秧歌已然成为一种承载欢乐、传承文化的民间艺术形式。
2.民歌说
秧歌本是民间的山歌。古人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所言极是。在清代,许多文人墨客热衷于创作“秧歌”,他们追求独特的艺术风格,力图在文风中展现新的元素和创意。同时,也有一些人通过写作秧歌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味,紧跟时代潮流。《凤阳歌》中也唱道:“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据说当年北京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曾编有秧歌两大册,说明秧歌作为民歌亦曾有过集结成册的鼎盛时期。这样的舞蹈形式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北方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时期已达到鼎盛。
民歌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秧歌在插秧时,笔者大胆猜想,大多会有一些类似山歌或号子的秧歌。号子的特点是“一领众和”,劳动人民在进行田间劳作时,由一人总领,其他人随声附和,边劳作边扭秧歌,充分表现自己的生活。
3.花鼓说
南方花鼓即北方秧歌。花鼓与秧歌同宗同源,实为一事。清·湖南《宁乡县志·风俗》中记载:“上元先数儿童秀丽者扎扮男女妆唱插秧、采茶等曲,曰‘打花鼓’。或跨竹马,谓之‘竹马灯’。”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中记载:“潮州灯节,有鱼龙之戏。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与京师无异,而采茶歌尤妙丽”。由路工编选的《清代北京竹枝词》,内有康熙年间宣城袁启旭纂孔尚任等人写的《燕九竹枝词》已将花鼓、秧歌合二为一了。曰:“秧歌初试内家装,小鼓花腔唱凤阳”。在其《平阳竹枝词·踏灯词》中记载:“秧歌竹马儿童戏,还到堂前舞一回”。唱秧歌、打花鼓、采茶歌、跑竹马均已融合。
宝山地秧歌在表演时也需要大量打击乐器进行伴奏,腰鼓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宝山地秧歌中花鼓所用鼓槌是经历过演变的。早时鼓槌为木质,长约七八十公分,鼓槌顶端稍细,在鼓槌尾端处系一长约五十五公分的红色丝绳,再在绳上系若干簇黄色丝穗,称之为“鼓鞭”,为棉麻材质。据传承人口述记载,后来他们会将铜钱或算盘珠绑在鼓鞭上,使之重量增加,便于击鼓发力。击鼓动作双腿半蹲,右手“鞭头击鼓”,左手“击鼓”,同时于下一拍击右鼓面,上身顺势立起,眼视左前下方。换言之,宝山地秧歌曾经使用过“鼓鞭”击鼓的方式。近年来,由于秧歌参演人员复杂,表演重点偏于展现剧情,秧歌表演中腰鼓的击法被逐渐简化,表演使用的普通木质鼓槌尾端系一红色绸缎,击鼓时使用鼓槌敲击。
(二)花鼓
花鼓,这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融合音乐、曲艺、戏曲和舞蹈等多个元素,同时还交织着众多非艺术领域的精髓。当人们深入探讨花鼓的定义、特征、形式及其产生、发展、演变和现状时,不难发现它既拥有独特的个性,又展现出中国艺术的深厚共性,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考,它在五代十国时期或许有所记载,当时可能是作为一种来自远方的珍贵贡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花鼓逐渐从宫廷内走出,成为佛家的礼器,象征着庄重与神圣;到了宋代,它更是融入民间百戏之中,成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这样的演变不仅展现了花鼓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体现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多样功能。
对于花鼓的溯源,学术界说法众说纷纭。但对于它的起源大体可归为以下四种:
1.神话、传说、民俗说
关于花鼓的起源,最早在大禹治水的典故中有所体现。 在《庄子·天下篇》《列子·杨朱篇》以及《孟子·离娄上》中,都流传着大禹治理淮水的故事。《水经注》中详细记载,荆山和涂山对峙而立,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地理联系。大禹为了治理泛滥的桐柏之水,决定凿开山体,让水流通畅。而在《吕氏春秋·音初》中,人们听到涂山氏之女为等待大禹而唱出的动人歌曲“候人兮猗”,这被视为南音的起源。
花鼓的表演多为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涉及音乐、民俗、舞蹈、社会生活等方面,往往会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从中反映出人民的生活和信仰;花鼓的表演形式也深受传说、民俗的影响,艺人们运用各种技巧和手段,加上夸张的动作、丰富的语言来增强故事感染力和表现力,使其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2.宋代民俗艺术说
李家瑞认为:“打花鼓就是古时候的‘三杖鼓’。”三杖鼓即为羯鼓。李家瑞作为民俗学家的代表,在探讨“打花鼓”这一民间艺术起源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实际上源于唐宋时期的“杖鼓”。这种观点认为,从唐代的“三杖鼓”开始,经历了宋代的演变,包括三杖鼓、花鼓棒、花鼓槌等多种形式,到了明代,它逐渐被称为“三棒鼓”。而到了清代,这一艺术形式又进一步丰富和变化,形成人们现在所熟知的“三棒鼓”,或者又称为“三根棒”“三根头”,以及俗称的“打花鼓”。据《湖北民俗志》记载,“三棒鼓”又被人们称作“打花鼓”,这一名称的由来正是源于其起源的唐代“三仗鼓”。其中,咸通年间王文举所创制的“杖鼓”被认为是“三棒鼓”或“打花鼓”的最初形态,它历经了时间的洗礼,逐渐演变并流传至今,成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民间艺术形式。
花鼓在表演中,舞蹈动作丰富多样,体现出民间舞蹈的独特魅力。随着不断传承发展,现如今的一些古庙庆典、闹元宵或过年等喜庆节日活动中,花鼓都会进行表演,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鼓的表演往往具有祈福纳祥的寓意,主要表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出民俗文化中的祈福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传承和发展不仅体现了民俗艺术的魅力,也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传承和交流传播。
3.秧歌说
关于花鼓与秧歌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常常依据多种历史文献和记载来探讨。例如,《缀白裘》中收录了凤阳的《花鼓》,而《帝乡纪略》则描述了泗洲插秧时,来自远方的男女们一边击壤一边互相对歌的情景。这些文献说明花鼓与秧歌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在《百戏竹枝词·打花鼓》的注解中,得知“打花鼓”这种艺术形式在凤阳地区多由妇女表演,并被称为“秧歌”,这进一步暗示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被视为农民在庆祝丰收或举行赛会时的一种娱乐活动。
此外,《霓裳续谱》中录有《凤阳歌来了》,其中歌词“酒醉饭饱,就唱秧歌”和《凤阳鼓凤阳锣》中的“凤阳姐儿们唱秧歌”等表述,都凸显了花鼓与秧歌之间的关联。这些歌词不仅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也体现了花鼓和秧歌作为民间艺术的普及性和受欢迎程度。
陈官短穗花鼓表演时所使用伴奏乐器虽少却精,短穗花鼓所用的花鼓与一般的腰鼓类似,花鼓的特殊击法是整个表演过程中的精髓所在。短穗花鼓的击打并不像其他地区大多数花鼓一样使用鼓槌敲击,而是用鼓槌一端的鼓穗击鼓。木质的鼓槌尾端系一约50公分的线绳,自上端三分之一处与末端分别结有一疙瘩,在二者中间的部分系有一枚横向的,似“豆角状”的结,因其两端呈尖形,广饶地区也俗称“猫耳朵”。再在两侧尖端处分别悬挂一枚小疙瘩,整条鼓穗四枚疙瘩外都包有丝穗。击鼓时挥舞鼓槌利用惯性带动鼓穗,使用最末端那枚疙瘩接触鼓面完成击打,这也是短穗花鼓不同于其他鼓类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显而易见的是,宝山地秧歌早时曾使用“鼓鞭”击鼓,与陈官短穗花鼓使用“鼓穗”击鼓同源共流,二者虽叫法不同,但其形态本质相同,这在山东地区乃至华东一带的民间艺术形式中都是不可多见的。
二者击鼓时都将鼓斜挂在腰部左侧,短穗花鼓击鼓重点虽是使用“鼓穗”击鼓,但常见的击鼓动作组合为右手做“抡穗后击鼓”与“抡穗前击鼓”,与此同时,左手做“绕腕击鼓”,“鼓穗”与鼓槌同时击鼓,但左右两只手击鼓节奏不同,击鼓材质不同致其音色不同。击鼓角色表演难度大,对鼓手的音乐与舞蹈的基本素养要求较高,无论在视觉还是听觉上都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相比短穗花鼓,宝山地秧歌只有“鼓子”这个角色击鼓,鼓子的舞蹈动作更为多样。关于鼓子,上文中提到与短穗花鼓类似的“鞭头击鼓”,除此之外,还有最基本的使用鼓槌击鼓。
综合以上各种文献和记载,可以得出一个观点:花鼓与秧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在表演形式、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4.傩文化说
傩舞,亦可称为鬼戏,是汉族古老而独特的宗教仪式舞蹈,旨在通过舞蹈形式祭拜神灵、驱除瘟疫、庆祝安宁。傩文化深深植根于华夏的远古文明中,“傩”不仅是流传甚广的宗教仪式,更是艺术与信仰交织的生动展现,它源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图腾的崇拜,以及古老的巫术传统。
通过对以上三种起源的学说判断,不难发现,傩文化才是共同的起源和艺术核心。据《中华舞蹈志·河北卷》载:民间傩舞可能就是迓鼓的渊源。清 ·光绪《米脂县志》云:“春节闹社火,俗名闹秧歌…… 有古乡人傩遗风。”《临江县志》:“耍龙灯,龙船、秧歌诸戏,十七日始罢,此《乡党》篇‘乡人傩’之义(意)也。”《续修陕西通志稿·风俗(四)》言:“秧歌颇具古乡傩意。”
对于花鼓和傩戏的关系,可以从史料中有所发现。在山西地区出土的《扇鼓神谱》古抄本中详细记录了当地的驱傩祭祀活动。这场活动不仅由手持扇鼓的“十二神家”参与,还得到了锣鼓队和花鼓队的热情支持。在名为“游村”的环节中,锣鼓队、“十二神家”和花鼓队一同在“遵行傩礼,禳瘟逐疫”的大纛旗下,穿行于村庄之间,旨在吸引村民们共同加入这场庄重的驱傩祭祀仪式,祈求平安健康,驱逐瘟疫和疾病。由此可见,傩文化乃是花鼓的艺术起源和核心。
花鼓在舞蹈动作和服饰道具上与傩舞相类似。傩舞的一些舞蹈动作从花鼓表演中借鉴而言,增强了表演的观赏性。在服饰道具上,傩舞和花鼓表演中,花鼓也受到傩舞的启发,通过特定的服饰和道具来塑造角色形象,增强表演效果。
傩文化起源于古代巫术和神道信仰,具有驱邪避邪的宗教功能。花鼓表演中,虽然形式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同样也蕴含着祈福纳祥、驱邪辟邪的寓意,这种融合使得花鼓表演在民间具有文化认同感。傩文化与花鼓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运用。这种运用不仅丰富了花鼓的表演形式和文化内涵,也促进了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花鼓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为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
三、秧歌与花鼓关系初论
对于秧歌与花鼓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关系,通过上述对比分析,笔者大胆猜测其二者具有一定的关系。
(一)共同起源
南方花鼓与北方秧歌虽然在地域上有所区别,但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社火、傩仪这一共同的文化源头。并且一开始都存在祭祀活动,百姓们祈求风调雨顺。从湖南《宁乡县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打花鼓”这一活动在上元灯节时的盛况,男女共舞,热闹非凡。学者林河在《傩史》中的观点为人们揭示了秧歌可能的传播路径,它可能是从南方传入北方,并在东北等地继续流传。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二者出现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不断延伸开来,最后不断发展为现在的艺术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方没有“秧”,但“秧歌”一词的流传和使用,无疑说明这种艺术形式在北方的广泛接受和融合。
明清时期,在市民大众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花鼓和秧歌这两种艺术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们不断吸收和融合各种民间艺术精华,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见到的丰富多彩pSWjLJv8qUVLvl1fUdAMEiRVq8YFzPCX7jfWdMS8Nck=的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南方的花鼓还是北方的秧歌,它们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值得珍视和传承。
(二)包含发展
根据“宝山地秧歌”和“陈官短穗花鼓”的描述,可以看出鼓在秧歌和花鼓这两种艺术形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记载:“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羣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这段文字记录了秧歌与鼓之间的联系,插秧劳动时击鼓作歌是肯定的。湖南《晃州厅志》载:“岁,农人连袂步于田中,以趾代锄,且行且拨,滕间(田埂上)击鼓为节,疾徐前却,颇以为戏。”据这段文字记载,可以推测出鼓在农人劳作的时候,起到了类似伴奏的作用。在激昂的鼓乐声中,舞者们灵动地展现了“三进一退”的舞步,或踩着高高的跷子,他们的步伐如诗如画,蜿蜒曲折,充满韵味和美感。
由此可见,花鼓极有可能是在秧歌的不断发展中慢慢分离出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三)二者为同一种艺术形式
秧歌中包含花鼓,花鼓中又有秧歌的元素,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笔者猜想,如今的秧歌与花鼓在早期展现出极为相似的艺术形式,或许可以认定为同种艺术形式。它们最开始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田间地头扭秧歌、打花鼓。但随着社会发展,许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也正因为这种艺术形式简单易学,为了养家糊口,所以成为老百姓街头乞讨卖艺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人越来越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秧歌和花鼓慢慢演变发展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秧歌与花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都是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宝山地秧歌”和“陈官短穗花鼓”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民间,发展于民间。但现如今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遭遇瓶颈,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它在传承发展中更加深刻的含义。对待传统艺术,不能简单地传承它的表演形式和技艺,更应该深层次探究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地从被动保护变为主动发展,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就能得以更好地继承发展,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参考文献:
[1]谭娜,刘妍,甄惠.陈官短穗花鼓文化内涵及非遗保护探析[J].现代交际,2020(16):113-114.
[2]易方星.山东民间舞蹈“短穗花鼓”艺术特征及文化内蕴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年.
[3]张树利,曲艳丽.黄河口短穗花鼓运动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02):153-156.
[4]殷亚昭.“秧歌”溯源——兼谈“南方花鼓”即“北方秧歌”[J].上海艺术家,1997(02):33-35.
[5]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中华舞蹈志·河北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89.
[6]大德,宁佑.陕北秧歌渊源新探[J].文艺研究,1985(03):143-144.
[7][清]李调元撰,张智主编.南越笔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8]黄雪伦.陈官短穗花鼓研究[D].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