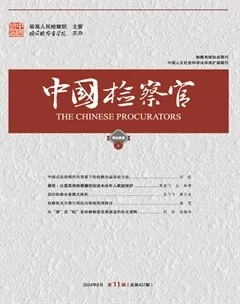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范围探讨
摘 要:行刑反向衔接是行政检察承担的一项新的职能,实践中对其范围存在难以把握的情形,需要从行刑反向衔接的本质出发予以精准界定。行刑反向衔接是一个多元共治的体系,检察机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划分行刑反向衔接职能的标准是由作出实体终局决定的机关承担行刑反向衔接职能。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是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并表达法律观点,并无对行政机关的责难。对于不起诉案件中的关联违法行为,不应纳入行刑反向衔接范围。对于不起诉的涉嫌犯罪行为损害公益符合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情形,应作为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办理。
关键词:行刑反向衔接范围 检察意见 可责性
行刑反向衔接是指,对于刑事司法程序中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移交有相应管辖权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1]长期以来,在检察机关内部,行刑反向衔接职能由刑事检察部门承担。2023年7月,最高检印发《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反向衔接工作由行政检察部门牵头负责。这既健全完善了对违法犯罪的治理体系,也调整优化了检察机关内部分工,丰富拓展了行政检察职能。作为一项新增的行政检察职能,明确其范围是精准规范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范围的实践之惑
(一)是否仅限于不起诉案件之惑
《刑事诉讼法》和《意见》均将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范围限定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但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还承担批准逮捕、监督刑事审判等多项职能,在此过程中发现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检察机关能否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实践中对此有疑问。据笔者观察,有检察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也有检察机关在研究探索对人民法院判决无罪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无论对这一问题持何种认识,都需要深入探讨规范背后的法理依据。
(二)是否仅限于不起诉决定所羁束的违法行为之惑
不起诉案件中的违法行为多样,既有受不起诉决定所羁束的违法行为,也有与之相关联的违法行为,还有在刑事案件中暴露出的违法行为。对这些违法行为,是否都应纳入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范围,实践中做法不一。根据《意见》规定,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由刑事检察部门移送行政检察部门,最高检为此设计了专门的办案流程。刑事检察履职中发现行政机关可能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情形,应当依照《人民检察院内部移送法律监督线索工作规定》,移送行政检察部门统一筛查办理。可见,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流转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线索流转不同,适用不同的程序。对前述问题的正确认识,直接关系办案程序的正确适用。
(三)是否包括损害公益的违法行为之惑
检察机关开展的行刑反向衔接是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的一种衔接机制,但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也包括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在违法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两种衔接机制存在竞合。如对于涉嫌污染环境的犯罪,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的责令违法行为人修复治理的职责,是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办理,还是作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应当予以明确。
二、检察职能范围内的行刑反向衔接
(一)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限定在不起诉案件的法理分析
行刑反向衔接是一个多元共治的体系,其不仅仅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更是刑事司法程序参与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共同责任。“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案卷材料退回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案件作出处理”“对不够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行政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人民检察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司法建议,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处理。”[2]从中,可以清晰看出不同刑事司法机关承担各自行刑反向衔接责任的划分标准,即由刑事司法程序的终结机关或者说是对刑事案件作出实体终局性决定的机关承担行刑反向衔接职能。
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不起诉案件包括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等。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是对刑事案件的完全终局判断,之后再无针对违法行为人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存疑不起诉的事实认定尚不具有确定性,在重新侦查收集证据达到证明犯罪标准时还存在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这种终局性决定不具有彻底性。但再次启动的刑事司法程序与之前案件在事实认定和证据支持上差别甚大,可视为新的案件。此外,存疑不起诉能否再次启动刑事司法程序尚有不确定性,为维护行政法秩序,有必要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认可存疑不起诉的终局性,对存疑不起诉的违法行为开展行刑反向衔接。
(二)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实施与监督
在行刑反向衔接体系中,检察机关既是实施者,又是监督者。作为实施者,检察机关应当将刑事案件不起诉和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告知、移送行政机关,并提出检察意见。该检察意见属于关口前移的预防性举措[3],并无监督属性,且依附于案件的告知和移送,故该职能履行体现的是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实施。作为监督者,检察机关还应当对其他主体实施反向衔接情况开展监督。对行刑反向衔接的监督本身,也是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重要内容。[4]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活动,检察监督应当有一定的谦抑性,以免侵蚀被监督对象的权限,破坏宪法构建的权力秩序。从近年来的立法实践看,将依职权监督案源限定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是贯彻监督谦抑性的重要举措。[5]从实践层面看,检察案件中涉及的违法情形,检察机关有发现的便利条件,也利于监督职能的履行。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落实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开展监督,应当限定在进入检察办案程序的刑事案件,主要是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案件中公安机关执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监督。检察机关办理批捕案件,是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判断,虽然可能会对公安机关就案件的实体处理产生影响,但该判断不是对实体的终局性决定,检察机关不能对此类案件实施行刑反向衔接。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分为绝对不捕、证据不足不捕和无逮捕必要性不捕。对绝对不捕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对需要公安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情况,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督促。对于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应当跟踪公安机关后续案件办理。在公安机关补充收集证据,后续刑事司法程序顺利推进的情况下,并无公安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余地。在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需要公安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予以跟踪,视情开展监督。对于无逮捕必要性不捕的案件,后续刑事司法程序仍会继续进行,公安机关不会对案件作出终局性判断,公安机关无需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对于人民法院承担的行刑反向衔接职能,检察机关在收到无罪、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后,应当跟踪人民法院履行行刑反向衔接职能情况,对人民法院怠于履行该职责的,应当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
三、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范围
根据行刑反向衔接的定义,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适用于不起诉决定所羁束的违法行为。准确把握其特质,有助于确立纳入行刑反向衔接的违法行为的实质标准,能够解答实践中的各种疑虑。
(一)对不起诉决定所羁束的违法行为未处理,行政机关无可责性
首先,对于行政机关通过正向衔接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侦查的案件,行政机关尽到了发现、调查的义务,仅是因为刑事优先性,需先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刑事处理。在检察机关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由于刑事司法程序的终结,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由刑事处理转化为行政处理,管辖权主体由公安机关变更为行政机关。这种变化转移,系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所形成,行政机关不存在怠于行使职权的可责性。
其次,对于公安机关自行发现线索侦办的案件,涉案违法行为既构成行政违法又构成刑事违法,尽管行政机关并未及时发现,但对此类违法行为,刑事责任的追究是首要的,查纠违法的责任主体是公安机关,行政机关未及时发现查处并无可责性。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即使行政机关及时发现也不能查处,而应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侦查。因此,对于公安机关自行侦办案件,行政机关未发现、未作出行政处罚,并无可责性。检察机关通过制发具有程序效力、无非难性的检察意见,既可以避免检察机关的观点过于强势而误导行政机关的判断,又可以将检察机关所采集的信息以及分析后的案件处理观点及时传送给行政机关,从而实现对违法犯罪的一体化治理。[6]
(二)行刑反向衔接不应涵盖关联违法行为
关联违法行为是指刑事案件中呈现但并非不起诉决定所羁束的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牵连型、刑事案件呈现型等情况。犯罪行为牵连型关联的违法行为与不起诉的涉嫌犯罪行为系两个行为,但二者存在密切联系,或为实施犯罪行为作准备,或为实施犯罪行为所欲达成之目的,亦或者有其他密切关系。刑事案件呈现型所关联的违法行为系在对刑事案件的深度审查中发现的与犯罪行为并无直接关联,但反映出行政监管漏洞,对犯罪形成间接影响的行为。
对于关联违法行为,不应将其纳入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范围。关联违法行为未受到刑事追究,没有刑事司法程序的羁束,行政机关对其的查处职责不应受影响,行政机关未对关联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存在行政不作为,其具有可责性。在此情形下,检察机关不应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而应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三)行刑反向衔接应涵盖损害公益的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行刑反向衔接体现了检察机关一体履职的办案理念,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实现了案件从刑事检察向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的过渡,行刑反向衔接成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和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来源。行刑反向衔接是实现转化的必经程序,有其独特性。首先,从法理层面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监督的是行政违法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机关,有专业人员从事执法活动,违法情形的出现不存在免责事由,行政违法行为是具有可责性的行为。在此意义上,违法性与可责性系同位概念。检察建议是具有责难性的监督方式。行刑反向衔接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履职要求,并无对行政机关的责难。因此,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存在本质区别。
其次,从规范层面看,最高检印发的《意见》,将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作为两项独立的工作提出要求。对行刑反向衔接中制发的检察意见,《意见》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作为其跟进监督措施,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二者不存在隶属关系。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都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只是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范围限定在损害公益的行政违法行为[7],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此在《意见》中对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工作要求,涉及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与行刑反向衔接的互不隶属性,意味着行刑反向衔接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也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两项相互独立接续跟进的检察职能,在对反向衔接的后续跟踪中,发现行政违法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应当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