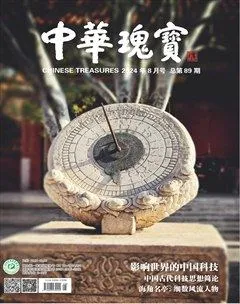《左传》节制观念与审美意识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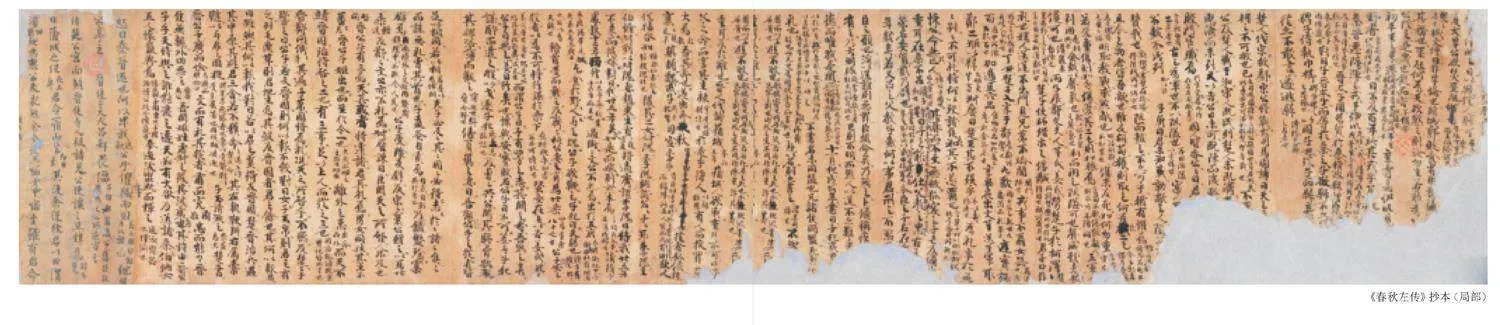

『节制』是《左传》的思想倾向之一,它影响了时人的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各种行为和活动。周代审美强调节制,其实是适应了礼的制度与秩序,这种审美意识经孔子的整合,形成了系统的美学理论。
《左传》没有明确表达美学的标准与观念,但其中所记载的人们的行为内容与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却可以引导我们思考时人的审美观念,我们常说的“中和”之美就体现在时人注重节制的生活方式中。所谓“节制”,可以理解为节俭而守制,是内在修养约束与外在法度要求的统一。
《左传》中的“节制”现象
《左传》中表示“约束”含义的词有“节”“俭”“克”“幅”“要”等。据统计,在相关语境下,“节”“俭”二字各出现了十次和九次;而“制”与“度”的使用频率更高,共约六十次。可见“节制”的确是《左传》的思想倾向之一,它影响了时人的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各种行为和活动。
在《左传》作者看来,当政者节俭的生活方式能够为国家振兴提供了基础保障。卫文公在国难当头之际,衣着朴素,选贤任能,鼓励生产,用勤俭之策,使卫国重新恢复元气。这样的叙述方式会引导读者得出节俭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用人、生产等国家大政方针一样重要的结论。《左传》比较系统而直接地阐述节俭的生活方式,是在对阖闾的书写中,吴王阖闾不以虚饰为美,其在位期间举贤任能,发展生产,举止有度,体恤百姓,最终使国家兴盛,雄霸南方。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加克制,外物与身份不相匹配的生活方式于己于国皆有害。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鹬冠,结果被郑伯派人杀害。节制体现在外物与身份匹配,否则即被视为“不衷”“不称”。鲁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齐国大夫庆封驾着华丽的车前来投奔鲁国,鲁国叔孙认为其“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这种谶语式的评价,体现了时人的审美倾向。庆封作为臣子,器用奢靡,嗜酒好田,劳民伤财,结果落得全族被诛的下场。楚灵王兴修章华台,荒淫无度,故“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无论君或臣,追求美的享受而失于节制,都将陷入危险境地。
《左传》主张节制欲望,认为美色有害。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景公病入膏肓,秦医和借“六气”和“五节”的原理,指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鲁成公二年(前589年),楚庄王、子反先后欲娶夏姬,被巫臣以“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的理由阻止。由此可见,《左传》中的审美活动,遵循相称、适度的原则,契合“礼”的秩序价值。
除了物质节俭与生理审美内外相称这一观念外,《左传》对待精神生活也秉持守制观念。鲁庄公二十年(前674年),王子颓叛乱之后,放纵淫泆,乐舞不倦,遭到郑、虢联军驱逐杀害。而郑厉公效尤王子颓,奏乐及遍舞,不久后也丢了性命。在乐舞的审美风格上,人们也追求“节制”。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在鲁观乐,先叹乐舞之美,再一一给出评价,强调了以适度为美的艺术评价标准。
礼乐是周文化的集中体现,但其内在精神却是节制美德。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郑国的公孙黑肱在病重后嘱托家臣和儿子“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尽归其余邑”,体现了敬戒而不贪的可贵品质,从而得到《左传》的认可。“薄祭”之所以不会被视作冒犯神明的行为,是因为《左传》对于“美”的评判,比起表面的浮华,更注重内在的充实。美在于真诚的德行,若仅强调“牲牷肥腯,粢盛丰备”的形式,就不能取信于神明。“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不仅是周人现实生活中的处事原则,也是其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乐制度原则。
殷周易代与“节制”观念的形成
“礼”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初文作“豊”,反映的是食物献祭、乐器演奏、玉币进奉等祭祀程序。殷商礼制源于祭祀歌舞这种特定的事神致福活动,具有“尚鬼”的宗教色彩。商代的宗教思想是“一元多神”的信仰体系,商王作为“一元多神”的代表,“率民”参与宗教活动,并在巫祝中介帮助下,通过占卜祭祀的仪式与“宾于帝”的“鬼”沟通,进而取悦、祈祷于“上帝”。商人“尚鬼”的精神,使得宗教礼制呈现出庄严、神秘的特点,因而影响了当时的审美倾向。工匠怀着恭敬虔诚之心精进制造技艺,使得青铜礼器上的花纹日趋繁复。殷商中后期所提倡的,主要是庄重雄浑、繁缛狞厉之美,有“文胜其质”的倾向。
商王生活不加节制,主要体现在对饮酒的态度上。《尚书》载微子言:“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纣过度饮酒,导致政治腐败、国家岌岌可危。除了嗜酒,后世还记载了商末王族其他的失当举止。譬如殷人尚声,商族不仅有祭祀专用的、不加节制的“巫乐”,还有供统治者纵情享受的“淫乐”。
《左传》以重“礼”之说贯穿始终,其言“礼”者凡462次,另有“礼食”“礼书”“礼经”“礼秩”“礼义”之文。《左传》言礼,不仅记录礼仪现象,还体现周人礼制观念—礼与“节制”的审美思想密切相关,这正是得益于周人对“殷礼”的改造。周部族趁商纣远征东夷,突袭殷商,一方面塑造、强调商末纣王“荒淫”的面目以示其亡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因于殷礼”又“有所损益”。这些举措丰富了“礼”的精神,使得神本位的宗教文化开始向人本位的伦理文化转变。周王朝吸取殷人耽酒乱国的教训,试图“拨乱反正”,自然更主张一种节制适度的美德。周代统治者用道德约束自我,并且督促臣民适度饮酒,崇尚节制,这项举措符合“礼义”精神。
周人在祭祀时也以节制为美。周人祭祀用“玄酒”“明水”“疏布”“蒲越”,他们认为神明是质朴的,应该尊其本来面目,这与商人对神以多为贵的印象不同。“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周人还通过控制祭祀的频率,对其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使风俗井然。
周代审美强调节制,其实是适应了礼的制度与秩序。而“礼”的秩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区分等级的功能,这在器用方面更加明显。比如雅乐,对于审美主体来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贵族官员需按规定欣赏乐舞,严禁逾矩滥用,其中也特别强调“节”的观念。
作为统治阶级,君王、大臣应该保持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以身作则、以俭矫世。晏子生活节俭,服饰粗劣,却拒绝齐景公的赏赐,指出“君就赐,使婴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婴服之于下,不可以为教”。如果说《左传》多述节制行为,那么比较完整从理论上阐述节制观念的则是《周易·节卦》—节制可致亨通,但过分的节制也是不合适的,应当持正、适中。君子应当效法“节卦”的义理,制定典章制度和必要的礼仪法度来作为行事的准则。
孔子对节制审美观的推动发展
孔子十分推崇以子产、晏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内外约束、节制审美的理论。孔子自身的审美活动,始终围绕“克己复礼为仁”体现的“节制”原则展开:“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麻为布,纯为丝。周人以麻冕为礼,但孔子并未选择继承前制,因为比起形式,“仁”所催生的“俭德”更接近礼之“义”(精神)。孔子灵活变通“礼仪”,具备合理性,“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不仅倡导“俭德”,强调道德对美的关键作用,还提出君子“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其评判标准恰当,契合了“中庸”不偏不倚的原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将“中庸”引入礼乐活动,使得社会秩序井然、氛围融洽,便导向了“中和”的审美境界。
所谓“中和”,主要以“中”为尺度,以“和”为理想价值。“和”字始见于战国金文,本义是指声音相应。“和”的美学特征,是从音乐艺术中发展而来的,最初强调“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神人以和”,然后才是“管乎人情”的“礼乐之和”。孔子的思想与行为,无疑是具有“礼乐中和”之特点的。《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将“度礼中行”与“厚施行”“薄赋敛”结合,体现出节制轻财、重礼保民的精神。孔子节制行为、中行合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和”的理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与礼互为体用、中正适度的秩序与对和谐境界的追求统一,就是孔子“中和”的价值,这体现了圣人所追求的一种社会和谐之美。
孔子试图对艺术进行“中”的规范,提倡通过美育达到社会和谐的终极之美,因此“中和”作为审美标准,常常被反映于“节情适度”“尽善尽美”“文质中道(彬彬)”等诸多美学命题的评价之中。比如“节情适度”是对主体的要求:在艺术创作或表演时,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否则就违背了审美情感的规律。“美”与“善”的“中和”,引申到人格方面,即“文质中道”。
孔子以射喻道,其道为中、为正。“文犹质,质犹文”,君子修饰文采又言辞雅洁,品行端正且道德高尚,合中合礼,达到了“彬彬”的适度与平衡,具有温和敦厚的特质。孔子以圣人为理想,强调“君子”,是将人格也纳入审美领域中。子思在其基础之上明确了“中庸”“中和”的内涵,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形式—“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是根本法则,与宇宙相联系,彰显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境界。
总而言之,周代的审美意识经孔子整合,形成了系统的美学理论。孔子在礼仪“节制”的基础上,更强调主体的内在修养与自我约束,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美善合一”等理论,这使得《左传》节制的观念更加丰富,也为儒家追求和谐适度、重视人格魅力的审美倾向奠定了基础。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