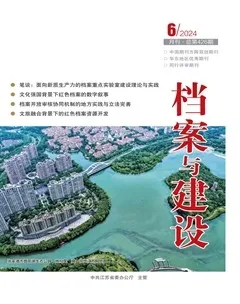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机理、运行机制与推进策略
摘 要:档案数据作为宝贵的社会信息资源,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数据要素化背景,文章从赋能前提、赋能动力、赋能保障三个角度阐述了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机理,围绕主体协同、数据共享、技术应用、政策优化四个维度探讨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档案数据进一步赋能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档案数据;数字政府建设;逻辑机理;推进策略
分类号:G270
Logical Mechanism,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Archival Data Enabling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Zhang Baojie, Geng Zhijie
(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As a valuable social information resource, archival da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ata factorization,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archival data empowering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empowering premise, empowering power, empowering guarantee,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rchival data empowering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round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ubject synergy, data shar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archival data empowering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archival data empowering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Archival Data;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Logical Mechanism; Promotion Strategy
数字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政府建设是塑造数字化生态系统、撬动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1](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勇于改革,创新发展,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2024年1月,《“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2](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印发,其核心在于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通过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各行业、各领域的数据驱动,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殷切希望,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加快数据要素赋能的迫切需求。档案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通过激活档案数据要素潜能,充分发挥档案数据的记忆保存、文化传承、资政治史、信息服务等功能,可以助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学界对档案数据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档案数据契合并有效支撑数字政府建设需求的特定方面予以深入研究,如档案制度构建[3]、档案数据治理[4]、档案职能延伸[5]等,从制度、路径等角度深入阐释档案数据在不同方面的行动内容与要求;二是从整体视角探讨档案部门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角色、实践框架、优化对策[6-8]等。可以看出,学界对档案部门参与数字政府建设已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但专门探讨档案数据“赋能”政府发展新形态的相关研究较匮乏,而从“参与”到“赋能”正成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本文着眼于《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剖析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机理与运行机制,为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构筑推进策略,以期为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1 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机理
《行动计划》强调数据的深度应用和价值释放,以数据驱动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档案数据既继承了档案的记录和保存功能,又具备数据要素需求性、共享性、非排他性等属性,是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内在特性、现实需求与政策期望是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基本逻辑。
1.1 赋能前提:数据资源禀赋
档案作为政府的重要信息资源,在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进程中,具有以下三点独特的优势。首先,档案是“确凿的原始明证、可信的事实存照、有效的历史资鉴和珍贵的社会记忆”[9],相比其他资源更加严谨、规范,在数据质量上具有更强的可靠性。其次,作为一项基础性、支撑性的工作,档案工作的本质属性是服务,档案事业承担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要职责,致力于为法治国家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国家记忆保护和传承等提供全方位服务。如档案机构通过分析公共决策部门的需求,制定出相应的服务策略,为公共决策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并在此过程中持续优化信息服务的方式和手段。[10]最后,档案数据是一种融合信息、知识、文化元素的数据资源,量大源广、价裕型多,内容覆盖了国防外交、民俗文化、就业养老、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丰富全面的数据资源保障。如在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在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中,档案数据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1.2 赋能动力:现实需求导向
数字政府建设对档案数据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需要档案承载的大量信息作为工作依凭,以促进政府工作规范高效、开放透明。档案作为政府治理和日常运行的真实记录,是监督和问责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重要凭证,通过查阅档案,可以为政务提供参考和研判的支持。其次,政府的科学化决策需要档案数据提供信息支撑和事实依据。档案数据蕴含着高质量的数据价值,能够助力数字政府决策高效化、科学化。如新冠疫情期间,福建、上海、山东等13家省级档案馆通过主动挖掘馆藏,提供“‘非典’期间各类疫情防控电子档案数据”“2003年上海抗击‘非典’档案摘编”“疫情防控专题档案资政参考”等档案资源,为领导及相关部门决策资政提供了知识储备和经验借鉴。[11]最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档案数据助力。为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数字政府致力于构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档案数据作为重要的社会信息资源,能够丰富公共服务的内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1.3 赋能依据:法规政策支持
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是档案工作在政策指引下的使命所在,法律支撑下的职能履行。《指导意见》在“加强重点共性应用支撑能力”中,提出要“深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服务利用,建设数字档案资源体系,提升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和应用水平”。档案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录与治理工具,是处理业务和履行职能的手段,必然要自我驱动数据化转型、智慧化服务,主动对接数字中国建设,以全新的理念和方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智能便捷服务。为此,2021年6月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12]强调要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主动融入数字政府建设,及时精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提出,“推进全国档案信息资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共享利用工作,制定数据共享标准,建设全国一体化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13]。可见,档案数据的开发利用、开放共享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档案数据的基础支撑作用符合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2 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运行机制
《行动计划》指出要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重视数据融汇、共享开放与开发,兼顾数据要素流通与安全,其中涉及顶层设计、实施主体、技术应用等诸多要素,为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良性运行提供了导向,档案机构需要依靠各层级之间的相互协调,围绕档案数据要素形成政策规范、流程有序、协同共治的档案数据运行机制。
2.1 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共塑档案赋能格局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数字政府超越了传统专业分工为基础的职能部门管理模式,更注重整体性和协同性。[14]也就是说,数字化业务流程驱动跨部门协同,推动打造以档案部门为主导,业务部门、数据管理机构、信息技术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档案数据运行管理的协同联动机制,才能够形成“群体智慧”,促进档案数据要素有序流动和高效运行,充分释放档案数据的价值能量。首先,在电子文件收集归档方面,档案部门需介入前端业务部门的数据归档,实现政务信息的档案化管理,从而保障档案数据收集齐全完整、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安全可用。其次,在档案数据开放共享方面,档案部门可从制度层面为数据体系化建设提供参考建议,数据管理机构对档案数据日常运行管理、多场景应用建设等进行指导。最后,在档案数据开发利用方面,档案部门借助第三方服务机构或个人提供的技术和工具,以实现档案数据的深度开发与价值释放,探寻群众利用档案的趋势和需求变化,从而助力政府构建高效的公共服务集成模式。因此,应加强部门间的纵横联系,强化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形成档案数据协同共治的向心力,共同推动档案数据安全流动、价值转化与成果共享,促进档案政务服务一体化。
2.2 根基:档案数据共享,实现价值融合共生
提升数据共享水平是高效利用数据要素资源的前提。过去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长期受到数据开放率低、资源共享难、业务协同难的困扰,制约政府数字化转型效能的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多次对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作出重要指示。[15]档案数据是“一个政府借以完成其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16],面向社会开放共享档案数据是国家建设数字政府必不可少的一环。应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速档案数据化进程,搭建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促进来源广泛、类型多样的档案数据整合集成、汇聚融合、关联重组,通过共享使静态离散的原始数据转变为动态流动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科技等其他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全面激活档案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知识价值等,实现数据价值增值,提升政府有序管理社会、推进文化建设、科学精准施策的履职能力,助力政府公共服务的再升级。当前,越来越多的省市、部门已经意识到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性,加速了档案数据统一管理与应用的进程,但囿于档案数据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档案数据语义化、结构化、关联化尚未有效开展,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17]
2.3 关键:应用新兴技术,延展档案赋能空间
档案数据赋能的一大特点是技术取向,技术驱动档案业务由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映射,再到知识空间跃迁,有力延伸了档案资源服务的时空触角,可以说,技术应用是展现档案赋能能力的关键。首先,在档案数据整理方面,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等技术前置元数据捕获、甄别、检测等环节,实现AI自动分类、排序和编号,提升了档案管理效率。[18]其次,在档案数据开发利用方面,随着公众对档案的价值诉求趋于复杂化,档案用户不再满足于传统检索查阅、图片展陈的线下静态被动服务,转而追求个性化、知识化、场景化的多维动态服务体验,数据挖掘、智能检索、虚拟现实等技术能够细化档案颗粒度,实现档案知识的定制化服务、可视化展演,增强用户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最后,在档案数据安全保护方面,档案信息质量将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电子签章、可信时间戳、区块链等技术为归档政务信息的可用、可信与安全提供了安全保障。因此,档案部门要更新信息技术理念,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业务融合、系统融合、数据融合,解决档案数据孤岛、数据污染、数据失真等质量问题,保证档案数据的真实可用,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高质量档案数据服务。
2.4 保障:优化政策布局,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任何工作的顺利运行,都要以法规标准作为支撑。数字政府建设要求全数字化的政策流程,信息共享也要打破原有的数据分布逻辑,档案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数据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业务开展中的权力诉求、任务分配、责任归属等存在差异,针对多元主体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应然之举。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档案制度的构建还有待完善,《指导意见》强调提升电子文件(档案)资源管理应用水平,在此背景下,只有少数省份在其“十四五”规划中纳入政府电子档案管理的有关内容。[19]在政务信息归档方面,现有政策标准存在平台系统不兼容以及各行业规定不统一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20]在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方面,各个保管主体之间缺乏制度性的互动机制,尚未厘清在数字档案长期保存工作中的责任与权力,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政策难以协同。[21]因此,要聚焦数字政府建设的整体目标,坚持系统思维和整体规划,形成环环相扣的政策布局,营造开放多元的档案数据公共服务生态环境。
3 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策略
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涉及多要素的系统性工程,档案数据化和数据档案化的快速发展为档案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建设奠定了法规、实践和理论基础,然而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档案数据服务仍然面临着协同机制实施困难[22]、服务乏力与权责混乱[23]、数据要素供需不平衡[24]、供给效能不高[25]等诸多现实困境。为有效衔接政府发展新形态需求,消弭制约档案数据要素价值彰显的沉疴,档案领域需要从优化档案制度设计、夯实档案资源底座、构筑政务互动平台、保障数据要素供给等方面进行探索。
3.1 加强档案制度设计,激发内生活力
通过搭建协同增效的顶层设计,破解机制壁垒及其引发的实践工作封闭性,落实和明确各项工作目标,实施重点和相应的保障配套措施,将内在驱动与外部秩序有效联结,使档案数据深度嵌入数字政府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第一,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明确主体职责分工。建立健全档案部门与数据管理机构、业务部门、信息化部门等主体在档案数据治理中的常态化沟通与联动机制,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总体目标充实档案数据资源运营的专业内容,将档案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安全保密、风险评估、流通监管纳入相关法规政策、工作规划的考量范畴之中。如2019年沪苏浙皖档案部门协商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工作协调会议机制,提升了民生档案服务协作水平。[26]此外,围绕档案数据的多方流转问题,确定数据权责具体关系,并将相关工作纳入业务评价与绩效考核,确保将档案数据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如杭州市档案部门与数据资源管理局积极配合,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和工作职责,落实档案数据的归档存储、整合共享、移交进馆等工作,提高了政务信息资源的管理效率。[27]
第二,完善配套标准规范,促进档案数据流通聚合。标准化建设可以提高数据的互操作性和一致性,使档案数据在不同机构和平台之间高效流通,实现数据的无缝集成和共享。结合国家相关规定,针对档案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基于不同馆藏、不同类型档案数据的特点,加强档案数据基础标准(包括数据质量、格式、元数据等)、安全管理标准、运行平台标准、安全技术标准的框架研究、制定和颁布[28],弥合数据鸿沟,实现对档案数据运行的全链条管控。如浙江省围绕政府数据归档制定相关标准规范,通过完善电子文件、电子档案乃至数据资源的归档、移交等措施,以“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制度建设”为基础夯实数字政府基础能力。[29]
3.2 加快档案数字转型,夯实资源基础
数据资源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地基”,档案数据只有通过集成汇聚、开放共享,挖掘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才能成倍数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数字政府搭建数字底座提供档案力量。
第一,加强档案开放数据的规模化建设,丰富数据资源体系。在“大档案观”的指导下,依据“统一平台、互通互联、存量共享、增量共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原则[30],丰富档案数据资源库。一方面,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OCR技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档案文本进行识别和提取,提高纸质档案的数据转化率与准确度。如江苏连云港、浙江萧山、广西梧州等地的档案部门,通过文字著录、OCR识别等方式对婚姻、工龄、学籍、出生医学证明等早期民生档案进行数据化处理,极大地提高了档案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广泛收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档案属性的数据,包括开放类公共数据、政务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网页数据等。[31]以数据的规模性和完整性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保障,提升政府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
第二,根据不同数据的特性,积极建设档案数据专题资源库。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将包括档案馆藏在内的多源异构数据提炼汇聚、关联融合,形成数据云、数据湖、数据体、数据集,建立数据仓储,以政府规划为导向,构筑文化专题、民生档案、重大活动等数据库,形成服务于政府治理的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如湖南省档案馆通过收集审核各地提交的有关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类档案”,已完成“两类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归集目录数据达420余万条,有助于协助政府部门针对贫困、疫情防控问题精准施策,在遇到问题时可作出及时响应,提高数字政府治理能力。[32]
3.3 搭建政务交流平台,保障信息畅通
数字政府背景下,电子文件、电子档案乃至数据资源的归档、移交、保存、利用等环节的全流程管理与服务需要依托在线交流平台,才能纾解档案数据在数字政府改革中出现的供需不匹配、信息不对称的困局。
第一,依托政务协同管理平台,强化信息资源的档案化治理。档案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政务文件管理平台,密切联系政府部门,探索电子档案单套制归档的解决方案,打通业务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渠道,提前融入业务系统的设计阶段,实现一站式服务平台中生成或流转的各类档案数据的及时捕获、自动检测和智能归档。如上海市打通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最后一公里”,实现政务服务在线全流程办理,截至2022年,市档案馆成批量接收了12家单位移交的“一网通办”电子档案14.22万件,共495GB。[33]
第二,构建一体化政务信息平台,优化档案政务服务。档案信息平台与数字政府信息平台的有效对接,可以一键式送达档案信息资源,打破政务信息与档案信息利用壁垒,提高档案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可访问性。将政府需要且有助于政务服务开展的档案信息资源统筹建设、集约共享,方便政务人员搜索、查询、利用档案,解决了传统检索方式要求关键词与原文完全一致的痛点问题,消弭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壑,实现政务服务集中化。如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目标和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要求,杭州市于2015年搭建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实现了跨馆查询、异地出证服务,促进了社会公众在事项办理时的便捷化和高效化。[34]
3.4 优化档案数据供给,精准定位需求
作为累积性的高价值密度数据,档案数据从“利用”到“赋能”转变,是提高政府数据服务能力的重要助益,在此过程中,档案数据安全流转、精准供给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强化安全防护技术应用,筑牢档案数据安全防线。数据安全是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的“生命线”[35],档案部门要着眼于数字政府整体安全,完善档案数据安全防范体系,通过身份认证技术、黑客入侵检测技术、区块链技术、病毒查杀技术等多种网络安全技术的综合应用,谨防数据流转过程中数据质量欠佳、隐私泄露、损毁破坏等安全风险,构建纵横交错的档案数据安全技术网,确保档案数据流转内容准确有效,推动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维护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如云南省档案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开展综合档案馆安全风险评估,进行风险隐患的排查,建构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将安全工作责任和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业务环节,切实保障档案信息安全。[36]
第二,深入挖掘档案数据价值,提供专业化知识服务。档案部门应洞察数字政府建设信息需求,运用数据挖掘、语义分析、知识发现等技术手段加强档案数据知识化开发,充分挖掘档案数据中的隐性知识元素,揭示数据间蕴含的内在联系,形成档案知识元。打通档案资源与知识创新间的脉络,构建以不同类型社会事件为核心数据的知识链,搭建档案资政服务网络,适时为政府机构提供具体的知识产品与政策咨询服务,将“档案库”变成“知识库”“思想库”[37],从而提高政府处理突发社会事件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决策风险。如青岛市档案馆建立了历史档案知识库,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供知识服务、决策参考服务,实现了档案馆由提供传统的信息服务迈向知识服务的新阶段,助力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38]
第三,建立档案数据利用反馈机制,提高精准化服务水平。公民视角和需求是数字政府服务的关注点[39],档案部门应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追踪并深度分析用户信息与过往行为数据,结合用户画像等主动预判用户需求,实现档案数据精准化服务功能,及时感知与回应公民的期望和诉求,提高政府履职能力。如浙江省嵊州市打造“个人全生命周期档案”综合智治应用,汇集个人从出生、婚育到养老等10个人生阶段相关数据,构建个人基本信息数据专题档案,满足了不同用户需求。[40]此外,运用量化工具建立评估指标,从不同维度、不同指标对档案数据利用进行评估,及时跟踪、分析与整合档案数据问题反馈,并进行动态调整与改进,不仅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还有助于提升档案政务服务精准化水平,达到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
4 结 语
档案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数据资源,为数字政府的科学化决策和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维度和深度的揭示和研判,从而促进更智能化的政府运作。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实现档案数据从参与到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转变,还需从制度设计、数字转型、平台搭建、内容供给等方面作出努力。因此档案部门应与政府其他部门加强交流、主动融入,把控赋能过程,特别是在数据要素化和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加强档案数据与政务部门联通共享,真正融入数字政府一体化生态。
作者贡献说明
张宝杰:提出论文选题,收集整理资料,撰写修改论文;耿志杰:设计研究思路,确定框架结构,指导论文修改。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23-11-09]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22-06/23/content_5697299.htm.
[2]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通知[EB/OL].[2024-02-28].https://www.cac.gov.cn/2024-01/05/ c_1706119078060945.htm.
[3]杨茜茜.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档案制度构建——以中央法规政策的分析为基础[J].档案与建设,2023(1):22-27.
[4]汪建军.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档案数据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档案与建设,2023(9):49-52.
[5]詹逸珂,陈析宇.合理实践“前端控制”——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档案管理职能的延伸[J].浙江档案,2021(8):17-19.
[6]易涛.政府数据开放的“档案参与”:历程、角色与路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2-90.
[7]周文泓,贺谭涛.档案部门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实践框架研究及展望[J].档案学研究,2024(1):110-118.
[8]舒怡娴,王思琪,熊小芳,等.我国档案部门参与政府数据开放行动的现状和优化对策[J].档案与建设,2023(11):43-47.
[9]金波.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档案参与”[J].求索,2021(3):135-143.
[10]王新才,张静文.档案服务质量提升的重点与能力要求研究——基于英国《档案服务认证标准》的解读[J].档案学研究,2020(3):137-143.
[11]王为久,吴志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档案部门开展工作的路径研究——基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31个省级档案部门工作开展的实证分析[J].档案学研究,2021(1):87-95.
[12]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3-11-08].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106/899650c1b1ec4c0e9ad3c2ca7310e ca4.shtml.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N].人民日报,2024-01-29(15).
[14]王伟玲.我国数字政府顶层设计的理念辨析与实践指向[J].行政管理改革,2021(6):40-50.
[15]开启新时代数字政府建设新篇章[EB/ OL].[2023-11-08].https://www.gov.cn/xinwen/ 2022-08/26/content_5706935.htm.
[16]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黄坤坊,等,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15.
[17]吕姗姗,周枫,金波,等.档案数据质量问题表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OL].情报科学:1-16[2024-05-0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2.1264. G2.20240126.1958.028.html.
[18]牛力,黎安润泽,刘慧琳.融合、延展、重构:物理与数字双空间业务转型视角下的档案信息技术应用思考[J].档案学通讯,2023(5):19-27.
[19]刘越男,李雪彤.档案事业在地方政府“十四五”规划的纳入情况研究——基于31个省份“十四五”规划的文本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2(9):8-13.
[20]杨智勇,桑梦瑶.“一网通办”背景下政务信息归档协同优化路径研究[J].档案管理,2023(3):62-65.
[21]耿志杰,王俞菲.协同治理视域下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政策探析与瞻望[J].档案与建设,2024(2):74-80.
[22]王运彬,王晓妍,陈淑华,等.公共服务集成视域下档案部门的协同合作与服务转型[J].档案学研究,2020(4):56-63.
[23]朱雯.我国档案立法体系建设公共性缺失的治理[J].浙江档案,2023(11):44-47.
[24]朱佳煊,张洋,潘长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档案公共服务均衡性与可及性[J].中国档案,2023(10):64-65.
[25]常大伟,翁慧诠,段莹茹.精准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服务供给的应然状态、实然困境与使然策略[J].档案管理,2023(4):69-72.
[26]徐未晚.互联互通加快促进长三角民生档案区域共享[N].中国档案报,2019-05-23(3).
[27]徐拥军,王露露.档案部门参与大数据战略的必备条件和关键问题——以浙江省为例[J].浙江档案,2018(11):11-14.
[28][35]金波,杨鹏.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策略探析[J].情报科学,2020(9):30-35.
[29]郑金月.建设融入数字政府大格局的新一代数字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创建工作综述[J].中国档案,2020(1):40-42.
[30]金波,杨鹏.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治理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0(4):29-37.
[31]周毅.档案数据治理的认识维度及其价值[J].档案与建设,2023(2):8-12.
[32]湖南完成“两类档案”归集和专题数据库建设[EB/OL].[2023-11-08].https://www.saac.gov. cn/daj/xwdt/202112/f639d9f9d5a241b8b2fa45d6b38bc5 8c.shtml.
[33]康勇.留存上海政务服务的数字记忆——上海市档案局全力推进“一网通办”电子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24(3):30-31.
[34]张国华.“最多跑一次”提升档案公共服务新高度[J].中国档案,2018(2):28-29.
[36]夏红.把牢政治方向 深耕主责主业 奋力谱写云南档案事业现代化新篇章——在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J].云南档案,2024(1):11-17.
[37]金波,杨鹏.“数智”赋能档案治理现代化:话语转向、范式变革与路径构筑[J].档案学研究,2022(2):4-11.
[38]青岛市数字档案馆_青岛市数字档案馆建设历程[EB/OL].[2024-04-08].https://www.danganj. com/zhdagjs/580.html.
[39]郑跃平,等.公共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导向的服务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71-173.
[40]汪伟民.浙江嵊州:“个人全生命周期档案”综合智治应用建设[J].中国档案,2023(8):30-31.
(责任编辑:孙 洁 陈 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