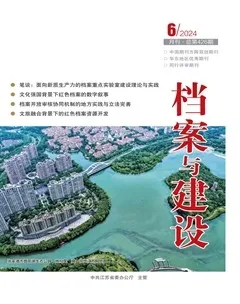助力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软法进路:实践场域、运行逻辑与未来面向
摘 要:软法治理对于强化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价值,是助力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在实践场域上,软法治理以档案“软性条款”和“社会软法”为规制载体,以档案政策、自律规范、档案标准为作用对象,完善档案规范的供给格局。在运行逻辑上,软法治理凭借“前软法”“后软法”“并行软法”和“独立软法”的外在形态,依托“软硬协同”“附属转接”“行政传导”和“资源辅助”的内在机制,推动档案资源的多元整合。价值在场、技术适配和制度保障是实现档案软法治理的优善面向。
关键词:档案治理现代化;档案法;档案软法;软法治理;软法滥用;软法审查
分类号:G271
The Soft Law Approach to Modernizing Chinese Style Archival Governance: Practical Field, Operational Logic, and Future Orientation
Fu Chengbin 1, 2
( 1.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Law School of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13 )
Abstract: Soft law governance has an important value in strengthening the archiv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ing archiv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modernizing Chinese style archival governance. In the practical field, soft law governance takes the “soft clauses” and “social soft laws” of archives as regulatory carriers, and takes archival policies, self-discipline norms, and archival standards as the objects of action to improve the supply pattern of archival norms.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logic, soft law governance relies on the external forms of “pre soft law”, “post soft law”, “parallel soft law”, and “independent soft law”, and relie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soft and hard coordination”, “subsidiary transfer”, “administrative transmission”, and “resources assistance”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of archival resources. The presence of value,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re the optimal aspects for achieving soft law governance of archives.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Archival Governance; The Archives Law; Archives Soft Law; Soft Law Governance; Abuse of Soft Law; Soft Law Review
在大陆法系传统法理中,成文法条款基本以“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责任”的三要素结构进行设置。[1]法条因具备“法律责任”的明确指引而具有明显“硬性”特质,这种“硬”特质不仅能保障法律条款在规范内容上蕴含“国家—命令”的深层法益,而且在司法适用层面也能借助“国家在场”的强制权威实现贯彻执行。因此,国家立法曾长期统摄于“硬法”之下,宣示“法的规范性”。直至20世纪中叶,“硬法”规制范式仍是法制建设的主流方向。但随着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兴起,新自然法学派的学术主张洛阳纸贵,“法即硬法”的立法格局为之松动。在社会法学派的学理演绎下,法条结构似可摒弃“责任”要素,代以“社会倡导”的规范形式,仅通过“假定”和“行为模式”的结构设置,也能同样实现对目标法益的立法保护。[2]由此,原本缺乏“惩戒罚责”(法律责任)的“瑕疵”硬法被冠以全新的“软法”之名,先是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中流行,而后延伸至国内法及各部门法中[3],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资源。
近年来,软法在我国环境、财税、教育等“传统领域”频繁现身,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法之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越发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软法建设中,档案工作自然没有置身事外,“档案软法治理”正在成为助力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进路。档案领域的软法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989年李金山等人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文简称《档案法》)“软法说”。[4]虽然该论题后经姜龙飞[5]、曹宇[6]、刘东斌[7]等学者几番争论,难定共识,但伴随廉睿所提及的《档案法》“软硬协同”互动格局[8]、张罡提出的《档案法》“软法性条款”规范识别路径[9],以及陈强、杨阳所申明的档案法规“软硬混治”发展朝向[10],软法问题再次成为档案领域关注的热点对象。时至今日,对过往文献进行学理总结,可以发现,档案学术共同体针对“档案软法”的研究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探讨《档案法》软法属性的“原始命题”[11];二是微观上构建《档案法》“软法条款”的效力通道。[12]至于《档案法》视域外的“更多发现”,则尚待学人进一步开辟新的航向。故此,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实然层面揭示档案软法的实践场域和运行逻辑,在应然层面擘画档案软法之治的优化路径,以实现对档案软法治理的范式扩充,为推进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加速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学理智识。
1 档案软法治理的实践场域:规制载体与作用对象
2021年,《档案法》完成实施32年来的首次修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档案立法的核心目的之一[13],档案事业沿着“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14]的发展方向不断深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15]的时代背景下,一场兴起于国家治理、延伸至档案领域的“现代化”运动徐徐展开、有序推进。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是指根植于中国档案治理实践,体现中国档案治理理念、治理智慧和治理特色,达至档案善治的现代化过程。[16]在此过程中,档案软法凭借其特殊的规制载体和作用对象,构造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自我实践场域。通过该实践场域,档案治理能获得更为充分的法治资源,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也因此进一步走深走实。
1.1 档案软法治理的规制载体
就实际存在而言,档案软法治理的规制载体呈现出“软性条款”与“社会软法”的双重法源格局。档案“软性条款”是寄身于“国家法”中的宣示性条款、陈述性条款、倡导性条款和赋权性条款。虽然这些条款从外在形态上看,以国家档案实在法为存在媒介,具备“硬法”的外观特征,因而属于形式意义上的“硬法”;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这类“形式硬法”通常不针对违法后果进行具体规定,即缺乏法条三要素中的“责任”要素,所生成的规范效力具有明显的“外硬内软”特性。例如,《档案法》作为我国档案领域的基本法,就内嵌了为数众多的“软性条款”。该法第3条有关档案工作领导原则(宣示性条款)、第7条档案建设贡献奖励(倡导性条款)、第43条档案检查配合义务(陈述性条款)、第29条档案开放利用权利(赋权性条款)等系皆如是。由于我国档案立法尚未实现“法典化”,因此,包括《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下文简称《档案法实施条例》)、《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在内的诸多成文法,成就了档案“软性条款”广泛出镜的文本“舞台”。
除“国家法”中的“软性条款”,档案规范中的另一种“软法资源”—— 档案“社会软法”,同样也是档案软法治理的重要载体。档案“社会软法”通常会以“办法”“规定”“规则”“规范”等标志性用语[17]的文件形式出现在档案规范中。例如,《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财产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DA/T 86—2021)等都属于档案“社会软法”。相较于国家法中“软性条款”所强调的规范主义,档案“社会软法”因其制定主体更为多元,规范内容更加开放,更重视功能主义,更符合“一定范围内社会对‘公共善’的认知与期待”[18],因此是档案软法治理最主要的承载平台。
总体而言,国家法律中的档案“软性条款”是档案软法治理较为规范的间接载体,而活跃于档案事业中的“社会软法”则构成了档案软法治理更为广泛的直接载体。档案“软性条款”和“社会软法”不但凸显出档案规范的本土特色,同时也使档案治理更有弹力、更富韧性。两者共同构筑成档案软法治理的基本外在场域。
1.2 档案软法治理的作用对象
档案软法治理的作用对象主要围绕档案政策、档案自律规范和档案标准展开。虽然已有学者指出司法“指导性案例”在理论上也应属于软法治理的“现实存在”[19],但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公布一例档案类指导案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软法治理的“作用对象”无疑与“规制载体”一样,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
一是档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涉及档案开放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主题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20]在此背景下,档案政策成为档案软法治理最首要的适用对象。例如,近些年,为妥善因应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安全、档案统计调查等现实问题颁布实施的《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办法》《档案馆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全国档案事业统计调查制度》等政策文件,都是软法治理作用于档案政策的具体实践。
二是自律规范。档案自律规范是由档案行政机关、行业协会、档案馆等享有档案规范制定权的主体,通过档案自律章程规定的特殊程序,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执行力的行业规范和公约。例如,《全国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档案馆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国家档案局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等。档案自律规范内容灵活多样,程序简便快捷,因此更易被软法治理的内在机制所吸收和利用,成为档案软法之治的重要实践对象。
三是档案标准。档案标准是以档案工作领域中重复性出现的事物和概念为规制对象所制订的各种标准的总称,是档案行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21]从本质上讲,档案标准是一种被广为遵守的档案“共识”,这种基于“共识”而生的制度规范,无疑具有软法的重要“协商”特质,因此成为档案软法治理的又一实践样态,如《中国档案机读目录格式》(GB/T 20163—2006)、《电子会计档案管理规范》(DA/T 94—2022)等。
作为助力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进路,档案软法治理在内部规范设计上,选取了“软性条款”和“社会软法”为规制载体,而在外化内容呈现上,又对准了档案政策、自律规范和档案标准,以此确定作用对象。作为档案软法治理的实践场域,一方面,“规制载体”及其项下的“软性条款”与“社会软法”,为档案治理寻求到了相较于档案硬法治理的另一种“软表达”,是理论意义上针对传统档案硬法治理而言的又一次“治域开发”;另一方面,“作用对象”及其项下的“档案政策”“自律规范”以及“档案标准”,本质上则是“规制载体”语境下的进一步梯度深化,是现实意义上针对档案软法治理规范及其规制载体的一次重新表达。因此,“规制载体”是较于档案硬法规范的一种“身份定位”,而“作用对象”无疑是规制载体的进一步顺接分化。两者对标明确、层次鲜明,共同建构起了档案软法治理的实践场域,不断推动着档案软法规范供给格局的升级和优化。
2 档案软法治理的运行逻辑:外在形态与内在机制
随着档案社会价值的不断提升,档案法治建设除了为档案事业提供基本的规范保障外,社会引导、政策支持、善举鼓励等附属性作用也越来越被看重。[22]档案治理开始由传统一元的“硬法规范”逐渐向二元的“软硬协同”治理模式渐进转型,“软法规范”成为档案治理的重要手段。从治理实践来看,档案治理视域下的“软法规范”是指以领域问题为导向,全面落实国家档案治理远景目标和多重政策手段的一种法律建构,内容上既涵盖大量传统管理性条款,同时也包括新兴的预防性和促进性条款规范。档案软法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要厘清具体实践场域,更要结合档案治理现实,从多维角度探讨其内在运行逻辑。综合而言,档案软法治理的运行逻辑主要是依托档案软法的外在形态和软法治理的内在机制予以实现。
2.1 档案软法治理的外在形态
档案软法治理的外在形态包括“前软法”“后软法”“并行软法”和“独立软法”。
一是“前软法”。“前软法”既可以基于对档案事业发展的未来考量,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来实现档案事业整体布局的规范配置(如《“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可以就未来可能出台的硬法规范,通过提前制定相关软法,对目标硬法进行可适用性与可接受性的预先评估(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实践中,“前软法”主要活跃于重大档案规范出台的“前立法”阶段,起着促进硬法“软着陆”的作用。
二是“后软法”。“后软法”的运作思路是在某一档案领域业已存在硬法规范前提下,通过再行制定相关软法规范,以实现对既有硬法的立法填补和科学释义。近年来,部分地区利用“后软法”在提升地方档案治理效能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第30条第2款针对“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人员培养”作出特殊制度规定。这一规范安排不但对上位法内容进行了细化补充,而且还对未尽事项进行了本土化创制,值得其他地方档案立法借鉴。
三是“并行软法”。“并行软法”存在于“前软法”与“后软法”之间,既强调软法对硬法的“铺陈”作用,同时也注重软法对硬法的“解释”功能,着眼点是软硬法规范同时作用于档案治理,最大限度发挥档案规范资源的协力效能。例如,《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是针对2016版《档案法》中提出的“档案安全”新内容所进行的特殊“并行规范”。
四是“独立软法”。“独立软法”是针对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专门颁布实施的独立于“硬法”之外的一类档案规范。例如,2020年,浙江、湖北等省份利用“独立软法”形式,及时颁布《浙江省档案局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档案工作的通知》《湖北省档案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档案收集归档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档案软法规范,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
以上四种外在形态是档案软法实现档案治理“功能补强”与“效用提升”的重要形式,构成了档案软法治理运行逻辑中的重要一环。
2.2 档案软法治理的内在机制
档案软法治理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软硬协同”“附属转接”“行政传导”和“资源辅助”。四种机制通过各自的运转机理,实现档案软法的功能发挥。
一是软硬协同机制。“软硬协同”是通过“软法”与“硬法”的内在协作和整合互动,完成档案“软法条款”的作用增溢与效能释放。例如,《档案法实施条例》第二章是针对“档案机构及其职责”所进行的“软性条款”设置,而《档案法》第48条则是针对上述内容所进行的“法律责任”硬性规制。两者在围绕档案部门法定职责的“赋权”与“限制”方面,实际形成了一个“软硬共治”的闭环系统,通过此种“整合”与“共治”的协同耦合机制,达到了对档案机构权责配置的规范目的。
二是附属转接机制。“附属转接”主要依托“委托立法”和“附属条款”进行。以《档案法》为例,在“委托立法”转接机制中,《档案法》将原本应当由其进行规范的“档案转让办法”和“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分别以“软法条款”第23条第2款和第37条第3款的授权形式,委托给了国家档案主管部门,要求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间接形式实现对档案业务的规范管理。而在“附属条款”转接机制中,《档案法》“软法条款”第51条通过立法移转技术,将涉档纠纷中的刑事、民事责任输送至《刑法》《民法典》的规范体系,由以借助其他部门法实现对档案纠纷的“定分止争”。
三是行政传导机制。“行政传导”是指档案软法基于档案管理体制的应力效应,额外获得了行政性的执行担保和效力保障。以《档案法》第8条第3款为例,本条是针对乡镇政府档案监督指导的软法规范,原本囿于“软性条款”而效力有限,但因我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行政工作原则,由此促成第8条第3款成为档案行政管理体制下的“硬法”表达。对该条款的“冒犯”,即意味着对档案行政管理体制的公然违反,当事人除要承担本条款自身固有的违法成本外,还要妥善应对随之而来的行政组织上的督导问责。
四是资源辅助机制。“资源辅助”是在档案软法实施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本土社会资源,凭借“社会在场”优势,推动档案治理进入流变的“社会法”之中,进而实现档案治理的社会化。例如,每年6月9日“国际档案日”和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国家宪法日)”,各地档案馆室和大中院校都将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以各种“社会供给”力量,全面贯彻档案安全、档案捐赠、档案红色记忆等档案软法倡导内容。
总体而言,上述四种内在机制分别围绕档案“软性条款”和“社会软法”,以各自不同的运作机理完成了档案软法规范的常态运行,实现了档案软法资源的功能发挥,是档案软法治理的重要保障和运行逻辑的核心环节。
3 档案软法治理的未来面向:价值在场、技术适配、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治理的法治逻辑始终受制于“法即硬法”的传统观念,造成“软法”在档案治理中的重要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软法”与“硬法”在档案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作用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硬法设定路径,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档案治理新时期,无论是立法理念在对“良法善治”的全面践行上,还是立法内容在对“依法治档”的全面推进中,档案治理现代化的提升不仅需要长期的“硬法在场”,也需要“软法”独特功能和实践价值的充分发挥。档案软法治理通过差异化的条款设定,有层次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档案治理需求,更能促进各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实质公平。且基于“共识”而形成的档案软法,运行成本也比硬法更为低廉,更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考量,因而能更好地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档案治理的各项客观发展需要。面向未来,档案软法治理应从价值在场、技术适配与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助力实现中国式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1 价值在场:深化软法治理理念,推动档案治理2.0建设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其著名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控制理论”。“控制论”认为,在复杂系统的背后有各种无法精确计算的干扰因素,如按事先认定的计算结果行事,最后往往会与目标偏离甚远。[23]依“控制论”看来,在向目标前进时,不应假设能一次抵达终点,而应通过不断检查纠偏,在满足系统多输入和多输出的控制要求下,采用持续优化调整的方式,实现预设目标。事实上,“控制论”所关注的“动态”控制方法,在档案事业“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念借鉴价值。我国传统档案治理奉行“国家—命令”式的硬法治理观,具有强制性、规制性和行政性特质。长期以来,档案硬法支撑起我国档案规范的基本架构,是档案治理法治体系的“实力担当”,为档案治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档案硬法毕竟资源有限,自身的时效性和适应性难以有效因应“法的滞后性”所带来的现实冲击,仅凭硬法规范来维护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免捉襟见肘。因此,档案治理在实现硬法的“良法”建设时,也需要借鉴“控制论”提倡的全过程“优化纠偏”理念,围绕档案事业的“善治”方向进一步迈进。[24]在此进程中,作为“硬法治理”的有机补充,“软法治理”能在档案治理过程中有效化解档案硬法因“一次抵达目标”所带来的过程扰动和着陆风险,对丰富档案治理体系、强化档案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是新时代助力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控制”进路。因此,档案治理要继续深化“规范集成”的施治理念,强化“软硬协同”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发挥档案软法在档案“领域法”中的功能优势,完善和提升档案软法治理的作用场域和运行逻辑,推动实现“档案治理2.0”的加速升级。
3.2 技术适配:构建软硬转化机制,保障协同耦合效能
在档案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档案软法虽能够调整硬法的治理不足,消弭规范性与时效性之间的二元张力,但这绝非意味着软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过度倚仗软法治理很可能遭受“软法反噬”,出现“软法滥用”的不利局面。例如,在《档案法》第五章“档案信息化建设”中,该章7项条款没有任何“硬法规范”踪迹,全部是软性条款。此种不当的“一味倡导”式规范配置,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司法实践中,该章内容因无法完全作为判决依据(准据条款),从而使其不得不面对诸多“僵尸条款”问题。这一现象实际上早已被学者提出的“《档案法》规范指引功能发挥不足,操作性明显减弱”[25]所证实。因此,为及时避免“软法滥用”现象扩大,构建一套“软法硬化”和“硬法软化”的“软硬互嵌”规范转化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软法—硬法”转化机制,既能规范档案软法的业务区间,也能推动档案硬法的流动演替,对持续释放档案软硬法之间的协同耦合效能作用巨大。事实上,基于现实需求的“软法硬化”的终极目标是顺应多元化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而非对既有档案规范秩序的“野蛮逾越”。同理,当某些硬法规范确已“尸位素餐”之际,将其适度“降格”至“软法”序列,本质上也并非对其全面抛弃,只是改变了“过时”硬法的作用场域,其社会规范的本质属性未曾变离。因此,为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档案“软法—硬法”转化系统建设,彰显硬法“国家在场”之威严,弘扬软法“社会在场”之价值,档案治理主体要适时提升档案规范交流互动频率,持续调整档案软硬法的业务区间,以“软法资源”与“硬法规范”共生共治为技术目标,着力推动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
3.3 制度保障:建立软法审查机制,实现治理体系升级
亚里士多德曾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6]。在推进档案软法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档案软法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还要持续推动档案软法的事后审查和质量评估建设。实践中,档案规范中的制度对抗、条款对冲等一系列硬软法斥反抵牾现象常有出现,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加大档案规范之间的法理冲突,严重损害档案软法治理的法治权威。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档案软法审查机制,无疑是实现档案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要加强档案软法数字平台建设,实现软法备案审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档案主管部门要结合档案软法备案审查工作的实际需要,统筹构建全国统一档案法规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积极拓展信息平台在档案软法立法评估、备案审查、指标建构等方面的业务功能,不断提升档案软法备案审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整体水平。其次要坚持主动性审查与针对性审查相结合,明确档案软法审查的重点内容。在档案软法审查工作中,上级主管部门要着重审查下级档案部门所制软法是否符合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档案重大改革方向,软法规范内容是否违反上位法规定,制定流程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等。对于确有违反档案法律以及档案法治精神和原则的,要责令制定机关限期修改或废止。最后是稳步推进档案软法的集中清理工作,着力构建系统完善的档案软法清退体系。针对档案软法规范体系中的过时法规,软法制定主体要适时进行集中清理,并将清退情况及时准确上报给档案规范备案审查机关。就档案软法的清退系统建构而言,要以持续推进软法清理的制度化和常态化为工作重心,要将体系建设上升为档案法律的效率机制[27],以此保障档案软法规范体系的持续更新。
4 结 语
在依法治档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档案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软法治理作为一种以多元利益、民主协商为标签的崭新制度,为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硬法治理的全新路径。档案治理新时期,为进一步助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实现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档案治理有必要超越过往单维、定向的硬法控制模式,转而倡导一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的“软法之治”新范式,在充分发挥档案软硬法混合优势与整合效应过程中,开拓一条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崭新进路,由以实现国家档案事业从自上而下的“硬”管理向自下而上的“软”治理渐进迁移。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15-122.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1-142.
[3][9]张罡.新《档案法》中的“软法性条款”:理论拓补与规范识别[J].档案学通讯,2022(3):72-79.
[4]李金山,康清.对档案执法的反思[J].档案管理,1989(5):27-28.
[5]姜龙飞.正视档案法规的“软法”之治[J].中国档案,2011(3):17.
[6]曹宇.《档案法》“软法”问题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5(6):79-82.
[7][11]刘东斌.对《档案法》“软法”说的思考[J].档案管理,2013(1):4-6.
[8]廉睿.《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效力变“硬”了吗?——以“软法性条款”为考察工具[J].档案学研究,2023(2):81-86.
[10]陈强,杨阳.档案治理法治化的规范进路——由“软硬分治”到“软硬混治”[J].档案学研究,2024(1):61-68.
[12]廉睿,郝钰凯.《档案法》中“软性条款”的运行机制考察[J].档案学通讯,2024(1):95-103.
[13]赵春庄.论档案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以新《档案法》为背景[J].档案与建设,2021(9):43-45,42.
[14]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3-02-27].https://www.saac. 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 5c890762868683.shtml.ldsaZjQTLrB5zlgaT/AfeQ==
[1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14(21):16-23.
[16]常大伟,邢富娟.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的生成背景、实践特质与发展路径[J].山西档案,2023(3):29-35.
[17]沈岿.自治、国家强制与软法——软法的形式和边界再探[J].法学家,2023(4):29-41,191-192.
[18]邢鸿飞,韩轶.中国语境下的软法治理的内涵解读[J].行政法学研究,2012(3):3-8,68.
[19]龙柯宇.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向[J].征信.2023(6):83-92.
[20]胡吉明,阳巧英.我国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的三维框架构建与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2(2):39-47.
[21]加小双,王文斐.我国档案标准化体系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J].档案与建设,2022(11):20-25.
[22]王琦.我国档案法治现代化建设:内涵界定、问题检视与实现机制[J].档案与建设,2022(5):8-11.
[23]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M].郝季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4-16.
[24]张帆,刘鸿浩.档案治理效能的三维逻辑阐释:概念出场、内容构成与提升路径[J].档案与建设,2023(10):21-26.
[25]王群,李浩然.《档案法》司法适用的实证与法理——以647份司法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J].档案学通讯,2023(5):52-60.
[2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27]李致.我国法律清理浅析[J].理论视野.2013(2):77-79.
(责任编辑:张 帆 李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