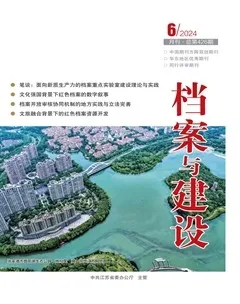档案服务企业数字化业务中的合同纠纷及解决路径研究
摘 要:随着档案服务市场的扩大,档案服务企业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同纠纷成为制约档案数字化业务开展的现实问题。文章对档案服务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合同纠纷案件展开调查,发现合同条款内容模糊、企业间分包挂靠关系混乱是其外在表征。在对法院判决结果梳理之后,文章根据在合同制定、执行及验收各环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以期为解答档案服务业中的合同纠纷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档案服务业;档案数字化;合同纠纷
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Contract Disputes and Solutions in the Digital Business of Archival Service Enterprises
Wang Yi, Ding Ningn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archival service market, contract disputes between archival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clients have become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chival busines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ract dispute cases in the digitization process of archival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finds that the ambiguity of contract terms and the confusion of subcontracting affilia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are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After sorting out the results of the court’s judgmen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targeted solu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tract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accept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olving contract disputes in the archival service industry.
Keywords: Archival Service Industry; Archival Digitization; Contract Dispute
档案服务业是“从事档案社会化服务的企业运用现代档案管理知识、技术和场所、设备、设施等要素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劳务服务、档案产品的新兴行业,是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档案服务企业作为档案服务业的主体,档案数字化是其主营业务之一。《“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快档案资源数字转型。加强国家档案数字资源规划管理,逐步建立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导的档案资源体系”[2]。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领下,档案部门积极寻求与档案服务企业之间的业务合作,档案数字化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然而,随着业务合作的加深,纠纷也相应增多,其中合同纠纷是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合同的签订与执行是档案数字化业务的重要环节,合同条款的合理与否、合同执行的成效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档案服务企业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水平高低。
合同纠纷是档案数字化业务的委托方与承包方均要面临的潜在风险,对合同纠纷产生机制和解决路径的探索是档案服务业风险防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档案服务业的现实状况,指出问题并提出防范风险的措施。例如,李海涛、王月琴对珠三角地区档案服务外包现状展开调研,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3]徐诗成、吴伟刚根据现有规范建构了档案服务外包项目监理模型,旨在规避潜在的风险隐患。[4]
档案数字化业务中的合同纠纷不仅是档案服务业内部的管理问题,也是档案领域的司法实践问题。法院对合同纠纷的判决过程和结果直接反映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目前,学界关于档案服务业法律方向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服务外包标准规范的设计,如徐拥军、陈嘉男根据实践需要,提出加强各层级档案服务外包法规标准建设的对策[5];二是针对档案服务业存在的司法风险点提出防范措施,如肖广锋总结归纳了档案服务外包过程中的4个司法风险点,并提出规避策略。[6]
如上所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档案服务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等方面。采用法律视角的研究则主要聚焦顶层设计层面,以档案服务企业为主体的司法判例研究相对较少,且鲜有从合同纠纷视角出发的深入探讨。因此,文章拟采用定性分析法开展案例研究,充分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裁判文书,旨在发现档案服务企业数字化业务合同纠纷背后的产生机制,并设计相应的解决路径,以期为档案服务业市场中合同纠纷的处置与风险化解提供借鉴。
1 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争议点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档案数字化”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共检索出219篇裁判文书,其中一级案由为“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的案件文书97篇,占总体的44.3%,占民事案由的54.8%。根据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修改,原“第四部分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已调整为“第四部分 合同、准合同纠纷”。[7]因此,文章将一级案由为“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的案件文书统一归类为合同纠纷案件。经过筛选并整合原被告为相同责任主体的案件文书后,共得到56件涉及合同纠纷案件的文书。案件的时间跨度为2015年至2023年,其中2015年至2020年相关案件数量连年增加,2020年达到高峰。尽管2020年之后案件数量略有下降,但与2020年之前相比仍保持在较高水平。2020年至2023年期间,共计有35件案件,占总数的62.5%,总体呈上升态势。这表明,近年来档案数字化业务中的合同纠纷问题已成为制约档案服务业市场发展的现实困境。
档案服务企业在档案数字化业务方面拥有广泛的服务对象,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类企业。广泛的客户主体与档案服务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类型的合同纠纷,如承揽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委托合同纠纷等。这些档案数字化合同纠纷案件中,往往存在着因合同条款内容不清、企业分包挂靠关系混乱所形成的争议点。这些争议点集中反映了在档案数字化服务中各主体之间的矛盾。
1.1 合同条款内容模糊
合同条款内容的疏漏和歧义会阻碍合同的履行。如果在合同签署之前不进行审慎核定,且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未对不明晰条款作出及时补充,那么在验收交付阶段这些问题极有可能暴露出来,在档案数字化的质量、尾款数目及交付等方面引发纠纷和矛盾。
(1)关于档案数字化工作内容理解争议
纸质档案数字化是档案数字化业务中的主要部分,在进行纸质档案数字化之前,往往需要对档案进行预处理,开展一定的档案整理工作。委托方应基于自身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承包方开展档案整理工作,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档案整理和数字化扫描的单价与页数,同时应写明档案整理工作环节和档案数字化扫描工作环节的数量与款项金额是分开计算还是统一计算,以避免后期因此产生合同纠纷。
在桐城市档案馆与安徽九之鼎数字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1)皖0881民初1675号],双方就合同中关于数字化档案数量的内容产生了争议。原被告之间合同约定的200万页数量是数字化扫描件200万页,还是档案整理著录页数加数字化扫描页数合计200万页?委托方认为“200万页”是完成档案数字化的数量,档案整理环节作为数字化工作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而承包方则认为档案整理的数量和档案数字化的数量应当分别计算,即二者相加总计“200万页”。由于双方对“200万页”的理解不一,承包方坚持认为自己已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拒绝开展剩余的数字化工作,导致合同最终无法履行完毕。
在龙岩五牛元科技有限公司、福州科易软件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2)闽0802民初4351号],承包方将档案目录的整理与著录相割裂,要求按照加工的卷数、目录著录条数、扫描页数、整理页数分别计算工作量,其认定的服务款项远超合同限定,无法与委托方达成一致,从而引发了合同纠纷。
(2)未对合同争议点及时补充
在实际履约过程中,需要数字化的档案数量常有增减变动,有时单价也会随之调整,此时应当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正或补充,以保障双方权益。若仅达成口头协定而未对合同条款进行书面补充,则容易在交付尾款时因尾款数目无法达成一致而产生争议。
在部分案件中,验收时承包方完成了超出合同规定的工作量,但委托方认为这部分不包含在合同规定范围内,拒绝支付超出部分的服务款。但实际上,超出部分档案的数字化经过了委托方的许可,若委托方不提供该部分档案,承包方也无从开展工作。当该部分工作量经过验收并得到委托方认可时,委托方应当依照合同规定对超出部分的价款予以给付。例如,在安徽亮达档案科技有限公司、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0)皖0303民初4975号],法院认定被告已经对案涉项目的实际工作量进行了最终验收,并出具了书面验收报告,原告也对验收报告中载明的完成情况进行了盖章确认。对此,按照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超出合同范围外工作成果的报酬。
1.2 企业间分包挂靠关系混乱
档案数字化项目工作内容复杂,加工档案数量规模庞大。为承揽招标项目,一些档案服务企业选择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甚至以挂靠的方式中标,由此产生了争议点。
(1)分包关系中的争议
档案服务企业作为分包方参与档案数字化项目时,委托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合同履行状况将直接关系分包方权益在承包方处的兑现。档案数字化的项目钱款通常由承包方流转,因种种原因而延迟给付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在委托方对分包方档案数字化工作水平不了解的情况下,数字化的质量和档案的安全性也难以得到保证。
当档案数字化分包合同出现纠纷时,法院首先需要对分包合同的有效性进行判定,考察该项目是否为招标项目、分包方是否是在委托方知情的情况下与承包方签订合同、其分包的内容是否涉及项目的关键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第二款规定,“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若中标企业将中标项目全权委托于分包方,或将项目关键主体委托于分包方,则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若已实际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承包方作为过错方,应对分包方的损失进行赔付。
若分包合同有效,则要确定分包合同的独立性。若分包合同是承包方作为甲方,分包方作为乙方,双方独立签署,不包含最初委托方的权利与义务,则认定该分包合同具有独立性,最初承包合同的履行情况与分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无关。当承包方以最初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为由拒绝履行分包合同时,将不予以支持。例如,在宁波宇东金属箱柜有限公司南京第一分公司与望江县档案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15)望民一初字第01290号],法院认定总包合同与分包合同系两份独立的合同,两被告之间是否违约不能免除其对原告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此时,承包方应当按照分包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对档案数字化工作予以验收,并及时给付价款。
(2)挂靠关系中的争议
“所谓挂靠,是指被挂靠企业允许他人在一定期间内使用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该权利义务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借权(从挂靠人的角度)或授权(从被挂靠企业的角度),只要这种借权或授权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就应当认定有效。”[8]档案服务企业在形成挂靠关系后,由被挂靠企业和委托方签订合同,挂靠企业履行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服务款项经由被挂靠企业流转到达挂靠企业手中。挂靠关系的双方不受项目服务合同制约,只受挂靠合同制约。被挂靠企业依照合同,有权向挂靠企业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
在广州协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0)粤0112民初7391号],两家档案服务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法院认定为挂靠关系。原告跟被告之间合作模式是原告委托被告进行投标,由被告中标后与最终用户承接相应项目,再与原告签订将项目工作交由原告完成,经过监理单位,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被告再向原告支付服务费,并扣除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在挂靠关系中,挂靠企业的款项由委托方支付,由被挂靠企业交付,若被挂靠企业不及时交付或克扣款项,挂靠企业的利益将会受损。档案服务企业之间的挂靠关系对于委托方而言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招标过程中审查的是被挂靠企业的资质,而实际履行合同的是挂靠企业,这使得委托方对于挂靠企业的档案数字化工作水平缺乏掌控。
2 法院对于合同纠纷的判决
法院依法对档案数字化业务相关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若发生一方违约或提出解除合同的情形,法院将依法判断违约方责任与解除合同行为的有效性。对于已终止的合同,法院将进行权利与义务的结算和清理,确保双方权益得到妥善处理。
2.1 判决依照法律
在《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有关档案服务企业数字化工作中的合同纠纷大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审理依据,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文简称《档案法》)和档案标准性法规如《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的参照却相对较少。《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委托档案整理、寄存、开发利用和数字化等服务的,应当与符合条件的档案服务企业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服务的范围、质量和技术标准等内容,并对受托方进行监督。受托方应当建立档案服务管理制度,遵守有关安全保密规定,确保档案的安全”。目前,《档案法》更多地站在委托方的角度强调合同条款的约定事项,缺乏对违约行为的制裁。因此,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往往难以依据《档案法》作出具体的判决,多是将其他法律作为审理依据。这一情况导致法院在判决过程中更注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契约精神,缺少对《档案法》中档案价值的关注。
2.2 违约方的确定
在双方均有意终止合同,或者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另一方未在三个月内诉诸法院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视作合同的权利义务实际终止,合同解除。法院需在司法过程中对违约方进行判定,明确合同无法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是由哪一方的违约行为所导致。若承包方因自身原因无法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数量和质量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则判定为承包方违约;若是委托方行为致使承EIyZn7HK/vh7QfldSvl1MJB3P5IgJcDXcRZZWwXItBw=包方无法妥善完成工作内容,则判定为委托方违约。
例如,在陆有安与长沙彩机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0)黔2631民初406号],合同规定“甲方未按时支付工程款给乙方,乙方有权停工,同时可以向黔东南移动公司反映情况,要求甲方必须支付工程款给乙方”。承包方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未得到应有的工程款,缺乏资金继续投入工作,导致工程停工,其事实是由委托方的行为造成的。因此,委托方以承包方未完全履行完毕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而拒绝给付款项的理由无法成立,应当由委托方承担违约责任,向承包方补齐服务款并支付违约金。
2.3 违约金与利息损失的判定
确定违约方之后,法院将会结合另一方的诉求参照合同判定违约金和利息损失。法院确认合同有效性,若合同无效,则合同中有关违约金的条款也不予生效,违约金的申请不予支持;若合同生效,则对利益受损方关于违约金的合理主张予以支持,对于不尽合理的违约金条款参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调整违约金数目,服务款逾期的违约金则以日、月、年不同利率水平进行计算。例如,在博罗县房产管理局与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17)粤1322民初4511号],法院认定,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根据合同第十二条第2项的约定,参照对民间借贷利率保护的法律规定等实际情况,法院认为应调整为以合同金额4012800元为基数,按每月2%从2017年10月14日起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计算。
针对服务款逾期的利息损失,判决焦点通常在于确定计算利息的起始日期。在合同未对承包方交付档案数字化工作成果的实际时间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往往将原告起诉的时间作为起始日期的判定依据。例如,在清远市清城怡丰印刷厂与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中天策划设计工作室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19)粤1802民初1294号],法院认为因《欠款证明》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利息应当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2019年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
2.4 计算档案数字化工作部分完成的报酬
若合同中委托方对于承包方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合格率有相应约定,委托方有权在承包方合格率无法达标时要求整改或解约。然而,若合同中缺少档案数字化的具体质量标准,则难以对承包方的工作成果进行鉴定,委托方此时因档案数字化成果不合格而拒绝支付尾款将构成违约责任。法院只能参考已完成的工作量并结合合同中的价格进行服务款的判定。在缺乏明确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委托方很难对档案数字化质量展开进一步的要求。对于服务款的判定,法院主要有两种计算方式:一是依照合同单价的约定计算,将已完成的数量乘以每件档案数字化的单价得出款项总额;二是将质量不佳的工作成果根据完成情况酌减一定比率的服务款。例如,在贵州医科大学、贵州秀城数字档案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1)黔01民终6342号],法院判定,就瑕疵部分原告应承担一定责任,该部分责任在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服务费160311元中酌情扣减10%,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服务费为144280元。
3 档案数字化合同纠纷解决路径
相关法律条款的缺位、行业标准的缺乏、质量验收的不足以及分包挂靠关系的混乱,都促使了档案数字化业务合同纠纷的产生。对此,亟须完善宏观层面的法律标准,对具体的合同签订与履行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管,以确保档案数字化业务的顺利进行。
3.1 完善合同参照法律规范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第1部分:总则》明确了档案服务外包合同主要参考条款,在第三章服务质量要求中列举了开展档案服务外包工作应当遵照的标准规范,但是对于档案数字化合格率的要求以及质量不达标的应对举措尚显不足。由档案数字化合格率不达标导致的多次整改,是委托方和承包方之间广泛存在的现实问题。若委托方未在合同中对合格率和检验措施、整改措施进行明确规定,并设置相应的解约违约条款,则可能导致对承包方的制约不足,整改困难,进而延缓委托方档案数字化的整体进程,甚至需要重新寻找承包方开展工作。
例如,在潘海平诉被告长沙力智数字房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17)湘1126民初92号],法院审理认为,合同对档案的数字化录入、扫描应达到的具体标准未作约定。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未制定相应的标准,致使原、被告虽提出申请要求对潘海平在双峰县房地产管理局房产档案的录入、扫描的数量及质量(合格率)进行鉴定,但由于没有可依据的标准进行比照,法院司法技术室及原、被告均未联系到相关的司法鉴定、审计、评估机构,致使司法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目前,档案领域的法律与标准主要侧重于对档案保管部门的约束,即档案数字化业务中的委托方,多是将档案保管部门作为主体,强调其寻找并监督档案服务企业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的职责,很少将档案服务企业作为主体去规范权责关系。这种导向下签订的合同,对于档案服务企业的约束力有限,进而影响档案数字化工作质量。
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增加以档案服务企业为主体的法律规范条款,完善档案数字化成果的标准检验体系,明确数字化质量合格的具体指标。同时,对档案数字化业务中的分包挂靠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在合同条款中将其与合同有效性相关联。这样让委托方和承包方都能有凭可依,避免或者减少合同纠纷的产生,为法院开展纠纷处理工作提供参照标准,改善当前档案相关法律标准在司法审理中的缺位局面。面对法院在档案数字化质量司法鉴定的困难,相关部门应当成立档案数字化质量的审计评估机构,助力司法鉴定,保证鉴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3.2 建立档案服务业行业协会
档案数字化整理与扫描工作技术含量低,准入门槛不高,档案服务行业内部服务水平良莠不齐,价格也参差不一。由于“档案服务行业的专业性服务资质不多,比如档案企业的整理资质、档案企业的数字化资质、寄存资质等缺乏”[9],委托方容易忽视档案服务企业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的业务水平,而更多地关注价格因素,可能因价格差异而产生纠纷。“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的统一管理结构来协调档案服务行业,甚至各地的档案服务行业处于各自经营的状态。”[10]因此,亟须建立档案服务行业协会[11],接受档案主管部门的监管和调控,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
由档案服务行业协会牵头,构建委托方和承包方认可的档案数字化资质评价体系,依据档案服务企业的开展服务年限、服务信用水平、过往合同纠纷、档案数字化软硬件配置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定。同时,作为第三方机构,档案服务行业协会应实时进行数字化项目质量监测。基于评定结果,档案服务行业协会可建立档案数字化服务推荐企业名单,以此肃清低价竞争、质量良莠不齐的行业乱象,推动档案数字化服务市场有序发展、合理竞争。档案服务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组织,具有更高的市场灵敏度,能够有效弥补档案主管部门监管的滞后性。
3.3 严格合同签订前的资质审查
部分档案服务企业为了承揽政府的招标项目,采取分包或者挂靠的方式开展档案数字化的业务。这种做法在原本的合同中引入了权责不明的第三方,极易产生合同纠纷。第三方挂靠的经营方式给委托方带来了潜在隐患,同时被挂靠企业也因挂靠企业的行为而面临一定的风险。
委托方在合同签订前,应对档案服务企业进行细致的资质审查,需确认承包方已获得的资质与档案数字化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如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同时,应对承包方之前承接的业务展开调查,对其服务质量具备相应的心理预期。在选择承包方时,审慎采用档案数字化业务水平不佳但是价格相对低廉的企业,避免产生分包纠纷。对于招标项目中的投标企业,应对企业工商信息进行核查,确定其具备履行招标合同的管理水平与数字化能力,明晰投标企业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以避免因复杂的三方关系而产生合同纠纷。
3.4 引入项目监理机制进行全过程监管
部分委托方未完全依照国家标准规范进行项目的全过程监管,甚至怠于行使自身的验收权,未及时安排数字化成果抽检工作,导致档案数字化成果未能达到国家标准与自身要求。而法院在判决过程中很难对档案数字化成果进行质量鉴定,需要委托方自身积极行使验收权。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委托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12]
对档案服务企业的劳动成果予以报酬是委托方应尽的义务,而验收行为则是保障委托方权益的重要手段。若委托方怠于行使验收权,或在验收后才发现质量问题拒绝支付尾款,则可能被视为违约行为,需依照合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例如,在汉中森林之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科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0)陕0112民初12952号],法院审理认为委托方“怠于行使其合同约定的验收权利,其既不验收原告的工作成果,亦不向原告支付剩余款项,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多数委托方是初次开展档案数字化外包项目,对提供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企业以及项目的进程和验收机制缺乏了解。许多案件是因委托方在档案数字化工作中的不当行为而引发的合同纠纷,如在签订合同之后质疑承包方服务资质、不履行合同义务、验收后未保留凭据等行为。因此,需要引入项目监理机制规范验收行为,通过引入专业的第三方作为监理主体,保障合同双方权利与义务的顺利履行,避免产生合同纠纷。[13]“监理主体应依据合同约定对档案数字化活动进行监理,并对采购方负责。在监理内容方面应做好质量控制、进度控制、经费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和协调工作等”[14],从而对档案数字化业务开展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协助并督促委托方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
4 结 语
档案服务企业在开展档案数字化业务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多以合同纠纷的形式集中体现。在司法审理过程中,法院对于档案数字化合同纠纷的判决更为重视合同的履行责任,对于档案数字化的质量与安全难以衡量。面临当下的诸多问题,需要规范档案数字化业务合同的各项条款,扭转档案服务企业在档案数字化业务中“重数量、轻质量”的价值导向。在委托方层面,需要进一步严格准入标准和资质审查,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始终以保障数字化质量与档案安全为宗旨,做好项目开展全过程的档案收集与管理。在承包方层面,应摒弃“一锤子买卖”的心态,不断提升档案数字化业务水平,培养档案意识和对档案的价值认知,积极完善相关资质,打造备受行业认可的档案服务企业品牌。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促进档案服务业市场的健康、繁荣和持续发展。
*本文系2023年度辽宁省档案局科技项目“基于AHP-熵值法的档案类专利质量评价及应用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B-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贡献说明
王毅:确定选题,确定论文框架,论文修改与定稿;丁宁宁:提出选题,查找资料和框架设计,撰写并修改论文。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邓小军,丁海斌.中国档案服务业企业蓝皮书(2016)[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2.
[2]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3-12-27].https://www.saac.gov.cn/ 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5c890762868683.shtml.
[3]李海涛,王月琴.我国珠三角地区档案服务外包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8(4):89-94.
[4]徐诗成,吴伟刚.档案服务外包项目监理模型的构建[J].档案与建设,2022(3):8-11.
[5]徐拥军,陈嘉男.我国档案管理服务外包法规标准建设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5(3):75-79.
[6]肖广锋.档案服务外包中存在的司法风险点及规避策略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裁判案件为例[J].浙江档案,2021(7):55-57.
[7]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EB/OL].[2023-12-27].https://www.court. gov.cn/shenpan/xiangqing/282031.html.
[8]挂靠关系与代理关系的区别与转换及对诉讼主体的影响[EB/OL].[2023-12-27].https://www. 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06/id/62485.shtml.
[9]王毅,蒋官兴.档案服务业企业专业服务资质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1(2):82-88.
[10]王毅,刘维贵.大数据时代档案服务业理论与实践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23:90.
[11]李海涛,杨晗.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档案行业协会建设[J].档案与建设,2022(8):30-34.
[12]贺奕静,杨智勇.角色、互动与运行机制——档案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研究[J].档案管理,2022(4):29-33.
[13]崔楠,周丽霞.基于博弈分析的档案外包服务监管实施对策[J].兰台世界,2022(3):40-45.
[14]柴兴转,谈隽.档案外包监理研究综述[J].档案与建设,2022(4):36-39.
(责任编辑:李倩楠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