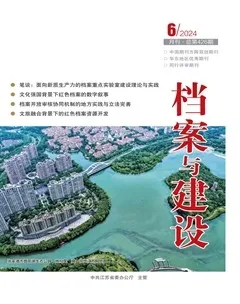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档案的数字叙事:要点、难点与切入点
主持人语:
档案文化生态是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档案文化的生发和存在状态,是档案文化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总和。档案文化生态建设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保护、对新兴文化形态的创新与引领,更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面向国家战略的档案文化生态建设”这一重要议题,正是对“文化生态”这一广阔未知域的深入追寻与前瞻性思考。本期起,受《档案与建设》编辑部委托,笔者特邀多位学界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议题展开论述,以期为丰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档案文化建设实践指明新方向、为新时代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开拓新思路。
聂云霞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摘 要: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红色档案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以数字化转型助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文章基于数字叙事理论,从叙事资源、叙事手法、叙事过程、叙事情节、叙事服务五个层面,探究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要点。在此基础上,以S省红色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为案例研究,明确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实践存在的难点与困境,并从叙事资源数字化、叙事成果创新性、叙事传播机制建立三个方面提出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切入策略。
关键词: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文化强国战略
分类号:G273.5
Digital Narrative of Red Archive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China’s Cultural Strength: Highlights,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 Points
Yan Jing , Du Yujie , Li Xueting
(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
Abstract: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red culture are the inner requirements of the building of China’s cultural strength as a socialist country. Red archives are an important material carrier of red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d archival resources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with cultural strength.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digital narra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ain points of digital narrative of red archives from five levels: narrative resources, narrative techniques, narrative process, narrative plot, and narrative service. On this basis, taking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red archival resour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a case for study, the difficulties and dilemma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narrative of red archives are clarified, and the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of the digital narrative of red archive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digitization of narrative resources, innovation of narrative results, and establishment of narrativ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Red Archives; Digital Narrative; Strategy of Building China’s Cultural Strength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之一。文化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发展情况与国家发展状况紧密相连。档案事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资政育人、赓续文化血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红色档案记载着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国家与民族的珍贵资源,也是红色文化的载体与宝库。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红色档案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尚存在一些现实困境,最直接的体现即民众对红色档案的认知度不足、认同感不够。在文化强国背景下,深挖红色档案中的红色基因、推动红色文化走向群众、增强民众对红色档案的认知与认同,是档案事业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来,数字叙事理论不断演化发展,为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存续红色记忆提供了理论指导。数字叙事具有叙事形式多样性、叙事时间空间化、叙事手段多媒体化、叙事传播交互性、叙事体验沉浸式等特征,不仅能够为做好红色档案的史实梳理、话语表达、时空呈现与场景建构,讲好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提供思想启迪[2],还能够为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档案资源的叙事性开发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目前,国内学者着眼于叙事学视角,提出了红色档案的数字叙事开发策略[3],设计了红色档案资源的组织路径[4],探索了红色档案资源社会共建模式[5],讨论了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如何赋能文化数字化战略[6]。但鲜有研究对接文化强国战略,探讨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相关问题,且现有成果多侧重于应用分析,对于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关键要素提炼等理论性研究较少,亦鲜有对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所面临困境的整体性剖析。因此,本文基于数字叙事理论,以S省红色档案叙事开发为主要案例,探究红色档案数字叙事进程的要点与困境,进而提出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实践切入点,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1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要点
1.1 叙事资源的数字化与数据化取向
近年来,技术环境的流转变迁显著影响了档案对象管理空间的变化,使之经历了从模拟态、数字态再到数据态的嬗变。[7]在此背景下,红色档案叙事的对象亦面临重构,突出表现为叙事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转向。在模拟态档案对象管理空间中,红色档案叙事的对象为实体档案,通过人工选材、整理、归类与编排,借助出版物、音像视频等传统载体实现叙事成果的传播。在数字转型环境下,只有加快推进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处理,才能进一步提升红色档案叙事能力,拓宽红色档案叙事成果传播范围:一方面,红色档案数字叙事能够改变传统叙事环境中的单维书写形式,借助对红色档案内容数据的聚类、关联,真正挖掘出红色档案中人、事、时、地、物等各类叙事要素的内在联系,并辅以叙事化组织和编排,更加全面、立体地讲述红色档案故事;另一方面,基于数字化、数据化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展的叙事活动,多以动态、实时更新的专题数据库、微系统或者其他专门数据化产品等作为成果输出[8],有利于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受众对信息的实时获取与双向交互,扩大红色档案叙事成果的传播和利用范围。
数字叙事理论视域下,叙事素材、叙事工具,以及两者的结合情况都影响着数字叙事的实现效果。[9] 其中,叙事广度的拓宽与叙事工具的应用息息相关,而叙事深度的提升则离不开叙事素材的高度集成、关联整合与细颗粒度挖掘。这既是数字叙事区别于传统叙事的关键所在,也是技术变迁环境下适应多模态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具体到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唯有加快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进程,形成可供阅读、编辑和二次开发的红色档案叙事素材,才能助推数字技术与档案叙事的深度融合,产出更加高质量的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成果。由此可见,红色档案叙事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取向与数字叙事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
1.2 叙事手法的人文化与艺术化取向
数字叙事借助新媒体技术将文字、声音、图像等叙事元素有机融合,使公众置身于所叙故事时空情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档案教育。[10]具体而言,数字叙事的多模态特征能够实现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语言及非语言符号的有机融合,以声像的有机融合渲染氛围、以精美的视觉设计还原场景。数字媒介的互动性特征能够实现高质量的人机交互,引导受众的深度参与,给予受众时间、空间和情感等多维度的沉浸体验。由此,数字叙事对叙事意境的营造和叙事主题的深化等叙事手法,为提升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成果的审美性与表现力提供了新思路。
红色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的奋斗历程,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优化红色档案叙事手法不仅需要关注叙事媒介的变化,更应在讲述和传播红色故事过程中,展现红色档案背后的家国情怀。数字叙事理论高度关注受众的沉浸体验,力求通过多种文本架构和互动模式的丰富组合,以更加生动、直观、易懂的方式,向受众呈现正常情况下无法通达的他人的心灵世界[11],帮助受众理解历史事件的生成逻辑、演化过程和当事人的心理变化,这与依托档案开展人文教育的目标要旨相契合。由此可见,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不仅能够以先进的技术手段打造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叙事世界,满足受众的审美体验,而且能够进一步增强受众在叙事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与认知共鸣,以此实现红色档案的记忆活7b6uJZD61UK716XoBorxBg==化,彰显红色档案叙事鲜明的人文底色。
1.3 叙事过程的互动式与沉浸式取向
从叙事过程看,叙事可以被视作“叙”(叙事过程)与“事”(叙事内容)的统一。基于红色档案资源开展的叙事活动,不仅关注叙事素材本身的丰富性及整合关联程度,还对叙事过程所能为受众提供的互动性与沉浸感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互动性”有助于激发受众的参与热情,受众可以通过情节设计、人机互动、角色扮演等方式参与红色档案叙事活动,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主动的叙事书写者,在亲身体验中深化对红色档案中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情感变化的认知;“沉浸性”则旨在深化受众的情感体验,借助数字媒介和红色档案的深度融合,打造极具临场感的虚拟世界和历史场景,实现受众与叙事环境的深度交互,在逼真的时空场景和细腻的情感流动中唤醒红色记忆。
数字叙事理论研究代表人物玛丽-劳尔·瑞安同样关注叙事活动中“互动”与“沉浸”的双重取向——沉浸性侧重叙事体验的感性维度,而互动性则体现了叙事体验的智性维度,叙事的审美品质就在于实现二者的恰当平衡。[12]一方面,瑞安关注读者的互动体验,认为真正的互动性是要具备在人与人、人与程序系统或者人与虚拟世界之间创造反馈回路的能力。[13]在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活动中,互动体验的最大特点是使叙事场景变得生动、活泼,拉近受众与红色人物的距离,创设足够的正反馈回路,以此吸引受众进行叙事体验。另一方面,瑞安极为重视数字叙事在时间、空间和情感层面为读者打造的沉浸体验。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平面叙事环境下叙事活动缺乏临场感的弊端。高质量的三维空间给予了受众更丰富的感官体验,使其对红色故事拥有更深刻的认知。因此,把握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互动式、沉浸式取向,有助于提升受众在叙事活动中的参与度和体验感,优化红色档案叙事效果。
1.4 叙事情节的故事化与在场化设计
叙事情节是具有特定时间和逻辑关系的序列,是人物角色的思维情感与行为动作得以呈现的平台。红色档案作为记录性文本,本身即对历史事件的叙事性描写,可从其中发现隐含的叙事情节及叙事结构。但红色档案厚重的历史感难免会让人产生潜在的距离感,单件红色档案的展示无法实现对历史情节的全面叙述,公众难以对历史事件产生连续性印象。即使是档案编研、档案展览等综合利用多件档案的叙事活动,也多为线性叙事模式,对原文本进行直接展出,难以串联其间的故事情节,有效发挥出以红色档案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效果。若想有效挖掘内蕴于红色档案文本中的红色基因,满足公众的利用需求,并引导公众对红色基因形成情感认同,则需对叙事情节进一步设计,使叙事文本更具可读性、连续性以及趣味性,为公众提供沉浸式在场化的情感体验。
瑞安根据传统叙事对文本架构的划分,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探讨了情节的表现形式。故事层构建了“串珠型”“决策型”“辫结型”“历险型”四种情节模型。结合情节模型和数字叙事中沉浸式互动的理念,可设计出三种情节结构。一是采取多视角叙事,对照主题需要,构成“平行故事世界”,通过不同人物故事线,更全面、生动地展现出档案所记载的历史故事。二是以空间叙事,打造情节地图,进一步实现对档案信息的跨越式选取。三是采用时间叙事方法,以历史事件的时间进程为主干,打造树状情节结构,由此丰富传统档案叙事的情节结构,使其更具故事化、可读性和在场化体验。话语层则阐述了运用网络、侧枝矢量、海葵、轨道切换等结构形成叙事类型的过程。以情节线索为中心,结合叙事类型与红色档案特点,可划分出四种内容设计形式。一是独立主线,以档案记载的典型事件或代表人物为素材,构建独立的故事情节,以此展现所选取档案内蕴的红色精神与红色基因。二是明线与暗线相结合,以网络或海葵架构打造档案叙事网络,形成灵活的故事次序。其中明线可设置为熟知的历史发展过程,暗线则反映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命运,以此使情节成为相互交织的命运线条走向。三是淡化线索,形成开放情节,实现受众对档案叙事产品的自由探索。四是构建主线线索的同时增加侧枝,以情节主线反映红色档案的时代主题,侧枝则可辅以评论、解说等内容,对档案历史背景进行解释说明,由此形成故事化、在场化的情节内容设计。
1.5 叙事服务的优质化与均等化取向
受众的阅读体验是考量叙事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数字叙事所构建的沉浸式、互动式、跨媒介的阅读平台,使叙事服务更加优质化,受众搜寻和阅读文本的机会更加均等。就红色档案中红色基因的挖掘与传承而言,其一,数字叙事实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互通,突破了时空距离对信息传播所设的壁垒,拓宽了红色档案的传播渠道。诸如专题数据库、主题网络游戏、档案文创等叙事产品,既展现了红色档案记录的历史故事,又为受众提供了更为便利、灵活的搜索和利用方式。其二,数字叙事注重对受众和文本之间关系的分析,并由此形成了不同角度的互动类型。在传统叙事中,受众无法改变既定叙事文本的内容结构,其探索性的阅读过程更多是对故事文本主题的思考,以及对故事文本所呈现文化价值的接受。数字叙事则通过特定文本类型和情节结构,实现受众对文本的自主选择和探索。受众从既定信息的阅读者转变为真正的探索者,由此实现了文本与受众的互动。其三,数字叙事支持沉浸式的叙事体验,其为受众阅读和利用行为提供的时间沉浸、空间沉浸和情感沉浸为叙事服务的优质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数字叙事将时间、空间、情感集合于文本之中,有助于受众对故事本身、历史背景以及人物形象进行理解,由此优化受众的阅读体验。
数字叙事通过形成不同类型数字文本,为受众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并支持受众在与文本的互动中自主探索故事世界,在信息传播方面拓宽了红色档案的传播范围。在文本阅读方面,数字叙事削弱了传统叙事文本对受众知识水平的要求,由此使叙事服务更加均等化。数字叙事所提供的多样化叙事产品能更大范围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在提供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为受众带来沉浸式互动式的阅读体验,由此实现叙事服务的优质化改进。
2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难点
2.1 叙事资源偏零散,数字化程度不足
资源数字化是开展数字叙事的基础。就红色档案而言,可用于数字叙事的资源面临着自身尚未全面数字化、已数字化的碎片化等问题。一方面,囿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原因,不同档案馆在红色档案的数字化保管方面存在差距。以S省为例,基于笔者的调研,虽然省内大多数档案馆已根据要求开展了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建设,将已有的红色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但部分档案馆尚未摸清自己的“红色档案家底”,对现有馆藏红色档案尚未实现全面数字化,并且数字化工作仍存在OCR识别正确率较低、缺少异地备份等问题。例如,部分档案馆红色档案数字化归档比例不足10%,且数字化成果仅为扫描存档,并未实现对文字内容的识别与提取;还有些档案馆由于馆藏红色档案数量较少,尚未建设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另一方面,许多档案馆虽然已经实现了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但资源分布呈现零散化、封闭化状态。这就导致在进行红色档案资源的管理时,各个档案馆往往“各自为政”,在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也是“以我为主”,与同级档案馆及各区县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之间的双向交流不足,更是缺乏与党史研究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藏有红色资源单位的合作,以致形成了“信息孤岛”现象。例如,一些档案馆建立的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目前仅对本地区档案系统内部开放,无法实现对外查询功能,导致红色档案资源存在缺漏不全、受众利用需要多“跑腿”等问题。
2.2 叙事手法偏局限,艺术性不足
在叙事手法上,传统模式下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以编研书稿、音像视频为主要途径,叙述红色档案历史故事、展现红色人物的方式较为严肃、生硬,难以激发受众的阅读(观看)兴趣,影响受众和叙事作品之间的深层次交互。挖掘红色档案、传承红色基因,内容导向是关键。但就目前红色档案开发内容而言,多集中于对某一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红色史实本身的呈现,对其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内涵挖掘不够。这就导致最终呈现的人物、事件、史实缺乏生气和活力,也难以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共鸣。例如,部分地区利用当地红色资源建设了红色人物纪念馆,馆内仅以文字形式陈列人物的生平事迹,缺乏与同类型人物、事件的联动,尚未实现跨情景多元叙事维度的展现。在这样的叙事情形下,受众对所呈现的内容难以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情感共鸣。
2.3 叙事过程互动性不足,交互偏单向
红色档案传统叙事往往存在单向性、低互动性等问题。一方面,开发者与受众缺乏双向交流。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通常由档案机构等官方主体主导,此类叙事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过硬的专业素养,可从权威视角阐释档案内容。但在开发红色档案和挖掘红色基因过程中,官方叙事难免会导致开发成果“曲高和寡”,使受众难以将其生活体验和红色档案叙事内容进行深度联系。例如,部分档案馆虽然打破时空限制,设置了红色档案虚拟展厅,但其专题展览浏览量普遍偏低。究其原因,线上红色档案展览虽在举办形式上进行了创新,但内容上陷入了“阳春白雪”的沉疴,难以真正吸引受众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开发者和受众缺乏实时互动。线上展览有效拓展了展览形式,弥补了线下展览的不足。一是参展门槛低,打破了时间、空间上的限制;二是可持续性高,可长期对观众开放,不受展出时间限制;三是互动更直观,可以较好地统计参观人次、互动数据、停留时长等信息。但实际调研显示,虽然S省多个地市档案馆已设立了红色档案网上展厅,但在实时互动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一些档案馆的官方网站在网络展厅部分设置了红色档案专题展览,但多为单一的图片、文字展览类型,较少采取全景互动展览形式。而且无论哪种类型的专题展览,整个网页仅有图像输出,没有设置实时互动模块,导致开发者与受众的实时性交流受限,在循环性改进、多线程互动方面仍待改善。
2.4 叙事情节较为单一,吸引力有待提升
从载体类型来看,红色档案大部分为文书档案,图片、音像档案资源较少。数字叙事下的红色档案编研,内容多以文字为主体,图像偏少;手法上多为线性叙事模式,编的多、研的少,叙事情节较为单向、呆板,甚至一些编研成果仅是将红色档案原原本本地数字化展出,并未设计任何叙事情节,可读性较差。虽然红色档案数字化编研成果数量较多、内容相对丰富,但碍于文字资料本身的局限性,如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等,仅以文字作为表达方式,难以完整呈现红色历史。若无相关背景知识,受众在接收和理解红色档案历史故事及其文化价值时则会遇到阻碍,更难以形成深刻印象,甚至可能会产生理解偏差,不利于对红色基因内涵和精神的深入解读。例如,部分档案馆利用馆藏红色资源编纂形成了历史档案汇编,文字内容丰富但配图寥寥,并且缺乏相关口述资料作为补充,叙事情节可读性不高、吸引力不足。
2.5 叙事服务有待优化,受众体验感仍需提升
就叙事服务而言,档案机构在提升受众体验、拓展红色档案社会性服务等方面仍有所欠缺。
一是叙事产品传播渠道较窄。红色档案的编研成果大多数流通于机构内部,受众类型往往集中于党政机关等特定群体。尽管档案展览等方式增强了红色档案的传播力度,但这种“内向型”的受众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其他社会群体了解红色档案叙事成果的机会。例如,部分档案馆开发的红色档案叙事成果仅藏于本馆或少量赠予相关单位,在社会层面并没有流通,普通公众只能在档案信息网上知其“姓名”而“难觅真容”。
二是对受众体验的重视不够。很多档案馆还未实现红色档案一站式查询利用,现有红色档案数据库起到的多为红色档案“保管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利用库”和“智慧库”的功能。以S省档案利用平台为例,部分档案馆尚未上传红色档案数字资源,而平台现有的绝大部分红色档案,仅展示了档案题名、责任者、形成时间等信息,受众无法在线查看档案全文,由此增加了普通公众利用红色档案的难度。
三是叙事成果宣传力度不足。目前红色档案叙事成果的主流宣发方式仍是官方媒体,且更多的是被动宣传,而非主动策划宣传,对于已有成果的宣传意识不强。例如,一些档案馆虽已完成了革命历史红色档案数据资源库建设,但目前也仅是在《中国档案报》和国家档案局门户网站进行宣发,并未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大众喜闻乐见且曝光率高的平台进行宣传。这也导致一些红色档案叙事成果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深。
四是未形成常态化宣传。S省内档案机构对红色档案叙事成果的宣传,多是为配合重点和热点事件而进行,尚未形成常态化的宣传机制。以抖音平台为例,S省16个地市的市级档案馆,开通官方账号的仅有2个,且常态化宣传力度有所不足,内容更新频率不高,导致浏览数量较少、影响力较低。
3 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 切入点
3.1 对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夯实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资源基础
数字化为文化强国建设蓄势赋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亟待建构数字化路径。[14]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部署了“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15]等八项重点任务。数字信息化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但仅依托数字技术的迅速更新迭代,无法展现文化数字化的深层内涵与社会价值。红色档案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为国家文化数字化重点任务的推进提供了物质基础。面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数字叙事理论指导下,应夯实红色档案资源基础,形成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安全共享的档案数字化叙事材料,为红色文化传播、红色基因挖掘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资源要素储备。
一是要完善和优化红色档案数字资源建设的体制机制。红色档案资源数目多、体量大,实现红色档案数字化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于此,在国家层面可由政府主导将红色档案资源纳入文化资源体系的一体化建设进程,出台和完善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相关国家规范和执行标准,为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提供制度保障;在社会层面,通过引导社会组织、社区单位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红色档案的收管存用工作,形成“日常化活动、社会性参与”的机制。
二是推进红色档案数字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增强红色档案征集力度。在宏观层面,应发挥档案部门的主导作用,修订、完善与档案信息共享相关的工作制度,必要时可将红色档案互通互联工作纳入档案监督范围,通过分层指导,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红色档案数据协同。例如,可由省级档案馆牵头,会同纪念馆、博物馆、党史部门、新闻单位、图书馆、文化馆等成立红色档案数据库共享联盟,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建设相关事宜。[16]在微观层面,可进一步提升红色档案的征集进馆力度,为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提供丰富的馆藏基础。档案部门应增强对红色档案价值的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公众对红色档案的认知程度,进而通过登记制、有偿制、奖励制相结合的方式,摸排并收集散落在民间、个人手中的优质红色档案资源。
3.2 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创新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成果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必须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以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文化生产传播方式,抢占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17]。在丰富红色档案资源、推进红色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上,亟须合理应用数字信息化技术,以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形式丰富、内容多样、文化价值突出的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产品,拓宽叙事产品的传播渠道,实现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成果服务社会大众的目标。
一是转变叙事思维,应用技术方法。文化创新发展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需要。公众的叙事接受程度是评估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数字叙事中,文本数字化编排是实现受众沉浸互动的重要因素。转变档案数字叙事思维,推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应从文本编排和受众服务两个主要方面着力。在数字叙事理论指导下,要转变以文字叙事为主导的传统叙事思维,借用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渠道展现红色档案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档案部门应充分了解通用型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应用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可能性和具体要求。同时,立足于受众需求,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多模态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如利用三维模拟、传感互动、视听结合等方式,改变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旁观模式,使其更易沉浸在红色档案营造的特定情境中,为受众带来更丰富、生动的视觉体验。
二是创新叙事情节,优化叙事体验。数字叙事的文本架构为档案叙事性开发提供了故事层和话语层的新方法。在叙事情节设计上,可综合应用网络、海葵、增加侧枝等叙事方法,使档案叙事的独立主线、明线和暗线相结合,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融入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尽可能还原叙事空间。通过设定符合时代的场景、人物、氛围,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任务设定、情节触发、人物对话等环节,打造开放性情节,增强受众与红色档案的互动性。例如,互动叙事游戏《隐形守护者》通过明线暗线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在抗战年代潜伏敌后、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故事,经由玩家选择,可以触发4条主线、100个分支结局。在情节结构上,通过打造多条人物故事线、树状情节时间线、情节地图等结构,丰富了叙事情节的可读性和在场化体验。
3.3 对接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建立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传播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强调,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18]。满足人民群众的数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数字文化权益是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打造文化消费新模式的内在要求。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服务的均等化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服务理念高度契合,但仍需拓宽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产品传播路径,建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联动机制,让公众看见红色档案,理解并认同红色文化。
发展档案文化产业是激发文化事业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能够为国家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与服务驱动。[19]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体两翼”[20],二者有机联动可助力实现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成果效益的最大化。数字叙事通过提供类型丰富的叙事产品、结合多种传播媒介,进一步消解时空距离对档案信息传播的限制,为拓宽红色档案叙事产品的传播范围提供了可能。在建立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传播机制的过程中,应立足叙事产品的内容特点,选择恰当的传播渠道,发挥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产品的品牌效应,推动红色档案文化事业发展,拓展红色档案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并探索二者相结合的传播机制。
一是实施跨区、跨馆、跨领域合作创新开发“红色档案+”模式。加大与图书馆、博物馆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合作,扩大红色档案的“朋友圈”,形成红色档案文化辐射效应;鼓励各级档案馆集群开发、优势互补,构建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成果共享平台。二是通过打造红色档案IP,扩大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产品的影响范围。目前,红色档案文化消费仍相对滞后,这就要求档案部门做好公众文化需求调研与分析,系统性、针对性地开发地区特色红色档案资源,形成多形式多维度的叙事产品矩阵,挖掘红色档案特色,打造红色档案专属的文化品牌。三是探索红色档案文化产业化路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探索产业化路径”[21]。于此,应创新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产品形态,发展以红色文化感知、红色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红色档案文化新业态,如打造红色档案数字藏品、数字纪念品等叙事成果;同时,探索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传播新模式,构建“大屏+小屏”“国内+海外”全方位、立体化、多媒介传播矩阵,在国家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彰显红色档案魅力。
4 结 语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是基于过去、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文化工作。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起点,充分利用红色档案资源,推动红色文化繁荣、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是时代所需,更是时代必需。在实践中,应把握好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要点、了解难点、找准切入点,突出红色档案的文化属性,树立协同一致的创新发展目标,真正做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2],让红色文化发挥出独特作用,扎实有力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以档案力量守护红色基因弦歌不辍,为文化强国注入红色动力。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数字叙事理论视域下山东红色档案中的红色基因挖掘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2CDSJ14)、北京市档案科研项目“红色档案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及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贡献说明
闫静:确定选题和文章内容框架,撰写、修改论文并定稿;杜玉洁:初稿撰写,案例研究和数据收集;李雪婷:数字叙事理论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4-03-10].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 content_5721685.htm.
[2][19]周林兴,黄星.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档案力量[N].中国档案报,2023-11-30(03).
[3][10]龙家庆.基于数字叙事理论的红色档案开发策略研究[J].档案管理,2023(4):66-68,72.
[4]陈艳红,陈晶晶.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J].档案学研究,2022(3):68-75.
[5]赵红颖,张卫东.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组织:数据化、情境化与故事化[J].档案与建设,2021(7):33-36.
[6]任越,焦俊杰.文化大数据:档案数字叙事的发展机遇与提升策略[J].北京档案,2023(5):10-14.
[7]钱毅.技术变迁环境下档案对象管理空间演化初探[J].档案学通讯,2018(2):10-14.
[8]周文泓,田欣,熊小芳,等.档案数据化的走向与实现策略——基于《“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展望[J].兰台世界,2022(3):21-25.
[9]黄夏基,卢泽蓉.我国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研究——基于省级综合档案馆门户网站的调查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3(6):31-34.
[11][12][13]张新军.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142,136,131.
[14]魏鹏举.文化强国的数字化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23):40-47.
[1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4-03-10].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2/ content_5691759.htm.
[16]积极建设红色档案数据库共享联盟[N].中国档案报,2023-03-10(03).
[17]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EB/OL].[2024-02-29].https://www. 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b02f3a88cf16b292471641d5ae7cff126764cccbd4f43db12e865124d2ca3862_5705612.htm.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4-02-25].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 content_5592681.htm eqid=a14468700001730f0000000264 80655e.
[20]高书生.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与布局[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1-18.
[21]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4-02-25].https://www.saac.gov. 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5c890762868683. shtml.
[22]习近平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EB/OL].[2024-02-25].https://www.gov.cn/xinwen/ 2014-12/15/content_2791542.htm.
(责任编辑:李倩楠 冯婧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