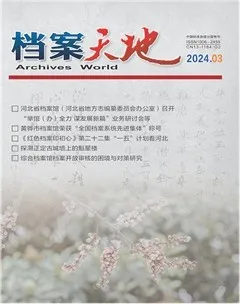具身传播视角下档案信息传播的机遇、挑战与实践策略
具身传播是一种强调身体在信息传递和接收中的物质性和认知作用的传播理念。具身传播视角下的档案信息传播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扩展现实等技术,从各类档案资源中整理挖掘档案资料,对档案进行主题宣传,让受众亲身感受历史文化,漫游在历史场景之中。笔者以“具身传播视角下的档案信息传播”为主题,检索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没有检索到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但间接有关的成果较为丰硕且值得借鉴。如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提出在智能时代,虚拟空间中“具身性”的表现也日益突出,同时具身认知在虚拟空间中也可能出现一些新形式的作用[1]。随着数智化进程的加速,具身技术正赋予档案资源新的生命力,不仅增强了档案内容的可访问性和互动性,而且为用户带来深度沉浸的体验,使档案资源的传播更富吸引力、更有教育意义。
在具身传播视角下,应重新审视档案信息传播的策略,思考在新技术驱动下,如何优化档案信息传播,进而实现其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为此,本文剖析具身技术对档案信息传播的支撑、驱动作用,结合具身传播理念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的应用与发展,详细分析在具身视角下档案信息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相应的案例,提出具体的实践策略和路径。
一、具身认知与具身传播
(一)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包括思考和决策)与我们身体的感觉和运动系统是紧密相连的。该理论强调心智活动与身体的互动关系,即认知活动并非仅仅发生在大脑中,而是整个身体参与的过程[2],强调在思维和知识处理等认知活动中,身体不仅是外部世界的被动接受者,而且是这些过程的积极贡献者。具身认知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对传统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梅洛-庞蒂的“具身主体性”观点、约翰逊和拉考夫的“隐喻”观点以及皮亚杰、维果斯基等心理学家的理论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具身认知理论是第二代认知科学,提出认知与身体密不可分,是有意义地感知并体验世界的主体存在状态[3]。梅洛-庞蒂通过具身的主体性对人类经验的四个维度(对自我、客体和他者的经验维度以及意义赋予维度)进行了整合与协调,将“身体性”推至核心位置,成为该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根基之一[4]。
(二)具身传播
“具身性”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概念,突出表现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对20世纪末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5]。有学者探讨了具身性研究的应用前景, 认为“具身性”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可以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具身传播起源于“具身性”的概念,认为人的身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工具,同时也是信息的创造者和阐释者。尤其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维持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具身传播是指在社会化与文化涵化的共同作用下,人的身体逐渐演化为一个兼具生产性与接收性的传播媒介。这种传播并非仅仅是将技术或情感强加于身体之上,而是人在特定活动中与周围环境实现深度交融的一种传播形态。它超越了简单的身体动作或情感表达,成为一种更深刻、全面的传播方式,能够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具身与传播之间的交互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媒介和技术三者之间的紧密互动与相互影响[6]。
(三)具身传播的基本要求
1.高度沉浸
5G通信技术与扩展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使万物皆媒,传播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播形态的高度沉浸化,使用户的感官得以延伸,创造了人机合一的沉浸体验感,虚拟与真实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高度沉浸的传播形态从感官上为具身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7]。
2.身体在场
身体在场是具身参与的基本要求,它是受众与环境建立直接联系、实现深度互动的基础。首先,身体在场为受众提供了直接感知环境的机会;其次,受众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可以更加直观地获取环境中的信息;同时身体在场有助于受众与他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从而帮助受众在社交和情感层面得到满足。具身传播突出了传播的多主体性、互动性和身体经验的重要性,为理解当代媒体和技术领域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重构了人们的身体体验与具身认知[8]。
二、具身传播视角下档案信息传播的全新机遇
具身传播不仅带来信息传播领域的变化与革新,也逐步与档案信息传播相结合,这将为档案信息传播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颠覆叙事模式
具身技术的加入不仅为叙事提供了新的形式和工具,也为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体验深度,对叙事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具身技术推动了叙事的跨媒介和跨平台演变,将传统的以文字、图像或视频为主的单一形式拓展至更复杂和互动的新媒体环境。这种技术支持非线性和动态的叙事结构,为受众提供了全面沉浸的感官体验,仿佛置身于故事的世界之中。在具身技术的引领下,受众转变成为积极的参与者,通过身体动作与故事互动,影响故事的创作和发展。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限制,让叙事跨越屏幕,给受众带来多感官的全方位沉浸化体验,共创独一无二的叙事旅程。
(二)打破隐性障碍
尽管运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能够为档案信息资源营造出一个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但技术的限制仍然会在用户和虚拟场景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障碍层,可能会影响用户对档案信息的感知和理解。然而,具身传播的理念为克服这些传播壁垒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强调通过身体经验和互动性强化信息的交流和体验,从而有助于档案信息更全面地被受众所接受和理解。依靠具身技术赋能,档案信息可以通过具身穿戴设备刺激受众的身体感知,使受众沉浸在叙事氛围中,通过触觉、嗅觉等真实可感的身体接触,可以切身体会档案内容,从而提高受众对于档案信息传播的体验感。档案信息传播进入了一个具身化的发展阶段。
近期,青岛故宫文创馆的沉浸式剧场融合了线下RPG类推理互动游戏与行进式互动戏剧演出,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与式文化体验。这种互动体验模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游客在多维空间中全面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例如,游客可以通过VR技术,身临其境游览故宫的各个角落,感受古代建筑的魅力;也可以通过AR技术,观看故宫文物的三维展示,了解文物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
(三)提升传播深度
传统的档案信息传播大多采用平面媒体进行报道,受众通过阅读文字或观看图片获取信息。这种方式通常是线性的,只能提供有限的、表面的信息传递,受众难以深入挖掘和理解档案中蕴含的丰富和复杂的意义。因此,档案信息与受众之间往往存在一种隔阂[9],导致档案资源的深层价值未能被充分发掘和传达,使档案信息传播的深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从而影响了档案信息的传播效果。具身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将受众的身体感知与档案内容相融合,可以将档案信息转化为更生动、直观的三维模型或场景,使受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档案所记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让受众对档案信息产生浓厚的兴趣,更能加深他们对档案内容的深度理解。
例如,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精心策划的“第七档案室”项目,以“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为蓝本,巧妙地将解谜书和实景解谜活动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档案教育文化创意。在“第七档案室”中,档案知识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和图片,而是被巧妙地融入沉浸式书本与实景体验之中。读者在翻阅解谜书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享受解谜带来的乐趣,更能在自主探索中深入了解档案知识。通过游戏的形式,凸显了档案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让受众在互动体验中更深刻地感受档案文化的魅力。
(四)完善媒介环境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蓬勃发展、媒介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人类知识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具身化”现象深刻改变了认知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媒介生态环境也与其产生共振效应,技术的发展、认知生态的变化,和媒介会产生相互作用,形成持续演进和完善[10]。
在当前媒介生态的背景下,可以清晰地感知媒介时代变迁中具身传播的发展机遇。档案信息传播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迎来具身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对此,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既要积极把握发展机遇,也要审慎防范潜在风险。我们的目标是借助具身技术的强大动力,推动档案信息传播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提前对风险的识别,清除传播障碍,不断完善档案信息资源传播的媒介生态环境,从而创新具身传播背景下的传播路径、提升传播体验、优化传播方式,并开发出更多衍生产品。最终,构建一个以具身媒介生态体系为基础的档案信息资源传播利用新模式,为档案信息的广泛传播和高效利用开辟新道路[11]。
三、具身传播视角下档案信息传播的主要挑战
在具身传播的赋能下,档案信息传播也面临相应挑战。一是具身传播的无障碍交互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二是叙事主题限制使内容表现形式单一,叙事结构较为封闭;三是专业技术人员缺位,使编研质量往往参差不齐,削弱了传播效果;四是过度夸大具身技术作用,可能会造成服务安全风险。
(一)具身传播的无障碍交互模式存在潜在风险
无障碍式交互也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信息交互传播与开放共享功能在给受众带来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可能给档案资源的保存及传播带来一些风险。元宇宙是典型的具身传播[12],本节以元宇宙为切入点,对元宇宙媒介下无障碍交互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讨论。
第一,海量数据支撑元宇宙媒介的构成,其中既包括档案部门需要提供的档案信息,还包括媒介构建、存储和收集的众多用户个人信息,媒介平台的信息互动传播与共享开放功能,对于保护档案信息安全以及用户的个人隐私而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元宇宙的共识机制中阐述了元宇宙是一个自由世界[13],与此同时,元宇宙媒介平台的开放程度与其他媒介平台相比是空前的,“元宇宙”建立起的虚拟社交平台,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无障碍的互动体验,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例如黑客攻击、文件数据泄露、用户信息窃取等诸多安全隐患。
第二,元宇宙媒介平台也为每个用户提供了空间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的权限,允许用户进行自由的内容生产和编辑。档案信息资源在利用其进行交互的同时,由于编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以及外部别有用心的情况,都可能会对档案信息的原创性、真实性造成很大破坏。
第三,元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空间,其本身更容易形成闭环,各个“元宇宙”之间交互连接,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元宇宙媒介具有的非权威化和去中心化的流媒体特质,使个体的信息接收环境日益固化,用户群体也更容易出现同质化的情况,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
(二)叙事主题限制使内容表现形式单一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囿于制作理念同质化、传播平台局限性以及表达形式模式化等问题,导致档案资源叙事题材的可选性大大降低,限制了选题范围与内容的深度表达,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同时,档案的具身传播虽然在很多方面为信息的展示和用户体验方面都带来了革新,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的内容传播。
第一,敏感或隐私内容。由于档案资料的敏感性、隐私问题或文化敏感性,涉及机密信息或敏感历史事件的档案,出于对隐私权和安全性的考虑,不宜通过具身形式公开传播,这种限制性选题导致叙事内容相对单一。
第二,复杂抽象概念。具身技术在感知能力上有限,可能无法完全捕捉或传达复杂抽象概念的全部细微之处,一些包含高度复杂或抽象理论的档案信息可能难以通过具身体验直观呈现,用户可能因此难以理解和吸收这些概念。
第三,灾难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记录悲剧或灾难(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的负面情境档案事件,使用虚拟显示等具身技术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情绪冲击和创伤体验。
(三)专业技术人员缺位导致传播效果降低
专业技术人员对于实现有效的具身传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掌握专业信息技术的人才以及高素质档案工作人员的缺位将会在多个层面削弱档案信息的传播效能,不仅可能影响用户体验,甚至可能威胁信息的安全与完整性。
第一,内容形式单一。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席可能导致档案资源素材的处理局限于基础的剪裁、拼接和编辑,无法充分挖掘和展现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缺少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可能使档案信息呈现为单一的文字或图片,不仅交互性不足,而且视觉呈现也缺乏吸引力。尽管通过简单拼接的素材可以为受众提供一种基础的全景式感受,但这种方法仍旧无法与沉浸式体验相媲美,缺乏引发内容本质上变化的能力。此外,传播内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特性也因此受限,导致信息呈现在多样性和定制化方面的不足[14],受众体验感差,影响受众对档案信息的理解和吸收。
第二,技术实施困难。没有专业的信息技术支持,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和虚拟化过程可能会遭遇技术障碍,导致无法高效地创建和管理沉浸式体验或增强现实内容。任何技术解决方案都需要持续的维护和用户支持。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维护更新可能会变得困难,导致系统过时或出现故障。
(四)具身技术作用夸大造成服务安全风险
具身技术虽然为档案信息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当前学界和业界对其作用的过分强调,容易走入“唯技术论”的误区,淡化人的主体地位与作用[15]。同时,对具身技术作用的夸大,容易让受众陷入“技术成瘾”的困境之中,把技术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沉迷于数字智能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给档案信息传播活动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
具身技术媒介虽具有多感官通道、高度情境性等诸多优势[16],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仍需要警惕“唯技术论”倾向,要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确保档案资源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四、具身传播视角下档案信息传播的实践策略
随着技术的发展,具身传播成为促进用户更深层次参与和体验档案资源的有效途径。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还能增强公众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同时,档案信息传播应该坚守社会责任,把握技术应用与信息伦理之间的界限,结合专业化的具身平台,创造沉浸式档案场景,为档案信息传播带来新的生机。
(一)增强档案传播风险防范,强化监管体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信息传递的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也为档案信息传播工作带来了无限活力。随着具身技术的应用,新的挑战和风险也会随之出现。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有助于更好地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潜在弊端。如果忽视具身传播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随着这些风险的持续累积,档案信息传播的良性发展势必会受到负面影响[17]。为达成档案信息传播更多元高效的目标,涉及传播流程的各参与方都要增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关机构及传媒行业须建立周密的风险防控体系,修补技术漏洞、增强行业自我监管、提升信息质量、打造良好传播生态。
完善的监管制度是确保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性和合法性的关键,同时也对促进档案传播工作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维护档案资源的完整性与安全性,同时也促进了公众对档案资料的便利获取和高效利用。这样既满足了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也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和进步。但当前,现有的法律法规可能还不够清晰或未能及时得到更新,以至于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因此,政府作为治理的核心必须承担适当责任,既要避免过度管控导致创新活力的丧失,也要防止权力过分下放引发治理秩序混乱。各职能部门需要通过优化制度框架弥补碎片化管理和控制能力不足的问题,增强制度的规范性,确保监管更加有效[18]。
(二)健全档案资源利用制度,扩充主题内容
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强调了“十四五”时期将强化档案资源的建设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强化档案资源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提升档案资源的质量和服务能力。档案资源对于保障国家的行政管理、社会运行、文化传承和科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开发与利用始终是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档案资源利用制度进行健全与完善,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档案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也能够保障档案资源的安全和完整,促进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扩展档案在教育和学习领域的应用,并融合具身技术,可以创造出模拟真实历史场景的学习环境,从而为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沉浸式学习体验。这种体验不仅能够增强学习者对历史事件的感性理解,还能促进更深层次的认知吸收和知识内化;同时,推动与艺术、文化、教育等其他行业的合作,开发跨领域项目,可以使档案资源服务于更广阔的主题和受众。例如,故宫博物院曾与北京市档案馆合作举办宫廷文物展览,利用馆藏的清代档案文献丰富展览内容,为观众提供更深入的历史背景解读,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总之,结合具身技术和推动跨行业合作,无疑将为档案信息传播带来新的内容和视角。
(三)提高档案工业人员水平,挖掘文化价值
档案工作者是档案利用服务的主体,也是档案信息传播工作的主力军,其专业程度和服务能力是保证档案信息传播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只有进一步加强档案专业人才的培训,使其适应新的信息技术环境,档案信息传播工作才能拥有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档案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历史知识和档案管理技能,还需要了解现代信息技术,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档案数字化和信息整合。
随着具身技术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的应用日益增多,档案部门主导地位正逐渐弱化,相反,它们在提供专业咨询和方向指引方面的社会职能得到了显著增强。此时档案工作者的职责亦在动态创新变革之中,档案工作者需要为受众提供相关技术指导和专业技术服务。目前档案部门更需要的是掌握具身技术的新型档案人才,因此人才的培养应侧重具身教育。这将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知,发掘档案中蕴含的文化底蕴与潜能,为档案传播工作的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四)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技术优势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不断加大对档案资源的开发力度,创新传播内容,探索新的研究角度,并扩展档案研究的新兴领域。这进一步迎合了公众对于与时俱进的档案信息传播的需求,并在内容与形式上塑造了人文知识传播的新范式[19]。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档案领域需要充分融合前沿的观念与技术手段,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开发,促进档案文化的传承,扩大档案的影响力,并增强公众对档案重要性的认识。
具身技术通过提供沉浸式体验、实时互动和定制化内容,正变革档案信息传播的方式与效果。这种技术不仅提升了受众的参与度和体验质量,还拓展了传播的新渠道和研究的新领域。它使档案信息变得更富吸引力、更易于理解,从而更广泛地被公众接纳。随着具身技术持续进步,其在传播行业的潜在力量正逐步得到挖掘,为传统的档案信息传播注入创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彭兰. 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 可分离的“虚拟实体” 、“数字化元件” 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J]. 新闻记者, 2019(12): 4-12.
[2] 叶浩生. “具身” 涵义的理论辨析[J]. 心理学报, 2014, 46(7): 1032-1042.
[3]冯碧莹,宣朝庆.“通国身”:“具身化”理论的本土想象[J].社会,2023,43(4):40-71.
[4] FUSAR-POLI P, STANGHELLINI G. Maurice Merleau-Ponty and the “embodied subjectivity” (1908-61)[J]. Med Anthropol Q, 2009, 23(2): 91-93.
[5] PINK S.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M]. New York:Sage, 2015.
[6] 芮必峰, 孙爽. 从离身到具身: 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5): 7-17.
[7] 林升梁, 叶立. 人机·交往·重塑: 作为“第六媒介” 的智能机器人[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10): 87-104, 128.
[8] 赵海明. 基于“人—机” 关系视角的具身传播再认识: 一种媒介现象学的诠释[J]. 新闻大学, 2022(7): 14-26, 116-117.
[9] 葛悦,谢诗艺.档案文创产品用户满意度影响因素探析:基于《第七档案室》解谜书的扎根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2(11):56-59.
[10] 余宏亮. 数字时代的知识变革与课程更新[J]. 课程 教材 教法, 2017, 37(2): 16-23, 60.
[11] 倪代川, 高妍, 李涵. 元宇宙视域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探析[J]. 山西档案, 2022(6): 108-117.
[12] 张洪忠, 斗维红, 任吴炯. 元宇宙:具身传播的场景想象[J]. 新闻界, 2022(1): 76-84.
[13] 鲁照旺. 元宇宙的秩序和规则[J]. 学术界, 2022(2): 65-79.
[14] 郑景之. 融媒体时代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新闻传播策略研究[D]. 西安: 西安工业大学, 2022.
[15] 杨保军. 再论“后新闻业时代”[J]. 编辑之友, 2022(10): 5-13.
[16] 张广君, 黄洁. 当代 “教学身体观” 的危机与重建[J]. 当代教育科学, 2023(3): 31-38.
[17] 祝金梦, 贾慧娟. 微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J]. 山西档案, 2021(1): 111-119, 93.
[18] 向安玲, 高爽, 彭影彤等. 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J]. 图书情报知识, 2022, 39(1): 30-38.
[19] 张澍雅.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服务的新思考[J].档案与建设,2019(3):37-40,32.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