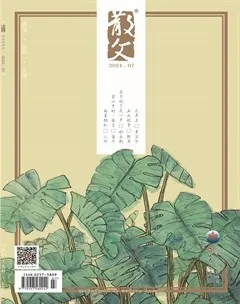枕中记
太多的历史风云、太多的人生理想、太多的深闺旧影,都和枕头相关,枕边书、枕边人、枕中梦、枕中语,说不尽的枕头事,写不尽的“枕中记”。唐人晁采一首《秋日再寄》,寄的全是枕边的诗与思:
珍簟生凉夜漏馀,梦中恍惚觉来初。
魂离不得空成病,面见无由浪寄书。
窗外江村钟响绝,枕边梧叶雨声疏。
此时最是思君处,肠断寒猿定不如。
《说文解字》释“枕”:卧所荐首者,从木,冘声。枕头就是人类躺卧时垫在颈项后面,使脑袋得以休息的卧具。从木,意味着早期(汉代以前)的枕头多以木材制作而成。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补充说:木枕即圆木枕,亦即《礼记·少仪》中的“颎”——“谓之颎者,圆转易醒,令人憬然,故郑注曰‘警枕’”。这个说法令人有些意外,枕头的本义在于让头颅得到放松和休养,这倒好了,放个滚动的圆木筒在脖子下面,随时提醒不要睡得太安稳?
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谈及枕头时说“枕制不一”,就是木枕,也不一定都是那种随时准备把人弄醒的颎。高濂记载了一种木枕的制作方法:“有用磁石为枕,如无大块,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镶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此时的枕头,已被赋予医学甚至玄学方面的意义。清人曹庭栋《养生随笔》中的“女廉药枕”(女廉的故事来自东方朔与汉武帝的传说),也是一种木枕,制工较为复杂:以赤心柏木,制枕如匣,纳以散风养血之剂;枕面密钻小孔,令透药气,外以衡布裹之而卧。还有一种黄杨木枕,取黄杨木作枕,必阴晦夜伐之则不裂,“木枕坚实,夏月昼卧或可用”。
最为人所熟知的古代枕头,大概就是瓷枕了。《遵生八笺》就记载了好几种瓷枕:
宋磁白定居多,有特烧为枕者,长可二尺五寸,阔六七寸者。有东青磁锦上花者,有划花定者,有孩儿捧荷偃卧,用花卷叶为枕者。此制精绝,皆余所目击,南方一时不可得也。
白定和花定烧制了大量瓷枕,较少为人所知的东青瓷也有瓷枕制售。冬青窑即北宋开封东窑,所烧瓷器釉色呈淡青色,世称“冬青”或“冻青”。清人兰浦《景德镇陶录》谓其“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
高濂所说的“有孩儿捧荷偃卧”,说的就是广为世人所知的宋代孩儿瓷枕。孩儿瓷枕以其呆萌俏皮的造型和精致的做工闻名于世。制成孩儿形态,让人看着心生欢喜之余,还有一层“宜男”的寓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男性劳动力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致使乞子风俗十分盛行。在河北定窑故地,还流传着“得瓷婴即得虎子”的说法。传世的三件最著名的定窑孩儿枕,均藏存于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中。据说乾隆皇帝酷喜定窑孩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孩儿枕中的一件,枕底便刻制着乾隆御题诗《咏定窑睡孩儿枕》:
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
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
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
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签劳。
使用瓷枕,成为宋人夏天纳凉消暑的重要手段。苏轼就爱睡瓷枕,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写道: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苏轼说他在十年之内四处飘泊无定,突然在异乡(宜兴)想念起故乡(眉州)来。接着写及在宜兴短暂的快乐时光,道人劝他要多喝鸡苏水,鸡苏水就是鸡苏汤,苏轼之后的官修医书《政和圣济总录》中有记录,以鸡苏、地黄汁、桑根白皮、生姜汁、葛根、小蓟根和淡竹茹煎制而成,有补血除热止吐等功效。“瓦枕”就是瓷枕,宋代政治家李纲的《吴亲寄瓷枕香垆颇佳以诗答之》可以为证:“远投瓦枕比琼瑜,方暑清凉惬慢肤。”诗题中为“瓷枕”,诗中变成了“瓦枕”。苏轼的瓦枕和藤床一起,成为其吐纳清凉竹风的神器。
女词人李清照也十分钟爱瓷枕:“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醉花阴》)词中的“玉枕”可能并非真正的玉质枕头,而是景德镇窑口烧制的一种被称为“影青”的青白瓷器,因其莹润光洁接近半透明,被世人唤作“陶玉”。词人以“凉初透”三字来形容,可谓得其神韵。李清照在一首失调名的词中写到一种名叫“山枕”的枕头:“犹将歌扇向人遮,水晶山枕象牙床。”这枕头在《浣溪沙》中再次出现:“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山枕看来也是瓷枕一类的硬枕,有《蝶恋花》可资佐证:“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如果是软枕,肯定是无法损伤钗头凤的。
陶瓷史学者陈万里的《陶枕》中载录一首宋代瓷枕题诗:
久夏天难暮,纱幮正午时。
忘机堪昼寝,一枕最幽宜。
看来夏天睡瓷枕,确有妙不可言之处。苏门弟子张耒有《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
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
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
梦入瑶都碧玉城,仙翁支颐饭未成。
鹤鸣月高夜三更,报秋不劳桐叶声。
我老耽书睡苦轻,绕床惟有书纵横。
不如华堂伴玉屏,宝钿欹斜云髻倾。
“巩人作枕坚且青”,应该就是高濂所说的开封冬青窑,这件河南烧制的青瓷瓷枕,不仅釉色好看、质地致密,其冰凉的特质,也让整个卧室陡然生出几丝凉风,睡于其上,清寒入梦,梦的天地也是一片瑶池碧玉,美人们的“宝钿欹斜”不断闪动。一件瓷枕,简直就是极乐世界的入口啊!
硬质枕头虽然各有妙处,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缺乏舒适性。无论古代的人、现代的人还是未来的人,除开小部分以苦行为乐的人,追求舒适和安逸总是人性不变的定律。对于与人终生相伴的枕头而言,这个定律恐怕还要体现得更为充分一些。
尽管软枕不易保存下来,但考古学者还是在长沙市马王堆墓中发现一件西汉绢枕,后来又在广州南越王墓中得到一件西汉素绢珍珠枕囊。
枕囊又称囊枕,是软枕中最为人所喜爱的一种。所谓枕囊,其实就是在布袋或皮袋中填入松软且有助睡眠的各种植物花叶、根须及碎壳,形成一囊状或柱状枕头,有点类以于现代的枕芯,只是填充得并没有那么瓷实,其形状也更容易变化一些。堪作枕囊囊芯的植物很多,以清香且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植物最受欢迎。清人曹庭栋在《养生随笔》中记载:
囊枕之物,乃制枕之要。绿豆皮可清热,微嫌质重;茶可除烦,恐易成末;惟通草为佳妙,轻松和软,不蔽耳聪。《千金方》云:“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枕头软者甚多,尽善无弊,殆莫过通草。
由此可知,填充枕囊的材料,有绿豆皮、茶叶和通草等。《千金方》所引的这首民谣非常有趣,朗朗上口,说尽了一个普通人独处的日常幸福,只要有只枕囊一类的软枕头,就很满足了。通草具有很好的松软性和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上就说:通草烧研酒服,治洗头风。
包括枕囊在内的各式软枕,至宋代始成为普通人家床榻必备。北宋张耒在《局中昼睡》中惬意地写道:
鸟啼花开千万思,春色醉人成午睡。
烧香扫地一室间,藜床布枕平生事。
春天的睡眠,必须枕着松软的布质枕囊,而不能是冷滑的瓷枕。对于枕囊,宋人持舒适性与疗愈作用兼顾的态度,但舒适性始终更加重要。当疲惫的头颅放到枕囊之上,便会油然产生一种归宿感,一种睡逢知音的感觉。南宋诗人王质就在《和郭子应》诗中写道:
北窗睡起复西窗,心事悠悠付枕囊。
日静无人惊燕雀,野青随意卧牛羊。
愁中故自伤游子,别后还应忆漫郎。
万里梅边寻斗米,夫君身世亦遑遑。
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在今天,当我们遇到挫折和委曲时,常常会拥枕而眠,甚或抱枕痛哭。
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中著录了传为张道陵撰《药枕方》一卷。王质在《绍陶录》也论及枕囊的药用:“药枕,纯贮甘菊、荆芥良佳,他方稍繁难集,以轻平为良。”从中可以得知,宋人进一步拓展了软枕的概念,除布枕、皮枕之外,还将介乎软硬之间的藤枕、竹编枕和绳枕纳入其家族。在各种植物枕囊中,王质提到的甘菊枕囊是颇受欢迎的一种。他的《栗里华阳窝辞》中就有首《栗里枕》歌谣:“块不枕头,防儿来偷。疾攑深投,安枕长流。在我窝兮不可忘,无烦酴酥入枕囊,但乞野菊花风香。”这只枕囊,就是用野菊花制成的,散发着独特的山野气息,比酴酥酒的芬芳还要让人难忘。相仿记载,在《遵生八笺》中也可以看到:“有菊枕,以甘菊作囊盛之,置皮枕、凉枕之上,覆以枕席,睡者妙甚。”
陆游尤爱菊花枕囊。他在《示村医》中说,菊花枕囊可以治疗头痛风疾:“玉函肘后了无功,每寓奇方啸傲中。衫袖玩橙清鼻观,枕囊贮菊愈头风。”又在一首诗中诉说,他二十岁时就写过一首流传甚广的菊枕诗,四十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早已年过花甲的他再次采摘菊花缝制枕囊时,“悽然有感”,于是写下两首七绝。其一: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閟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其二: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睡在菊花枕囊上,梦见四十三年岁月如电光石火般闪过,逝去的再也唤不回来了。
又过了将近二十年,诗人已经八十多岁,在一首秋天的《晚菊》中,陆游再次写到了菊花枕囊:
蒲柳如懦夫,望秋已凋黄。
菊花如志士,过时有馀香。
眷言东篱下,数株弄秋光。
粲粲滋夕露,英英傲晨霜。
高人寄幽情,采以泛酒觞。
投分真耐久,岁晚归枕囊。
这是诗人最后写到心爱的菊花枕囊,此时的诗人年华不再,生命如同蒲柳一般在秋天中凋零。“投分真耐久,岁晚归枕囊”,一个“归”字,写出诗人与枕囊的深切关联,那里不仅是他安睡之所,亦是他最后的精神之乡。
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也爱菊花枕囊:
性迟故故待霜天,珠蕾金苞带露鲜。
曾有餐之充雅操,又云饮者享高年。
骚留楚客芳菲在,史视胡公粪土然。
莫道先生真鼻塞,幽芗常在枕囊边。
(《菊》)
即使得了严重感冒或犯了老鼻炎,别的味道闻不到了,从枕囊中透出的菊花香味,却可以嗅得清清彻彻。
黄庭坚喜欢的则是另一种决明子枕囊:
茵席絮剪茧,枕囊收决明。
南风入昼梦,起坐是松声。
(《次韵吉老十小诗》)
除决明子枕囊之外,黄山谷也喜欢菊花枕囊:
肌肤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芳。
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
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
输与能诗王主簿,瑶台影里据胡床。
(《观王主簿家酴醾》)
诗中有条自注:“《千金方》:菊花作枕袋,大能去头风,明眼目。”由此可知这件枕囊不是决明子而是菊花枕囊。王主簿家的春酒酿得太香,诗人希望那“彻骨”的香味一直彻进枕囊之中。此诗写成之后被众口传诵为佳话,宋人罗烨《醉翁谈录》中还收录一首同样写及此事的诗:“千古才名老豫章,暗将妙质比幽香,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这个“老豫章”,就是诗人黄庭坚。
南宋词人史达祖的《鹧鸪天》,则呈现了枕囊最温柔缠绵的另一面:
睡袖无端几摺香。有人丹脸可占霜。半窗月印梅犹瘦,一律瓶笙夜正长。情艳艳,酒狂狂。小屏谁与画鸳鸯。
解衣恰恨敲金钏,惊起春风傍枕囊。
人还没有走,枕囊之上已起春风。
而在吴文英的《满江红》中,想象中的人已经走了,徒留枕囊让人怀想——
芳井韵,寒泉咽。霜著处,微红湿。共评花索句,看谁先得。好漉乌巾连夜醉,莫愁金钿无人拾。算遗踪、犹有枕囊留,相思物。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