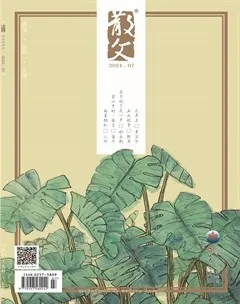雨中谒小津
镰仓的平交道
2017年的夏天,镰仓的那个火车平交道,长久地留在我的印象中。那一瞬,被同行郭医生拍了下来,是一张好照片,与我印象中的那个景象合并在一起——夜色中,一辆淡绿色的火车正飞驰而过,车厢明亮,但光影被速度拖拽得一片模糊,栏杆之上,两盏红色的信号灯,一高一低,甚为妖艳。
很多年前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黑白影像,俯拍镜头,一列蒸汽火车冒着白烟穿行在镰仓的海岸边。我还记得小津的摄像说过,小津基本上只拍室内,如果要出外景,他就拍火车,而且基本上只拍他所定居的镰仓的火车。
幼年每次在平交道等待通过的时候,那些飞驰而过的列车总是把我弄得怔怔的。那种奔赴的激情,在童年的我的心中,有一种无比向往的美妙。
因为是铁路局子弟的缘故,我很小就开始坐火车,中学之前多次往返于成都与老家上海以及曾经上过小学的南京之间。但火车并没有把我真正地带到远方,奔赴的激情也没有达成根本的效果。火车,只是把童年的我送出去,又送回来,最终,长大了的我也没有离开我出生的城市。
当时,在镰仓,我们骑着车刚通过平交道,警示铃声即时响起,预告火车即将通过。我回头看时,栏杆已经放下,紧接着一辆火车飞驰而过。应该是短途火车,只有几节车厢。目力所及,明亮的车厢里面的景象是相当清晰的,夜归的人们在车里或站或坐,没有一个朝车窗外张望。
在火车上,每个人的脸都差不多,不光神情,连五官都差不多。那是一种特别的状态——因为不在乎任何外界的观看而产生的放空和呆滞。我早就发现,人的模样之所以差别如此之大,并不是生理性的原因,而是心理性的原因。面孔之千差万别,是出于心理上的千沟万壑;当被一种共同的心理所充填的时候,人的面孔就趋于这个物种所具有的共性了——就像我们看到同一个品种的猫和狗会觉得长得差不多一样。它们还是和我们人类很亲近的物种,说远一点的——谁能分清一只羊和另一只羊呢?
这个发现,是在我很不愿意回忆起的一个场景里产生的。当时我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有几面墙铺满了受难者的照片。这些照片是那些犹太人刚刚入营后,纳粹统一拍的:囚服,剃光了头发的脑袋,一张正面照加一张侧面照……无数的面孔在这里几乎一模一样,因为其背后的心理只有一种——绝望恐惧。
全世界的平交道都是这样的吧——一种特别的注视,单向的,车内的人被车外的人注视。这列短途火车飞驰而过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太宰治在一个短篇小说里写到,男人和女人散步至铁路旁,两个个性执拗的人情绪紧绷。男人用手杖抽打着铁路边的青芦苇,心想干脆向这个他恨之入骨的女人求婚算了。恰在此时,一辆列车通过,轰鸣声持续了很久,待最后一节车厢过去之后,男人可以说话了,他说的是:“日本的火车也不赖哦。”
镰仓的夜晚有海水的味道,但似乎海水的味道也太过浓烈了。我们一行人向酒店借了自行车,先是骑到附近的烤肉店吃了一顿,然后准备就近找一个7-11,买一些牛奶鸡蛋三明治什么的,当明天的早点。
由谷歌地图导航,骑车穿行在静谧的镰仓小巷之中,路灯昏黑,周遭无人,一栋栋小房子在小巷的两边趴伏着,有灯光在窗帘的后面,但没有一点声音泄出来。我们五个人,一个尾随一个,似乎发了狂,骑得飞快,遇到一个巷口的转弯也不减速,豁出去一般的扑来转去。那是一种难以辨识的心情,又疯狂又冷静。
谷崎润一郎在其《痴人之爱》中,曾经有一段关于镰仓夏夜的描述
海岸边夜间的空气使我感到那么柔和,清爽。这一感觉并非只有这天晚上才有,不过今天傍晚这儿下过一场阵雨,湿淋淋的草叶和雨露滴落的松树枝头静静弥漫而起的水蒸气,令人感受到沁人肺腑的潮湿的香味儿。不时有闪亮的水塘映入眼帘,沙子路已经平了,十分干净,不见一点灰尘扬起。就像踏在平整泥地上一样,人力车夫的脚步轻轻啪啪地落在地面上。一家别墅的铝塑围墙里传来留声机中的音乐声,有一两个身穿白色浴衣的人影在来回走动,一派置身于避暑胜地的真切心情油然而生。
《痴人之爱》是谷崎润一郎早年“西洋崇拜”阶段的代表作,取材于他的个人生活。在这本小说中,那种陷入“爱情”(其实就是单纯的情欲)后的荒唐和屈辱感,相当浓烈,跟镰仓夏夜的静谧似乎不匹配。不过就深浓的夜色而言,倒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在镰仓的夏夜,我好像并没有闻到海水的腥味之外的气味,至少,肯定没有闻到松树的香味,也没有看到水塘。但经过路边的一道花墙,枝叶和不知名的白色小碎花探向路中间,在路灯照耀下,有水光盈盈的感觉。我低头伏肩,继续猛蹬自行车,冲了过去。
这一趟骑行中唯一的停留,就是在平交道回望火车的时候,不知道具体有多长时间。从平交道撤回目光,往前看,伊北坐在车凳上,单脚点地,在不远处等着。
他背对着我们,朝前面看着。前面是轮廓森然的房屋和昏黄的街道。他对平交道估计没有什么兴趣,也许小街小巷之间温吞墨汁一般的夜色更对他的胃口。我和他多次一同旅行,在我因某个对象停留下来时,他总是在一边静静地等着,从不催促。偶尔能够遇到他也同时感兴趣的对象,但这种时候不多。旅行途中,他像平时一样,话很少,也很少拍照,他就是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不太容易被触动,或者也可以说是触点很高。这一点,好像跟我也很像,我在旅途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情绪高涨的人,即便心境是愉快的,情绪也依旧沉静。此时的伊北,整个人正好被笼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之下,那个背影看上去,就是愉快而沉静的。
雨中赶往圆觉寺
那天下午,我们在雨中赶往圆觉寺。
时间有点紧了,我们租的这辆车,必须在晚上八点以前开至成田机场归还。圆觉寺的茶庵似乎很有名,之前看过有人写在圆觉寺临高喝茶的美妙滋味。但我们没有时间喝茶了,于是直奔目标——圆觉寺的墓园。
我在入口处找了一张纸,写下我要找的墓主的名字,给工作人员看,让他们给予明确的指示,免得我们在依山而建的偌大寺庙里迷失方向。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走错了一个路口,爬上了另一个坡顶。坡顶是一处茶庵,风景甚佳,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享受了。
终于找到寺庙的墓园,意外地相当有规模。赶紧请同行的人帮我一起找,我说,墓碑上没有名字,就一个字:“无”。
过了一会儿,郭医生轻声招呼道:“找到了,在这儿。”
墓园里再没有其他人,就我们几个。天色清灰,雨丝中有白亮的光芒。
我已经扔掉了雨伞,汗水仿佛比雨水更加急促。来到“无”字墓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小津安二郎先生的墓,而我这么匆忙且狼狈,跟他的淡定从容多不匹配啊。但这次到镰仓,我必须要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墓前,献上我的敬意。
我对电影的理解依靠某种顿悟,这种顿悟又延伸到其他方面的阅读之中,进而有所得,这些收获,很多都是来自小津安二郎。我的个人阅读史中一直都有一些要用粗体字标明重点的名字,“小津安二郎”是其中字号很大很显眼的一个。在欣赏他的作品之前,我已经看过很多电影了,脑子里充塞了很多似乎很“有趣”的东西,但这些“有趣”很难触底。不能触底的东西就飘忽,就虚浮,就不结实。我是通过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这个路径走向小津的,先是看了文德斯的记录片《寻找小津》,然后才开始一部接一部地看起小津安二郎。
最早知道“无”字墓碑,就是因为在《寻找小津》里面看到。
熟悉小津电影的人,都知道他的两个御用演员,一位是原节子,一位是笠智众。1983年,笠智众带着文德斯来到圆觉寺小津的墓前。在那个影像中,墓前供奉着白色和紫色的菊花,还有一个浅绿色的茶杯。
笠智众那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他说,他是在拍小津的电影过程中学会了忘我,并在小津精准有序、井井有条的工作风格中得到了训练。他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然后把角色描绘在这张白纸上面。他只想成为小津笔下的一抹淡彩。笠智众说,虽然他自己只比小津小一岁,但在精神上,小津更像是他的父亲。
在记录片里,从圆觉寺下来,在北镰仓的车站,笠智众被几个中年女观众认出,要求合影。文德斯以为这是小津电影的影响使然,后来才知道,笠智众之所以被认出,其实是因为他刚刚在一部电视连续剧里出演了一个角色。至于小津的电影以及笠智众在其中所饰演的那些父亲角色,没人记得。
在《寻找小津》里,文德斯还采访了小津的摄像。摄像用小津拍摄最后一部影片《秋刀鱼之味》的摄像机(50mm,小津只用这种摄像机),为文德斯演绎小津在室内拍摄时的场景。摄像机被放得位置非常低,直接搁在榻榻米上面,就是人们坐着看出去的视线。这是拍摄中景的位置;如果要拍摄近景或特写,就会把摄影机向上倾斜,或者垫高一些,以免图像扭曲变形。
固定焦距,固定机位,这台摄像机像是入了定一般。
在访谈的最后,摄像潸然泪下,他告诉文德斯,世界上没有小津,他感到很孤独。他说,小津不仅仅是一个导演,而是一个国王,小津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带走了某种精神上很根本的东西。
记录片里的这一段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后,另一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悲伤还是那么的浓重。现在,我离文德斯的这些画面又有了三十四年的距离了,对着在雨中显得更为凝重的“无”字墓碑,我也很想深究一下,在此安眠的这位令人敬重的先生,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怎样亲密的孤独的存在。我很想去摸一下那个“无”字,但最终还是没有。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