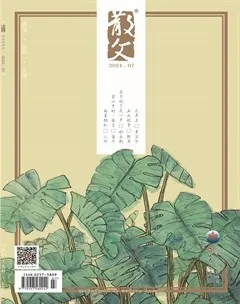独角
整个屋子空荡荡的,里里外外,一个人都没有,就连几乎整日形影不离、从不舍得将他一个人丢下的老外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大人们呢,他们都去了哪儿?大约是下地去了,要么是上山打柴去了,也有可能是赶集去了,大人们总有要忙的事。
总是追逐打闹不休的表兄弟表姐妹们呢,他们怎么也都不见了踪影?为什么只剩下他一个?回忆是那么的深,深不见底,就像一口幽深的井,即使头顶着炽烈的阳光,从井口望下去,依然是黑咕隆咚一片,除了水面晃荡的影影绰绰,什么都看不清。
这是一个突兀的场景,这个场景之前如何开端,之后如何结束?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追踪,如同某部电影里某个不完整的片段。这是一段被记忆剪辑过的、貌似毫无意义的电影片段。
记忆总是如此的难以捉摸,许多时候,它并不受控于我们,它会说不清道不明地存档着一些漫不经心的片段,却将人生一些重要的数据删除,格式化,再也无从恢复。
所有的原因必会导致一个结果,所有的结果都能够追溯到一个缘由。而所有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或者目的。为何记忆要这般剪辑,为何这些数据会在人生的记忆中一再地显现?它们必定是在人生中正在或将会起着某种不容忽视的作用,必定是在提示着什么。
屋子里幽暗昏昧,虽然时当正午,外头阳光白炽炽的,但从房顶的两三片明瓦、竹筋草泥糊就的四壁穿漏的破洞处投射进屋内的光柱,并不足以将屋子照亮。他踞坐在灶边的蒲墩上望着火塘,火塘里的火灰还有未褪尽的余温,灰堆里还有明灭着的火星。烟火一日复一日从灶膛里蹿吐出舌头来,先是将灶台边的墙壁舔黑,接着像苔藓一样,朝四面房壁、屋顶的瓦片慢慢蔓延开去。年深月久,殃及屋内的所有什物:竹条碗柜、米缸、水缸、搭向阁楼的木梯、风车、笸箩、预先置备的寿材、架床、蚊帐、棉被。年复一年,那些苔藓一层又一层冒发,一层又一层覆盖,厚黑如漆。射进屋内的明晃晃的阳光被那些黑吞噬、销蚀,它们不愿阳光在它们的地盘绽放,不愿事物在时光里新鲜明亮。
从矩形的明瓦和四壁无数不规则破洞里垂直或者倾斜着射进屋里来的阳光,落在地上,无一不执拗地呈现出浑圆的光斑。那些光柱也是浑圆的,且是笔直的,像一杆杆长枪,扎在屋子的五脏六腑,也扎透了他的五脏六腑,在他心上,开出一扇忽闪忽闪的天窗。
并不是所有的光柱都落在了地上,一些光柱落在了墙壁,一些落在灶台,一些落在水缸,一些落在搭向二楼的木梯上,一些甚至穿透碗柜,让躲藏在碗柜里木讷不语的粗瓷大碗迸射出数道刺眼的箭。还有一两个,径直落在了他的膝头。他张开手,将掌心承住一片亮,怔怔地望着。这个世界一些前所未见的秘密在他的人生中首次展现,将他一时间推入恍惚:那些轻薄、温热的光,在屋内的幽晦中开凿出一道道亮堂通透的隧道,他现在看见,隧道里并非只有光,里面悬浮游走着许多披着亮袍的细微之物。人们通常把它们唤作灰尘,或者飞尘、粉尘,然后不容分说依据字面将它们判定为无生命之物。可是,谁知道呢!我们或许不应该这么草率。这些细微之物,虽然也许不具有生命属性,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它们必无灵性。较之于生命,灵性的维度是要高出许多的。这些细微的尘芥,一直隐形匿迹于你我身边的广袤虚空,与你我朝夕与共,却从不故意彰显身形,为你我所觉知。现在,它们从虚空的暗处飘游过来,撞见了光,在他眼前示现曼妙的舞姿,轻盈、优雅,像追光里跳着芭蕾的舞者。这些舞者,旁若无人,兀自将它们轻盈的足尖跳跃、滑步、旋转,在舞台上摩擦出轻微的振荡,一圈又一圈,一阵又一阵,悄静无声,不可言说。
时隔多年,他依然会不时回顾当时情境,彼时彼刻,究竟谁是舞者?谁是自己?谁是微尘?谁是舞台?又是谁,安排了冥冥时空中的这场遭遇?
那些飘飞如仙的舞者,只在光柱中显现了一时片刻,便又消隐于光的边缘。昏暗的空间衬得光柱愈发明媚,疏密的光柱却使昏暗的虚空愈加冥魅,忽明忽暗的光影、若隐若现的舞者,将周遭的一切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之中。他忽然意识到,长久以来,它们早已于暗处悄然观察着我们,既然我们不屑,它们便也不想为我们所认识,不愿意与我们打交道,而只愿意向光袒露。多年以后,当他知晓,我们不过是更为巨大的时空中的一粒粒尘埃,这让他重新拾起敬畏之心,那些看似了无生气的卑微的事物,很难说不是某些精灵或者精魂的附着体。在人短暂的一生中,有限的感知与认知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世界时空,与你我平行、交错,虽朝夕与共却从不为你我所知,从不为你我所察?
屋子里好安静啊,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安静极了,什么声响都没有。平日里猫在瓦面上蹑手蹑脚的行走、狗向着阴暗处莫名的示威、鸡鸭们的喋喋不休、匿身于某片木板或竹片隐秘处的天牛幼虫咯吱咯吱的咀嚼、风穿过墙壁破洞的呜咽,以及随风吹来的鸟唣,所有这些声音都消失不见。可是,这么说也不对。分明还有一个声音,唯一余存着的声音,嗡——像一根针,轻细、柔韧、绵长不绝。他不能确定这是声音,因为他寻找不出它的来处。可是,他也不能确定这不是声音,因为耳蜗深处分明有声响在回旋。莫非,这是时间的声音吗?时间是像风一样滑过,还是像水一样奔流?无论如何,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声音,时间也是。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声音——低至极点的声音。
无边的空寂里,弥漫着另一些同样是隐形的事物,是的,它们是一些被称为味道的东西。屋子里总是少不了味道的,灶灰的温暾、猪潲的酸馊、玉米糊的黏腻、水缸周围的潮气,它们现在在屋子里弥散开来,慢慢地将平日里习以为常的存在凸显出来。记忆便是在当日此时,将它们捕捉,转变为数据,存储为一个个文件夹,牢牢占据着C盘内的一角。
嗯,灶台边上那些用来引火的松针的味道真好闻啊,它们似乎具有某种清洁的功效,让被它浸泡、清洗的东西都变得干净、清新、舒畅、愉悦。并不止于松针,向阳墙边堆叠晾晒着的一捆捆大人们从山上打回来的柴草,也具有同样的功效。玉米秸、竹鞭、蕨草、芒萁、雀梅、桃金娘、樟树枝、扫帚棕、八角枝以及不知名的杂草杂木,它们在日光的熏烤下释放出个性分明的体味,那些浓烈的、极具穿透的气味穿透竹骨泥糊的屋壁,穿透他的梦境,穿透一切,在时光里周游、飘荡。
人生中许多疑问即使想破头也并不一定会当即获得正解,答案也许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渐渐明朗:这些貌似漫不经心的记忆,汇集于人生的根部,生成细密的须根,默不作声,却暗中引导着,或者毋宁说是控制着他,有选择地滤取生命中某些至关重要的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左右了他的体格、高度、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人生走向,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今天把它们叙述成文字。
譬如一条河流,始于源头的清澈活水,流过山川,流过长长的岁月,来到中游,去到下游,难免泥沙俱下,被一些沟渠污染、毒害,但只要源头能够保持洁净,总还是能够发挥正本清源的功效。
至于那些青草汁、松树林、樟树枝、石头、泥土,甚至牲畜的屎尿味,则像中药,在人漫漫的一生中,时时起着扶正祛邪的效用。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