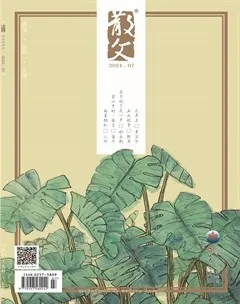痛吻
见到一个少闻的国际节日,说“7月6日是国际接吻日”。此节日最初由英国人发起,二十年前就得到联合国批准,一些国家在这天专门设立亲吻区,当日区域内可狂吻陌生人。
人性亘古不变,但古时礼教枷锁横档,男女大防沁入骨髓,由是,虽说记载中有“接吻的历史已有三千年”(我对此表示怀疑,自人类诞生起,接吻当是亲昵之本能,表达爱意的一种天然方式),但在我有限的古典文学阅读里,未能直接见到“亲吻”“接吻”“吻别”之类的词。有若干诗词句子,也只是提及“吻”这个字,状态的描摹闪烁其词,如左思《娇女诗》有“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杜牧有“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卢仝《月蚀诗》写“须臾痴蟆精,两吻自决坼”,明面上写的“两(再)吻”,却是以“痴情于蛤蟆精,两吻诀别”来借喻。
语言文字再怎么渲染气氛、揭示场景,关于“接吻”,还是一图胜千言。中国画,哪怕是写意的“接吻”,对视觉来说,也较文字描述直接得多,写实得多,在照相术发明之前,那就是“下真人真物一等”了。多年披观古代流传下来的人物画,何啻千百,但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幅有画男女“接吻”场面的。也许春宫画里有,但我未曾看过,想如有,也是粗暴的“死磕”。花鸟走兽,盘点迄今所见者,也只两幅,均为清代之作:八大山人所绘的纸本墨笔《松树双鹿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任伯年所画纸本设色之《荷花双鸭图》(现藏中国美术馆)。《松树双鹿图》是八大山人晚年之作,图绘一角山崖,崖边上一株古松遒然挺立,崖下一公一母两只梅花鹿亲密地偎在一起。远处背景中山崖和苍松画面疏淡,笔墨劲简,近景处的双鹿则以淡墨着笔。外侧犄角雄健的公鹿于站立中做回首状,而内侧的母鹿墨色更淡,接近画幅底色,以缠绕公鹿的形态与公鹿亲昵,情深状貌跃然纸上。
相对来说,任伯年四十四岁即1884年所作的《荷花双鸭图》,画面就比较宁静、温馨,像他要描绘的一个梦。宽大的荷花,真似遮风挡雨的屋子。忠贞双鸭,在无风也无浪的轻轻、清清水面上,交合双喙,算是一种爱意表达的“接吻”。文化喻义“附会”而言,水代表着财运,有了丰沛的经济,一对佳人生活才有保障乃至充裕;“鸭子”“莲花”出现在水里,一个代表生机,一个代表干净,也可视为“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干净钱财”之冀望与彩头。
这两幅“吻画”,从用笔用墨技艺来说,还是较传统,与同时代画家类比,题材并没有什么突破;和画家自己同一时期的创作比较,也似乎大同小异。但说是惊雷炸响,就在于他们“敢于”这样画,这种艺术表现的突破,无论他们个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窃以为总是有些“石破天惊”的味道。遗憾的是,无论八大山人还是任伯年,艺术史家在论述他们的创作时,似乎都没有对这两幅画予以特别的留意;一览之下,他们平素善于检索、鉴赏的眼光,都未对这别样之作“高看一眼”或“特别垂青”。
吻是伴侣间表达浓情蜜意的一种自然体现。虽然是不同时期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清初,一幅是近现代,但目睹这两幅“吻画”,由不得你不去探寻这画面背后创作者的身世、情感经历,特别是有关其“另一半”的信息。他这幅画,是否献给了她?传递着怎样的一时难用文字或口头说出的情愫,而选择以视觉语言“传吾意”?
诗人、作家、画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肉体凡胎,有着人所共通的七情六欲。苏东坡与王朝云、赵明诚与李清照、黄道周与蔡玉卿……前朝留下来的爱恋、灵魂伴侣故事,在笔墨流泻纸楮之前,也一定萦回于他们的心间脑际。但翻册检籍,对于身世飘零的八大,神龙难全首尾见,我们并未发现这位孤苦者有哪位佳人、恋人、情人或夫人为之红袖添香。他笔下的这对野鹿,是某种情感记录的物化留痕,还是更为强调生存的艰难、运命的遭际?山崖之中,公母鹿相依相靠,时刻处于饥馑、危险、忧患与恐惧之中。前些年,我在“读艺小札”中写下如是惊见的感受:
即便是在亲吻,雄鹿仍警觉地察看着四围可能的异动、危机——这多像现代人的生存,孤独、焦虑、紧张、幽僻……一如当下疫情中,每一个个体的焦灼、慌张、恍惚、惶恐、撕裂。
即便“情深而对吻”,但仔细品咂公鹿那以唇相抵中的眼神,仍能分明感受到满是警觉,空气紧张、滞重乃至凝固,隐隐透露出命运的莫测与不安全感,连这最温情、亲密的时光,也被一种沉闷而危险的气氛笼罩。
或许世人都能在此图画中,看到自己。
由是,此画面与其说是双鹿在山野亲吻,不如说是两个个体在彼此生命历程中的短暂交集与相互抚慰。也许下一秒,它们就因故分离,如花朵坠落悬崖,血瓣绽开,复归于寂灭。
古典画图的现代性乃至先锋性,八大此图,可为一证。
几年前,一部名为《八大山人》的电影,说是依据一幅《个山小像》,虚构了八大山人和“黄安平”的一段爱情故事。影片由江西作家熊相仔根据八大山人的生平资料再创作,企望“用一个天才的幻觉,诠释了八大山人是真疯还是假疯这个历史疑惑。主观的镜头再现了八大山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强烈个性,采用八大山人的留白风格留给观众诸多想象空间”。不过,整部电影看过来,笔者没有发现涉及这幅《松树双鹿图》的内容,也未能从中看出八大山人画画寄寓着“与爱情有关”。
近代以来,风气更开化,艺术家与另一半之情感生活、爱情传奇,愈见多彩,如张大千、刘海粟,包括后来对画出此帧扣喙相“吻”荷塘浮鸭的任伯年极度推崇的徐悲鸿。而任伯年呢,家中的那位夫人,则是刻薄吝啬,完全将其视作摇钱树。有这样的桥段:某日,吴昌硕拿着一幅刚画好的荷花图上门请教任伯年,任伯年提笔给吴昌硕改画,正在兴头上,任伯年的夫人突然出现,拿着一大扫把就将吴昌硕赶出门,大叫道:你快走,快走!我们画画的时间,都被你耽搁了。老婆的逼压将任氏塑成了一个劳碌命,有时候他停笔慢慢吃个饭,或者剃个头、干些其他的事,老婆就会抱怨他荒废,少挣了润笔的银子。据说任的家分为上下两层,楼上专供其创作,妻子则在楼下应付前来索画的客商。妻子常常接受大量的订单,任伯年有时不得不在一日之内画十几幅,甚至几十幅。巨大的工作量使他常常体力不支,只好靠抽鸦片提神。
在此长年累月一张又一张兑现客商画单的过程中,从未闻任伯年有过一二女弟子,或邂逅红粉佳人,以安抚他痛楚劳累的灵魂。1896年,五十六岁的任伯年病逝于上海。死之前,为尽男人的责任,为妻子儿女日后生活有个来源,他取出一辈子的积蓄请表姐夫去绍兴帮忙购田。表姐夫乃一赌棍,将任氏的购田款全部输光,用一张假田契欺骗他,直待病入膏肓时任伯年才得知实情。
就八大和任伯年而言,尽管他们在笔下创新而大胆地表现了“吻”,我仍深觉泰戈尔的一句“生命报我以痛吻,我却回报以歌吟”才是他们生命的切近写照。八大痛苦一生,任氏虽有生活伴侣,却是催命妇,困顿、流离、辛酸、愁苦……命运给了他们“痛吻”,他们仍以超常的绘画膂力,在坚忍中,不屈不挠地释放自由意志,高扬超凡的生命力。他们“从死亡中看到梦境,从日落看到痛苦的黄金”,将“诅咒变成了葡萄园”,让笔墨绽放成艺术的花朵、时间的瑰宝。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