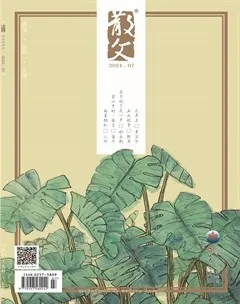小酒馆
那是你吗?
我寻声望过去,在遥远的边地,一个孤旷的小镇,一家干打垒小馆,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两盘小菜,一壶酒。他看上去眼神游离,心里不踏实,品咂着酒,挥发颓意,怎么看都是一个无法融入当地的局外人。是我,羁旅在外,过路此地的一个出差人。
“天哪,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这是在江南,嫩凉天气,淡烟轻雨,饱览了大好的风景,伴着黄昏的细雨走进小吃一条街,又莫名地惆怅。忽听有人喊名字,扭头一看——“嘿,这也太巧了吧?”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奇遇他乡,吊着膀子走进一家小酒馆,相谈甚欢。
难以入眠的夜,我时常在记忆中寻找小酒馆。它们已然遥远、模糊,好似埋在雾中的一个又一个小岛。是想喝酒了,还是怀旧?最初,我找不到缘由。
去年的落叶季,在公交车站牌边,我等车去医院种牙,接到战友电话,得知另一战友不久于人世,那一刻的感觉是:多一颗牙少一颗牙还重要吗?憾怨关山遥迢,无法回老家探视战友。转眼枝吐新芽,战友又来电话,啜泣,说起前前后后的事,一个细节令人泪出——战友故去的当天,走步群里显示他走了九步,另一友人马上送去鼓励,@他:祝贺!
九步,让人百感交集的九步,又触动了存续于大脑的渴念,能将这个渴念转化为情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现实世界,随便到一个地方,街边、小巷里,还有可以逛街般漫步的商厦内,手机导航都可以很快为你找到一家属意的餐馆。但对于像我这种退休后旅居异地的人来说,地域限制,年纪也要考虑,即便渴念奔现,大多是四字结局——来去匆匆。
去小酒馆就是要喝酒,酒能让人敞开心扉。一个男人在度过童年、少年时代之后,迟早要学会喝酒,这条“社会定律”可以套牢我辈大部分男人。我常将生平第一次喝酒的经历拎出来调侃。十九岁下乡,同宿舍的同学互助,帮我在林场给家里打了一车烧柴,用母亲单位的福利车拉回县城。家里招待同学由父亲陪,按家规我上不了桌。同学趁父亲下桌的空当倒了小半碗酒,白酒加汽水,逼我喝。我一饮而尽,等醒来时,发现自己伏在后窗台上,窗外是一片小菜园,几只鸡正在窗台下面扒来扒去。后来去沈阳读书,逢中国足球首次跻身奥运会,与几名同学吃夜宵庆贺,归来时将路灯下滚动的纸盒当球踢,一脚踢飞了一只新皮鞋的后跟,半个月生活费踢没了,再无觅处。
这样的糗事往往会成为多年后另一个小酒馆里的笑谈。转眼,几十年过来了,围桌同酌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家人,星散四方,去过的那么多小酒馆也淡出了脑海。即便重回旧地,今已非昨,小酒馆遍布大街小巷,再也找不到从前的那一个。带着这样厚重的履历再入小酒馆,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呼朋唤友,喧哗,吵闹,使酒骂座,喝到最后定要人扶。再不会发生不虞之事,只有感今追昔,借酒回味——年轻的时候总在想,日后的自己会比早前的自己更……更……全部是美好的憧憬,换一套大房子,谋一个舒适的位置,得一个什么样的大奖。依次抵达早前期待的一个个“日后”,得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暗示:前方将会有比失落、懊悔、伤感、疾病更多的东西等着你。年轻时总是不确定明天会有多么美好,所以一直盼着惊喜,等着奇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处现在也总会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是你吗?
一座四线城市,一家大医院。从母亲的病床边离开,你走进街边的一家小酒馆。饺子酒,你打算吃饱喝足后回到小旅店里好好地睡一觉,解解乏。饺子端上来,酒杯斟满,想起母亲的一句话:少年不知膝盖贵,老来走路痛掉泪。于是,与你结成母与子关系的那个人占据了你的大脑,一幕又一幕的往事让你陷情其中,迟迟没有动筷。老板娘看见你好像低头在与对面的一个虚拟人说话,推心置腹,还以为你精神有问题。饺子和酒壶渐凉,你还坐在那里一动未动,直至眼里噙泪,掩面离开。老板娘哪里知道你刚才想起了一句诗——此时有子不如无。
完全记不得这家小酒馆的模样。精致?简陋?只知道天下所有的小酒馆都不负责为顾客提供孤独、惆怅、忧伤类的精神产品,这一切均须由你自带。
“怎么忘了拍个照留念?”她发来一条微信。
她和我是作家班同学,疫情前我在群里得知她在北京,遂找了个地方,约了两位在京的下班同学与她小聚。多年不见的同学见了面,没觉得老到哪里去。她母亲是老北京,九十多岁了,她则工作生活在大连,与姐姐轮流照料母亲。疫情拖棚,三年时间里最犯讳的事情就是走动,很可能会产生麻烦的后果,所以她来去北京也没再声张。突然放开了,亦喜亦悲。在放开一段时间后,我收到她发来的微信,约个时间吃个饭。我隐约感觉她年近百岁的老母亲这次走了。这样大的事,她也没叫外人,已经将母亲的后事妥善安排完,准备返回大连。
餐后,见到她发来的微信时,我已离开几分钟,在车上。
我回她:“下次。”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下次。”只有文字,看不见她的表情。
我说什么好呢?“一定会的。”
“好,借你吉言。”她回。
人与车在街上川流不息,我大脑里呈现出大海涨潮退潮的画面,想的是人的退化。每一个失眠之夜,往事都会像海潮一样涌上我的心岸。早上醒来,海潮退回大海,望着朝气蓬勃的大海,我茫然,再也找不到昨夜纷纷上岸来到你脚下、俯身可掬在手中的潮水,不知退去的潮水会不会再次涌现在自己面前。这次小聚,我发现自己在退化,具体表现就是喝了玉米露而没有喝酒,这在我的小酒馆经历中尚属首次。此前的某天夜里,我左臂突然发麻几分钟,接着去看急诊,医生和家人告诫我要管控心脑血管疾病。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或已开始走下坡路,无可返回,只能一路下行,如果还可以找一句成语安慰自己,那就是:不负当下!
立秋后,我又赴延庆北张庄一家民宿与朋友聚会。八月下旬的北京依然是炎蒸天气,地处盆地的北张庄则像开了空调,凉爽宜人。这是我旅京后第一次做客京郊农家。一大桌友朋中有一红衣老兄,据说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介绍到谁他皆谦蔼地抱拳与点头。酒过三巡,他开始上话,谁说话他都能自然而然地接过去,纳入他的频道,开始长篇叙述。他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对,都是好观点、好理论,只是早被大众听腻,于是有人打断他,调侃他“上下五千年”。他还是停不下来,后来无论说什么也没人听了,邻桌之间展开私聊,他频频四顾再也插不上话,不知什么时候退了席,再未回桌。
认识红衣老兄约等于让我照了一次镜子,得到一个善意的提醒。人老了,话多,急于将自己的经历展示出来,把见识告诉别人,说着说着,就进入“吹嘘自己、贬低别人”的模式,遭人嫌弃自己还认识不到。我提醒自己,虽还未七老八十,但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没必要总在人前刷存在感。聚会,最好是小众,三两好友,一张小桌,席间你一句,我一句,他再添两句,你来我往,把一次聚会黏缀成一个故事。非要滔滔不绝,最好转入内心世界,内心是独白的天堂,自己与自己交谈,不失为一种修行。
去内心找一家小酒馆吧,这是我对自己发出的倡议。我也试过聊天工具,但怎么也找不到小酒馆的氛围,网络虚拟不出老友见面的喜悦,层出不穷的表情包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人的真情实感。在人的世界里,有什么能抵得上一个“真”字?岁月衰老了一张脸,内心却越来越丰富,这一点年轻人恐怕还是比不了。年轻,意味着有大把的时间去接受迎面而来的人生;年老,思力滞钝,可以在内心建起一个小酒馆,从中享受慢生活。
夜渐深,在大街上奔走一天跑累了的大小汽车像鸟一样归了巢,白日里片刻不停的轮胎碾轧沥青的转动渐息,我也回到影影绰绰的记忆中,找到一家隐藏在时光深处的小酒馆,与往事一醉方休。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