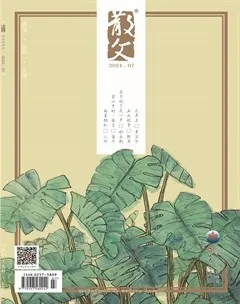旧梦连环·汪集
从心所欲,不逾矩
《受戒》显然是汪曾祺的心爱之作,他的自选集就以此为书名。要问这个小说写的是什么——当然,最好还是不要这么问——他也会回答你:“我写了人性的解放。”简明的答案反而煞风景,其实他已经把什么都写在小说里了。
早些年,我也不知道汪曾祺在写什么,我只是爱读。《受戒》的核心,是小和尚明子和小姑娘小英子的朦胧爱情,但我更喜欢的是其他闲笔,或旁衬:荸荠庵的事、庵赵庄的事、英子家的事;念经、拜忏、放焰口;插秧、薅草、割稻子。庵里三师父仁渡唱的一段安徽小调,别有意味: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每次看这段我都要笑,这词有种说不出的幽默,三个人都有份:安徽山里人的原创、仁渡和尚的戏谑,以及汪曾祺的白描。啥事情“讲得听不得”?一个姐儿一个小郎,还有啥了不得的大事,天下人同此心罢了。这歌子的态度无比正确:“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人之常情,顺其自然。汪曾祺的写法就是自然而然,这境界他走过了几十年山水才抵达。
四川画家张晓红创作的连环画《受戒》1994年发表于《连环画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连环画已式微,难得这作品峻拔明丽,很好地呼应了汪老的原作。因是刊物发表,图幅安排得有大有小,以凸显某些重点画面,同时让版面错落好看。倘若交给我,我也会选几幅放大。比如英子家日子过得很兴旺,怎么表现?她家有田,本来够吃了,又租种了庵上十亩田,更是有余,这“有吃”没有画,画的是“有穿”——画上赵大娘正给大英子试一件衣裳,帮她扣扣子;大英子面露喜色,小英子在她面前屈膝半蹲,举着面镜子给姐姐照;她身后站着她爹,也是喜笑颜开,看着女儿试衣服。这情景好喜气,不仅画出了日子兴旺,还刻画了英子一家人的形象,爹结实,娘精神,真合了汪曾祺的描写:娘女三个,“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格挣挣”是苏北方言,我们能意会理解,就是光鲜,齐整得见棱见角。同时,这幅画还照应了大英子已有了人家,在准备嫁妆的后文。
“明子没事常找小英子玩”,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英子家像个小岛,三面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荸荠庵,明子就从这条路过来找她。原作中说岛上种了桑树,画家依靠想象,在此画了两棵大柳树。正是春天,杨柳枝漫天飘拂,明子和小英子各自手里拿着根柳枝,嬉闹追打。面朝我们的是小英子,背对我们的是明子,他俩还是十几岁,两小无猜,竹马青梅,这春意盎然的图景,与他们多么配衬哪!
小英子是个非常活泼的少女,从她弓身给姐姐照镜子的姿态就可看出来。大英子的衣裳,深色的花朵,小英子的衣裳,浅色的小点,对比明显,但比衣裳更明显的,是姿态——大英子背着柴草进门,小英子正要牵牛出门,看张开的胳臂就知道是她,这个咋呼劲儿!有三幅连续的画面,是姐姐发愁没有好的绣花样子,妹妹把明子保举了来——她推他、搡他到桌前,他坐下拿起笔描花样子。这三幅图都以四方桌、靠背椅、长条凳为道具,辅以一只黑母鸡带着几只鸡娃在桌边觅食为帮腔,角度变换,桌椅的位置也有变化,而在明子画画的第三幅里,小英子的姿态突然安静了。画面的取景使她正面对着我们,她低着头,凝神屏息,看明子落笔,她的神态真美,双手也服帖在身侧,桌下的两只脚也收拢了。
英子和明子一起插秧的图画我也喜欢,田里的秧苗整整齐齐,横平竖直,他插得比她快,多出两行,缺出的一小方块她正在弯腰补齐。■荸荠是她最爱干的活儿,光脚在滑溜溜的泥里踩着,顺便踩明子的脚。她挎着一篮子荸荠走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左、右、左、右,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小和尚的心乱了。心乱不容易画,能画的,是那一串美丽的脚印。
前面,描绘三师父仁渡飞铙的画幅,我觉得可以画得更加张扬。仁渡聪明能干,经忏俱通,能拉会唱,飞铙是他的绝技。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旋转,再以各种漂亮的姿势接住,“犀牛望月”“苏秦背剑”……想象一下那潇洒的炫技,画面可以尽情放飞,而不必画好些个和尚围在身边,使他不得施展。仁渡是有相好的,但同时又是规规矩矩的,并不乱来。庵里二师父也是有家眷的,叫嫂子或师娘。庵里没有清规,早上睡到自然醒,起来扫扫地、念念经、挑水、喂猪,有法事就做法事,无事就打牌,过年杀猪,平时也吃肉。
在这个地方,当和尚是一门营生。明子小时候,爹娘送他去当和尚,他的和尚舅舅让他喊一嗓子试试,听后连连称赞:“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画上的小明子,挺胸凸肚,张大了嘴巴喊号子:“格当嘚——”颇为憨态可掬。与此相照应,后面明子真的当和尚了,舅舅教他念经,他一个胖大汉也是同一个模子的口型和姿势,令人忍俊不禁。
明子是听安排听调教的。他爹送他去学堂,爷儿俩脚步姿势一式一样,他在前爹在后,朝右;舅舅带他去当和尚,甥舅俩脚步姿势也一式一样,舅在前甥在后,朝左。这两幅图对见,有意思。
明子和小英子一起玩着就长大了。英子在田里薅草,秧很高,看不见人,就听见她脆亮的嗓子在里面唱。明子的嗓子更了得,打场时喊号子,一声“格当嘚——”九转十三弯,英子在家里对全家竖起大拇指:“听,一十三省数第一!”这话说得漂亮,手势也漂亮,这一对小人儿,着实般配!
明子要受戒了。烧戒疤,当沙弥尾,将来好当方丈。但是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明子说。她忽然趴在他耳朵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这个小姑娘啊。最后几幅图,她划船来接明子,头发跟平常一样绾个髻,不知怎么有点像个小媳妇的样子,其实“当老婆”是什么意思,她还不一定明白呢。以她的想法,大约就是爹和娘的样子,就是姐姐要出阁嫁人的光景,就是两个人一起过一辈子的意思。反正眼前这个小子,是她喜欢的,他也喜欢她,她是知道的。
两个人并排划船,低语,耳语。连续的几幅划船图,两人的神情都在背影上,她左一划,他右一划。“嗯。”“‘嗯’什么呀?要不要?”“要!”“你喊什么!快点划!”她羞涩地低了头,小船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吐穗了,有的结了蒲棒。最后一幅图画的是芦花荡,部分留白,未曾点染之处是水面和天空,一只水鸟惊飞起来。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写的,也许有意味,也许无,以景收束。
汪曾祺在小说后附笔:“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写这个小说时他六十岁了,他笔下的明子和小英子,只是纯真、本真,其间的分寸拿捏得恰好,增一分减一分都错了火候。不过,主线之外,我还是更喜欢他用笔的“乱孱”,这是大英子嘴里说的绣花针法,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由浅入深,不露痕迹。他信笔乱孱,而笔笔都在章法中,笔笔有用,组织严密,散而不乱。文章,不经过年轻时的紧张严密,便不能够抵达年老时的松弛周致。
春如线
《大淖记事》里记的事,不只是巧云和十一子。全文分六节,前三节都在写大淖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乡风民生,后一半篇幅才写巧云和十一子的恋爱故事,与此地风俗相互映照,彼此烘托,风俗之于故事如同彩云托月。所谓风俗小说,此为最。
1983年,我从《连环画报》上看熟了《大淖记事》。这个连环画版本,改编与绘画都深得原作精髓。若干年后我会发现,画家下了好大的功夫,特意设计了一个题图,由八幅小画拼成一个方形,围绕着中间的题目“大淖记事”,脱离文字脚本成为一个独立画幅。这八幅小画分别选取大淖风物中的某个物象来描绘,对照小说细读,它们都是文中描写过的——
屋顶的一角,茅草盖顶,压着半片破缸瓦瓮,防止大风把茅草刮走;
烧饭的“锅腔子”,是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柴,因无处出烟,烟就横溢出来,飘在河面上;
小食摊,摊贩敲着梆子,卖馄饨、饺面;
锡匠担子,一头是风箱,一头是炭炉和方砖;
锡质器具,这地方兴用锡器,尤其给女儿的嫁妆中必有这样一对精美的大锡罐;
大淖姑娘的发髻,一侧插着柳枝、艾叶、栀子花或夹竹桃;
挑担姑娘的箩筐,里面是荸荠、菱角、连枝藕……
这些物象是大淖的细节,也暗含着小说情节的线索。左上角的长方小幅,画了一座高塔,《大淖记事》里没有这座塔,它形似沈从文的《边城》中贯穿始终的“白塔”。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承关系,画家了然于心,故此融会贯通地将塔安置在这里,寄寓对乡土的守望。八幅小画,彼此接洽勾连,仿佛大淖风情微缩的万花筒。
正文四十九幅图,纯粹白描,最突出的是画家对线条的运用,源自传统又有创造。水是线,烟是线,房屋是线,渔网是线,柳条是线,芦苇是线,长发是线,心事更是线。线有游动,有转折,有灵性,有情意;线是虚实相生,无中生有;线勾勒出景物风俗,还原了有情世界。
大淖的乡民,世代相传,多为挑夫。描绘大淖挑夫的两幅,虽然间隔开,却是相互呼应。男挑夫们挑的是竹子,扎成捆,竹梢拖在地上,挑夫们一律向右,仰着头,迎着风,齐刷刷地走,衣襟都吹向身后;女挑夫,姑娘媳妇们,挑的是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画面掉转角度,仿佛倾斜着从她们上方俯瞰,她们一排排从画面的右上方走过来,步履婀娜,筐篮轻盈,走向下方的柳树林。这两幅画合纵连横,组合成富有韵律的动势,不输汪曾祺的文字描述:男挑夫们,要换肩的时候,打头的把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从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姑娘媳妇们挑着轻巧的鲜货,“风摆柳似的嚓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十一子是小锡匠,长得一表人才。看汪曾祺对他的描写:肩宽腰细,挺拔厮称,唇红齿白,浓眉大眼,青鞋净袜,走路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除了“浓眉大眼”稍嫌浮泛俗,其他形容都准确而不俗。画上的十一子亮相,果然一表人才,且恰好去掉了“浓眉大眼”。他正在拉琴,神态沉静,周遭那些挤过来看锡匠们吹拉弹唱的姑娘媳妇,都在偷偷地看他。他穿着对襟衫褂,身材挺拔,可以想象汪曾祺的形容:“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
世间有一种类型的美,是难以着力去达到的。普通人企盼一表人才,着力追求的结果,往往只能是“浓眉大眼”,而碰到那种清逸的线条、独特的气质,顿时落败,明白更高级的美,是一种标格,而非五官。画中十一子是这种美,画《大淖记事》的线条也有相似感觉,别出心裁,胜过工整规整。线哪,怎样落在一张白纸上呢?
仿佛也是这个道理,巧云“长成了一朵花”的着力特写,不及其他几幅更有美感——她和十一子在柳荫下做伴,他拉风箱,她织席,她织出的席蜿蜒盘成好长的卷垛,两人的心事谁也不说;巧云晚上洗衣落水,十一子扎到水底将她救起,他一手抱她,一手向上划水,两人的身体线条如此和谐。好一对鸳鸯,谁说不是呢。
他把她横抱着送回家,穿过布满画面的杨柳枝条。这画面很像多年前,巧云的爹在一株大柳树下遇到一个女子向他问路,也是漫天的杨柳枝条,将两人围绕。巧云的爹也曾是当年的十一子,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专能上高跳。这个萍水相逢的女子跟了他四年,给他留下个女儿,又跟人跑了。爹舍不得巧云受委屈,不再续娶,也舍不得巧云挑扁担,只自己一个人挑。天有不测风云,他一脚踏空从三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腰,从此只能靠在床头绩一捆又一捆女儿结网用的麻线。麻线绕成一个个的线团,蚊帐是一根根颤巍巍的线条。巧云不愿撇下爹去嫁人。
十一子横抱着巧云穿过柔软荡漾的柳枝,两人的心都被柳枝拂动。他把她安顿好就走了,在这个夜晚巧云却被另一人撬门而入占有。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是这个人呢?既不能够去杀了他,也不能跳到淖里去淹死。巧云披散着长发,呆坐。放下了菜刀,又拿起了镜子。心里乱糟糟,却突然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模样——你是多么美呀,唉!
她约十一子晚上到大淖中央的沙洲上。于是就有了原作中倾倒众生的那一句:“月亮真好啊!”图画无法表现得超过这几个字,只好如此处置——船停泊在沙洲旁,沙洲上的茅草丛很高,看不见人,只见一对鸟儿飞向天边的大圆月。
世间美到极致的事物,都会趋向残缺,现实层面,巧云是被强横之人霸占,他岂肯善罢甘休?带了人来,捆走小锡匠,将他打得奄奄一息,而他竟宁死不悔。
官府不受理诉状,锡匠们上街游行,顶香请愿。他们的锡匠担子是温和坚定的线条,他们头顶的香束是笔直庄严的线条,县衙门里齐整然而倾斜的地砖是心乱如麻的线条,四邻见证对于行凶者枉法者是压倒性的线条。那个人被驱逐了,十一子和巧云在一起了。一家三口,两个卧病,巧云找出爹用过的箩筐,出去挑担了。
画家还额外绘制了一幅彩图,用在当期画报的封面上。画分三层,上层是三个姑娘媳妇的特写,中间那个面如芙蓉又似佛像的女子,必是巧云;中间一层是几个青年男子,挑着担子前行;下层是挑担的姑娘媳妇们,发髻上插着柳枝、艾叶、栀子花,或夹竹桃……这就是大淖,民风淳美的大淖,和他们值得骄傲的年轻人!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