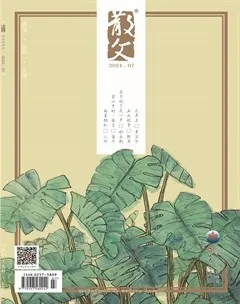读史三札
野蛮人
在《武士和女俘的故事》里,博尔赫斯讲述了伦巴底武士德罗图夫特的生平。这个本该扫荡亚平宁的野蛮人,看到罗马的宏伟城阙,禀应上苍之邀,倒戈守卫文明,他丧了命,墓碑上镌刻着他看不懂的拉丁文。博尔赫斯请读者构想一下德罗图夫特的永恒形象,他意识到这名野蛮人绝非孤案,指称那些渴望把中国变成无边牧场的蒙古人一个个手执金觞,终老于农耕世界。其实,今人已无缘窃尝德罗图夫特的神秘激情,博尔赫斯深知我们的智虑根本派不上用场,于是以各种文学譬喻再举一例——被印第安人俘获的英国女人回归野蛮——来撩拨读者迟钝的感受力。若将德罗图夫特视作纯粹的象征,将一支支南下或西进的游牧部族人格化,那么,我们会看到他在千年岁月里不断诞生与死亡,直到世界突然进化成了不同形态。
《草原帝国》将欧亚大草原与日耳曼尼亚相比,将威胁中国、波斯的突厥人与威胁罗马的哥特人相比。“正如法兰克人把自己看成是罗马传统的保卫者以反对日耳曼人新的入侵浪潮一样,拓跋氏也像前者注视莱茵河一样守卫着黄河,以对付那些来自草原故乡深处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野蛮的塞尔柱克人同样以阿拉伯波斯文化的捍卫者自视,他们并未摧灭哈里发的帝国,而是加以补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有时,蛮族的行为大大超过了既得利益者的自保防御之举。拓跋氏皇帝改汉姓,学习汉文化,强制部属与汉人通婚。对那些仍生息在蛮荒境地的堂兄弟部落,他们似乎憎恶至极,所以北伐的力度总是大于南征,经常超过必要的程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多次诛讨柔然,几乎将其屠戮、驱除殆尽。他们拥抱文明的态度或许初始时稍显迟疑,但很快就变得灼炽难匹,犹如外表矜重而内心火烫的女人投入一场热烈的恋爱。北魏对佛教的狂热,让作者想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对基督教的狂热。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的造诣优越于南朝,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因为太短命,儿子又太有名,他雄才大略而好佛的事迹方会被梁武帝所掩。今天有人想以宗教摆脱个人虚幻,或推升社会道德水准,此议可行与否且存而不论,反正历史上宗教的作用从来也不是填补空无匮乏,而是纾解过于旺盛的精力:要么将民众导向一个伟大目标,要么逐渐消磨、耗尽他们。“这些勇猛的武士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容易受到博爱教条的感动。”无论是匈奴、突厥、鲜卑还是后来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子孙,无不扑向文明的怀抱,成为半个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以致忘了自己的好战禀性。“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满族人完全中国化的日子总会到来。那时,他们要么被北方游牧部族打败,要么被中国人消解同化。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规律。”
历史无善无恶。野蛮人的血脉融入文明,蛰伏沉睡。不管是博尔赫斯笔下的英国女俘,抑或是《现代启示录》里陷入狂悖的科茨上校,他们被唤醒的野性完成了一个千百年的循环。“我讲的两个故事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博尔赫斯说,“对于上帝而言,这枚钱币的正反面是一模一样的。”文明和野蛮有时候互相破毁,有时候汇合且迸发出唐朝般闪耀经久的光彩。连接中国、波斯、罗马的商道如此艰辛,而从保加利亚到兴安岭的辽旷草原则任君驰骋。文明之路很窄,野蛮之路很宽。
生于北京,死于巴格达
1291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儿汗国,并顺道返回家乡。很多人怀疑他是否真来过中国,因为在其叙述里,惊人的详确和难以解释的讹谬交织并存。当时去波斯做生意的威尼斯人一定知道列班·扫马的大名,沿商路开设货栈的热那亚人对他更是熟悉。而马可·波罗在伊儿汗国的旧京蔑剌哈城或新京桃里寺城游荡期间,到处可见扫马的幻影。这位旅行家生长于元大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称其为“畏兀尔的奥德修斯”。他父亲是巡察使,家庭信仰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三十岁之前,扫马没想过离开北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在另一位马可的狂热鼓动下启程西行。两人携带诸王赐予的金银财物,穿过广浩的元朝疆土,穿过因长期战争而荒敝的喀什噶尔,手持海都汗颁赐的安全特许证穿过战场,穿过呼罗珊,在蔑剌哈城附近拜见了波斯的总主教。彼时伊儿汗国的两代君王,自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的兄弟、征服者旭烈兀,至扫马即将觐谒的国主阿八哈,皆袒护景教而压制别徒。实际上,旭烈兀及其继任者所统领的,是一支隐去旗号的十字军,曾联合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和叙利亚的法兰克人攻下圣城耶路撒冷。对于马可和列班·扫马的到来,阿八哈给予褒赏。然而此时耶路撒冷正处在伊斯兰的脊柱、突厥人的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之下,扫马唯有等待。
阿八哈殁后,其胞弟贴古迭儿缵继大统。阿八哈之子阿鲁浑借机发动内战,推翻叔父,践祚称王。这位伊儿汗国的第四任君主拟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结盟,击败突厥人的埃及王朝,瓜分叙利亚。揣着阿鲁浑写给教宗的信函,扫马出使欧洲,受到塞尔柱克苏丹和拜占庭皇帝的友好欢迎。在那不勒斯,他碰到一场海战。在罗马,他试图向红衣主教团剖明蒙古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性。扫马瞻仰了圣彼得教堂,赓即前往法兰西拜见金发菲利普。抵达热那亚当天,东方使者收获了全城人的致敬。他来到巴黎,不久又赶赴波尔多拜见英王爱德华一世。然而两位君主均无意与伊儿汗国组成军事联盟。扫马折回梵蒂冈教廷之际,新教皇已经选出,他亲自为特使授圣餐,让他在各种场合坐上首席。据说,这位来自北京的教士从未梦想到如此热烈的场面,以至十分满足,然而他带回伊儿汗国的消息却令阿鲁浑王大失所望。最后的日月里,列班·扫马担任过声誉崇高的宫廷牧师,并于巴格达以波斯文撰述回忆录。在那里,有个年轻人胸中燃烧着宗教热忱,用叙利亚语为老头子写了一部传记,里面充满对《圣经》泛滥的征引,以及对上帝无休止的咏赞。欲通阅其著作,读者和上帝都必须忍耐。他就是我寤寐以求的小说主人公。拉班·扫马那幽远的中国记忆,通过他的笔墨,传给了威尼斯旅行者马可·波罗。而他得救于爱情,或沉沦于永劫,他的作品在伊斯兰世界难见天日,直到六百年后,手抄本才被一名穷困潦倒的占星家重新发现。时岁流逝,列班·扫马生活过的国家历尽沧桑,因为宗教藩篱和现实政治,它们对他的故事置若罔闻。我们本可以说扫马是元朝的玄奘,伊朗人则不妨说他是波斯的伊本·白图泰。可这并没有发生,仅仅由于他生活在一个传承业已断绝的文明之中。蒙古征服者与景教徒在伊朗的统御业已倾覆,在中国亦然。在天主教世界,列班·扫马同样是消亡的异端。然而,故事和人的意志不朽,作为永恒的财富它们不会消逝。
埃丽莎的三重复仇
罗马第一作家维吉尔为何立下遗嘱,请托友人瓦留斯和图卡焚毁《埃涅阿斯纪》的手稿?很可能是因为,从整体效果来看,这部花费十几年光阴敷写的史诗巨构并没有达至维吉尔的预想,它多多少少悖逆了作家复兴宗教信仰的希求,甚至,揄扬屋大维是奉天承运的圣明统治者的这一初衷,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销蚀。狄多女王见弃而饮刃自戕的悲剧,应当说,不仅未令幽幽神旨、缈缈命数在读者心中引发虔诚和敬畏,反倒让人们洞悉其荒颓空虚的实质。或许维吉尔本欲赓续古典,却因叙事艺术的惯性乃至强制,不自觉地反给了古典沉重一击。以此推之,称他是首位近代意义上的作家,也无可厚非。不过,若进一步剖析,我们发现,按今人之经验,凭狄多女王的言行欲使埃涅阿斯浪子回头,同样万难办到。关于爱情的相近见解,跨越两千余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和维吉尔的心灵间搭起了桥梁。我愿视之为观念层面的复仇,亦即迦太基女王狄多的终极复仇——正是她,也不妨说正是维吉尔南辕北辙的铺叙,导致诸神自《埃涅阿斯纪》流传那一刻开YddKZS4yaQFHYjzK8+m15Q==始,便逐渐从文学领域和思想领域退场。请注意,恰恰得益于这轮真实、深彻且无计扭转的退场,得益于它续续扩散的无形漪澜,今天的创作者才认出了《埃涅阿斯纪》的内楗:埃涅阿斯与狄多女王坠入爱河,是整部史诗的必然环节,至于其余篇章,要么是伪必然,要么彻底就是自由环节。
回头看。狄多女王的第一重复仇,亦即叙事层面的复仇,已在文本中迅速实现。第二重复仇,亦即历史层面的复仇,则由兵临城下的名将汉尼拔和公元五世纪南侵的日耳曼人实现。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谛视,那么以下补充并不算题外话:维吉尔响应——至少在表面上响应——伟大帝王的号召,想用一部雄阔而忧伤的巨著佐证罗马称霸世界洵乃神意天命。然而,若神意天命当真存在,罗马也在这神意天命中殄灭无胤了。缘何昔之熇熇而今之凉凉也?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载述三次布匿战争后规诫道:胜利者不可过于无情,因为终有一日,胜利者会变成失败者。罗马对迦太基过于无情,正如埃涅阿斯对狄多女王过于无情。
r4dlEUFStncYxvXGAMeSNQ==语调与真实
“我蓄志泄愤报怨/今日才一朝如愿/花生米被我踢在裤裆上/我与他瞠目相见……”
1944年,湘桂战事失利,史迪威将罗斯福的一封信当面转交蒋介石,随后写下一首小诗自娱。他把蒋称为“花生米”,认定湖南、广西和第一次缅甸之战的败绩要归咎于这位统兵数百万的委员长。黄仁宇在《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里写道:“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让给史迪威,但是(史)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迪威身为军人,从战局上指责蒋介石固然未可厚非,但他或许并不了解当日之中国。曾担任一线部队下级军官的黄仁宇,谙尝“国军”的种种实况,认为中国能够抵挡日军一百多万优势力量整整八年,“今日想来仍有余悸”。长期以来,“组织动员能力”的渊源始终由迷雾遮罩。我们惯于使用“国民性”去忖度不同文明的层级差距,去诠析为什么仅用“一纸命令”便能轻易指挥整体缴械的日军。“他们一切循规蹈矩,唯恐不符合我们的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黄仁宇的理论或许让我们第一次看清那些真实历史中静悄悄的转捩点。美国人不理解中国,所以他们的经济史学家才会要求黄仁宇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之前,“务必先根据人口统计和耕地面积的确实数字”。黄仁宇倾力向他们申说,岂止当世学者无法确知明代的耕地面积,即便是明朝皇帝和户部官员,也不会清楚实际数目。
民国,古今移变的关键阶段。恢宏的移变仍在继续,厘革物事的力量屡显峥嵘。若不洞晓这一移变的方向和意义,那么,不管哪一类文章,都将与真实及真理相去甚远。不懂得民国诸般苦困挣扎的根本症结,其语调必然虚浮不堪,必然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文艺腔,充斥着令读者无法忍受的慷慨激昂或各类角色智识的普遍贬低。更可怕的,是与之相应的种种情感,人的爱恋,人的奋争,也将徘徊于荏弱、浅稚、空乏的可悲境地。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