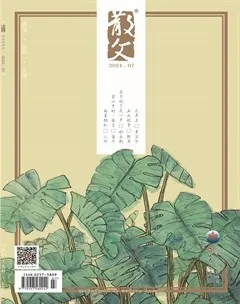家山岁时·春夏
立春
二十四节气之首,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传统国画颜料中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萌黄。近水溪边先得绿,它是早春时节水边垂柳刚刚萌发的颜色,像茸茸的鹅黄,远望淡如烟雾,若有若无。知时节的有心人,不会错过乍见萌黄的惊喜。要知道,虽然仍然寒冷,但一点萌黄告诉我们,大地深处正酝酿着浩大的生机,天地就要苏醒了!
南宋人张栻《立春偶成》有云:“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春打六九头”,打扫春节期间的炮仗皮时,你会发现,碎纸下边,野蒿棵子已绿湛湛刺入你的眼皮。
立春日有时出现在腊月底,也有时出现在正月初,还有的年份发生一年俩春或当年无春的情况。如果一年赶上两个打春,老人说:“一年打俩春,豆子贵如金。”预兆此年旱涝灾害多于往年,庄稼可能歉收。
在立春日的头一天晚上,有的人家将一截高粱秆从中间劈开,均匀放入十二颗黄豆,然后用线将两爿高粱秆捆上扔进水缸,隔两天捞出打开,顺向看,哪颗豆子湿得厉害,就认为哪个月份的雨水大。
立春的这一天,山乡人要吃豆芽干饭。寓意种下的种子都能够发芽、出苗。还要折一根椿树枝,放火上燎了,扔进水缸里,认为这样做能解除瘟气。老人说,立春阳气上升,如果在一个竹筒里放上鸡毛插进地里,立春这一刻,鸡毛就会自动飞出来。
惊蛰
二十四节气中,只有这一个节气是以动物的习性命名的。
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天气回暖,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于洞穴或土中冬眠的动物。
“万物出乎震”,飒飒细雨或滚滚春雷,惊醒了沉睡一冬的走兽和昆虫,它们纷纷离开蛰居的处所,重返大自然怀抱。无论动物或植物,都愉快地吸收着天地的滋润,尽情舒展生机。
陶渊明《拟古·其三》有云: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在山乡,天上第一次打雷时,人要全身抖动几下,说抖抖身子一年不长虱子。过去,虱子是寄生于人身上的常物,城里人和乡村人都遭其害。其身小若芝麻,短粗,六足。未吸人血时,干瘪成两层皮,吸了人血,即膨胀为球体,大了数倍。着人身,其痒难耐。乡村人对付它的办法是,把衣服火烤或水煮,它经受不住烤,掉到火中,听着啪啪作响,人心里特别解气。城里人则通过常换衣服来解此烦恼。
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山里的虱子觉得日子不好过了,就往城里走。同样,城里的虱子也觉得不好过,往山里走。两伙虱子在卢沟桥上遇上了,城里虱子问山里虱子:“你是哪里的,到城里去干什么?”山里的虱子叹口气说:“嗐!别提了,我家住破棉袄,一天三遍烤,别说吃上肉,性命都难保。”城里的虱子听了更伤心,言道:“唉!我还不如你呢。我家住绫罗缎,一天三遍换,别说喝上血,脚都没地儿站。”互诉了苦衷,它们就留在了卢沟桥,所以说卢沟桥的虱子(狮子)数不清。
冻人不冻地,惊蛰地化通。“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春耕大忙季节到来了。农谚说:“过了惊蛰节,长工不能歇。”“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京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这时重点是耙地保墒,给返青的冬小麦灌溉、追起身肥,另及早春作物的播种,如顶凌播种大麦,再者薯类育苗。
谷雨
二十四节气之六,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春深气暖,得见春雨。北方的春季雨少,“春雨贵如油”,盼望春雨是个心事。若按期望而来,农民最喜不过,种植谷物的耧铃声便愉快地在桃杏花纷落的坡地上响起。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此一时节,地上小草通通发芽,树上新叶绿上枝头,坡上山蛮荆花(毛杜鹃)红成一片。山中有了布谷鸟的叫声,告诉人们快快播种。农田活计,主要是种春棒子和耩谷。
春种时节欢快而繁忙,田间地头欢声笑语,老年人不时说上几句笑话,年轻人则互相调侃,用娱乐性把忙和累掩盖。
有一种鸟应季,它比鸽子略大,羽毛华美,头上长冠状羽毛,鸟喙较长,发的声音像牛叫,山里人叫它“地牛”。倘若听到它的叫声,预示今年会是一个好年景,可是它偏不爱叫唤。
假如在谷雨节的第一天下雨,就叫“天苍雨”,是今年风调雨顺的好兆头。老人讲,遇上“天苍雨”,种在石头盖儿上也一样打粮食。
立夏
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树绿了,草绿了,山绿了。杏花、梨花、海棠花、李子花相继开放,人们伴着花香,每天早起晚归忙于春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时光宝贵。
山乡人种玉米,在大块地,用两头骡子拉犁,一个组合三个人工。一人牵牲口,一人扶犁,牵牲口的掌控方向,扶犁的把握开沟深浅和行距宽窄。在他俩之后往往是一位有经验的中年妇女往豁开的沟中撒种。撒种是否均匀,全看这个妇女。还有一两青年在组合之外耕不到的地方用镐招一招地头,将地块补种齐,名为“招漏犁”。
一块地耕种完,卸犁,换上“盖”。盖是长约三尺宽约二尺梳子样的木质农具,一人站在盖上,用盖把地耙平,确保种子盖得严实。孩子喜欢蹲在盖上,搂抱着大人的腿,随着盖前行和颠动,觉得是最好玩的事。
旱地种谷比种玉米简单。由一个有种地经验的长者和两个青年共同完成。耩地的农具叫作耧。耧上有一个木斗,斗内隔开成两个室,一个放谷种,一个放捣碎的干鸡粪,耧斗下部有一个控制种子和鸡粪流量的开关。拉耧的小伙将襻绳套在双肩,往前拉,长者在后边扶着耧把,不停地摇动。能否出全苗,能否均匀,全在扶耧把式的这一关。有钱买子,无钱买苗,播种量一定要比正常多一点。不拉耧的小伙子则用双脚把耩过了的垄沟踩平。俩青年轮换,一天下来仨人都累得不轻。
种完了玉米,那地还有闲处,就在玉米地间作蔓菁和黄豆,地沿上再种豆角。待豆角长出,第一排玉米自然就成了豆角的秧架。在谷子地间作的是高粱和小豆。还在田边地头点种上倭瓜、麻子、豇豆和大青豆。一地多得,一点不让地闲着。另一些小块地和山坡地,用来压山药或种绿豆、小豆等多种杂粮。
平原上的栽白薯、查苗、补种、间苗、定苗,中耕除草、治虫,一并进行。
小满
二十四节气之八。陶渊明《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孟夏天气,还未真正酷热。花事虽然不再繁华,但树木生机葱茏,渐渐成荫。鸟雀和鸣,上下枝条,出入叶底之间。微雨,好风,草木,花鸟,无不充满欣欣然的活力。小满之名,来自农作物的生长。庄稼的籽粒盈实为满,小满则是稍稍充盈,籽粒灌浆之初。既耕且种,庄稼在和风细雨中发育成长,渐有起色。将满而未满,因为有憧憬,也是美好的时刻。
山乡亦有另一番景象。当地有“立夏领头青,小满叶子圆”的说法。小满时节,树叶全长圆了。
梯田种完了,山乡人开始上山种胡萝卜和土豆。种胡萝卜要先把地刨松,然后让能手撒种。胡萝卜籽很小,带羽状的毛边,播撒时非常讲究技术。全撒完了,检验入土的菜籽疏密是否适宜,即随意在浮土上边摁一个手印,在这一手印下能数出四五粒种子,就算合适,闲话甭讲。然后用镐头平拖,扒拉一遍,就完成了整个过程。
种土豆,也叫“压山药”。取出地窖里储存的土豆,每个土豆按胚芽切成两三瓣,依行距刨五到十厘米深的沟,将胚芽掩上土,边刨边埋,比种萝卜轻松。
山地上干活,年轻人心气很盛,贪玩的心还有,会利用休息时间用山核桃树树皮卷一个“喇叭”,长约一米,粗如牛腿,一头大一头小,叫“牛腿嗡”。牛腿嗡的小头用细山核桃树枝的皮做引子,使劲一吹,呜呜哇哇,声音高亢。待傍晚收工迤逦而归,暮色中的他边走边吹,似一支雄壮的队伍凯旋。家里的孩子听到牛腿嗡的奏乐,忙跑出家门争抢,给大街添了热闹。
种地靠人,收成靠天,山地没有水利灌溉,收成好坏全凭老天爷赐予。平常年景,山地平均亩产两百斤左右。细粮几乎为零,粗粮杂粮一应俱全。贫乏年景也有很多野菜和树叶可以充饥。因此这里的老人说:“一百二十行,不如武装郎。”这“武装郎”指的就是山地农民。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粮食不够,野菜来补。
山地产粮虽然有限,灾害也经常发生,却饿不死勤劳朴实的山地居民。“穷进山,富入川”,平原人相信这一经验。
夏至
此日,白天时间最长,过了这一天,白昼即日渐缩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天气炎热了,时令进入盛夏,是庄稼生长最旺盛的时期。“过了夏至不种黍”,转入农作物的中期管理阶段。
玉米从初期到成熟要耪(除草松土)三遍地。修理的程度分别为:头遍浅,二遍深,三遍除草根。耪头一遍地用小锄,人蹲着,一挪一挪往前蹭,连松土带间苗。此际最难受的,是因为二茬玉米种在麦茬地里,割过了的麦子还留有坚挺挺的麦茬,耪地就要卸麦茬,那手掌背必然会被麦茬蹭伤。没见不流血的。耪二遍地时,庄稼已经定型,是玉米的“喇叭口”时期,半人高了,根系已很发达,更需要土质疏松,促其吸收营养,所以得用四五尺长的大锄进行深耪。不十分遭罪。第三遍,玉米已长大成人,钻出了天穗,为了减少杂草与庄稼争肥,并避免剩余杂草继续结籽,要用大锄耪掉草根,将搂起来的土连埋带盖,不让杂草安宁存在,同时从长远看,地表干净也有利于秋播小麦,免得犁头挂杂草。做一明二眼观三,农民可不是那么简单。
玉米喜水喜肥,但不喜过度干旱和水涝。在玉米生长过程中,起码要浇两次水、追一次肥。
谷子就像猫有九条命,生存能力强,跟农民的关系“铁”。它耐干旱,耐贫瘠,不十分牵扯人的精力。产量是低了一点,亩产难上两百斤,但它又是玉米以外重要的粮食作物。谷子难耪的时候是头遍。小苗出土,才两三寸高,就要进行除草、除掉酸枣树拐子,给它间苗。这项劳动,男人往往比不过女人。别看小伙子能蹦能跳,能背能扛,可让他长时间蹲着,一手拿小锄除草一手不停歇地间苗,一会儿他就蹲得两腿酸胀受不了,不得不时而站起身来晃一晃。最难堪的还不是这,是他夹在妇女群里,左右都挨着姑嫂姐妹。妇女心灵手巧,眼光准,用不了多久就把棒小伙子甩在后面。她们会不断地回过头来奚落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快些吧,这么笨谁家给媳妇哇!”小伙子自然脸上发烧,加紧进度,但又出现了质量问题,一不留神把应保留的谷苗和应剔除的莠草弄了个相反,被发现了又要遭训……
莠子这东西,最能以假乱真。它和谷子长在一起,于幼苗之期最不容易厘清。一旦发现弄混,往往已成定局。
莠和谷不容易划分,还缘于谷子有多个品种,品种不同,出苗的标志色便也不同。每年耪谷,生产队长或有经验的老农都要大声提醒:注意啦,今年地里绿秆的是谷苗,红秆的是莠子,别留错了!而到另一块地,又说这块地红秆的是谷苗,绿秆的是莠子。还有时说:长得干净的是谷苗,带茸毛的是莠子。给年轻人一次次“上课”,年轻人一次次接受“训令”。
“谷锄三遍不见糠,棉锄三遍白如霜。”盛夏之季,人们没有计时的习惯,全是日未出而作,日入了深山老林方才将息,蹚着露水进地,踩着星星回家。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无论男人女人,都尽显疲惫。这也是一年四季当中,乡民最为沉寂、娱乐活动最少的时候。
小暑
杜甫在《江村》中歌咏: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这首诗表现出作者的闲适之情,而现实却并非像他描述的那样清幽可人。一个月内,小暑大暑接踵而至,真正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期。盛夏溽暑。溽者,湿也,热也。“挥汗如雨”,是真切的形容。
自夏至以来,又是半月,太阳光直射点已稍稍南移,在黄经105°左右。入夏及至而今,天地间热能储蓄已久,又加雷雨频至,热气上下蒸腾,扑面而来的都是热浪连连。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恰在中伏之时。伏者,阴气迫于阳气而藏伏地下也。暑气既增热毒,又添烦躁,农人实实没有那有闲阶级的风度。
潮湿多雨的季节来了,农历到了五月末或六月初。“六月六,看谷秀”,农民一宗宗希望和喜悦出现在眼前:谷穗一个个秀出来了,如一群留着木梳子背头的小小子潜在田间,煞是喜人;玉米也开始“卖花红线儿”(玉米穗的粉红色雌蕊)了,红扑扑的,像女孩的脸。小暑节气中耪地,最苦最累,在玉米秧比人高的地里,男人光大膀子,女人穿短衫,手握大锄,汗如雨下。玉米叶锯齿状的边缘在胳膊、肩膀和胸脯上划出一道一道血印,汗水流入伤口,杀棱棱钻心地疼。但是没有人叫苦,因为这早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锄地何为?其由在“锄头有水,锄头有火,锄头有肥”。旱天耪地打乱了地表的微小气孔,减少水分的蒸发;涝时耪地能疏松土壤,加快水分的蒸发;土地疏松,透气性强了,能促进庄稼根系与忧困较量。
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把人的皮肤晒得黝黑,汗碱和泥土,是衣服上最显著的标志。阳光下的田地,闪动着皮肤的亮光,荡漾着锄头的音响,也能听到开朗的笑声。
小暑节里,蝉开始鸣叫了。山里的蝉有几种,有的叫声节奏明快,长短交替,有的从头至尾一个腔调,不变音。还有的叽叽叽叽连续不停,好像兴奋交感神经太强盛,没有停歇的时候。又一种,看上去也就手指肚大小,但声音既长且慢,自己悠扬得很,却没有人给它起名字。
山民最喜爱的是一种鸣鸣蝉,小孩子最爱学它的叫声。这蝉对空气湿度特敏感,能提示人关注天气变化。如果它在早晨太阳出来以前叫,预示今天很可能下雨。若在连阴雨的天气中叫,就是告诉你天气很快就要放晴了。
大暑
大暑赶在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这时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大部分地区的旱、涝、风、雹灾害也最为频繁,抗旱排涝和田间管理的任务也就最重。
山区进入雨水最多的时节。一年的劳苦也有了甜头。农人得愿,终于可以歇伏、“挂锄”了。劳动日程转向了不紧不慢的割蒿草和沤绿肥。
田间小路上,人随身携带的家什不再是空空的了。有的篮子里搁着豆角,有的背篓里装着蔓菁和倭瓜。脚步悠悠,心情悠悠,如踩在五彩云头。
此一时,萤火虫舞得最欢。夜间,它与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这些个小灯笼,孩子们爱玩。他们原以为发光的地方会烫手,可逮住一只,用手指摸一摸它的腹部,竟一点也不烫,孩子们好生奇怪。
谚语说:“大暑小暑,灌死老鼠。”此际特别爱下雨,有时连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不停,让木头的大驴槽都长了蘑菇。老不晴天,人特别容易忧郁,老人就用布片做一个手拿笤帚的小布人,挂在房檐下,叫它为“扫天晴”。风吹来,手拿笤帚的小布人晃晃悠悠,转来转去。不久后天气放晴,老人这时就要说:“瞧,还是我有主意吧!”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