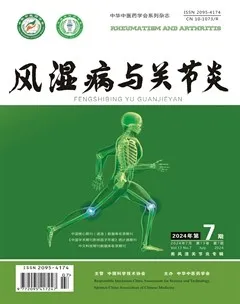田雪梅主任医师基于“重阳思想”论治类风湿关节炎
【摘 要】 中医药治疗“痹病”历史悠久,具有独特优势。田雪梅主任医师临床基于“重阳思想”辨治类风湿关节炎屡收成效。从“重阳思想”出发探讨其发病机制,认为“阳化气”功能不足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始动因素,痰浊、瘀血等阴邪阻滞筋骨关节为其外象,疾病后期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仅用温阳药或化痰消瘀药恐难达到满意疗效。故田雪梅主任医师临床辨治类风湿关节炎谨守阳气不足之病机,兼以化瘀通络、清热利湿,“阳化气”不足与“阴成形”过盛同时兼顾,达到“温阳”与“通阳”相辅相成之功效。
【关键词】 类风湿关节炎;重阳思想;阳化气,阴成形;阳主阴从;阳虚;温通阳气;田雪梅
田雪梅为甘肃省名中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中医院风湿骨病中心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风湿病如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系统性硬化病等。
RA是一种慢性、对称性、进行性自身免疫病。有研究表明,RA全球患病率为0.5%~1%[1],我国患病率为0.42%,由于RA导致的关节活动明显受限及躯体残疾,使得RA患者生活质量显著低于正常人[2]。疾病早期,规范使用西药治疗可有效控制病情,但产生的骨髓抑制、肝肾毒性、感染和肿瘤等不良反应亦限制其广泛使用。RA属中医学“痹病”范畴,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辨证论治,不仅能够取得较好疗效,且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田雪梅主任医师认为,“阳气”影响风湿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临证运用“重阳思想”、以“温通阳气”为基本原则治疗风湿病效果显著,现将其思想分享如下。
1 “重阳思想”探析
“重阳思想”萌芽于《周易》,奠基于《黄帝内经》,继承发展于张仲景和张景岳时期,发扬于郑钦安和祝味菊,核心思想为“阳主阴从”,纲领性观点为“阳化气,阴成形”,历代医家在“重阳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和疾病观。
1.1 理论探源 《系传·系辞上》开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于天……乃顺承天。”以阴阳观,乾代表阳,以天为代表,坤代表阴,顺从于阳,《周易》的“重阳思想”观一看便知。《黄帝内经》在强调阴阳互根互用、对立制约的同时,更承认阳气的主导地位。《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卫外者也。”“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张景岳在《类经·阴阳类》提及:“火,天地之阳气也,天非此火……故万物之生皆由阳气。”又《景岳全书》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强调真阳之于人体犹如太阳之于天地,人体赖以真阳之气生存。郑钦安在《医理真传》谓:“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祝味菊在《伤寒质难》云:“人以阳气为生,天以日光为明。宇宙万物,同兹日光;贤愚强弱,同兹气阳……故善养阳者多寿,好戕阳者多夭。”强调百病皆由伤及阳气而起。
1.2 核心思想为“阳主阴从” 《周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阴和阳并非完全平等,阳健阴顺,“阳主阴从”才是两者本质。《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阳在动态交互过程中达到“阴平阳秘”,前提是阳气的固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只有阳气生发才有阴气的生长,阳气消退之后才有阴气的隐藏,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体阴阳在“阳主阴从”的主导下保持平衡,从而达到生命的和谐状态。
1.3 纲领性观点为“阳化气,阴成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阳化气,阴成形”观点是“重阳思想”的又一体现。张景岳提出:“阳动而散,故化气,阴静而凝,故成形。”阳主动而散,主气化,可促进脏器发挥正常功能,阴主静而凝敛,主万物成形,使自然界万物凝聚为自身有形物质。自然界一切生化,人体所有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过程都可以用“阳化气,阴成形”来概括,两者相互制约,维持着动态平衡与协调。
1.4 在治则中的指导作用 基于《黄帝内经》“重阳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以此衍生出众多学术流派。张仲景在《伤寒论》六经病中重视“扶阳气”,即三阳病宣通阳气,三阴病温补阳气[3]。“温补学派”代表医家张景岳倡导“阳常不足”之说,治疗上偏重温补,其创制的“右归丸”为温补肾阳之名方。“火神派”代表医家郑钦安在《医理真传》谓:“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知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认为世人阳虚阴盛居多,治病立法重在温扶坎中之阳[4],治疗多用辛热之附子、干姜、肉桂。清代医家祝味菊认为,阳气盛衰可决人之死生,临床善用附子,崇尚温阳。
2 基于“重阳思想”论RA发病
2.1 “阳气不足”是RA发病基础 现代医家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经验,认为RA发生总责之于正虚为本,邪盛为标,正虚即营卫失和、气血亏损、肝肾不足。《灵枢·百病始生》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田雪梅主任医师认为,RA的发生与阳气亏虚密不可分。林珮琴在《类证治裁》写到:“诸痹,良由阳气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久而成痹。”可谓一语中的。田雪梅主任医师认为,RA发病与脾、肾密切相关,脾肾功能正常,脾肾阳气运行互济,才能化生气、血、津、精,使骨髓充盈,骨骼强硬。且《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谓:“阳气者……柔则养筋。”阳气充足则四肢百骸、筋骨肌肉皆有所养;反之,则卒病痼疾随之而生。
2.1.1 肾阳虚与RA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证治准绳》曰:“有风,有寒,有湿……皆标也,肾虚其本也。”道出RA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肾虚。“命门者,先天之火也”,肾阳作为推动全身运转的源动力,对维持各个脏器和人体稳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程国彭曰:“命门之火可生脾土也。”肾阳亏虚,脾土无“火”以温出现食少便溏、腹胀;“肾主藏精”,为人体生长发育之根,后天“脾精”和先天“元阳”无以相互滋养,机体抗邪无力,外邪入侵;又“肾主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外邪痹阻筋骨肌肉关节,出现四肢拘急、屈伸不利,发为RA。
2.1.2 脾阳虚与RA 《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云:“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阳充,一则气血津液生化有源,四肢肌肉得到充分的水谷精微的充养,收缩自如;二则下滋先天“元阳”。反之,则运化呆滞,升降失常,水谷不得化精滋养四肢百骸,出现四肢肌肉萎缩不用、纳差乏力、痞满腹胀;湿浊不化,酿湿生痰,因痰致瘀,痰瘀互结,壅塞脉络,留滞关节发为RA。张杰等[5]认为,RA患者出现的肌肉含量减少、骨骼肌萎缩和内脏脂肪和含量增多是由于脾虚所致。
2.1.3 阳虚体质和RA发病 《灵枢·五变》有云:“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则刚……况于人乎!”形象说明体质在人发病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田雪梅主任医师认为,RA的发病与体质密不可分,正如章虚谷在《外感温热篇》注解中所说:“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阳强弱而为病。”外感风寒湿邪气是RA发病的关键因素,同气相求,易感风寒湿者,必是阳气素虚,先天禀赋不足体质。现代研究表明,阳虚体质者T、B淋巴细胞免疫活性下降,对外界致病因子的防御抗邪能力下降,与内源性致病因素的调节能力失常有关[6]。多项研究证明,RA患者中阳虚质占比高于其他偏颇体质,更易体现疾病易感性[7-10];且阳虚质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免疫调节相关的miR-146a及早期炎症相关的白细胞介素-17表达显著高于平和质的RA患者[11-12]。
2.2 “阳化气,阴成形”功能失调是RA病理关键 中医学认为,生命就是生物体的气化运动,气化运动的本质就是化气与成形,两者始终保持相对平衡,人体脏器功能的正常运行和有形之态的维持,均赖于阳气的气化推动作用。若是阴阳功能失调,致“阳化气”不足,“阴成形”呈优势发展,就会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正如《温疫论》载:“阳气愈消,阴凝不化,邪气留而不行。”故从病理角度出发,人体一切成形的疾病均可概括为“阴成形”太过,如甲状腺结节、肿瘤、结石、肥胖症等。
RA患者临床多有关节漫肿如梭、免疫球蛋白增多、滑膜增厚及血管翳强化、骨质破坏,部分患者可出现类风湿结节,乃有形之病理产物堆积。《万病回春》云:“凡骨节疼痛,如寒热发肿块者,是湿痰流注经络。”由于阳气亏虚,失去其温煦推动作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失常,气血津液失其正常的输布聚散之能,从有益的阴精凝敛成形转化为有害的有形阴邪,最终发展成为癥瘕积聚。阳虚化气不足,气不周流,血液流速减慢,红细胞沉降率加快,血液呈凝滞状态,阳虚易感寒湿邪气,寒凝脉管,脉管血流量减低,管径变小,微循环障碍,日久酿生病理产物,痰浊、湿热、瘀血堆积于局部难以及时改善,终致“阳虚阴结”,同样“阴成形”太过又会加重“阳虚”,两者互为因果。
3 “温通阳气”是RA治疗大法
RA的发生乃寒湿、痰浊、瘀血相互交织而成,究其根本是体内气血津液代谢失衡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停聚于人体筋骨关节,其本质是阳虚不化、阴毒积聚。“无阳则阴无以化”,故田雪梅主任医师认为,“温阳化气”应贯穿RA治疗始终,在此基础上辅以“通阳祛邪”消已成之积阴。
3.1 “温阳化气”贯穿始终 《扁鹊心书》谓:“凡治痹,非温不可。”通过查阅文献,多名医家运用温阳通络、益气温阳、温阳散寒除湿等治法诊疗RA取得显著疗效。综合而言,不难得出各个医家均以“顾护阳气”为核心要义[13-15]。
《中藏经》指出:“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阴宜长损,阳宜长益,顺阳者生,逆阳者死。”RA患者在临床中多呈现“阳虚”为主的疾病状态,表现为关节疼痛遇冷加重、畏寒、乏力、食欲减退、舌质淡胖、苔薄白等症状,故其治疗以“温扶阳气”为主,在五脏则温补脾肾阳气。李玲慧等[16]研究发现,温肾阳复方右归丸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提高成骨细胞分泌碱性磷酸酶的能力;孙鑫等[17-18]认为,温补脾肾方药可延缓骨破坏,促进骨修复,改善骨骼肌肌纤维成分,增加肌糖原含量。
3.2 “通阳消积”祛邪化阴 清代医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云:“其实痹者,闭而不通之谓也……致湿痰浊血,流注凝涩而得之。”《类证治裁·痹证》曰:“痹久必有瘀血。”又《医学心传录·痹证寒湿与风乘》曰:“风寒湿气侵入肌肤,流注经络,则津液为之不清,或变痰饮,或成瘀血,闭塞隧道,故作痛走注,或麻木不仁。”痹证顽固难愈,日久正气亏虚,邪气稽留,损伤气血,痰、瘀、寒、湿等病理产物痹阻经络,互相胶着,深入骨骱,腐蚀筋骨;并作为新的致病因素阻遏阳气,影响病情进展。故治痹不但要温扶阳气以扶正,还应兼顾化瘀通络、祛寒除湿、涤痰散结以通达阳气。阳气得通,则气血调和而诸症自除。
4 病案举例
患者,女,28岁,2023年7月30日初诊。以四肢多关节疼痛9年余,加重1个月为主诉。现病史:患者于2014年无明显诱因出现双手掌指关节、双侧膝关节疼痛,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予藏药口服、药浴治疗。口服中药期间逐渐出现四肢多关节间歇性疼痛,以双手近端指间关节、双腕关节、双肘关节、双肩关节为主,双手晨僵持续时间 > 1 h;1个月前受凉后加重。入院专科检查:双手近端指间关节2,3,左手掌指关节2,3,右手掌指关节2,3,4压痛(+),双侧腕关节肿胀伴活动受限,压痛(+),双手握力减低;双侧肩关节压痛(+),上举、背伸均受限;双膝关节屈曲畸形,髌周压痛(±),浮髌试验(-),伸直、内旋、外旋轻度受限;双下肢末梢血运可。入院实验室检查:类风湿因子(RF)105 U·mL-1,红细胞沉降率(ESR)26 mm·h-1,C反应蛋白(CRP)76.0 mg·L-1,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抗体)132 U·mL-1。DAS28评分4.36分。刻诊:精神差,自觉乏力,平素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四肢多关节肿痛伴活动受限,双膝关节僵硬、屈曲畸形,食欲欠佳,舌质淡,苔白腻,脉细弱。西医诊断: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诊断:痹病(寒湿痹阻型)。治宜祛寒除湿、通络止痛。给予益气温阳方加减,方药:黄芪30 g、炙黄芪30 g、党参20 g、麸炒白术30 g、炙甘草10 g、干姜20 g、茯苓30 g、猪苓15 g、泽泻20 g、桂枝15 g、淫羊藿15 g、肉桂6 g、当归10 g、川芎10 g、羌活10 g、独活15 g、防风12 g。14剂,每日1剂,早、晚饭后半小时温服。
2023年8月7日二诊,患者精神可,四肢多关节肿痛及活动受限症状较前缓解,双手晨僵时间缩短,舌质黯,苔白,脉沉细。实验室检查:RF92 U·mL-1,ESR 21 mm·h-1,CRP 4.0 mg·L-1,抗CCP抗体105 U·mL-1。DAS28评分3.68分。继上方加海风藤10 g、络石藤10 g、桑枝15 g舒筋活络止痛,嘱服用2周后门诊复查。
2023年10月25日三诊,患者诸症好转,继续服用上述汤剂14 d。此后多次复诊,以上方为基础加减治疗1个月余。后诉怕风怕冷症状消失,体力增加,生活质量改善。嘱其避风寒,畅情志,不适随诊。
按语:患者平素乏力、怕风怕冷,属于气阳两虚之偏颇体质,遂于感受风寒湿邪气后无力驱邪外出,痹阻于肌肉关节筋骨。且RA为消耗性疾病,该患者RA病史9年,长期服用藏药,日久重伤脾胃,正气益亏。患者腰膝酸软,纳差乏力,舌淡,苔白腻,脉细弱,均为脾肾阳虚、寒湿阻滞之征象。临证使用益气温阳方脾肾同治,温阳补气。方中炙黄芪补气升阳、散寒止痛,配合生黄芪益气补中,且炙黄芪还具有行血通痹之功效;羌活、独活祛风除湿、消肿止痛,配合当归、川芎、防风活血祛风;党参、麸炒白术、炙甘草补气健脾;干姜温中散寒,回阳通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桂枝、淫羊藿、肉桂共奏温通肾阳、利水渗湿之功;海风藤、络石藤、桑枝通经络、止痹痛。现代研究证明,温肾健脾中药治疗RA有极大的优势,和西药联合使用不仅可以增加疗效,还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19-20]。纵观全方,融散寒除湿、温通脾肾、活血通络于一炉,使寒湿除、气血旺、肾元充、血脉通而诸症自除。
5 小 结
阳气不足是RA及其常见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内因,肾中阳气不足,逐渐波及脾、肺等多脏阳气,导致气血化生乏源,正虚不能抗邪,感邪日久酿生痰浊、瘀血等病理产物,渐阴损及阳,阴阳失衡,脏腑受损[21]。田雪梅主任医师认为,阳气亏虚、化气不足致痰浊、瘀血等病理产物堆积是RA病机关键。临证当谨守阳气不足之病机,“温阳化气”辅以“通阳祛邪”,两者同时兼顾,达到治疗疾病目的。中医重视阳气思想绵延几千年,时至今日,为临床中医药治疗RA提供新的遣方用药思路。
参考文献
[1] BRIGGS AM,PERSAUD JG,DEVERELL ML,et al.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including muscu-loskeletal health:a systematic policy analysis among OECD coun-tries[J].BMJ Glob Health,2019,4(5):1806-1829.
[2] 曾小峰,朱松林,谭爱春,等.我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和生存质量研究的系统评价[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3,13(3):300-307.
[3] 罗试计.浅析《伤寒论》中扶阳气思想[J].四川中医,2012,30(1):39-40.
[4] 成西,郭雨晴.从中国哲学“重阳”思想探讨“火神派”理论源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5):638-639.
[5] 陶宁,张杰.张杰基于“脾虚生湿”论治类风湿关节炎经验撷萃[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23(12):59-63.
[6] 王琦,姚实林,董静,等.阳虚体质者内分泌及免疫功能变化[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8,6(12):1226-1232.
[7] 张磊.106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变形与体质相关性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8] 李博,胡秋侠,谭锦辉,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医体质分布及miR-146a表达[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39(9):1045-1049.
[9] 朱丽芳,陆蕾,李伟.中医体质类型与类风湿关节炎相关性探析[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0,9(7):20-23.
[10] 周春瑜,陈艳林,付庭娜,等.中医体质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研究进展[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0,9(7):67-70.
[11] 李博,胡秋侠,谭锦辉,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医体质分布及miR-146a表达[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39(9):1045-1049.
[12] 王涛,王钢,王佳,等.302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医体质分布及IL-17的表达[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28(4):586-589.
[13] 吴金联.益气温阳方治疗气虚寒凝型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研究[D].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2020.
[14] 汪宗清,侯卫,聂红科,等.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探讨温阳通络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作用机
制[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5):120-129.
[15] 卢曼.温阳散寒除湿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对血清TL1A、TNF-α水平的影响[J].内蒙古中医药,2020,39(11):36-37.
[16] 李玲慧,詹红生,丁道芳,等.温肾阳、滋肾阴中药复方对大鼠成骨细胞活性及Wnt/β-catenin通路影响的差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70-73.
[17] 孙鑫,杨芳,邓洋洋,等.补肾、健脾、活血方法对骨质疏松症小鼠骨及骨骼肌中Ca2+-Mg2+-ATP酶含量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4):416-417.
[18] 金成日,姜奥,杨芳.补肾、健脾、活血法对去卵巢致骨质疏松症大鼠骨骼、骨骼肌IκBα含量影响的对比研究[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17,23(2):244-247.
[19] 刘春丽.温阳通络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研
究[D].昆明:云南中医学院,2017.
[20] 唐宇俊.温阳活络汤联合DMARDs药治疗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观察[D].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16.
[21] 陈霞,何晓芳,韦尼.基于温扶阳气法论治类风湿关节炎探析[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2,11(6):53-56,64.
收稿日期:2024-02-14;修回日期:202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