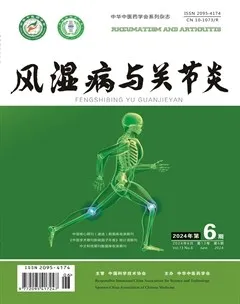卢思俭教授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
【摘 要】 卢思俭教授在治疗风湿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运气、体质、脉证三位一体”的诊疗思路,并应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治。同时,结合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特点,治疗过程中重视祛除湿热伏邪、顾护脾胃以及虫类药物的应用。
【关键词】 系统性红斑狼疮;五运六气;“运气、体质、脉证三位一体”理论;临床经验;卢思俭
卢思俭教授是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从事临床40载,善于运用五运六气、体质及经方诊治风湿病及内科杂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以自身免疫性炎症为突出表现的弥漫性结缔组织病。发病机制复杂,临床上以全身症状、骨骼肌肉及内脏炎症等多系统受累为主要表现。卢思俭教授根据《黄帝内经》五运六气有关“天、人、邪”天人相应理论、伏邪理论和张仲景有关体质、脉证的理论,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体质易感性以及祛邪为主,形成了运气、体质、脉证并治三位一体的疾病诊疗思路。同时,结合SLE发病特点,治疗过程中重视祛除湿热伏邪、顾护脾胃以及虫类药物的应用,临床治疗取得良好疗效,现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1 运气、体质、脉证三位一体理论与SLE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五运六气对疾病是存在影响的。如苏颖[1]认为,五运六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万物象变,气化使然”,即自然之气,化育万物,五运六气之气化太过与不及影响人体脏腑气机造成异常。《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当五运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太过、不及或非时而至,可影响人体正常生理活动和自我调节能力,成为致病因素。《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言:“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不足以言生化。”诊治患者时要结合自然气候变化规律对人体的影响,否则不足以完整地辨识人体疾病。因此,卢思俭强调,临床面对SLE的发病、复发及加重,需充分考虑五运六气变化对疾病的影响。
中医学对体质的认识由来已久,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湿家”“盛人”“饮家”“荣人”等,即现今所说的各种体质。书中条文既有对体质发病的症状表现,也有相应的治疗方药。《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曰:“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体在天地气交、气候环境的变化之中会受到其影响。《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详细论述了五运六气对生物繁殖及生长的影响,在不同的运气年份呈现生命特征的差异性,从而成为影响人体体质形成的因素之一。
卢思俭教授认为,体质的形成及疾病的发生,除与先、后天的五运六气相关外,还与后天的生活起居、环境、饮食等因素相关,这与西医学提到SLE发病受遗传因素、激素水平、紫外线照射、药物食物等综合因素影响是相通的。因此,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需重视体质因素。
在脉证方面,卢思俭教授观察SLE患者临床常见发热、关节肿痛、面赤、斑疹、周身酸痛、乏力、口干渴、心烦不安、坐卧辗转反侧、舌质红,苔白腻或黄腻等表现,认为湿热之邪所致证象较为常见。脉象参以薛雪《湿热论》所提湿热证之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随症见,不拘一格”为指导,以症为主,脉症相合,辨证论治。治疗宗以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为法,选方用药以经方、时方为基础底方,结合运气、患者体质及脉证特点等加减运用药物。
2 祛除湿热伏邪为要,时时顾护脾胃
SLE多属中医学“阴阳毒”范畴。阴阳毒见于《金匮要略》,系毒邪侵袭血脉,现于面部、咽喉及周身。近年来,国内各医家对SLE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研究颇多,认为毒邪是主因,尤以热毒为重,同时又有肝肾虚、血瘀等因素。如张鸣鹤[2]认为,本病因先天禀赋不足,感受外邪热毒,或有蕴热化生热毒,侵袭肌肤或损伤脏腑所致,治宜清热解毒、益气补肾。范永升[3]认为,SLE的病机与肾虚、热毒有关,治疗以肾虚为本,补益肾阴扶助正气有利于热毒祛除。禤国维[4]认为,SLE的病机关键是肾阴不足,其他证型皆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治以清热解毒、滋阴补肾、活血化瘀等法。
卢思俭教授治疗SLE参考古今医家治疗方法,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认为SLE患者体内伏邪为发病关键。清代刘吉仁在《伏邪新书》中提到:“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已发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亦谓之曰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陷,暂时假愈,后仍复作者,亦谓之伏邪;有已发治愈,而未能尽除病根,遗邪内伏后又复发,亦谓之伏邪。”SLE病情有此特点,即早期症状隐匿,病邪伏于体内不易发现,发病时或患者未予重视,或治疗不得法,致使病情延误,邪盛正伤。加之本病不能根治,患者擅自停药或更改药物用量,不能坚持治疗,导致疾病迁延反复,难以控制。因此,病邪长期伏于体内不易祛除,并成为疾病反复发作的原因。
卢思俭教授认为,SLE患者伏邪中以湿、热最为常见。湿邪内伏的产生或因患者本即痰湿体质;或因机体正气不足以抵御外邪,久处湿地、淋雨渍水而感外湿;或过食生冷、肥甘厚味,脾胃失运而生内湿;再或患者因病情缠绵难愈,思虑较重,伤脾生湿,终致津液输布失常,水湿饮邪停留周身。湿邪性质黏腻、缠绵,易留滞于筋骨、肌肉之间而难去。《素问·痹论篇》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流连筋骨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当湿邪流连筋骨间者,则缠绵难愈。如若不及时祛除,则病情越发严重。因此,祛湿尤为重要。卢思俭教授同时指出,SLE患者病久邪郁化热倾向明显,历代医家也多提出SLE以热毒为主因。在病情发展过程中,若久病热邪侵袭阳明,阳明正邪交争,邪盛正衰津液不保而入三阴,病情演变将更为复杂。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辨别并重视祛除热邪这一关键因素。
此外,《素问·热论篇》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水谷精微化生于胃,十二经脉气血来源于胃,若胃气耗散,则患者病情危矣。患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疾病的救治,尤其是危重阶段,更要保得一分胃气,以获得一分生机。脾胃又为健运之本,有健运祛湿的功能,因此,在SLE治疗过程中需时时顾护脾胃。
3 虫类药物的应用
卢思俭教授认为,SLE初发病位较浅,然不能根治,或失治误治,或反复发作及加重,病久邪深。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指出:“经以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然经年累月,外邪留著,气血皆伤,化为败瘀凝痰,混处经络。”寻常植物药往往效力不达,因此常采用叶天士“邪留经络,须以搜剔动药”的治疗思想,加用虫类药搜剔病邪,可显著提高疗效。
虫类药选择常以全蝎、蜈蚣为用,均有息风镇痉、解毒散结、通络止痛的功效,相须为用可协同增效。全蝎通行全身,蜈蚣尤善治局部痹痛,临床可单用或配对同用,久病患者需两者同用,以使功效增加。其他虫类药也可以根据患者症状表现结合舌脉选择使用,如地龙、僵蚕、蚕砂、水蛭、土鳖虫等[5]。
4 病案举例
【病案1】患者,女,36岁,2018年3月1日
就诊。以头晕、乏力1个月,肢体偏废、口角歪斜1 d为主诉。患者患有SLE 20余年,用药不规律,多次病情复发加重在外院治疗。重时给予输血、大剂量激素冲击及输注丙种球蛋白等治疗。患者来诊前1个月因再次擅自停药,出现头晕、乏力明显。自服醋酸泼尼松30 mg,每日1次,症状缓解不明显,后加至60 mg,每日1次;吗替麦考酚酯片1 g,每日1次。病情仍未缓解,渐加重,出现肢体偏废、口角歪斜。患者就诊时神志清,精神不振,语声低微,体胖,左侧肢体痿弱不能自已,口角歪斜,头晕,心慌,乏力,左胁肋胀痛,双目及皮肤黄染,纳差,眠可,二便调,舌质红,苔白厚浊,脉细数。查体:左侧肢体肌力Ⅱ级。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3.95×109·L-1,红细胞计数1.54×1012·L-1,血红蛋白47 g·L-1,血小板计数54×109·L-1。红细胞沉降率118 mm·h-1,C反应蛋白51.17 mg·L-1。生化全套:总胆红素56.7 μmol·L-1,直接胆红素7.5 μmol·L-1,间接胆红素49.20 μmol·L-1,谷氨酰转移酶51.5 U·L-1,白蛋白33.8 g·L-1。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47.54 mg·L-1,尿白细胞(++)。抗ENA抗体谱:抗双链DNA抗体(阳性)。影像学检查腹部CT示:①脾脏增大,脾内片状低密度影;②胆囊结石;③腹水。颅脑CT示:右侧额、颞叶片状低密度影;考虑脑梗死。西医诊断:①SLE;②狼疮性脑病;③狼疮性肝损害;④狼疮性血液系统损害;⑤狼疮性肾炎;⑥胆囊结石。中医诊断:阴阳毒(痰湿瘀阻,时感外邪)。中医治法:开达膜原,理痰清热通络。方药以达原饮加减:厚朴15 g、槟榔10 g、草果6 g、茵陈30 g、茯苓15 g、泽泻15 g、半夏12 g、黄芩12 g、全蝎5 g、蜈蚣2 g、甘草10 g、知母12 g。3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用。西药维持患者就诊前醋酸泼尼松片60 mg,每日1次,口服;吗替麦考酚酯片1 g,每日1次,口服;加用硫酸羟氯喹0.2 g,每日2次,口服;配合补钙抗骨质疏松、抗感染等治疗。
2018年3月3日二诊,患者左侧肢体活动较前灵活(肌力3级),余症改善,舌质红,苔白厚浊,脉滑数,在上方基础上加栀子10 g、生薏苡仁45 g、大黄3 g、炒苍术15 g,配以茵陈蒿汤加味清热利湿。
2018年3月7日三诊,患者左侧肢体可自已(肌力3级),诸症持续改善,舌质红,苔厚色白黄相兼,脉滑数。二诊方加大青叶30 g、金银花30 g、忍冬藤30 g加强清热解毒效力。
2018年3月10日四诊,患者诸症持续改善,舌质红,苔白微黄,脉滑数。三诊方去忍冬藤、知母,加半枝莲30 g、菊花15 g清热解毒。
2018年3月13日五诊,患者诸症改善明显,诉咽痒咳嗽,舌尖红,苔薄白,脉滑数。四诊方去厚朴、槟榔、草果、茯苓、半夏等,加浙贝母12 g化痰止咳。
2018年3月18日六诊,患者神志清,精神可,肢体活动几近灵活(肌力4级),口角歪斜恢复十之八九,双目及皮肤色略黄,余症消失,纳眠可,二便调,舌尖红,苔薄白,脉滑数。复查血常规:血红蛋白84 g·L-1,血小板计数121×109·L-1。
红细胞沉降率13 mm·h-1。肝功能:总胆红素
22.4 μmol·L-1,直接胆红素9.4 μmol·L-1,间接胆红素13.00 μmol·L-1,谷氨酰转移酶66.8 U·L-1,余未见明显异常。守方继用,药物略调。
治疗1个月后,患者病情稳定,中药汤剂加工成丸剂,长期服用;醋酸泼尼松逐渐减量;配合补钙治疗;硫酸羟氯喹0.2 g,每日2次,口服,维持治疗。
按语:本例患者素体痰湿内盛,体胖臃肿,苔白厚浊,平素治疗不当,邪盛正衰,邪伏膜原,时遇外邪触动疾病再发。运气外邪触发肝风痰浊,上犯脑络而突发肢体痿弱;遇少阳肝胆,则黄疸胁痛。正气衰败,出现极度疲乏,心慌,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及血红蛋白显著下降。是以正虚邪伏于膜原,时遇外邪触动伏邪而发。
2018年岁运太火,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发病时恰值初之气,主气厥阴风木,客气少阳相火。岁运太火,初之气厥阴风木加少阳相火,肝风引热,引动伏邪,风痰火热上扰,阻滞经络,出现中经络。痰湿、热邪阻于中焦,肝失疏泄,黄疸外发。脉数、舌红苔厚浊亦是邪气盛实的表现。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因此,患者舌脉虽有热毒久伏之象,但苔却白厚浊,以湿有寒为重。血冷气虚,不足以充,故脉细。在后续的治疗中外寒邪去,热象突显,而脉变为滑数。初之气厥阴风木加客气少阳相火,气机升降失常,故左胁肋胀痛。
方药选用达原饮针对膜原伏邪及太阳寒水所致寒热夹杂而透达膜原,治其邪。茵陈、茯苓、泽泻等为茵陈五苓散加减之意利湿退黄。全蝎、蜈蚣通络剔邪,针对治疗肢体活动不灵、口角歪斜等症状。半夏、茯苓、甘草又有二陈汤之意运化痰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患者病邪久伏,发病恰2018年立春后,有至春病温倾向。治疗过程中加用大黄、栀子、半枝莲等清热药物阻止热邪进一步发展,防止热邪再入阳明。若阳明正邪交争津液不保而入三阴,病情将更为复杂。
【病案2】患者,女,41岁,2021年11月17日
就诊。以反复发作性头晕,甚有晕厥1个月余为主诉。患者2008年确诊SLE,并有狼疮性肾炎、血液系统损害。曾使用环磷酰胺、他克莫司、硫酸羟氯喹等药物治疗,病情控制可,之后于2018年停用上述药物。既往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曾使用干扰素治疗,未定期监测乙型肝炎病毒并自行停药。患者就诊时头晕伴呕吐,重时晕厥,耳鸣,气短乏力,晨起颜面水肿,咽中黏腻,平素因家中琐事思虑重,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厚黏腻微黄,脉沉缓。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未见异常。尿常规示:尿蛋白(+)。肝功能、肾功能未见异常。补体C4 0.13 g·L-1。颅脑CT未见异常。西医诊断:①SLE;②狼疮性肾炎;
③胆囊结石。中医诊断:阴阳毒(伏邪内闭)。中医治法:解毒利湿,升清降浊。方药以升降散合泽泻汤加减:甘草15 g、白花蛇舌草20 g、半枝莲20 g、蔓荆子15 g、泽泻30 g、白术15 g、金银花20 g、蝉蜕6 g、僵蚕6 g、姜黄10 g、熟大黄1 g、合欢皮15 g、茯苓30 g。3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用。西药加用硫酸羟氯喹0.2 g,每日2次,口服。
2021年11月25日二诊,患者头晕、耳鸣减轻,未呕吐及晕厥,咽中黏腻减轻,仍感气短乏力,在上方基础上加太子参15 g、当归10 g、厚朴12 g以益血行气。
2021年12月2日三诊,患者头晕、耳鸣几无,余症亦明显改善,舌淡红,苔白微黄。复查尿蛋白正常,乙型肝炎病毒DNA测定5.41×109 IU·mL-1,
加用抗病毒药物。
此后患者无明显不适,未规律服用中药。因复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57 U·L-1,尿蛋白(+++),于2022年2月12日来诊,在上方基础上加用五味子、田基黄、茵陈、猪苓等药物治疗,未新增西药。2022年2月26日,患者诉时有乏力,余无明显不适,复查肝功能、尿常规均在正常范围,上方重用黄芪60 g,去升降散加蒿芩清胆汤加减,以透邪外出。
按语:本例患者SLE病史多年,未规律用药,邪伏于体内,充斥内外,阻滞气机,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故头晕、呕吐及耳鸣。气机失调,津液输布失常,故颜面水肿,咽中黏腻。久病正气耗伤,加之思虑较重,故气短、乏力。升降散中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伏邪杂气得消。泽泻汤及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金银花、茯苓等清利湿热伏邪。蔓荆子、合欢皮针对性治疗头晕、情绪烦闷等。之后在消散伏邪的基础上,换用蒿芩清胆汤透邪外出,祛伏邪重视祛湿为要。
5 小 结
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情反复,病程绵长,其治疗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卢思俭教授在长期的临床治疗中,运用运气、体质、脉症三位一体的诊疗思路治疗SLE,体现出其注重天人相应的关系即五运六气对疾病以及患者体质、脉症的影响。治疗时又结合SLE发病特点,重视祛除湿热伏邪以缓解病情并防止病情反复,重视时时顾护脾胃,尤其病重患者更应保留一分胃气以获一分生机,重视虫类药物的应用较寻常药物对祛除顽邪更有疗效,为治疗SLE提供更为全面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苏颖.《素问》“万物象变,气化使然”探析[J].吉林中医药,2014,34(11):1090-1092.
[2] 王占奎,张立亭,付新利.张鸣鹤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J].中医杂志,2009,50(7):596-597.
[3] 谢志军,卞华.范永升教授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经
验[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4):396-397.
[4] 吴晓霞.禤国维辨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J].辽宁中医杂志,2008,35(5):673.
[5] 向玮.卢思俭主任医师运用虫类药治痹经验[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0,9(9):45-47.
收稿日期:2023-12-06;修回日期:2024-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