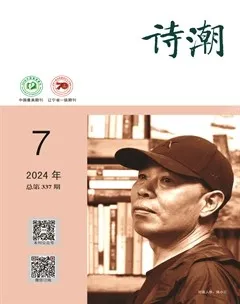随笔三题
无人之地
拉开门,下楼,走出胡同,拐到街上,穿过街道、车辆和人群,上坡,沿着台阶一步步走上来,这就到了山顶。这是早上或者夜晚,你坐在一棵树下,望着事实上并不在关注着的远处——雾霭将散的半空或者灯火摇曳的楼群。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轻易地走出了家门,就走到了山顶,或者不是山顶但与山顶一样的那些无人之地。
今天是这样,后天是这样,后天之后的某一天也是这样。你体内驱使着你的那点儿什么,会一次次地驱使你重复这个行为。更准确地说,在有生之年都会驱使你重复这个行为。
你,碰巧作为一个诗人,这一点或许表现得更明显。当然,你从来没觉得作为一个诗人比作为一个世人有什么特异之处,不不不,你并不会为自己的诗人身份而感到倨傲、高贵或者高人一等。你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诗人,你比一个世人更能自觉到这一点,也更加需要这一点。现在,你比成为诗人之前更多地走出家门,走到山顶,走到江边,走到旷野,走到草丛,走到密林深处,走到太古的岩石间——一切无人之地都成了你的目的地。
那些地方,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你?当你还不是诗人的时候,你也曾经一次次地自问。
自幼在乡野间长大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但并不是全部。是的,乡野,这样的出身和成长环境让你比你的很多城市同龄人更亲近于那些无人之地,对熟悉的场景的寻找出于早年形成的某种心理需求——你的城市同龄人更亲近于街道、广场、公园、商场、影院、游戏厅,这在逻辑上是一样的。问题是不单单是你,你相信而且知道,你的诸多城市同龄人很多时候也会像你一样,一次次地走出家门,走向你前往过的那些无人之地。
投身于无人之地带来的那份本然的壮阔,把自己变成和一棵树、一株草、一条河流、一块石头一样的自然万物中的一种,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如果这个回答显得矫情同时也不完全准确的话,那么可以再补充一点——人,所有人,骨子里或许都拥有至少潜藏有离开有人之地的那种需求,也即独自面对除了人之外的自然万物的那种需求。
如果抛开诗人的身份,这应该就是现在的你对以前的你的回答。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你,作为一个诗人的你,现在还面临着一份对曾经不是诗人的你的回答,或者说面临着一份对更广大的不是诗人的世人的回答——他们虽然并未提问,但你理应给出回答。
此时此刻,坐在距你家不足一百米的你经常登临的这座小山的山顶上,身为诗人的你又一次想到了那个自问——以及暗夜中那些此起彼伏的他问。现在,深夜十一点,那些即将和已经躺卧在梦乡里的人,正等着你作为一个诗人的回答。你没有回答,你坐着,仰着头,望着那趟正在闪烁着灯光的夜航飞机,它周围那几颗并不算明亮的星星,以及它们背后那张暗蓝色的大幕——你也不知道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点儿坐在这里。
在世人看来,这么晚了还坐在这儿傻不棱登的你,就是个精神病。也许,你自己也不禁这么觉得,你甚至还看见了自己在旁边望着自己讥笑。但是,这份觉得和讥笑并没有促使你起身离开,你继续坐着,继续仰着头——在某些时候,你觉得自己就像个巫师,自己置身的周遭就像个道场,你坐在那儿,头上好像伸出了一根天线,通灵般地接收着什么。
你接收到了什么?天上有什么,空气中有什么,你就接收到了什么。几亿年前发出的一粒光子,它穿过茫茫外太空,穿过厚厚的大气层,又穿过那些正摇曳着的树叶缝隙,终于抵达了你的眼睛;几千年前坐在篱笆院子里的一个古人,他望着在远处夜幕中隐现出来的那条山脊线,重重地摇了摇蒲扇,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此时此刻他就坐在你的身体里叹着气……当然,当然还有别的什么,一些你正在接收着的但并不能确定是什么的什么。
平静,淡然,并不刻意地接收着那些正在到来的什么,但有那么一瞬间,你为自己有那么一瞬间能置身于——同时也是置神于——那份广大浩荡又亘古久远之中而激动不已。
烟火间
胭脂路,粮道街,在这座城市所有类型的街道中,它们是与你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一种——店铺林立,满街飘香,热干面店、米粉店、饺子店、牛肉面店、卤菜店、锅盔店、麻辣烫店、抄手店、烧烤店……作为这座城市最具烟火气且与你咫尺之遥的美食街之二,它们和你的密切关系表现在日复一日地召唤着你前往。而在你们——读到这篇文字的读者们——所在的那些城市,当然也不乏这样的街道,也不乏被它们一再召唤过去的你们。
饮食,人之大欲中的第一种,当然是第一目的。多数时候,这在你身上也同样成立,你和被召唤过去的其他人一样,也是为了走进那些店铺中的一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形成了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某些时候你并不是为了走进那些店铺中的一家,你只是为了走到那样的街头,置身于街头的那些烟火气和被烟火缭绕着的人群之中。
当然,还不只是那样的街道,还有菜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公园、商场、影院等一切人群聚集之地,甚至电影、电视剧、直播间、短视频里那些有人聚集的“地方”,它们也都在召唤着你前往——更准确地说,是聚集在那些“地方”的那些人在召唤着你前往。
背着手——或打开手机——走进他们之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就能体味到只有置身于人群之中才能体味到的那份感受——你和他们是同类项,你正在被眼前的他们合并。
提溜着一塑料袋馒头的那个中年妇女,靠着一棵树正在吃热干面的那个背着双肩包的小年轻,在几条猪肉后面正刷手机突然咧嘴一笑的那个汉子,拖着音响唱着歌同时又向你伸出手来渴望着被施舍的那对老夫妻,以及从你眼前正经过的从某处来到这里又将前往另一处的那个骑共享单车的女孩子……你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越过你或者你越过他们,你的目不转睛地观看或者背过头去,你的心头一动或者无动于衷,也就是你被合并的方式。
在这里,这些人群聚集之地,人群——博尔赫斯所说的那个幻象——现在被具体化为了一张张脸庞,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满面风尘的和轻松惬意的,他们构成了你对人群的概括性认知。你并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很可能也不会再见到。然而置身于他们之间,擦肩而过或者抬头一望的某个瞬间,你不经意地记住或者内化了他们当时当刻的表情、衣着和形象,他们呈现的一切让你以意识不到的方式储存在了自己的感受记忆中。
是的,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诗人,你都不会被他们真正合并。不,这倒不是源于“他人即地狱”的认识,也不是出于人性深处那份与生俱来的自我和自私。很简单,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他们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和他们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偶然出现在某处的人群,你对他们并不负有擦肩而过和匆匆一瞥之外的责任——而反过来也同样如此。
绝大多数时候你和他们并不在一起——你甚至也看不见他们,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一个人待着。你在想着你自己的那些事,你明天要去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你刚才订的桶装水半个小时后才能送来,你窗台上那盆虎皮兰已经枯了,你晚上要骑动感单车……
但是,即便如此,作为一个诗人,你还是会下意识地和他们在一起。在你眼前或者脑海里的那片幻觉大幕上,他们正朝你走来或者彼此忙碌着,成为某种形而上的实在——现在你意识到了你自己,正跷着腿坐在椅子上的自己,你自己也就是你见过的那些他们的代表,那些在统计学意义上被掩盖着和替代着的零,你就是那些零的总和,你就是人类。
空气中有什么突然抵达了你,拿起你的手,让你的手又拿起笔或者打开电脑,敲下一篇分行的文字。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写出了一首诗,你代表那些零写出了一首诗,然而你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你知道,在最本质的意义上,那篇分行文字或者那首诗,只不过是你见过并记得的那些平静、叹息、摇头、快乐、愁苦、无聊的一种替代方式——让你感到骄傲的,仅仅是这样的方式降临到了你头上,你是黑暗里被选中的骑手,仅此而已。
家 宅
被楼顶两条边线切出来的那片天空中,有一只鸽子降落了下来。坐在书房里的你看见了它,注视着它的降落,降落之后的来回走动,在你的注视中它又飞走了。它抛弃了你,把你重新还给了你自己。跟它一样,云缝间的一架飞机,对面窗台上的一只橘猫,山坡上那家酒店阳台上的一个身影,也都会被你注视,也都会抛弃你——重新把你还给你自己。
是客体提醒了主体,让主体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一点,你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没有这种意识和自觉的,无论是正处于忙碌状态的你,还是正处于闲暇状态的你,无论置身于人群之中的你,还是落单为独自一人的你,你都在下意识中淡忘了自己。
即使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独居,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这套独属于你一个人的两室一厅以物理的方式把你与这个世界隔开了,把你以一个个体的形象单独凸显了出来,你也并不会比其他人建立起更多的自我意识——就像你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却并不会感觉到在呼吸一样。你宅着,待在家里,待在一个独属于你一个人的世界里,但你仍然与窗外你看见和看不见的那些在一起,仍然与脑海里你想到的和想不到的那些在一起。
不,你并不是说人是社会关系中的动物,并不是说人际、集体、利益、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审美等等都在规训着你进而牵系着你。你的意思是,面对那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经典之问该怎么回答——你的这个你到底是谁,你在哪种意义上构成了你自己。

窗外的鸽子、飞机、橘猫、身影都回答不了你这个扪心之问,把你与这个世界隔开的这套两室一厅也同样回答不了,相反,它们还在加重你这个扪心之问。像古往今来所有来到过这个星球的那些发出过这个扪心之问的人一样,你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春色烂漫的窗前,带到了水流不息的江边,带到了俯瞰尘世的山顶,带到了人潮汹涌的街头,甚至带到了鼾声如雷的梦里,你曾经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你没有自己,你是你的一个幻象。
太阳底下无新事,太阳底下也无新人,你承认并且接受这一点。是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你也在接受——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每个人都在接受着的那些内容,作为曾经、正在和将要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人类群体的一员,你只是复制和被复制之间的一个过渡者。
诗人这个身份的降临,或许让你在复制和被复制的命运之外重新发现了自己,可以构成独一无二的你的那个自己。在这里你无意于强调诗人比小说家、散文家、导演、画家或者其他创作身份的独异,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它成为你的身份,你愿意——并非坚持——以这重身份从事与其相关的内容,仅此而已。你的自觉,来源于作为一个诗人的自觉。
你不上班,除了不得不外出的时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你都一个人待在构成你的世界的那套两室一厅之内,敲敲打打,涂涂抹抹。与之前那个扪心自问自己为谁却找不到答案的你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你不但拥有了你,更进一步的是,你还要在诗人这个群体中也找到你,模仿的你不是你,改写的你不是你,某种流派中的你不是你,大师阴影中的你不是你,甚至你觉得是你然而事实上只是你们或者他们的某种变体的你也不是你。你努力去寻找并且渴望成为的,是在眼睛中睁开眼睛、在笔中拿起笔、在字中写下字的那个你。
现在,夜已经深了,然而你不觉得那是夜;四周是墙壁,然而你也不觉得那是墙壁。
嗯,在你此时此刻的感受里,你正处在你所经历的所有时刻中的最新一刻,你正站在你从这里前往这个星球上任何一处的那个起点。你相信你拥有那个最新一刻和那个起点,你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种古老而又新鲜的能力——你坐下来,打开电脑,你一无所有,只有文字这个唯一的工具,你敲打着,看着它们从屏幕上一个个地蹦出来,就像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人举着石块在山壁上敲打着——他看着那些粗糙但新鲜的凿痕被敲打出来。现在,你相信是你正在做着的事情构成了你的存在,你看着那些字句——也就等于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