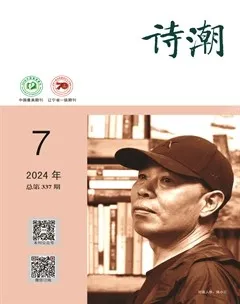柳沄诗歌代表作品选
一种过程
一只肥大的桃子
一只光芒四射的桃子
从枝头上宁静地落下来
就像凡·高割掉的耳朵,那么沉重
一只富贵的桃子
一只被风雨诅咒过的桃子
一只盛满水声的桃子
从那个高度上掉下来
并且像落日那样,弹了几下
一位美丽的少女匆匆走来
弯腰去拾那枚桃子
当她抬起头时
已成老妇
得意的事情大概都会这样
——这种念头在我心中一闪
那桃子和女人
就突然腐烂了
世界说:嘘
别出声……
瓷 器
比生命更脆弱的事物
是那些精美的瓷器
我的任何一次失手
都会使它们遭到粉碎
在此之前
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
坠地时又将尖叫释放出来
这是一种过程,倏忽即逝
如此,千篇一律的瓷器
谁也挽救不了谁
黄昏的太阳雄心消沉
围绕着那些瓷器
日子鸟一样乱飞
瓷器过分完美,使我残缺
如果将它们埋入地下
那么我漫长的一生
就只能是瓷器的某个瞬间
但在另一种意义里,瓷器
坚硬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它们更喜欢待在高高的古玩架上
与哲人的面孔保持一致
许多时候,我不忍回首
那样它们会走动起来
而瓷器一经走动
举步便是深渊
因此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瓷器宁肯粉身碎骨
而拒绝腐烂
是的,瓷器太高贵了
反而不堪一击
在瓷器跌落的地方
遍地都是呻吟和牙齿
瓷器粉碎时
其愤怒是锋利的
它逼迫我的伤口
重新绽开
天气出奇地好
天气出奇地好
好得阳光全都流出来了
在浸透我的同时
又不惊动我
只是我长时间地忽略了
这个细节
我长时间地坐在
街边公园的木椅上
远远地离开
那个坐在编辑部里
埋头看稿的自己
这是初冬
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
是那股笔直地,从
不远处的热电厂升起来的青烟
闲着的时候
闲不下来的,是人
那青烟似的一生
——沿着一架长长的
肉眼看不见的梯子
费劲地爬到
梯子够不到的地方
然后就散了
我得再坐一会儿
平静地想一些
和青烟和梯子
无关的事情
被一块石头瞧着
它在瞧着我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
一直蹲在那儿瞧着我
像我瞧着它那样
瞧着我。我是想说
——像我瞧着一位
缩颈抱膝的男子那样
好奇地瞧着我
山里的落日
落得格外早
而透明的余晖
使我莫明地想到
透明的福尔马林
它蹲在那儿
继续瞧着我
像一位缩颈抱膝的男子
在瞧着一块,从未
瞧过的石头那样
饶有兴致地瞧着我
瞧着我
于福尔马林似的余晖中
若有所悟地坐在
身体与遗体之间
滋 味
撂下电话
女儿急着往外走
将刚咬了一口的苹果
随手丢在茶几上
很红的苹果
很好看很好吃的苹果
无奈地摇晃那么几下
就再也不动了
我能猜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初恋远比任何一只苹果
都更有滋味
连招呼也不打
女儿推门就出去了
那跑下楼梯的脚步声
把我带出老远
女儿确实长大了
她已有太多的理由
在丢下一只苹果的同时
把我也丢在屋里
然而,无论我如何想
女儿的突然离开都好比一次停电
我很难一下子
摸到蜡烛和火柴
有好大一会儿
我跟那只发呆的苹果
一样静,一样
缓不过神来
不一样的是心里的滋味
我无法像被咬过的苹果那样
很甜很甜地对待着
所遭遇到的一切……
孕 女
在女人与母亲之间
她歪歪扭扭地
朝着下一刻走去
几缕从侧面照过来的余晖
使她的轮廓有些丑陋
丑陋使她暗自幸福
使那过于膨胀的腹部
比一只再也盛不下的米瓮
还要满足
但时候尚早
她怎样满足
就得怎样沉重
重要的是今天
是在成为母亲之前
用母亲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而命运的调音师
正将她的孕期从C调调到B调
之间是一道男人看不见的坡
并且越来越陡地通向
母子相见的时刻
她如此吃力地向上走着
使分娩如日出那样喷薄
无 题
我从来都不是那块
从峰顶滚落的石头
我只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中途
突然停下来
我只是像看待自己一样
去看待那块石头
时间久了,我干脆
把滚动时所发出的
巨大声响,称作痛快
只见它时而高高地弹起
时而笔直地下坠……
既然如此,那么
什么样的磕碰和摔打
才能让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
截然分开
这多么奇怪!在一个
十分平静的午后
竟然想到一块不能平静的石头
其荒唐程度,丝毫不亚于
将一行一行写诗
当成一口一口吐血
此刻,它顺着
因假设而陡峭的山坡
越滚越快,越滚越快
直到深深的谷底接纳了它
直到它与自己的经历
紧紧地搂抱成一团
天是怎么黑下来的
天是怎么黑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
让天黑下来的
黑得那么深
那么彻底
像即将淹没一切的潮水
但又不是
黑得我关掉屋里的灯
就看见了窗外的月亮
黑得月光一片也没有增多
一片也没有减少
黑得星星越来越密
越密就越像
读不懂的古希腊字母
哦,黑得
天下那么多的人
几乎同时闭上了眼睛
并且因为相爱
而同床异梦
两座山
两座山,面对面
站立了很久
中间是一条
叫作细河的河
汛期,河面宽阔
依然被叫作细河
两座山隔河而视
那姿态,说它们是在互相睥睨
就和说它们是在相互仰慕
一样有道理
此时的天色
已被一群一群登山的游人
一层一层地走暗
对面的山顶上,几位
同行的伙伴在不停地喊我
像喊着一个
丢了魂的人
两座山不为所动
在它们看来:恨够不着的
爱同样够不着
回去的路上
我忍不住再次回过头去
静谧的星空下,那两座山
一样高的同时也一样矮
当然,这跟我非要写这首诗
没有什么关系
为此着迷
那颗渐渐挨近
地平线的落日
越来越像一颗
暗淡的落日
我一直为此着迷
我曾在另一首诗中写过
——看上去,落日纹丝不动
却无时不在急速地下坠
有那么几次,它试图
让自己停在结束的地方
此刻,它好像已稳稳地
停在了那个地方
我愿意相信:那个地方
是钟摆无力再摆动的地方
是一张面孔在阅尽自己的一生之后
合目而逝的地方
因此,它无法不平静
平静得叫人分不清
是世界抛弃了它,还是
它正在抛弃这个世界
而当它消失
天空也没有出现一个
似乎应该出现的
巨大豁口
冬日的街头
我站在这儿
等一位异性朋友,等待
使我跟周围的几棵
东摇西晃的街树
形异但神似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
打她的手机
如敲一扇,怎么
也敲不开的门
我几次对自己说
——等会儿,再等一会儿
等来的却是两辆轿车
在我的眼前追尾
那么漂亮的轿车
一下子变得那么难看
好比一条狗在嗅另一条狗
我扭过头去,发现
我的影子不知什么时候
已被下午的阳光
钉在了粗糙的墙上
那黑乎乎的影子
无论我怎么瞅
都酷似一张
刚刚挂上去的兽皮
我吃惊于这一想象
好像我不是在等候那位
迟迟等不来的异性朋友
而是在目送一位
扬长而去的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