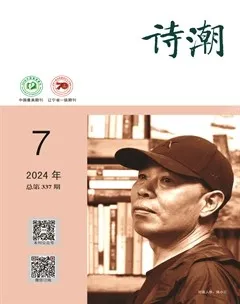老德的诗 [组诗]
同伴们
能走下去的同伴们,越来越少了
有些人累了,有些人拐了腿
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找不到任何解释的理由
我呢,也不是那么光明正大
有时候走走,有时候停停
甚至躺在床上,摸着那些暖暖的被子
一个月也不愿意睁开眼睛
当然,这也是一种迷茫
再走下去,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阴影
这时,靠在一棵树上
才知道鸟鸣,比你想象的还有意义
他们确实是我的同伴,是一个个
秘密的个体,而我的秘密
在我诗中已道尽了。现在
我常常牵着两只狗,在街上穿行
此刻,午夜十二点
我承认我喝多了,但是
还是忍不住翻开了
卡佛,我想了解他有
多少酒精度;在玛丽安与
安娜之间,又作了何种
选择。这样的夜色
出奇地安静,雪还没下
男人是不是可以
在诗中,为自己
涂脂抹粉;在开篇
就把自己打扮成
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这时
突然,有一双手伸了过来
把卡佛合上了,并随手关上了灯
日落西山
开始是
脚痛
后面是
手痛
然后是脑袋
有点痛
突然
喉咙也痛
后面是
胃痛
心痛
等什么也
不痛了
太阳也就落山了
石器时代
我想回到石器时代,晚上
围着一堆篝火,仰望着星空
那时,我身边的人
再也不会为意识形态的不同
争得面红耳赤。他们
每天就想着打磨自己的利石
围剿着丛林里的猎物
努力地让自己活下去
然后,在一个月圆之夜
把女人抱在怀里,传宗接代
亲人不容易那么死去
一大早,母亲便掀开
我的被子,说我养的两只
白鹅,飞上了屋顶
你必须现在就起床,想办法
把它们,抓下来
半夜,我正在和朋友喝酒
又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
男人可以喝酒,但
必须在酒杯中分清,谁是
革命的敌人,谁又是革命的朋友
我的父亲已经死了20年
我的母亲去年才走
只要我活着
他们在我心里就死不了
命运之诗
昨天晚上,我喝高了
在回家的路上,掉了一首诗
我以为找不到了,没想到
它孤零零地贴在马路
中央,还没等我伸出手
一辆卡车驶了过来,这首诗
又被轮胎卷走了
我有点难过,但不伤心
我依稀记得,这是首
命运之诗,我们都想摆脱
自己的命运,时至今日,却没有
动物志
嘿嘿,那就先说下狗吧
它嗅觉太灵敏了
只要我半夜回家,不管
醉与没醉,它都会
伸着前肢,趴在我身上
猫呢,确实很乖
天天龟缩在自己的空间里
喵喵叫个不停
一旦嫁出去了,便再也
不知道我的门牌号码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
狗像儿子,猫呢
更像女儿,但是
在我那个年代,计划生育了
不管生儿子还是女儿,只能一个
现在,他们长大了
而我却老了,一年三节
当然希望他们回家
但他们长大了
不但学会了躺平,还懂得英文
如果,你跟他们说
孔子、卡斯特罗
他们装着听不懂
再劝他们早点儿结婚
传宗接代,他们瞬间便把你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