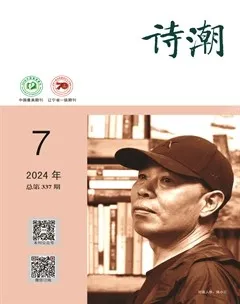所获 [十二首]
鲸
把一个鲸的模型
放在桌子上。你抚摸它。
你不能在大海里抚摸它。
你现在在房间里抚摸它。
就像喜悦,隔着冬日
的一件毛衣。你不能
在你的孤独里抚摸它。
你现在在我的身体上抚摸它。
在溪流中
孩子们在溪流中,驱赶着鱼儿。
银色鱼儿。游得飞快,
为躲闪他们而聚散不定。
水声、嬉闹声和悠长的蝉鸣
交织在一起,我还听到
身旁山楂树丛中的山楂砰砰落地的声音。
这些声音都好听。在这个下午
对我有治愈性。但马上我又
怀疑起我内心的这种安静的真实性——
它是灵魂的本真安静还是
肉体的佯装安静?
在溪间石头上,我也学孩子们的样儿,
脱了鞋子。坐下。赤脚
悬于水中一动不动,让好奇
的鱼儿们围过来,磨蹭或啄它们。
大欢喜
我们中,拥有大欢喜者少而又少。
俗家拥有慧识者、佛家拥有般若者、
未经纷纭世事便知晓过去未来者。
我们,心中留存的是如此之少,
且都是悲苦事、惊惶事,且都是
琐碎的、灰烬一般的。我们中的男人,
须经女人教育,同样地,我们中的女人,
须经男人教育。刚柔相济之后,
才能生出大欢喜。这便是新生婴儿和
襁褓中的心,只能感知自己而又忘我。
初春记
三月初仍有候鸟,离开我们。
湖边,绿萼和迎春花在开放,
由着自己的性子(或造物者的性子)。
有一两种花儿这么着,我们应知足,
就像十人中有一人可爱,我们应知足,
不必因对人类的妒忌心
预知不够而久耿于怀,或放大它。
仰头看,候鸟的排列;低头看,
花瓣的层次。远处,天与地在同一个
平面上,仿佛从没被对折过:没有折痕。
日出记
旭日之金光,周围
有湛蓝镶边,还在扩展……
一个词语会成为一个磁极:永远。
但“永远”岂止是一个词语。
金色童年。金色老年。用文学语言
这么说话总令人羞惭,但我又
不得不这么说话。唯此你
才会领悟。站在山顶上,你
随眼前万物显现而对应生出耳目,
并重返这世界——“永远”,
情感的学问,首先是色彩学。
悲喜律法
活着自有律法。玄奥并非哲学。
不要把感官享受与精神诉求对立起来。
我肯定,这人世只有一次。
一人、一物、一念、一秒钟,都是客体。
伤感、恨、安宁、幸福,都是主观性。
我知道,没有一件专属于我的事物。
午后掠过我头顶的一只白颈长尾鸟,
在灼热的沙地上投下影子。
我不认为,与我的悲喜有关。
快乐的教义
快乐的教义。去表现什么。
心中的故乡,如蜂鸣。那是你,
许多发音的小翅膀。为趋光性
所困。你的心,得到了最好的药物疗愈。
想着你的早餐、出门穿的衣服、想见的人。
张臂如拍翅。去拥抱什么。
去魔法岛
以分钟、小时计算时间,并无
特别的道理。待在这儿,在圆形房子里,
是义务,也是自愿的惩罚。
哀悼我们的孤单,并且否定。
我们的时间,当然以我们
的一生计算——去魔法岛,
兑换我们的时间。万籁俱寂时,
称量某一刻,惊奇于自己才是施予者。
修 正
初春夜,紫荆花梨花开着。
木栅栏外是树篱。心中
一个异国,身外一个异国。
失眠时,你会爱上一个熟睡的人,
羡慕她睡得比你香甜。她是对
宁静的一种修正。一种秩序,
教会你等待、忍受。仿佛她是
你身上本来就有的、久已
忘怀的、正在消逝的某种东西。
自然艺术
艺术的源头是:
一个小女孩儿,赶着两只小鸭子,
往河边去。她和它们一样小。
她把自己当成它们的妈妈。
艺术的表现形式是:
她和它们,都光着脚,
摇摇晃晃,在河边砂砾地上,
留下黄泥脚印。
艺术的旨趣是:
柔弱、娇小、安静,以及
小脚丫和翅膀雏形
左右摆动的样子。
河边,三叶草和野豌豆
都开过花了,都凋谢了。
记录、拍摄或画:
我必须马上成为艺术家。
冬 景
几乎是灰色。我对
眼前事物,做不到冷静相待。
荒草枯木的境界,其实
也难得。视野,更纯净。
我感觉,我在衰老。继续衰老。
虽然无法阻止,但我总想,
比以前慢一些,心里更明白一些。
看到河对岸有人(他也
看到了我)。今日晴好,
却是片段式的。河里有冰。
这个世界的情诗(十一)
这是最好的。我们有一个星空、一个
大地。古老的说法是“阴和阳”,更亲密
的说法是“我和你”。我们喜欢后一种。
晴朗之夜它们同步旋转,雨夜它们
错乱运行。就像表盘上的时针和分针,各有
节奏又相互配合。瞧,这世事多复杂,多精密。